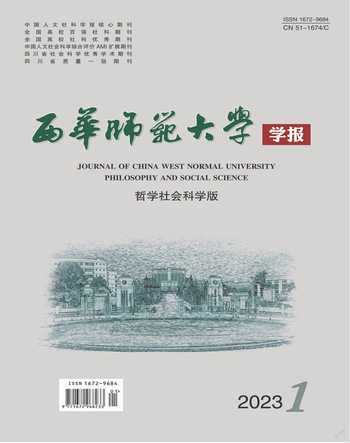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2023-06-19任剑涛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现代化自晚明开启其进程以来的、一个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的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史持续五百年发展的一个中国果实。只有在现代化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锁钥。现代化史展现出高度关联的社会环节,构成了现代化史的复杂性与中心性线索: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大历史线索中,才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历史;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国别结构图中,才能辨认“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但世界现代化史并不将“中国式现代化”标示为绝对例外的历史产物,它约束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现代化是上位特征,中国式是下位特征,现代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规定了国家方向与发展状态。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性;个别性;大历史;小历史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9684(2023)01-0001-11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正式提出的一个命题。这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学术命题。从政治命题上来讲,其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设定目标、指引发展;从学术命题上看,可以从多个维度上展开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史。其中一个维度,就是从现代化史的脉络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史的角度,在总体上归属于历史学范畴。历史学的分析,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且自古至今延续的一个思维模式。但是,历史学的分析并不是直接从历史中抽取出政治结论的活动。从历史中引申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模式,是试图在活的历史进程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从现代化的总体进程来讲,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世界进程、国家表现;从现代化的世界与国别关系来讲,大历史与小历史、全球史与国别史、规范性与例外性,构成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
一、现代化话语的重启与世界进程
在中国,“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说是对现代化话语的重启。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有两段话可以作为重启现代化话语的强势表述。一段话是:“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另一段话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22正是这两段话,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内涵凸显出来:前一段话将“中国式现代化”前一百年与未来一百年关联起来,从而将二十、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连接起来,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丰富内涵灌注其中;后一段话则将中国现代化史与世界现代化史关联起来,从而将中国现代化历程放置到世界现代化的长时段中来关照,同时将世界现代化史的当下进程放置到中国这一特定空间中加以审视。前一段话凸显的是中国自身历史变迁所指示的现代化历史方向:一个曾经领先世界的大国,在世界现代化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落后于世界步伐,如今,以国内生产总值的疾速增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国力提升,将重现其历史辉煌;后一段话凸显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受全球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体现了世界现代化史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又表现出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特点,因此为世界现代化史增添了颇具中国国家特色的新意蕴。
分析起来,中国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话语,已经退场将近30年。退场,不是指存在性隐退,即从中国的话语场中彻底消失;而是指重要性退场,即现代化话语不再成为像1980年代那样令人瞩目的核心话题。这与1990年起始的中国话语场重大转变直接相关:在1990年代,由于旨在反思現代化进程的缺失以及现代化话语的缺陷,中国引入了“现代性”(modernity)话语[2]。现代性成为现代化的话语替代者。现代性话语对仍然在展开中的现代化世界进程缺乏认同性关注,因此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甚少关注,其关注的焦点是现代性的非西方贡献以及西方现代化的缺陷。同时,也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曲折起伏的状态,不如人们所意料的那样一往无前,故人们对广义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前景很难做出准确描述与分析。这就让现代性话语旨在反思现代化缺陷、将现代化扩展为一个不是由西方国家驱动,而是由全球自驱、贯通古今的漫长演进过程。据此,似乎更为平等地看待了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对现代化所做的贡献,这是现代性话语广泛流行开来的缘由。它不仅在西方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场中盛行,而且也成为全球现代话语的一个流行范式。在现代性话语流行于中国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现代化社会变迁的关注,逐渐弱于对现代性问题的热议。直到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才再次将现代化重新安顿在中国社会中心议题的位置上。
如前引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凸显其世界共性。这是需要从两个角度分别呈现的现代化史内涵。由于1840年以来,中国愈来愈将国家目光聚焦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因此国家关怀强烈到抑制了世界眼光。故而,在中国现代化的国家特色与世界共性之间,需要将审视的目光首先投向后者。就此而言,需要明确强调的是,一部现代化史,就是一部世界进程史;一部世界现代史,就是一部现代化史。这可以从现代化的时间线索与空间结构两个维度加以认知:就前者讲,现代化的世界进程,起于16世纪到19世纪,这一时期出现了现代化和传统社会运作模式的“大分流”①。一般而言,人们将“大分流”理解为东西社会的大分流,其实这一理解相对狭隘了一点。因为,所谓东西社会,实际上就是欧亚社会。这是一个以欧亚大陆为背景论述的世界史,是一个陆权时代的概念。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地域非常广袤,政治体繁多,发展状态非常复杂。起之于16世纪止于19世纪的大分流,可以说是欧洲社会区别于非欧洲社会,包括亚非拉与发达的欧美之间的一个分流。从历史视角看,起至16世纪的现代化世界总体进程,在大分流之前就开启了它不短的历史积累过程。从13世纪的英格兰肇始,历经4个多世纪的渐进推进,终于在17世纪后期生成了第一个现代国家。而在英格兰建构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因为对法国的战争,也同时推动了欧洲大陆的种种变革。欧洲大陆内部的种种新生因素的持续发展,让欧洲地区成为人类现代转变的第一个区域:在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情况下,“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将现代化国家方案带给了整个欧洲[3]83-149。美国革命将英国的现代建国方案创造性移植过去,促使北美地区转型为现代国家,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第二个区域。接着,现代化浪潮席卷欧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让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上演了一幕幕从地区到国家、再到区域,最后到全球的历史大剧。现代化的近期发展,竞争的是全球现代化的第三个区域。惜乎从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的南美到同一个世纪的80、90年代的东亚,第三个现代化区域都曾崭露轮廓,但未能正式落地。
就后者即现代化的空间扩展来看,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化,以三个势不可挡地呈现出的全世界意味的特征展示给世人:
一者,由科技带动,以市场经济推进,促成了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4]404。这是马恩二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先知性预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拓展市场空间,以跨国公司与国际资本集团为载体,确实将其发展初期的地区市场、成型期的统一国家市场,最终打造成全球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由此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最直接而强劲的动力。由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直接植根于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之中,因此经济的现代一体化有力地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共同进步步伐。中国人1980年代熟稔于心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就正是对一个不可阻挡的、席卷全球的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反映;进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宣告了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全球体系。
二者,现代化进程表现为现代政治机制的形成。现代政制,也就是现代民主政体,从个别国家推向全球范围,构成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另一大特点。溯源及流,现代政制起源于英格兰13世纪的宪政变革运动,也就是人所熟知的大宪章的签署,到1688年光荣革命方始确立起立宪民主政体。经由法国大革命,现代政制不仅具有了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基本价值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框架,而且开启了它的世界历史进程。这个世界化过程,呈现出的一条基本线索是:从英格兰到英国其他地区、再到西欧、中欧、东欧、北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依宪治国的政制成为一个限权的民主化、世界化进程。这一进程,在亨廷顿那里被表述为民主三波,“第一波民主化起源于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在约100年的时间里,在30多个国家中生成了最低限度的全国性民主制度;“第二波短短的民主化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主的世界进程略有推进;“第三波民主化,……尽管碰到了抵制和挫折,迈向民主化的运动变成几乎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而且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5]15-21。在民主三波中伴有两次回流,但总体上民主的世界化进程线索是清晰可见的。在中国,关于民主一度流行的否定性批判,最终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锤定音,宣告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民主的承诺。
三者,现代化进程塑就了全球趋同的社会生活方式。最简单地讲,就是在政治理念上让长期混生的公私领域显著分流;在实体运作上,公私生活呈现出一种高度关联的嵌套状态。公和私的清晰界限、基于公和私分化后的互动,是西欧在现代早期对人类生活的独特贡献。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从欧洲席卷全球。全球大流动对生活空间的拓展,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公私生活划界,人们不再以公共生活为人生唯一目的所寄;在公共生活之外拓展广泛的私人生活空间,公共权力以保护私人空间不受侵犯,私人不再直接将自己的私生活推演到公共领域。这些现代生活样态,逐渐成为全球趋同的生活模式。“公共—私人二分体的现代剥离不仅使它们从传统与社会实践共同场域分离一事成为必要,而且彼此分离:将公共从私人中分出。”[6]4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代面相:一方面它意味着公共、尤其是公共权力不再能随意干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标志着私人生活具有其划定的固有区域,它可以接受公权力的合法介入,但要求公权力按照法律行事。在中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公私、私私关系的清晰划界,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了法律保障。
从现代化世界进程的上述三个意义上,可以推出一个基本结论:现代化确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因为在总体性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这些主要构成要素上,均呈现出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化驅动力。三者的合力,不仅直接推动了现代化的世界化进程,也成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动力机制。可以说,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不是哪个国家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怎么接受的问题。其间的差别体现为:在不同国家,由于现代转变的目标存在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因此现代化发展程度出现明显差别;也因为在发展位置上存在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因此现代化的优势呈现与劣势克制存在明显落差;还因为在实现现代化目标的结果状态上呈现为一个先后、优劣的问题,因此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完成度的差异相当悬殊。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上述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以国家作为主体单位推进的。在这一特定意义上,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世界进程,而是由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共同推动的现代化变迁。在国家权力是不是规范地作用于现代化进程上面,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广泛差异,这是国家间的现代化结果产生重大差异的决定性原因。
二、现代化三波
可以说,一部世界现代化史,在形式结构上,被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在实质结构上,呈现为前述的统一时间线索与空间结构组合中。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史,不是自始至终都展现为“世界的”面目,相反,它展现于实实在在的具体国家进程之中。如此一说,是不是构成对现代化世界史的挑战呢?既然现代化世界史是由国家史所构成的,那不如在一个一个具体国家的范围内去具体认识现代化史,那样岂不更为切实和可靠呢?这是一个需要分析的断言。在现代化的世界史总是从国别史体现出来的意义上讲,离开具体国家所言说的现代化史确实是不存在的。因此确实需要从具体国家的现代化状态上去认知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但从现代化之所以被命名为现代化来讲,就是因为它超出一个具体国家而具有的国家间共性:其不仅体现为任何国家免不了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洪流之中,而且在一波接一波的现代化世界大潮中,国家间的发展所呈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趋同性特点,愈来愈令人瞩目。
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家的发展程度高低,主要是看它规不规范、现不现代;而对国家自身的现代进程来讲,则看其是否可以建构规范的政体,并且按照规范政体的原则持之以恒地运行下去。就此而言,其一,现代化的世界史起点,就是那个为现代世界确立起国家典范的国度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点,这是现代化世界史开其端绪的重要标志。在时间上讲,从13世纪开其端绪,到17世纪中后期结出现代国家的果实;在空间上讲,大致限于英格兰范围。对此,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现代因素的浮现、成长和成熟,但从总体上讲,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与英格兰的现代化开端与发展媲美。其二,当现代化的国家典范溢出其原生国家范围,并且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内驱力相互结合的时候,它就获得了世界范围扩展的强有力支点,构成现代化的世界史进程的第一波浪潮。其时空要素可以表述为:17、18世纪的西欧、中欧部分国家,是为此轮现代化世界史进程的重要载体。现代化世界史的第一波,卷入其中的基本上是欧洲文化圈的国家,因此以其文化同质性,呈现出现代化世界史的欧洲特性。这是现代化世界史从英格兰、经由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因此浮现现代化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论的缘故。
现代化世界史的第二波浪潮是从19世纪的欧洲文化圈扩展到亚洲、尤其是东亚文化圈,这是现代化向相异文化圈的扩展进程。在这一波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极少数非西欧国家如日本、中欧的德国,得以跻身现代化国家行列,证明了现代化并不是西欧文化的单一产品。现代化世界大潮的真正到来,是在20世纪现代化世界史的第三波浪潮到来之际,这让当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之中:尽管取得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的国家仍然不是很多,但在现代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尤其是在经济成长的特定领域中,呈现现代化轮廓的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国家愈来愈多。此间,像以前那样明确采取反现代化立场的国家愈来愈少,而认同现代化目标的国家愈来愈多;抗拒现代化的思想主张明显减少,而促成对现代化世界史做出不同于西方国家贡献的国度明显增多。
对此可以做相对详实的回顾。现代化的世界史起始点确定无疑是在13世纪的英格兰②。英格兰以政治现代化奠基,在此基础上寻求经济现代化,终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多重意义上的总体性现代国家。英格兰以此为所有后来尝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垂范。“从12世纪开始,英格兰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之间发生了一次大分流,在英格兰,前文描述的所有特点不仅延续下来,而且有增无已:反城市主义,商贸天赋,共同体的缺位,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审理,普通法的非成文法性质,法律意义上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缺位,教会与君王之间的张力,核心家庭体系——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妇女相对平等,子女没有天生继承权;所有这些表征都在持续和巩固。”[7]349-350而13—18世纪的欧洲大陆,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英格兰则在立宪政制与社会经济成长的相互推动下,于17世纪最终确立了立宪君主政制,18世纪开创了现代工业文明,成为政治、经济与社会携手发展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并因此成为整个欧洲发展的引擎。“有不少事物历来被认为是英格兰的‘出口产品,其中较重要的有工业革命、农业革命、民主政治范式、英格兰法律的多项原则、现代科学的多个侧面、包括铁路在内的多项技术。”[7]357英格兰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现代典范国家。一旦将现代化的世界史起点确定在13世纪的英格兰,那么世界现代化史的“英格兰中心”也就挺立起来,曾经困扰非西方国家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也就不攻自破,让这些国家踌躇在西方与在自己之间如何选边站,如何避免所谓学习西方的理智与捍卫传统的情感之间的对峙。这样的困境,不再构成人们面对现代化挑战在心理上犹疑的观念障碍:因为从西欧开始,再到中欧、东欧,也是学习英格兰而开启其现代化进程的。是英格蘭一个国家,而不是大不列颠一个地区,将现代化方案贡献给整个世界[8]。因此,在东西社会、中西社会的恩恩怨怨中难以被认取的现代化方案,也就不应被视为“西化”方案。
因为,今日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承惠于英格兰才成为现代国家的。现代化突破英格兰范围,向西欧扩展,直接推动了“世仇”法国的现代化转变。同处西欧的法国,曾经在14—15世纪与英国之间展开过“百年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既是对两国的伤害,也是对两国退出基督教世界社会、进入民族国家的直接推动。但在现代国家建构的竞争中,率先确立起民族国家模式的法国,反而在规范的现代国家建构上面,明显落后于英国。到18世纪,法国国内对是不是向英国学习,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看法: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非常仰慕英国,他由衷抒发一种崇英情感:“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如果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9]23但法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使得法国人一方面欣赏英国,但更多的却是抗拒英国。就在伏尔泰被英国深深折服的当下,像蒙布兰就对英国人的浅薄、粗俗和堕落加以猛烈的抨击,且认定英国的民众政府意味着混乱、下流和争斗,不堪为法国所取法[9]48-49。尽管在1789年代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英式现代原则被大革命深深镌刻进法国人的灵魂深处,但不改法国人对英国人的矛盾看法。相对于英格兰来讲,后进的法国,已经在学习还是拒斥英国上自相矛盾,以致于让法国的现代进程很难兼综内外优势,直取现代建国成果,从而不得不在帝国与共和国之间徘徊良久,才终于坐实于现代国家的平台。这可以帮助人们知晓,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在认取现代化典范国家时,其爱恨交加、欲迎还拒,会对国家的现代进程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这预示着,这样的矛盾心境,将会以更加激烈的状态,呈现在其他更为后发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逐渐从西欧推向中东欧的时候,德国与苏俄的现代国家建构,经历了远比法国还要悲壮的历史曲折。德国一直自认为是与西欧国家不同、兼有东西欧优点的独特国家,因此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官方努力激发德国人对英国的不满,以便抵挡“英国的立宪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的影响”[10]168。而在纳粹德国阶段,就更是以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严厉拒斥,来制造德意志民族就是“主人民族”的幻觉,结果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从根本上说,问题就在于德意志人在相信或者认定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你要么为刀俎,要么就是鱼肉之时,是否正确,此种信念不仅是纳粹所传授,也是德意志政治思想主流传统予以相信或者认定的”[11]111。正是由于德国行进在一条抗拒主流现代化方案的畸形道路上,因此才造成国家在经历三次殖民与准殖民的曲折后方始实现现代化的巨大历史起伏:1806年被拿破仑占领、1918年战败后被割地赔款、1945年战败以后国家被肢解。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国家。以独得欧亚两洲优势、自诩“双头鹰”的苏俄,更是以对抗性极强的意识形态来颠覆现代化典范,以期实现更令人满意的现代化理想目标。但结果国家走上一条难以自我调适的弯路,至今未能完成国家现代化的基本任务。
现代化世界浪潮的第二波,终于越出欧洲文化圈的范围,扩展到亚洲地区。这里所谓的扩展,不是在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实力已经到达一个地域范围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先发的西方现代国家达到一个地方,且引起这个地方的现代转变的特定意义上讲的。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的力量最早到达的地区之一是非洲、接着是拉丁美洲,亚洲的普遍殖民过程相对后发。但因为非洲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变迁相应比较迟缓,反而让亚洲国家在现代社会变迁上着人先鞭:起初,中日两国对现代化也是极尽抗拒,试图激发“国粹”以拒斥西学;但随后中日两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先是中国声势喜人的洋务运动,几乎让中国露出了工业化的曙光;然后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一举将日本推向亚洲工业强国的位置③。惜乎中国受制于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现代化功败垂成;日本制定了帝国宪法,但同样没有走向规范国家状态,以致于给亚洲带来巨大的战争灾难。在二战以后,日本终于成为一个相对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代价也非常沉重:以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和控制换取了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转轨契机。
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现代化世界进程的第三波。这一方面体现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2]。正是“第三世界”出现的这一普遍变化,引发了殖民体系的最终崩溃。普遍浮现的民族国家,至少从国家形式结构上展现出现代化的轮廓。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围绕现代化目标展开的国家间竞争,现代化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调,这就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所熟知的“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的两大基本主题;再一方面,则先后表现为南美地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的生机勃勃,展现出世界第三个现代化区域的诱人前景。尽管南美地区的现代化出现挫折,但韩国成功跻身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认定的现代国家行列[13],中国成长为世界范围内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二的庞大经济体。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世界大潮席卷“第三世界”,并且带动起相关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势头,现代化的世界史图景已经完整呈现在世人面前。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世界”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大潮之后,现代化的绩效差别相当悬殊。这提示人们,进入现代化轨道,并不直接保证现代化的效果。一个国家,试图收到现代化的预期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推进的持续性、合理性与有效性。
三、追赶历史步伐
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其发端上计算,已经迈过了800年的长时段了。在这一时段的早期,尽管由不同国家先后领衔现代化的国家建构进程,但最后由英国完成了现代化的临门一脚: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人类摸索出了一条有效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的立宪民主进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促成的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为人类的现代经济发展指引了方向;随着英国社会变迁呈现出诸社会要素相互支持的进步性态势,一个现代国家的完整轮廓呈现出来:就英国建构现代国家而言,脱离基督教世界社会、建立民族国家的步伐晚于法国,冲破国门、致力拓展海外领土和世界市场的步伐晚于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同一时期携手进步的国家如意大利一时展现的发展态势并不弱于英国,但英国最后在现代化的国家间竞争中力拔头筹,成为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并且向此后所有尝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垂范。英国的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简言之,英国的现代化并不寻求一个毫无缺陷的理想国家状态,而是致力于平衡七拱八翘的社会要素,使国家保持在现代化的动态运行轨道上。“英格兰开风气之先,成功地保持了国家需求、教会需求、家庭需求、经济需求之间的恰到好处的平衡,使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凌驾于其他。这导致了个人的责任和自由,也导致了无休止的矛盾和混沌。因此,英格兰的为伟大贡献或许是向世人证明,混沌、混淆、矛盾和悖论应当受到欢迎。”[14]358这或许是一个独领现代化世界风潮的英国的“优雅”与“从容”的表现,兴许也是英格兰的独特国家气质所致:它能够为国家的现代转变偿付几百年漫长的时间代价,也愿意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让社会慢慢与新生机制磨合,更乐意在渐进的过程中保守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这是一种幸运。这也是其他所有尝试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心仪的状态。
其他国家几乎很难享有英格兰这样的国家运气。一方面,这是因为英格兰本身就是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依靠国内不同力量的磨合、国家间激烈的竞争,而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脱颖而出的。因此,赢得现代化竞争先机的英国,势必会努力维持这种国家间竞争优势,抑制其他国家取代英国的国际竞争有利地位。这正是英国营造国际殖民体系,并且在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中,一直与欧陆大国法国、德国展开激烈竞争,以至于诉诸历时绵长的战争的缘故。现代化唯一的典范性国家尚且如此这般进入国际竞争领域,其所承受的现代化发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可知赢得现代化竞争先机的不易④。另一方面,在与英国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欧洲国家,诸如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在国家间竞争受压的情况下,更是亟于改变国家的不利处境,以便胜过英国的国家势头,赢得其所期望的国家利益。在法国,为赢得国家发展优势,获取国家间竞争优势,走上了以意识形态革命以求一步到位的国家建构歧路;在德国,则走上了一条为赢得国家“生存空间”而诉诸战争的国家建构邪路;在日本,为了全面赢得亚洲的国家间竞争优势,也不惜以军国主义、战争手段实现其国家目的。之所以这些国家以竭尽全力的方式进行国家动员,以期占据现代化竞争的优势地位,就是因为它们不再可能像英国那样从容地付出数百年时间,以耐心地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国家必须迅速解决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否则国家就会处于一个前景堪忧、甚至彻底消亡的境地。这种紧迫感,在中国1980年代四处响起的“球籍”危机声中便可以理解。
现代化的世界史,基调由英国奠定,主要篇章则由随英国而起的其他现代国家接连书写。但不管后起的国家,尤其是美国书写了超过它曾经的宗主国英国的多么精彩的篇章,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都是追赶英国发展的历史步伐的结果。现代化的先发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存在争论;同理,后发现代化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也出现了广泛的争论。从总体上讲,先发现代化固然有其筚路蓝缕的艰辛,但具有得其先机的独特优势,竞争者相对较少,胜出机会相对较高。就此而言,很难将先发现代化国家归于劣势范畴。但后发的优势与劣势确实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一方面,现代化后来者的优势明显:不再面对未知局面,存在可资借鉴的先例,减少早期现代化阶段的摸索与代价,保有协调与控制的优势,较容易获得先发国家的支持与帮助。另一方面,现代化后来者的劣勢也同样令人瞩目:必须大规模地创建现代化的必要基础性条件,社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不匹配,与先发现代化国家存在难以弥补的差距而对发展信心造成挫伤。换言之,从追赶的处境华丽转身为引导的角色,几乎没有可能[15]814-818。由此可以推知,追赶现代化历史步伐的后发现代国家,从总体上讲,是处在一个现代化国家间竞争的不利地位上的。
但尽管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处在一个现代化史的晚发状态,并不意味着就固定处在一个永久追赶而无以超越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位置上。只不过,从现代化史上看,这类国家为数不多、弯路不少,但这给人以追赶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强烈希望。一种将整个国家权力的能力聚集起来谋求发展的现代化经济模式,似乎构成一种有效促进国家现代化经济成长的强健模式。这就是为日韩等国家有效实践过的发展型国家(the developmental state)建构。发展型国家是一个发展经济学概念,所指是国家权力体系倾其所能地致力推动经济增长。其基本特征是:一小批最具管理才能的、廉价的政府官僚确定并选择需要发展的产业,并运用国家干预市场的方法实施产业推进;国家政治体系中的立法与司法机构被限定在“安全阀”职能上,但促使官僚体系获得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国家干预市场的方法多样、得当且有效[16]45-47]。可以说,一个比较规范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是一个聚集国家权力优势谋求发展的特殊政经体制。发展型国家在是与不是的两个边界上得到规定:它是适度聚集国家权力以谋求发展的机制,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市场积极互动的机制;它不是一个为了扩张国家权力而剥夺市场动能的机制,不是一个国家权力独大且支配市场的机制。因此,真正将国家安顿在发展型国家平台上,是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模式。而作为追赶型发展的东亚国家日本与韩国,正是以发展型国家来推动国家经济的疾速成长的,并且因此跻身现代化发达国家行列⑤。
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种广义上的追赶型现代化。这是在特定的、英国作为第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上做出的断言。在狭义上,追赶型现代化国家主要是指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言的。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处境相对不利:一是前述三个方面呈现的那种不利,二是追赶型现代化国家始终处在一种落后于人的紧张状态,因此很难走出高度张力情况下的决策蹙迫性,故追赶本身便成为一种逐渐固化的心理障碍,让追赶型国家的现代化转变变得尤为艰巨。追赶型国家为了避免掉进发展陷阱,即为发展而发展、因停滞而回流,想方設法,终归迈过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这类国家,为数不多。这是因为,发展型国家的走向不过有二:要么走向规范的现代立宪政制,废止发展型国家在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纵横捭阖;要么步入苏俄式的国家陷阱,让国家权力成为支配一切资源的主体,结果耗竭国家建构现代化的资源,终致国家崩溃。在所谓规范权力的现代国家主流类型、苏俄式的吞噬型国家与发展型国家这三类国家之间⑥,不存在一个发展型国家独自长久运行的可能性。而一个发展型国家如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则需要处理好下述三对基本关系,方有望实现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是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世界史进程的现代化和以国别为单位推进的现代化,体现出大历史与小历史、全球史与国别史之间的关联性错位关系。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实则一致的说法: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来讲,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被纳入全球大历史的范畴,大历史、全球史与小历史、国别史之间的高度关联,毋庸多言;但大历史与全球史并不等于是小历史或国别史相加,前者的共同性与后者的特殊性迥异其趣,因此在具体的历史表现上一定是错位的。所谓大历史,一般指长时段、大范围的历史。大时段是指百年以上、千年以下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大范围则是指全球性、世界化的历史。现代化的大历史一般从15世纪正式起计,但萌动于13、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最终则在18世纪浮现出现代国家的世界性模式。这样一个大时段、大尺度的现代化世界史,经过数百年的变化,从传统中开出现代;这样一个大范围的现代化世界史,经过数百年的演进,从世界社会、专制国家中开出了“民族-民主”国家,其构成了现代化世界进程的基本面相。
然而,不管是在时间尺度上、还是在空间尺度上,大历史都是在“民族-民主”国家为单位的具体进程中来呈现的。以农村史、农民史、农业史为代表的传统国家,如何走向以城市史、市民史和工业史为支点的现代国家,在各个国家的表现状态与发展情形,都大为不同。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如前引述,它致力实现了社会变迁中种种要素的平衡发展,因此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性国家。而法国的表现就不尽如人意: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农民所拥有的私有土地比例是全欧洲最高的,但这激发了农民更大的利益欲望,反而掀动了全盘改造国家的意识形态风潮。结果,“大革命”成为全盘颠覆“旧制度”的方式,国家反而陷入了现代化转型的颠踬状态⑦。可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简单地融入大历史、现代化史洪流之中就可以达成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一定是在大历史与小历史、全球史与国别史之间打破旧的平衡,达成新的发展平衡的结果。
二是共同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可以说是这个国家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属于现代化世界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其共性所在;同时,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又都是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状态、现实因素磨合的结果,这是其个别性体现。因此,认识诸如英国式现代化、俄国式现代化、法国式现代化等这类基于国家特殊情况的现代化史实,既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国度现代化的独特性,也可以从中辨认出它们的共同性。如果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未能呈现出超越国别个性的共同性,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被公认为现代化国家;如果在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呈现出它们各自的个别性,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就很可能是止于表象的现代营造,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要言之,就共性而言,政治上的限权、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生活上的公私分流,构成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化国家的共同标准;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个别性,一定是其历史发展、现代转变的结果。就前者而言,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有共同标准需要遵循的;就后者论,现代化没有逼使各个国家都按照某一既定程序、或某个国家的既定方案去推进的模式,现代化的国家特色因此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条条大路通罗马”。
三是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的关系。所谓规范性,在与“价值”相对时,指的是在价值分歧者之间所承诺的同一件事情的一个大体一致的表述;在与“操作”相对时,指的是一套较为程序化、标准化的作业规程。规范性可以从共同性上体现,但不限于共同性。因为规范性不仅着眼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同性,还对保持这种共同性的必要条件、作业方式给予关注。现代化的规范性,构成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标准:政治上是否规范了国家权力、经济上是不是引入了市场准则、社会上有没有遵守友爱互助的行为逻辑等等。现代化的规范性含义,并不无视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尤其是国家进程的特殊性。现代化的例外性,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发展和实际情形,包括其所在国别和具体进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差异性。一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特点,多多少少、程度不同地显现为这个国家的例外特性:就其呈现国家现代化的独异性来讲,它只能是这个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这就是现代化例外性的鲜明呈现。从具体国家这个特定角度看,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例外性、甚或独异性特点。所谓独异性,强调的是此事物不同于彼事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它是“不普适的,不可置换的,不可类比的。一个独异的客体,一个独异的主体、一个独异的地方,一个独异的事件”[17]36。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现代化是独异的,美国的现代化也是独异的,中国的现代化同样也是独异的,其他各个国家的现代化也都是独异的。但在看到所有国家的现代化独异性或例外性特点之余,若没有注意到他们共同呈现的规范特征,就不能把它们表现的某些相类变化命名为现代化。因此,人们有必要在规范性和例外性之间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四、长时段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诚如前述,现代化的世界史是理解现代化史的一个重要维度,而现代化史的国别史则是理解现代化史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这是现代化史既显现出它的历史趋同性,又呈现出它的丰富多样性的地方。这也正是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时,既强调它“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体现中国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的两重特性共在的原因。如果说前面基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就是现代化世界史的特征,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宏大背景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有必要從中国国情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国情视角展开的相关理解,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两个视角:一是中共二十大报告所列举的、基于现实维度的国家情况,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3-25。这些基于中国基本国情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特点,主要是基于现实向度的国家情况所做出的概观。其中也有历史维度的含义,如在阐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特点时,就明显是在历史维度得到定位的:“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23不走一些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这便是再明确不过的历史理解进路了;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则是指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再重蹈历史覆辙,而遵循历史所指引的国家现代化正道以谋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于其他四个方面的分述中出现的历史性辞藻,如“历史耐心”“历史过程”“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也都主要是在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当下问题时确立的历史参照系。从总体上讲,基于中国现实国情所阐述的中国式现代化,主要还是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在当下所必须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断。从较为明确的历史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含义,主要还是从报告所着重强调的两个时间节点上呈现出来,这就是承继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百年,一个是过去向度的,一个是未来向度的,贯通起来,则是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一脉相承的一条历史线索,如果说百年历史线索还相对短暂的话,那么将这一向度的历史线索拉长,则可以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古典背景与早期现代积累两条延长性的历史线索。而正是在千年、五百年与一百年的三个时间段中,我们获得了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相当充分的历史依据。
首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长时段、大间距的历史眼光。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处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大历史轴线上所注定的事情。在前现代化的漫长阶段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国家权力一直管理着非常广袤的土地,儒家思想为国家权力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绵长的支持,国家的自足性维系之历史连贯性非常显著。国家的历史轮廓相当明显,古典中国的社会特征是:“(1)传统取向的;(2)农业的;(3)身份取向与层阶取向的;(4)神圣的(sacred)权威的(authoritarian);(5)以原级团队(primary group)为社会主要结构;(6)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关系取向(ascription)的;(7)功能普化的(functionally diffuse);(8)准开放的二元社会(dual society)。”[18]10金耀基归纳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些特征,可能容有争议,但大体上足以用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则不会有根本分歧。中国古典社会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历经千年的中国历史运行的产物。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就是脱开传统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相应也就必须是建构一个现代取向的、工业的、契约化的、理性化的、次生社会团队的、普遍主义的、成就取向的、专业化的社会。这是一个大历史的转变,转变的历史性要素是:“从身份到契约(status-contract);从神圣到世俗(sacred-secular);从区社到社会(community-society);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agraria-industria);从原级团体到次级团体(primary-secondary proup);从特殊主义到普遍主义(partcularism-univiersalism);从关系到成就(ascription-achievement);从普化到专化(diffuseness-specificity)”[18]61-62。这些变化的趋向,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第一个基本定势。这里需要区分的基本界限是:任意的支持举措,都是对现代化的推动;任何的逆转尝试,都是反现代化的举措。对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而言,反思是必要的,反对是不可取的。原因很简单,反思现代化,可以促使现代化健康发展;反对现代化,是要逆转社会变迁的方向,根本是徒劳无功的。这是从人类历史的长时段、大历史角度得出的结论。
其次,从中国晚明中西文化接触以来的历史看,中国近400年历史的大方向,是向现代化的中国转变。晚明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从总体上来看,是和平、宁静,富有声势和效果的。西方古典科学与文化,随传教士东来,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伴随着耶稣会士大批来华,基督教第三次传人中国,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机械工程与物理、火器技术、地理、医药等自然科学, 以及语言学、音乐、绘画、哲学等传人中国。为了使在华的传教活动在欧洲本土获得理解和支持,耶稣会士在来中国以后,也用写信、著书等方式,将了解到的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文化成就,通报给欧洲,从而使中国文化得以传向西方。在这次东西文化的交流热潮中,更多的是西方文化传人中国”[19]。到清朝,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势头未减,惜乎没有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现代化转变。直到晚清,历经清政府对现代化的全面抗拒,到洋务运动在物质器物层次对现代化的接受,再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全变”,才掀起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波高潮。但中国的这一波现代化,最终在清政府的“皇族内阁”闹剧中收场。由此宣告了从晚明到晚清这一长波的中国现代化归于失败。
再次,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期历史线索看,中国现代化历经了民国阶段的失败,人民共和国早期的严重挫折,到改革开放重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终于迎来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波高潮。中国现代化的这一短波,以百年为时间尺度,以70年、40年和10年为三个基本时间节点:“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百年的时间起点,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近代以来战争的首次获胜者出现在国际社会之际,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中国现代社会变迁历史大幕之际,还是国共两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展开其历史幅度的时刻;而百年的最近终点,则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疾速增长,总量蹿升到世界第二位。简言之,这是一个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发展阶段。在三个时间的基本节点上,展现的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个关键时刻:70年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权力机制的一个时间段,40年是中国摸索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新时期,10年则是中国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递进的新阶段。历史推进的步伐,与现代化的世界史步伐恰相吻合;现代化的中国样式,则是与中国现代化史主调一致性的鲜明体现。在此,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历史变迁的高位规范;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现代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体现。缺乏现代化这个基本坐标,我们无以理解中国现代历史;缺乏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我们无以确认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现代化史的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乃是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何以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背景性条件。缺乏这个必要的背景,人们就很难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之所以以“中国式现代化”来表述或界定的理由。从晚明、晚清、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政治体对现代化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一波三折:从晚明不知历史大势而固守陈规,演变到晚清明知历史大势却不顺势而为,再到民国阶段内忧外患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最后到人民共和国顽强延续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终于摸索清楚中国现代化的国家进路。就现代化的结构层面看,从晚清现代化主要沿循物质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展开,一直到人民共和国前期主要致力推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也仍然是沿循物质器物现代化的线索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再到“国家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层面现代化,最终落实到社会各个层面或领域的现代化方案,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方案上,中国的现代化史呈现出一条有进有退、终于奔向现代化世界史意义上的综合目标的线索。从长时段、大历史到清醒面对现实的历史演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回向当下现实,终于展开了一幅完整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画卷:“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24-25这是历经现代化的艰难曲折之后,才得以“中国式现代化”谋划而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化面貌。
在中国现代化史的两个历史维度中,现代化史的世界史维度,乃是由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所构成的一个总体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是汇入这一进程的一个历史组成部分;现代化史的中国式维度,则是由中国转出传统、转进现代的历史巨变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构成这一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决不能将“中国式现代化”认定为绝无依傍、横空出世的现代化模式。这不是说世界现代化的大历史就自然而然将中国汇入其中,明清两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被现代化世界史自然驱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这就需要中国主动、自觉和理性地融入这一历史巨变进程,国家史才成为世界史的一个部分,现代化才成为中国历史变迁的主调。同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也不是一个随历史的自然时间推进就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有中国人顽强认取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并且不为历史曲折所动摇,坚韧地守护现代化的转变决心,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史才会凸显其历史基调,才会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现代化面目崭露给世人。因此,要想真正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设想,还需要以同样坚韧的现代化信心与决心去应对前路必然存在的种种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26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既定,但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以极为艰巨的努力为前提。所谓“历史使人明智”的道理在此。
[责任编辑:张思军]
注释:
① 對“大分流”进行系统论证的,是加州大学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对两个时间节点尤为强调,一是1800年以前东西方社会变迁过程的相似性,二是1800年以后欧洲在资本主义、市场成长与工业革命表现出独异性,从而成就了“欧洲奇迹”。参见该书史建云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1-4页。
② 這是一个以1215年英国贵族与约翰王签署《大宪章》为政治限权标志的现代化起始说,在人类学家眼中,12世纪的英格兰社会已经浮现一些现代因素,后引历史人类学家麦克法兰的辨析,堪为代表。
③ 相对而言,日本的现代化起势晚于中国,但后劲强于中国。依田憙家指出,从19世纪中期到后期,“当时的中国,民间还不存在主张制度改革的势力。在理念上日本已经摆脱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而中国仍未脱离‘中体西用,因而对欧美的关心仅限于武器、机械及与此有关方面的引进。”氏著:《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④ 只要浏览斯蒂芬·克拉克的《英法千年争斗史》(刘建波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有关章节,以及保罗·M·肯尼迪:《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王萍等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有关章节,就可以知晓英国崛起与维续中的国家承压情况。
⑤ 参见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第三章“无蜘蛛之网,无网之蜘蛛:发展型国家的谱系”,第四章“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体从何而来?韩国‘发展型国家的日本谱系”。
⑥ 参见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第三章“无蜘蛛之网,无网之蜘蛛:发展型国家的谱系”,第75页。
⑦ 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分析,非常到位。“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显得最无法忍受。”冯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4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曾军.从“一种现代性”到“两种现代性”——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的反思[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90-95.
[3] 钱乘旦,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6] 迈克尔·麦吉恩.家庭生活秘史[M].胡振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 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M].管可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 任剑涛.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N].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03-02.
[9] 伊恩·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M].刘雪岚,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10]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M].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德意志问题[M].林国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2]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EB/OL][2022-12-21].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2/65450/4429430.html.
[13]王明远.韩国跻身“发达国家”,不只靠“富”[[EB/OL]].新京报.(2021-07-08)[2022-12-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4727962204435121&wfr=spider&for=pc.
[14]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M].管可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5]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G]//谢中立,等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黄东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6]查默斯·约翰逊.发展型国家:概念的探索[C]//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17]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M].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8]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9]南炳文.明代文化特色浅论[J].历史教学,1999(10):19-21.
Understanding“Chinese Modernization”in the Contextof Modernization History
REN Jian-ta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62,China)
Abstract:“Chinese modernization”is a new proposition,which is not only a summary of the current mod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but also a Chinese achievemen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history for five hundred years.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history.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shows highly related social links,which constitute the complexity and centrality clu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Only in the macro historical clue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can we understand the micro history of“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driving force of“Chinese modernization”can only be identified in the country structure char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Chinese modernization”must be a composite structure of the modernized politics,economics,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But the world modernization history does not mark“Chinese modernization”as an absolutely exceptional historical product,it restricts and def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Chinese modernization”:the modernization is the upper feature,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lower feature,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 defined by modernization as the national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e.
Key words:modernization;Chinese modernization;inter-community;individuality;macro-history;micro-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