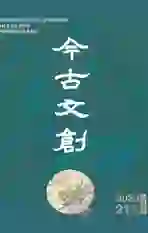从存在主义视阈下解读余华作品《文城》
2023-06-15卢思健
卢思健
【摘要】余华的《文城》看似是与《活着》类似的宿命式悲剧故事,内核却蕴含着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基于存在主义视阈下,本文以海德格尔、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解读《文城》文本里对荒诞的命运、追寻的虚无、异化的生存、暴力的书写以及悲剧性的死亡的阐释,发掘小说对其理论的运用和对人生价值问题的表达,进而探索人性之本质和个体存在的生命价值。
【关键词】《文城》;存在主义;荒诞;暴力;死亡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1-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1.011
余华2021年新发表的长篇小说《文城》讲述了一个动荡年代的北方男人林祥福,一路向南,追寻女儿的母亲小美的家乡“文城”的故事。经过一番波折后,根据小美对自己故乡的描述,他认定了南方的溪镇就是“文城”,于是他留在溪镇建立家业,历经战争、匪乱,最后被悍匪杀害离世,结果直至生命结束也没能再与小美重逢。这部长篇小说是余华回归之作,《文城》在创作上依旧聚焦于人物生命个体的悲苦命运、坚韧追寻与温情守望,再度延续着余华一贯的怪诞笔触、暴力美学和少许魔幻色彩的风格,不动声色地展现出人性的恶,以此来表现人性的阴暗和社会的荒谬,在荒诞中走向苦难,脱离苦难。
一、荒诞的命运与追寻的虚无
余华善于通过“荒诞的故事情节”“荒诞的人生体验”以及“荒诞的存在感”来对人的生存状况展开叙述,他深受卡夫卡的启发与影响,力图在其虚构的世界中复刻现实世界的荒谬与残酷,不自觉中渗透着存在主义思想。
在余华的笔下,他经常将人物放置于特定的艰难境遇之中,来探索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边缘,来表述人在困境中的抉择与出路。小说《文城》里,小美曾与林祥福度过一段短暂的幸福时光,却在偷了林祥福世代积蓄的金条后悄然离去。面对小美的两次离开,第一次,林祥福哭着跪在父母坟墓前痛斥小美不是个好女人,对她心灰意冷;第二次,林祥福决定无论如何要到南方找到这个再次背叛他的女人。对林祥福而言,他对小美一无所知,这样的追寻是荒诞的。常人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林祥福却怀着一股虚无且荒诞的信任义无反顾地踏上他的“寻妻之路”,甚至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随后他就离开了故乡去追赶近乎没有的希望。这一做法或许不被人理解,却是林祥福基于个人的成长性格做出的选择。萨特认为“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人是自由的,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而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理念的不同,寻找小美是林祥福个体本身做出的选择,他没有受到外部观念的影响,因为他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自由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
林祥福向南而行,在江南的二十多个城镇之间来回穿梭,春去夏来,却没有人认识“文城”究竟在何处。在茫茫人海中漫无目的地寻找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虚妄的事。希望渐渐渺茫之时,他听到码头的船家与年轻姑娘的谈笑声与小美和阿强的口音腔调十分相仿,“林祥福觉得这里很像阿强所说的文城,他几次向人询问:‘这里是文城吗?得到的回答都是:‘这是溪镇。林祥福接下去问:‘文城在哪里?林祥福看见迷茫的眼神,还有果断的摇头,这里没有人知道文城。” ①他开始意识到文城可能是不存在的,后来,“文城”已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精神寄托的家园,是林祥福“追寻”的目标,也是他跋山涉水“追寻”的完整家庭;是溪镇百姓“守护”的故乡,是溪镇的兵民守卫无数次慌忙逃难,却终究没有离开的城;是小美和阿强“追逐”的幻梦,他们私奔外逃,到过上海、定川甚至更北的地方,无数个落脚之地却没有一个心之归属,他们对自由的追逐终究变成虚无缥缈的幻境,阿强随口说出的“文城”可能就是自己曾臆想的远方和故乡。
为了女儿的成长,林祥福在几经徘徊后决定重回溪镇等待小美。戏剧性的是,余华在结尾《文城补》中揭露溪镇其实就是文城。而小美第二次离开后便和阿强一起回到溪镇,正是在林祥福踏着暴风雪而来抱着女儿路过城隍阁时,遭受连日雪冻灾难的小美和阿强跪在城隍阁外的空地上冻僵而死,他们相遇而错过,命运般的巧合更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荒诞性”。萨特曾在《恶心》一书中说,“世界是荒诞的”,在他看来客观世界是一种自在的、纯粹的、偶然的、不合理的存在,毫无规律法则可言。荒诞是世界的本质,而存在是偶然的,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所有存在都是具有偶然性,正如小美的死是偶然的,也是荒诞的。溪镇连遭多日暴雪,為了祈求上天庇佑灾难过去,抑或是为抚平内心对女儿的愧疚,小美决定去城隍庙祭拜苍天,没想到被冻死在城隍庙外。她死前仍跪在雪地中祈祷,雪花纷纷扬扬落在她的头发上、身上、眼睛上,她却目光茫然,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这种不可预见性的偶然证实了存在之偶然,存在之荒诞。
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他人是一个存在的客体,“客体”无时无刻不在打击恐吓、威胁甚至毁灭“自我”,所谓“他人即地狱”,由此生出孤独恐惧、悲伤绝望之感。然人亦可通过与命运的抗争,即个体的“自由选择”,竭力消除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异化。存在即面临“选择”,人们自以为可以对命运自由地做出最佳选择,其实这一根本的“选择”在无差别意识中决定了我们与事物,他人与我们自己的关系,这个“选择”指向了另一世界的“存在”。林祥福选择去寻找小美,寻找文城,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但其实,人世间一切的动机与欲望,都只能运作于一个“被选择”的世界之中。正因如此,这个选择本身就是荒诞的,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在选择发生的时候已有定论。林祥福为了给女儿喂奶认识顾益民,“偶然”知道城隍阁正举行祭拜苍天仪式,又“偶然”地经过这里时,恰好小美也“选择”来到城隍阁,本以为命运终于让他们相遇结束互相追寻的精神折磨,又接连不断的错过发生反转,最终天人永隔。人类的行为与选择会决定存在的结果导向,“荒诞”是人生的常态,“自由选择”其实也是“被选择”,人都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最终走向,正如林祥福最终还是在同一个地方与小美错过,仅仅一步之遥。
二、异化的生存
当人被“抛弃”到一个无法用理性去解释、毫无逻辑的、异化的、荒诞的现实当中,就会产生一种“被抛弃状态”,马丁·海德格尔称之为“畏”,这也是萨特在《恶心》一书中所述的荒诞感、恐惧感情绪,这种异化的情绪体验在存在主义哲学里被称为生存状态。《文城》里溪镇匪患时期的描写正是对这种生存状态和异化现实的反映。清末民初,在那个军阀混乱、盗匪肆虐的年代,习惯安居乐业的溪镇的百姓们面对土匪进城的动乱惊慌失措,害怕土匪对自己处以“耕田”“压杠子”“划鲫鱼”“摇电话”“拉风箱”和“坐快活椅”等酷刑,甚至匪夷所思地用土匪的刑罚“耕田”进行比赛。在听到北洋军残部正往溪镇而来时,逃难的恐慌在百姓中蔓延,于是麇集蜂萃的人群跟风制作竹筏妄图坐着竹筏藏进万亩荡的大片芦苇里,结果纷纷掉落竹筏沉入寒冷刺骨的水中冻僵而亡。饥荒遍地、民不聊生,百姓的生存空间被压榨,也使得像和尚一类的本性善良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当土匪。个体的生存体验表现出对生存状态改变的极度不安,使得大多数人在面对异化的环境中表现出了惊慌、痛苦、孤独、焦虑、恐惧等潜意识情绪和生存感受,人物的行为变得不合常理,无可避免地掉落到生存陷阱之中。作者在小说中展现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百姓的生存现状,揭示人在异化的生存环境中的情绪体验和现实人生随时遭遇不幸的悲苦,更甚之,触及了人异化生存的社会根源。“异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想法和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却不是独立存在的,无可避免地会与周围的人和事物发生联系。马克思指出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很难离开周围的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当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遭遇重大的冲击时,个体的生存状态就会不自觉“异化”,从而形成一种保护个体的新的机制。
三、暴力的书写
西方现代行为学创始人康拉德·洛伦茨在《论攻击》认为,“人的好斗性是一种真正的无意识的本能。这种好斗性即侵犯性,有其自身的释放机制,同性欲和人类其他本能一样,会引起特殊的、极其强烈的快感。” ②在余华的作品里,无论是在《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往事与刑罚》《祖先》,还是如今的《文城》都描绘过一些非常暴力血腥的画面,作者对暴力的关注显现出他对人性之恶的关注,人性之恶以“暴力”制裁的方式来获得胜利。
土匪头子张一斧作为《文城》里的最大反派,无疑是凶残暴力的,以他为首的土匪们在万亩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围攻溪镇虐杀独耳兵团,绑架商会会长顾益民百般虐待,残忍杀害林祥福,为了泄恨血洗齐家村。“大群土匪走来时又是朝人开枪又是挥刀砍人,村民乱窜逃命,那些女人们,看见自己的孩子在枪声里倒地,发出凄厉的叫声,一个个扑了上去,手持利斧的张一斧对准扑上来的女人乱砍,其他土匪也用長刀砍向她们。四溅的鲜血让空气里飘满血腥气息,后面的女人看见前面的女人被砍下肩膀、砍下胳膊、砍下脑袋,仍然视而不见地扑向自己的孩子。” ③在描写血洗齐家村时,余华冷静又细致地描述了张一斧等土匪的恶行,通过这些血腥场景的铺排去展现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形象,用善恶、强弱的对比,暴力残酷的书写来凸显人性中的扭曲、邪恶与变态,探讨社会与人性的可能与纠缠,让人看到异化的社会环境下,被放大的人性内心的邪恶之花。作者意图以张一斧等鲜血淋漓的暴力之丑反衬林祥福、陈永良等人的真善美,暴力的书写最终是凸显对人性善恶的挣扎和深刻的省思。
四、悲剧性的死亡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的事实并不只是经验意义上的可能性,死亡是自我存在的内在可能性,“我”随时都可能要死,而且“我”也肯定会死,无论是死于哪种方式,因此死又是“自我”存在的极端性。而在明知生之不可能之时,仍朝着生的可能性存在前行,走向人生的终结,直面死亡,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生”。唯有真正的“向死而生”才能体悟到生命之本质,冲破对死亡的恐惧,实现向死之自由。《文城》里林祥福的从容赴死与存在主义的“向死而生”在内核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林祥福与女儿在溪镇度过了一段平稳幸福的时光,可是苦难从未远离他。在张一斧设计抓走民兵团首领顾益民,并以此要挟溪镇交出民兵团的枪支时,林祥福主动做代表赎回顾益民。出发前林祥福已经预示到此行凶多吉少,他留下三封信分别给田大、顾益民和女儿林百家,他写下“叶落该归根,人故当还乡”,随后又用笔抹去了。此时的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仍然残留着最后一丝期待。林祥福在去往匪窝的路上不断想起女儿林百家,回忆自己的一生。余华用了一个长长的铺垫暗示林祥福终将到来的死亡,这一延宕的手法也增强了结局冲突的尖锐性和情节的紧张性,让观众对结局导向有了一定的预判和心理建设过程,更凸显了结局的悲剧性,也强化了林祥福的明知生之不可能仍前行。这就是海德格尔“先行决断”的死亡观,人在走向终极存在的过程中预见了前路即是死亡也不畏惧,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林祥福的坦然赴死正是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最佳诠释。
林祥福的预感没有错,张一斧没有打算放过他。到了匪窝后,张一斧谎称已经杀害了顾益民并做成炒肝,激怒林祥福与他搏斗,最后用尖刀戳进林祥福的左耳根处,杀死了林祥福。“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尖刀还插在左耳根那里,他的头微微偏向左侧。他微张着嘴巴眯缝着眼睛像是在微笑,生命之光熄灭时,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 ④余华对林祥福的死作了模糊处理,生命之光将熄时,林祥福面带微笑,死亡对他而言已不是恐惧,而是存在的终极意义。林祥福的死亡具有一种英雄式的悲剧性力度,生,如果不伴随着死亡,就无所谓生。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如果我让死亡进入我的生命,接受它,直面它,就可以摆脱死亡的恐惧和生活的琐碎——那时候我才会自由地成为自己。” ⑤死亡让人获得更豁达的胸怀,摆脱对死亡的畏惧,在超脱的精神境界中正视生与死,这才是“向死而生”内核所在。
在《文城补》里,余华补叙了小美的故事,她是“文城”故事成立的核心,却一直隐而不现,直到最后才在读者的上帝视角下揭开面纱。小美与阿强其实是一对溪镇上的年轻夫妇。在小美被婆婆欺辱赶回娘家时,阿强带她逃离了溪镇,阿强是她唯一的慰藉和救赎,所以她无法说服自己在遇到林祥福后就抛弃阿强,同时她又时刻牵挂着尚在襁褓的女儿和善良忠厚的林祥福。当她知道林祥福带着女儿找到溪镇,与阿强的惊慌失措不同,她是认命般的泰然处之,“阿强胆战心惊,他觉得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他们偷窃金条的事一旦暴露出去,就有牢狱之灾。而小美却已认命,如果牢狱之灾不可避免,她会泰然接受。小美说:‘我们罪该如此。” ⑥因为离林祥福越远,她对林祥福和女儿的牵挂、愧疚反而越深,她甚至期待林祥福找到他们,接受命运的惩罚。当小美跪在雪地里,像蝼蚁一样同许多人冻死之时,她心怀歉疚地走向了自己的归途。小美的死亡看似是没有意义的,而实际上死亡却是她一直追寻的内心安宁。死亡的自觉正是生的自觉,因为小美不再畏惧死亡,正视死亡,为了自己心中的虔诚做出选择,因而促使她在死亡之后真正回归到人的本真状态,强化了悲剧的美学价值。
小说的最后,小美和林祥福终于在死亡之后碰面了,一个在坟土中,一个在坟旁的棺材里。“小美长眠十七年之后,才在这里迎来林祥福。”片刻后,田家兄弟拉着棺材的车向北行去。这种灵魂意义上的重逢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局,充满了遗憾和惋惜,正是这种缺憾的留白、强烈的悲剧感和对美好事物消亡的极致展现,使得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对个体生命思考的艺术价值倾向更加明晰,死亡的深层悲剧美学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五、结语
关于余华,以往人们认为其深受卡夫卡的影响,作品中多呈现现实主义的先锋色彩。然而对于作家思想及作品的解读不是定式的,是多维的,从各种不同角度剖析作家作品,更能直面作家的内心世界,挖掘人性的多面性。概而观之,余华在《文城》里并不过分探求时代流转变迁的原因,而是关注时代变革中个体的价值命运,从林祥福为了一个虚无的文城去追寻小美踪迹却几番错过来质问命运的荒诞;从遭遇匪患的溪镇百姓面對灾祸惊慌、恐惧的生存感受诠释异化的生存环境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从对匪徒凶残、暴力的书写凸显对人性善恶的挣扎和深刻的省思;从林祥福和小美悲剧性的死亡揭示对生命意义、对人生、对个体存在价值的思考,以重新追问和体认生命生存的价值意义。余华历时八年创作的这部长篇,正如《文城》的卷首语所说:“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人生之存在,并无预设的意义,因此人具有绝对的选择自由,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选择,兜兜转转间,营营役役中,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意义。
注释:
①③④⑥余华:《文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58页,第206页,第197-198页,第326页。
②(奥)康拉德·洛伦茨著,刘小涛、何长安译:《论攻击》,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⑤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2页。
参考文献:
[1]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2](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3](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文集:第一卷[M].沈志明,艾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