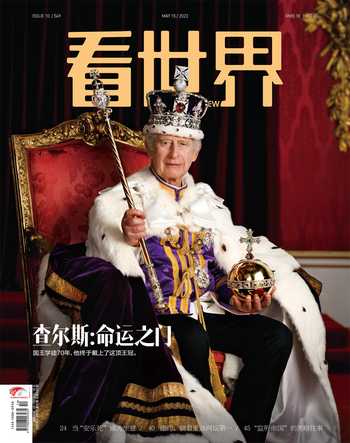德国告别核时代,是否正当时?
2023-06-12费雪
费雪

2023年3月29日,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内卡韦斯特海姆核电站,能源供应商EnBW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即将关闭2号机组
据德新社报道,4月15日晚,“伊萨尔2号”“内卡韦斯特海姆”和“埃姆斯兰”核电站与电网分离,宣告德国长达60多年的“核时代”正式结束。
同一天,德国首都柏林勃兰登堡门两侧,举行了两场集会:一侧,是反核活动人士庆祝他们的胜利;另一侧,示威者却在以游行反对德国政府关闭核电站的决定。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勃兰登堡门和柏林墙曾共同见证了德国近半世纪的分裂,如今又再度成为德国因核能意识形态差异,而壁垒分明的见证者。
的确,欢呼、叹息和质疑交织错杂下,核电站停机后,还有更多的矛盾形势,留待德国去面对。
民意反转
纵览民用核能在德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国内对“拥核”与“弃核”反复拉锯的纠结态度,深受国际能源重大事件的影响。
从1957年西德第一座核反应堆投入运行、1959年《核能法》颁布,到1960年卡尔实验核电站落成并于次年投入使用,这一时期德国核电事业逐渐发端。
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应对国际油价在1974年与1980年的两次飙升,德国的核电研究与应用也相应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包括各地二期、三期工程在内,德国共计修建了31座核电站,这贡献了德国总发电量的1/4。
但对核能的质疑也一路影随,安全问题则是争论中心的“风暴眼”。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催生了德国国内的反核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80年德国绿党的成立。
自1986年前联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后,德国核电装机增长量开始走向下坡—在两德统一当年,仅有的两座基于苏联技术的原东德核电站宣布关停。
而高达41%的断崖式下跌则出现在2011年。德国国民始于上世纪末的“核能大辩论”,因目睹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巨大不幸,终于达成了“退核共识”:在该年6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当即关闭8座核电站、其余9座于2022年底退出的决议。
根据次年德国媒体展开的民意调查,此时支持2022年退核的问卷受访者达76%。
但今年4月初发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在停运最后3座核电站这件事上,竟有超半数受访者(59%)持反对意见,赞成者比例则下滑至34%。
民意“翻转”的肇因,是俄乌战争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
为支持乌克兰,2022年以来,美国联合其欧洲盟友“瞄准俄罗斯经济的大动脉”,对俄能源类商品出口予以制裁。但力的作用也是相互的—为实施反制,俄罗斯亦以能源为武器,紧紧扼住了欧洲的咽喉。
要知道,到2021年,德国所用天然气的55%,都源自俄罗斯国有公司Gazprom。限供使德国国民的注意力,立刻转移到对高昂能源账单的忧虑上。

2023年4月15日,德国慕尼黑,反核活动人士在奥迪昂广场庆祝最后三座核电站关闭
德国经济记者Peter Tiede就曾发出了警告:“任何认为乌克兰冲突与他们无关的德国人,最迟在加油站和燃气灶旁,就会感受到要支付的代价—能源成本将上涨30%到70%!”
2022年9月26日,德國“北溪1号”和“北溪2号”海底天然气管道突发3处严重损坏,更使德国民众的能源负担雪上加霜。自此,德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的生命线被切断,恢复供气遥遥无期。
涟漪效应的传导十分迅速,来自下萨克森州的Guido Kuschenek对德国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幅度感到震惊:“我家往常的天然气预付款是每月86欧元。从(2022年)10月14日开始,我们每月要支付大约666欧元,几乎是以前的8倍!”
这不是个例。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所长Marcel Fratzscher指出,目前德国三分之一的家庭,没有足够储蓄来承担愈发高昂的取暖等能源成本。
对核能的质疑也一路影随,安全问题则是争论中心的“风暴眼”。
当财务窘境迫在眉睫,德国民众自然不愿再失去核电这一廉价稳供的选项。“屋漏偏逢连夜雨”,悲观情绪正在德国加速蔓延:在德国有调查显示,只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2023年他们个人的经济状况会更好;而多达40%的人担心着情况进一步恶化。
退核之争
在德国,2021年的三党联合组阁联合执政,尚属历史首次。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交通灯”政府,按下了坚持退核的同意键,却并不意味着国家共同意志的形成—恰恰相反,官员公开分边站队的局面出现,可见矛盾正在激化。
德国经济研究所能源、运输和环境部门主管肯弗特(Claudia Kemfert)曾表示,目前德国仅有5%的电力来自核电,可以很容易被取代,停电之虞并不存在。
不过情况似乎并没有她宣称的这样乐观。事实上,德国总理朔尔茨作出同意退核延期执行的妥协,就证明了在能源价格飙升的压力环境中,反对关闭核电站的声音在德国政府内部相当响亮。
但德国的反核车轮已持续转动了几十年,想要“开倒车”又谈何容易。以出自绿党的德国环境部长莱姆克为代表,主张全面淘汰核能的一方如此辩护:“核电的风险最终是无法控制的。淘汰非友好型能源(核电)将使德国更加安全,并避免了更多核废料。”
然而规避可能发生的核灾难,亦有其必然承受的代价。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便痛斥,在各国致力于能源来源多样化时,停运核电站无疑是与世界趋势背道而驰的“绝对错误的决定”,德国将因此面临电价上涨和企业外移的风险。
被打上问号的还不止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保守派人士直言,更大的隐患恰恰埋在德国绿党和左翼人士主张的环保领域。他们呼吁,在德国陷于能源市场被动态势之时,应摆脱“唯绿”的教条主义,避免盲目弃核导致国民生产生活重又依赖化石燃料。
在全面无核化决议实施前夕,该派代表人物德国财政部长、自民党党首林德纳便再次高调反对了联邦政府淘汰核能的路线,为保留仅存的3座核电站做最后的努力。
这些顾虑不无道理。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气候和能源政策教授斯托克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自福岛核事故以来,德国减少核能带来的能源缺口,主要由煤炭能源的增加所填补。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公布数据也可为佐证—2022年传统能源发电占德国总发电量过半,其中燃煤发电便达33.3%;而在德国最后3座核电站关停后,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塞斯的团队估算,德国每年还将增排1500万吨二氧化碳。
这也就是说,当下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以“充裕的天然气储备、新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持续发展的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核能的想法,大概率无法实现,退核并没有促使德国迅速走上一条“更可持续、更有利于气候”的道路。

2023年1月14日,德国卢布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液化天然气终端前转动障碍轮,象征位于波罗的海的液化天然气输送终端正式投入使用

2023年1月8日,德国勃兰登堡州,建设中的风力涡轮机
风电项目的规划和审批,平均需要4到5年的时间,难以立刻挑起大梁。
转型之困
那么,中长期来看,世界能否期待德国能源转型成功?
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发言人表示,在全面退出核电后,德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到那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将达到80%;至2035年,德国将100%由可再生能源供电。
对于这一发展目标,来自欧洲国际经济学领域顶尖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的能源专家Georg Zachmann坦言,即便是在有核电填补市场的情况下,德国都显得“雄心高于现实”。
而抛弃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技术选择,未来还计划关闭所有燃煤电厂,如何保持能源供需平衡,势必会成为德国政府一个棘手的问题。
據德国官方数据,2022全年,德国发电量为506.8太瓦时,其中,共计46%的能源供给都来自可再生能源,较十年前25%的份额近乎翻了一倍,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势头不可谓不猛。
但核心矛盾依然存在:可再生能源的客观增速,无法跟上政府的主观期望。
德国总理朔尔茨做过估算,德国需要在未来几年内,每天安装4到5台风力涡轮机,才能满足绿色能源目标—但实际上,2022年全年,德国仅安装了551台风力涡轮机,还不足朔尔茨预设数目的一半。
德国风能行业协会(BWE)还宣称,风电项目的规划和审批,平均需要4到5年的时间,难以立刻挑起大梁。
光伏面临的困境也是同理。按照计划,2030年,德国光伏发电总量要达到200GW,对比之下,现在只有7GW/年的光伏发电量简直是杯水车薪。
支持德国能源转型的智囊团体Agora Energiewende计算后指出,德国需将太阳能设备的安装速度立刻提高一倍以上,才有可能实现供需平衡。
而回溯昔年德国光伏产业“过山车”般的发展历程,这一构想恐亦难如愿:从2009年开始,德国光伏装机量进入快车道,2012年的新装机量,更是达到了超越当下水平的8GW。但彼时,德国日电力需求峰值才8600万千瓦,电网平均负荷仅为6000多万千瓦/日。
眼见供大于求,德国政府踩了急刹车。其后短短两年,德国光伏新增装机量便萎缩至1GW—骤减近九成,致使光伏行业破产浪潮席卷,至今未能恢复如初。
也许正如BBC所认为的那样,种种不利因素都指向一个结论—德国现在告别核电,“还不是时候”。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