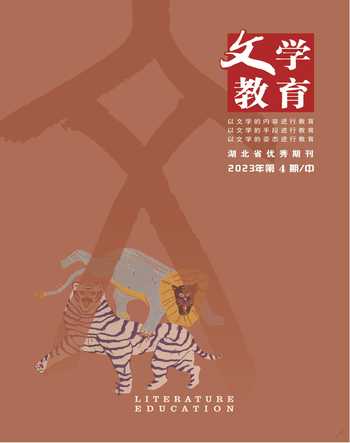相遇2050
2023-06-12杨天宝
杨天宝

现在是2050年,我是一名历史学家。从很小时开始,我就想当历史学家;我想每天看着三千年前故事的人绝对比盯着手机的人帅了许多。历史学家留着汉代中国人一样的辫子,抽着维多利亚时期的哈瓦那雪茄,用着派克1950年款的钢笔——我承认,以上的看法受我学物理的父亲的影响。父亲从小就是个文学天才,曾在一个早自习的时间里同时写完两篇作文,一篇是上周的,一篇是上上周的,最后都变成范文在班上读。但他大学时还是学了物理,因为他对1990年的历史学很失望,偏偏那几十年里这套理论又从未变过。父亲认为历史学是绝对公正的,具体来说,是和意识形态这些东西分开的;但那时候的历史书里三句不离当代的什么什么最好,似乎历史也成了大话体系的一部分。他对我说,要像中国最早的史家司马史公那样,用最公正的笔去写,别人怎么阻挠你都不要改一个字。我说,但我怕也受了宫刑,你老杨家就断子绝孙了。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小时候我学得最好的一门课是数学。但当时我几乎用尽全力在学历史,初中第一次考试拿到了12分(满分100)的好成绩;父亲气得满脸发紫,但好处是他之前有点毛病的脑血管被这一气搞通了,他现在七十来岁还能跑步全拜我所赐。我初二的时候被选去参加数学联赛,做完正半面一百分的题就以为结束了,后来拿了一百分却发现自己是全场中游,因为反面的卷子我根本没看见!我就跟竞赛教练说我不太适合搞这一行,然后头也不回走了。直到中考前父亲拉住我长谈,讲了他年轻时怎么突破瓶颈云云。最后他起身时撞了一下柜子,掉下来的木匣砸中了我的头;我昏过去半个小时,醒来后仿佛参透了命理,最后我所有文科加起来只扣掉了两分。
我参透的命理很简单:把我先前所想的东西反过来写,就能把错的变成对的。比如说,之前我写:与史实的契合度是评价历史论文的关键;现在我写:字写得好不好是写作的唯一捷径。以前只能写东方古代怎样腐朽,现在只能写西方当代怎么黑暗。如此这般,上了高中以后我名正言顺当了历史课代表。历史老师从不管我,因为我从未跌到过第二名。可在这些成功背后的我每次都更加迷惘:我之前到底是哪里搞错了?有时候上一题还在写:儒家思想禁锢人的精神;下一题又是:儒家思想指引我们前进。我问遍了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出答案,或是说没有答案能让我明白。是大家都不够聪明,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不懂,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装傻,我和这个问题斗争了整整三十年。
到了2050年,事情又变得不一样。2020年的人更喜欢批评,你写了一点和他们不同的就被说成“破坏团结”“标新立异”;写了和其他人一样的又变成“没有新意”“人云亦云”。可藏在这下面的是,圈里和圈外的人可谓渐行渐远,里面的人写的外面看不懂,外面的人说的里面听不见。2050年的各位试图握手言和,可思想上的分歧怎么可能平复得了,最后变成了我对你點头,你对我点头,可能还夸对面长得好看,然后走开。在我还是一个历史研究员的时候事情就在向这方面发展。我写了一篇名为《关于汉高祖刘邦是同性恋这件事》的长文章交给我的领导;她看了第一页的第一行和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后点了点头,说:你的字不错。我一直没有告诉她,其实我是用电脑打的。后来那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我还拿到了稿费,算是为后来我成为历史学家开了个头。
2040年的时候我被借调到某个大学讲选修课。我自信地选了思想史作为主内容,却发现他们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除了孔孟荀朱王之外的任何一位思想家。我决定先讲讲古希腊,从泰勒斯开始。第一课结束之后学生们都以看外星生物的眼光看着我,再就是让我把一周二十几节课全上完等等。我拔脚飞奔,当然心里仍是有点开心,毕竟学生喜欢我讲课。然而下午校领导就来找我,先说什么学校最近花大价钱买进全新的摄像头,能以8k画质和FLAC音质把一切细节都录下来。我说,那一定很适合拍片。领导浑了我一眼说,你不要嬉皮笑脸,我知道你很优秀,但你现在讲的东西很危险,会害了年轻一代。我说,苏格拉底当时也被说“毒害年轻一代”,人家是世界最有名的哲学家。他说,那你又错了,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哲学家只有那几位;我劝你深刻反思一下。我愣住了,直到他离开时关上门我才反应过来。
2050年又有人找我讲课,我说,能不能讲点我自己想讲的。来者说,您是学界专家,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真的吗。他说,我们保证。我说,讲几节课。他说,就一节,我们搞的是面向全校师生的讲座,您忘了吗。我才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那些专家院士来也只讲一节课就走,海报却挂满了半个学校;现在我也到了这一步,可能得点点头承认我自己老了吧。我到达地方之后看到海报上写着“知名历史学家杨九,代表作《历史的必然》等”。其实我的两本书分别叫《历史的偶然》和《历史的遗憾》,可他们似乎并不承认历史有“偶然”一词,甚至把那本书归在“文学”一类。第二本书我吸取教训,可他们好像也不许我们“遗憾”,毕竟历史是永恒发展的……
我问,你们为什么学历史。有人回答,要做伟大新时代的记录者。我再问,所有人都八九不离十。我突然感到一种悲哀,2020年我的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学历史,我说“为了公正地评判”,我同桌说“为了看清过去而面对未来”;所有人的理由都不一样。更久以前我问父亲为什么喜欢历史,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又问学生,你们最喜欢哪段历史。断续有人回答: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三大改造……甚至还有说文化大革命的。我特别问那位学生,你为什么喜欢文化大革命?他支吾了一会儿说,因为我听说革命都代表先进的战胜腐朽的。
从此我下定决心再不去学校里给孩子们讲课。但留在我任职的研究所里实在过于无聊。2010年起我接触到电脑,那时年少的我几乎学会了一切。2050年的网络可谓极为简约。因为2030年我们全都装上了国产的操作系统,从此桌面上就只剩办公程序和几个音乐视频软件。游戏什么的早已绝迹,2030年我隔壁寝室的研究生被抓去了强制戒网所,就在强制戒毒所的隔壁。这之前有这样的事情:2020年游戏被与毒品划了等号。有的孩子玩了游戏发现身体一切正常,就觉得吸毒应该也是这种感觉,于是乎吸毒的人数骤增。我母亲之前是戒毒局的,那时正准备换工作,硬是被拦了下来,加薪加保险让她多呆几年。国家级操作系统出现以后,人们开始销毁或抛弃电脑,这样一来电信系统的岗位都空了出来。极大地缓解了IT产业的内卷。起码我回母校的时候,信息楼已经结满蜘蛛网了。
以上就是到2050年为止我经历的一些重要的是,下面我还想写一些琐事,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拆我的棺材板,谢谢。
2050年的人际关系与前一百年的所有时间段都大不一样。或许是因为2020年时的人们有太多的争吵,2030有太多的急转,2040又太过死寂;2050年的人们既孤独,又团结。其实这二者是不冲突的,孤独的人在一片大海中漂流,为了不被风浪卷走便聚到一起,但仍是以各自抓住的木板漂着的。互联网时代人们的怒火随着电脑的淡出而消却,摇摆的年代所有人都习惯了独自奋斗,而今日大家重新连结起来,只是纽带变得更加虚幻,究竟是什么,也许以后的历史学家才能讲得清楚。
2030年的我曾以为婚姻关系会很快解体,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有几年人们高度反对结婚,可真正能在房价车价前经济独立的人可谓少之又少;最终仍然选择了妥协。不过我倒是至今未婚,你问为什么:几乎没人看得上一个看上去能被风吹倒,却长了一米九个子的人。我看上去像一根牙签,学生们都这么说;可他们不知道我十几岁时是足球队的主力,只能说是他们的不幸。人们对婚姻的选择也几乎依旧。最大的改变是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重点是要会玩。我舅舅的孩子就很会用钱,不买车,买了两台游戏机,任天堂和索尼都玩,禁令出来前夫妻俩带儿子一起玩马里奥赛车。工作和生活的契合度仍是关键,当然有件事是肯定的:没有任何一件工作和历史研究相契合;如果有,那一定是赚钱,因为它与任何一件事都契合。
为什么有这样的结论,因为写历史的要想文章发表,必须遵循两个原则:把现在的制度写好,把现在的人写坏。这件事王小波在1995年就发现了,而2050年仍旧如此。许多自信的人看了就想:你凭什么说我们不行啊。还有的沉湎过去的人想:你凭什么瞧不起古代啊,最后是两边不讨好,像粘了锅的烧饼一样只能丢掉。所以哦别说结婚了,我们走在路上都怕给人认出来。和我同办公室的小张就有一天被找了麻烦。停车场里有人把他的车擦了,交警来问身份时他说自己是写某某史论的;那交警当即变脸:你丫就是那个说当代人只懂利己的?二十四字里哪有利己了?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最后一分钱也没让赔。
三十岁之前父母也催过我结婚。后来我告诉他们,之前受了情伤,现在什么也不想做了,等哪一天缓过来吧。后来二老沉迷钓鱼,再没有管过我。写到这里我才想起来2030年第一个解体的反而是亲子关系。其实两代动物之间的矛盾从人类诞生前就存在于世界上了,可谓是生物的本能之一。中国人的老祖宗不同意,偏偏加上三纲五常试图扭转;2020年我上学时老师还在说:在古代,骂父母老师是要杀头的。可我查遍二十四史,也没找到哪个传主因为骂老师而死,只看到有人因为老师被杀而受牵连。老祖宗说,百善孝为先。我们现代人说要批判吸收,又说在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用之前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中国当代的精神面貌是:放不下过去的,拿不出未来的,看不起自己的,受不了别人的。我倒觉得值得商榷,毕竟2050年的人们都放下了过去。
2030年的某一天突然有一所学校的孩子造反了。他们联名写信,说家长们所有的话都在说学校做得不好,最后小卖部没了,信息课停了,外语课改了,图书馆也关了。他们开始质疑计划生育时代以来的家庭关系。这件事越闹越凶,所有老一辈的人都说:这都是为了你们好。所有孩子都说:这就是一种绑架。后来我们评价时大都秉持一个观点:无论这场争吵最后谁获胜,都足以证明前段时间的家庭教育完全失败。果然最后上面介入,各打二十大板收场。有了这个先河,家长更怕孩子起义,孩子更烦家长管束。终于在2033年的某一天,一封遗书震惊了全中国。一个成绩一直在班上二十名开外的男孩,他用大段的笔墨写自己已经非常努力,仍被看作是为了能偷懒而故意进行的伪装,证据是成绩一直没有上去。他写道:那就像等了一年的花儿死在春天的酸雨之下。那时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发病率已达到接近百分之十。
我小时候有一个观点:叛逆是历史的原动力。越长大我越同意这句话,但我们却一直想让别人服从。1911年到1949年的革命好不容易让人把辫子剃掉了,现在又重新长回来,我百思不得其解。在2050年我说,你们这是封建余孽;别人只说,对对对。说话这件事似乎正在失去意义,我才想起沉默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可现在是,沉默中没有爆发也没有灭亡,沉默本身也在沉默着。
下面再来说说我自己。2018年我情窦初开,喜欢一个当时比我优秀得多的女孩。我们一起逛过街,互相送礼物,放学一起走,一起聊期末考试。直到她突然转身离开,我才发现我什么也不能也不曾给她。后来我身边陆续有人走过,而我从会想起那个叫C的女孩。那道伤疤像无意中抓破胸口后留下的痕迹,不痛,却几乎不会再痊愈。我想那也许是丘比特对我射出的一箭。其实我也撒了谎,我想成为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和她约定过,以后要把这段日子写进历史书里。可在2050年,历史书里连人名都很少出现了,因为个人对历史的作用是不存在的,这样看起来司马迁也显得尤为荒谬。
我做梦时仍经常回到被木匣砸中的那个夜晚。听说那是家传的宝物,而它确实让我走上了一条自己挺喜欢的路。如果没有那样的巧合,也许我也成了一名理科生,也许早已从了大流结婚生子,并又告诉我的子女我曾是多么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这让我总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是幸運的,毕竟更多更多的人一辈子也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人连自己喜欢什么也不明白。只是那个从小带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是大家不够聪明,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还是只有我一个人沉醉在自己的理想乡里,像一颗曳尾的彗星燃烧殆尽,我一直没有搞明白。
那个叫C的女孩曾对我说,有人关心你,会为了你的情绪变化而喜怨哀乐,实在是一件莫大的幸事。而我只会对她说,谢谢,对不起,噢,明白。所以我究竟有没有成为我梦想中那样遗世独立洒脱善良的人,其实是个巨大的问号。她曾说我是她最好的朋友也无法相比的存在,后来也只是对我失望,连一句话也未曾留下;她其实是另一颗星星的轨迹。这样看来,许多事从开始前就注定是冲突的,可2050年的历史学家们,竟然天真到想在书里用“规律”用“秩序”抹去这样的矛盾,用“他们”抹去“我们”,这真是件搞笑的事情。
现在是2050年,而我仍在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我究竟在做什么呢?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夏天离去,桂花刚刚送出芳香;明天会和今天一样,没有人会写我曾在今天做过什么。这个名字在我死后还属不属于自己,这个我也说不准。不过至少现在,我成了读者诸君生命的一部分,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这真是一种解脱,你说是不是?
(作者单位:武汉市外国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