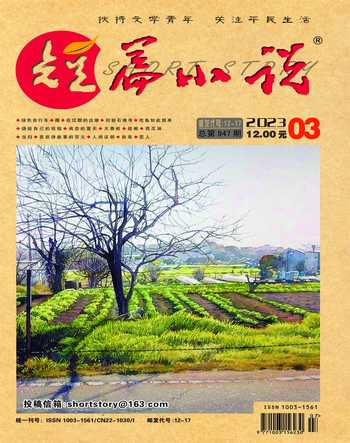病态的夏天
2023-06-09王善常
王善常
一
今年的这个夏天不同寻常,出奇的热。气象预报说最高气温三十八度,三十八度是发烧。就是说,这个夏天是病态的。
齐自新坐在街边的石凳上,两小时了,一动不动,像石凳的一部分。之前坐在那时,他头上还是浓密的树荫,但现在已经下午两点多了,太阳慢慢向西走,树荫慢慢向东走,他就慢慢地暴露在了太阳底下。
街对面有一家发廊,门口的音箱一整天都在放歌曲。齐自新数过,十七首,循环着放。这些歌曲大都是流行歌曲,节奏快、热情,和天气挺相配。但其中却有一首不是流行歌曲,是民歌《草原之夜》,在《小苹果》之后,在《最炫民族风》之前。齐自新闹不明白,店主为何会把这首民歌和流行歌曲编在一起放,这种安排隐含着一种突兀,一种格格不入,像一只洁白的绵羊误入了猪群。
在播放其他十六首歌时,齐自新就关闭了耳朵功能,只看路上的行人。他这几年养成了个习惯,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街旁,看路上的行人。他喜欢揣摩和猜测那些陌生人的人生。他知道每一个匆匆走过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虽然他无法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但正是因为无法真正了解,才让他的这种猜测和揣摩更具有了意义。什么意义呢?齐自新自己也说不明白,反正就是一种令他愉悦的体验。也是,意义按词典上解释,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物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这就够了,他要的就是这个。
播放《草原之夜》时,齐自新就收回目光,闭上眼睛,细听。每当乐曲响起,仿佛已经不再是夏天,不再是正午。阳光穿过他的眼睑,他满眼映出的是红色的、温暖的海洋。红色、温暖,但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是凉爽,于是他更用力地闭紧了眼睛。这时,他眼前就呈现出了一片深蓝,是闪着繁星的草原之夜。空旷、苍凉。
被暴晒了将近一个钟头,齐自新似乎才感觉到阳光的热度。他把思绪从遥远的草原扯回来,有些恋恋不舍和意犹未尽,又抬手抹了抹脑门,汗水黏稠,似乎含着许多的油脂。他快被晒化了。
齐自新上大学时有个绰号。因为他总是习惯性地、不知不觉地陷入沉思,所以在同学们看来,他的样子就有些呆愣和迷糊,加上他是寝室中的老二,所以室友们就送他个绰号:二迷糊。对于这个绰号,他倒是觉得挺适合自己。二在北方有呆傻的意思,但在他想来,所谓的呆傻,不过是做事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思路而已,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立场去讨好他人呢?所以二还应该是与众不同,是特立独行,是坚持自己,是随心而活。迷糊是糊涂的意思,他觉得也挺好,对待这个世界不必太过清醒,清醒是一种残忍,凡事看清看透都会失去美感,失去追求的乐趣。
齐自新站起身。可能是坐得太久,加之天气太热的缘故,他刚一直起身子,就感觉头有些晕,眼前似乎有一张黑色的帷幕慢慢地垂下来,并且有无数个金星在四处乱飞,像细小的烟花,更像飞舞的萤火虫,挺美。但挺美倒是挺美,他却担心自己会在这美里摔倒,所以他赶紧又坐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再次慢慢站起身。
二
完事后,王雪莓光着身子,进卫生间冲洗去了。她有洁癖,事前事后都要一丝不苟地洗净身子。齐自新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四肢极力伸展,像平铺的一张纸,一张被弄皱了的,疲倦的纸。他身上密布着一层汗珠,细密的,像清晨粘在草叶上的微小露水。他不想动,只想这样一直躺着,躺到天荒地老都行。他感觉身体中的所有气力都没了,都被这个夏天和王雪莓榨走了。
王雪莓是齐自新的前妻。他们已经离婚有将近两年了。这期间,她有时会回来看看依旧单身的齐自新,给他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上床睡一觉,然后带走女儿齐笑尘的抚养费。
王雪莓围着浴巾,从卫生间走出来,随手把一条干净的湿毛巾扔给床上的齐自新。
王雪莓说,擦一下身子吧,看你身上的汗,你越来越不行了,你是不是肾虚啊?
齐自新说,天气太热吧?漫不经心地擦了几下身子,然后把毛巾丢在床头柜上。又问,笑尘没说想我?你一会儿就该去幼儿园接她去了吧?
王雪莓说,没说想你,她也知道你是她爸爸,但对你的感情太淡漠,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咱俩离婚时她刚刚记事儿。王雪莓开始熟练地穿三角裤,戴胸罩,然后穿上了连衣裙。她在落地镜前侧着身子照了照自己的左边,又侧过身子照了照右边,才转过身来,正对着镜子,用一把大齿的梳子梳湿漉漉的长发。
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胖了?王雪莓问躺在床上一丝不挂的齐自新,同时把脸贴近镜片,用手去摸眼角上一道细不可见的皱纹。
下次回来记得把笑尘带来,我怕我们父女俩总不见面,会越来越生疏。齐自新没有回答王雪莓关于胖瘦的问题,在他看來,女人的胖瘦乃至外貌,对别人来说都不太重要,最在意的永远是她们自己。
王雪莓说,行,下次咱们去游乐园,这样也许她会对你有些好感。停了几秒,又说,对了,我听我同事说,她上星期天看见你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吃饭了,你有女朋友了?人怎么样?不要光看女人漂不漂亮,要找就找一个能容忍和接受你,能安下心来和你过日子的女人。
齐自新说,不是女朋友,她有丈夫,算是情人吧,彼此都空虚,互相利用,打发寂寞而已。说完歪着身子,从床头柜上拿过一支烟,点着。王雪莓撇撇嘴,没再说什么,她和齐自新已经不再是夫妻了,她懒得过分关注他的私生活。
你不是也有男朋友了吗?只要对笑尘好,你们就结婚吧!齐自新吸了一口烟,烟在他的肺里存留了好几秒,才被吐出来。他本想吐出几个烟圈的,但没有成功,只是第一个勉强能看出些形状。他有些懊丧,伸手拂散那些烟雾,像在拂去恼人的昨天。
我结不结婚要你管,你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王雪莓走过去,拿下了齐自新手中的烟,摁死在烟灰缸里。又说,虽然他对我也很好,但我总觉得他不适合我,与其稀里糊涂草率地跟他结婚,还不如回来和你过呢,先这么处着吧,走一步说一步,我现在对婚姻也没什么期待了。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活着就是为了等死,什么都提不起我对生活的兴趣。这一刻她的眼中布满了荒凉的伤感。
王雪莓拿起包,说,好了,我走了,还要去接笑尘呢,冰箱里有我给你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三鲜馅的,一会儿你自己煮吧。
钱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我躺一会儿,你自己去拿吧。齐自新懒懒地说。
王雪莓说,这次就不拿了,我这个月刚得了一笔奖金,足够了,钱留着你花吧,记得节省,一个单身男人总是喜欢挥霍钱。
王雪莓走了。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房间里,齐自新疲乏地笑了笑。这个女人,和他共同生活了五年。他又想起了他们热恋时的情景,那时的她纯真而可爱,像一只猫,一双眼睛里含满了笑,总缠着他讲笑话,即使是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笑话,也会令她前仰后合,用手不住地捶他的胸脯。时间可以改变一切,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事物,更没有永恒的快乐和幸福,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一定的期限后改变其自身的性质,人也一样。
天太热,齐自新想起身去冲个凉,但他刚要翻转身体坐起来,就又放弃了。宽大的双人床此刻充满了魔力,吸住了他的身体。他平躺在床上,深深地闭上了眼睛。
这个夏天太热,总是令他觉得疲惫和燥热,看来必须装一台空调了,虽然他讨厌空调。
三
齐自新是一所重点高中的老师。他毕业那年本不想去做老师,在他看来,教师这个行业肩负的责任太大,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散漫不负责的人,他怕误人子弟,从而让他的良心过意不去。但现在他却觉得做老师也不错,一年寒暑假加起来就将近三个月。他喜欢慢节奏的生活,不用工作,身上少了负担,只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自己。齐自新骨子里是一个消极的人,内心深处总是隐藏着一丝不易被别人察觉的悲观。他想,人生不过是一支被命运这张弓射出去的箭矢,慢慢地失去能量,慢慢地减缓速度,最后不可避免地陨落尘埃。
现在是暑假,齐自新不愿一个人待在家里,家里闷热、黏滞、寂寞,像一个牢笼,像一潭泥淖。
齐自新慢腾腾地走在街上,漫无目的。已经有二十多天没下雨了,空气里充斥着微小的、沾满各种气味的尘埃。
女人化妆品被汗水分解的气味、男人身上的汗水混合了灰尘发酵的气味、遥远的垃圾桶里腐烂的水果和蔬菜的气味及汽车排出来的燃烧过的汽油的气味,这些气味在温热的空气里翻腾着,给人以闹哄哄的感觉,像一群无知男女的一场狂欢。
齐自新低头走着,看着大理石方砖铺成的地面,和地面上走过的一双双大小形状各异的脚。
忽然,齐自新感觉自己撞到了一个人,于是惊觉地抬起了头。
這不是齐自新吗?被撞的人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男人,白胖,头发油亮,闪着世俗的光。待他看清齐自新的面目后,就收住了将发未发的怒气,惊喜地大叫了一声,同时夸张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了一下齐自新。
啊!是曹波啊!真是太巧了,不是说你高中毕业后就去北京了吗?齐自新也很惊喜。曹波是他高中时的同学,当时他俩算是亲密的好朋友,成天腻在一起,无话不说,无恶不作。高中毕业后,他俩有将近二十年没见面了。
别说了,一言难尽。你现在还好吧?曹波说,这么多年没看见你,很想你,有时自觉不自觉,就会回忆起咱俩高中时的那段时光。
是呀!那时我们多淘气,往女生的书包里塞癞蛤蟆,在学校的围墙上给自己心仪的女生写情书。齐自新感觉自己干涩的眼睛开始湿润起来,他想说这句话,他急于要和旧日的老同学一起畅谈,但他没有说出口,因为曹波说完他自己的那句话后,就看了看手表,然后紧接着就歉意地说,不好意思,齐自新,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大热天里,咱俩本应该找一个地方痛快地喝几大杯冰啤的,可是我恰巧有事。这样吧,改天咱俩好好聚一下,我做东。
好吧,你忙去吧!齐自新把刚到嘴边的话生生地咽了回去,心里弥漫起薄雾一样的失望。他站在太阳底下,看着曹波渐走渐远的背影。曹波胖了许多,走路的姿势也不再洒脱有力了。岁月真是一把猪饲料,不知不觉间喂肥了许多清瘦的少年。
收回目光,齐自新继续慢慢地向前走。他觉得有些憋闷,呼吸都有些困难,似乎有一块烧红的石头正重压着胸膛。他想歇息一下,走到路边,去扶路边的铁栅栏,但手刚一触到铁栅栏,就马上像触电了一样缩了回来。铁栅栏在阳光的炙烤下,蓄积了惊人的热量,像一个阴谋,他的手几乎被瞬间烫伤。
齐自新走进了一家啤酒屋。啤酒屋是炎热的夏季人们最愿去的地方,那里冷气开放,可以用大杯畅饮冰啤。啤酒屋里有几十张桌子,现在几乎都坐满了躲避酷暑的人。齐自新站在门口四处张望,试图找到一个空闲的座位,这时他看到了曹波。曹波正一个人仰头往喉咙里灌着一大杯啤酒。
齐自新脑海里响起了曹波之前的话:不好意思,齐自新,这么多年没见面了,在这大热天里,咱俩本应该找一个地方,去痛快地喝几大杯冰啤的,可是我恰巧有事。这样吧,改天咱俩好好聚一下,我做东。
齐自新赶紧把目光转向别处,带着莫名其妙的羞愧,觉得自己刚刚窥探到了别人的隐私,做了件亏心事一样。就在他收回目光的瞬间,他用余光又看了一下曹波,曹波刚把酒杯放下,眼睛也恰好看到了齐自新,他的目光是慌乱的,但又是镇静的,他赶紧又埋下头,那意思分明是怕被齐自新发现。
齐自新心里十分难受,有一种悲哀的感觉,转身走出了啤酒屋。他和曹波是同班同学,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他和曹波今天的不期而遇只是一个巧合。他再次回忆起曹波刚才相遇时说的话,有机会好好聚一下,怎么聚呢?如果彼此不真心相会,那么按概率讲在这个中等城市里,两个人相遇的概率该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曹波真想和齐自新再次见面,那么他至少应该留下联系方式,而事实上曹波连电话号码都没有告诉他。
看来朋友都是阶段性的,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变化,之前的感情都会慢慢地淡化,直至出现一层隔膜,再见时只是尴尬和局促,于是都想着尽快地逃离。
四
齐自新迷茫地在街上逛着。天很晴,没有一丝云彩,但天的颜色却一点儿都不蓝,是那种浑浊的灰白色,仿佛头上的不是天空,而是一个巨大的、密不透气的帐篷,整个世界都被捂在了这个帐篷里,恹恹欲睡。
有不大不小的热风,吹在人身上,不但感觉不到一丁点儿的凉爽,反倒有着更加温热的感觉。齐自新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半仰着头看路边那排大叶杨。这种杨树的叶子很大,叶子的正面是近于发黑的深绿色,叶子的背面是灰白色。风一吹,满树的叶子纷纷翻转过来,露出叶子下面的灰白,远远地看去,这灰白的叶片一簇簇地招摇着,在刺目的阳光下仿佛开了一树银白的花。
天气虽然热,但街上却依旧塞满了形形色色的人。透过女人几乎透明的上衣,齐自新在后面能看见她们肋下被胸罩挤压出来的肉,肥腻、丰满、颤巍巍地带着温水的波纹,男人们脸上都没有生气,仿佛已经被炎热蒸发殆尽,只剩下千篇一律木讷呆板的面具。所有人都像一具具提线木偶,无数细小繁杂透明的丝线从他们的身体上升起来,升到模糊的天空之上。天空之上真的有无所不能的神吗?
手机铃声唤醒了齐自新,是张玉玲。他盯着电话屏看了十几秒,最后还是点了一下接通键。
你怎么才接我的电话,不方便吗?张玉玲的声音让人浑身燥热,像蛋糕上高纯度的奶油。
不是,我在街上呢,刚听到铃声。齐自新用手背抹了一下脑门上的汗珠,转身走到街边的阴影处。
张玉玲说,你过来一下呗,我老公出差了,我想你了。
齐自新咂了一下嘴,没回答。他忽然觉得胃里很不舒服,他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胃里只有一些混合着胃液的矿泉水。他有些恶心,于是努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喉结吃力地滑动了一下,干涩而费力,像干抹布擦过陶瓷。
你到底来不来啊?张玉玲的愠怒也充满了诱惑。
好吧!齐自新有气无力地回答,张玉玲的邀请一点儿也激不起他的兴趣,但他不得不去她那一趟,就像懒惰的小学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糊弄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齐自新和张玉玲已经交往将近一年了,彼此谈不上谁爱谁,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彼此又需要着。就像火车上两个陌生的旅人彼此间的攀谈和热情一样,不过是为了打发寂寞无聊的旅途罢了。转眼火车进站,他们会毫无留恋地背起行囊,挤进滚滚的人流,从此再无交集。
张玉玲准备了一瓶进口红酒。她捧着自己的脸,默默地看着齐自新,但她的眼神是空洞迷离的,似乎在她眼前坐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处遥远的、模模糊糊的风景。
来吧,我们一对寂寞孤独的人,干一杯。张玉玲说,冲着齐自新比了一下手中的高脚杯。
是,一对寂寞孤独的人,干一杯。齐自新说,也冲着张玉玲扬了扬酒杯。他是孤独的,但他知道对面的張玉玲也同样是孤独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试图摆脱这种状态,但每一个人都是徒劳的。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独立,一个人无法真正找到和另一个人之间准确的契合点,也许是上帝创造人时,就把孤独的因子埋藏在了人类的基因里。
我给你温了水,你去卫生间冲一下,这天太热了。张玉玲说。
冲完了身子,齐自新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自己。恍惚间,他竟觉得镜子中的那个人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但虽然陌生,镜中人却能够看穿他的一切。他有些不服气,倔强地用冷漠的眼神与镜中人对视。但渐渐的,他竟然觉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脊背也有些发寒。他知道自己这张皮囊下的那些悲观、猥琐、虚伪、自卑、孤独都被镜子中的那个人压榨出来了。他打了一个冷战,赶紧逃出了卫生间。
虽然张玉玲为了今天的这次见面准备了红酒,还播放了一曲优美的音乐,但是他俩在床上依旧都心不在焉,难以提起激情,最后只能草草了事。可他们彼此并没有怨言。他们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这事上,只把它当作为了摆脱寂寞而不得不完成的一个程序,就像一个吸烟的人一样,总是在无聊的时候下意识地抽出一根烟点燃,但他需要的不一定是香烟的味道,只是需要那个习惯性的动作而已。这是一种依赖,虚无的依赖,有些自欺欺人。
你不爱你丈夫吗?齐自新脸冲天花板躺着,问身边的张玉玲。天花板上是淡粉色的花纹,旋转着,让人看久了会头晕,像遥远的、不相干人的梦境。
张玉玲说,怎么说呢?我爱他,但我说不明白,你知道人都是空虚的,必须变换着方法来填充自己空虚的心,否则一个好好的人会慢慢地崩溃。
是吧。齐自新不再看天花板。他闭上了眼睛,脸上是忧郁的颜色。
五
这个暑假似乎太过漫长,一开始,齐自新还迫切地期盼着暑假的到来,但现在,他却十分想念给学生上课的时光。几十双纯真却不安分的眼睛盯着他,他可以天马行空地乱讲一气,但学生们依旧爱听,依旧用纯真而不安分的眼睛看着他。能够有人倾听自己所说的一切是幸福的,虽然自己说的不一定是心里话,虽然倾听者也许没有明白他要表达的意图。
炎热像一根挥舞着的鞭子,驱赶着行人加快了脚步。在这个世界上,走路从来都不是目的,走路只是奔向目的必须完成的无意义的过程,所以每一个人都急于缩短甚至省略这个过程,尤其在这个闷热的夏天,走路就是一种煎熬和受罪。但齐自新却依旧慢吞吞地走着。在他看来,人生没有什么目的,要说有也只能说死亡是目的,所以人生中的所有事情都不必刻意地加快节奏,走路也是。
地下街的入口处坐着一个老年的乞丐,似乎腿有些毛病,但也许没有毛病。他在那静静地坐着,身前放着一个小塑料盆,盆里装着一些零钱。齐自新这几天闲逛时观察了他许多次,他安静地坐在那儿,从不回避阳光的照射,也从来不像其他乞丐那样,看见有人走过就用一副可怜相磕头作揖。
齐自新百无聊赖而且疲惫得难受,索性就坐在了乞丐旁边的石阶上。他从裤袋里拿出一包烟,衔在嘴里一根,想了想,又拿出一根递向老年乞丐。
谢谢,我不吸烟!乞丐翻了一下暗黄的眼珠,瞅了瞅齐自新说,如果你有好心,可以施舍给我一点儿钱。乞丐很老了,脸上有许多皱纹,由于常年在日光下乞讨,脸被晒得很黑,他一说话,就有一部分皱纹被撑开,露出里面白色的底子。齐自新翻了翻自己的钱包,出门时忘记带钱了,只剩了五十多元。他把所有的钱一股脑地放在了乞丐身前的塑料盆里。乞丐并没有惊喜,把那张五十的钞票拣出来,折叠好,揣进衣兜里,又对齐自新说了声谢谢。
人活着都挺不容易的,是吧?齐自新鼓起勇气问老乞丐,心里其实是在问自己。
你在说你自己不容易吧?人活着没啥不容易的,自己活自己的,想太多就不容易了。老乞丐说,眼睛不再去看齐自新,他仿佛知道齐自新此刻心里所想的一切。齊自新一抖,心中升起一丝恐惧。这个老乞丐常年在这乞讨,可谓阅人无数,因此能够轻易地看透别人的心思。
现在做你们这一行也越来越难了吧?齐自新压下那丝恐惧,继续问。因为刚才他给了老乞丐五十多元钱,他觉得老乞丐为了回报他的施舍,应该会回答他。
说不容易就不容易,说容易就容易。我告诉你,我们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失业,因为你们这帮人能够通过给我们施舍几个小钱,使自己高尚起来,人都喜欢用各种办法抬高自己,当你们给我几角钱后,心里就会增添不少优越感。其实你们大多数都不是在施舍,只是在用几个小钱给自己买个心情。老乞丐说,言语里充满了让人害怕的智慧。
齐自新听了这一番话,肃然起敬,顿时觉得这个老乞丐很不简单,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于是身子向他挪了几分。但他刚要再问些别的,老乞丐却说,别问我啥了,你走吧,你在这和我闲聊会影响我工作。对了,告诉你,我不是残疾人,我的腿没有毛病,这是我为了乞讨的需要才装出来的。你走吧!
齐自新把要问的话重新吞回肚子,悻悻地站起身来。其实他不是想问老乞丐什么问题,在他的心里,他觉得什么问题自己都已经有了答案。他只是想在别人的嘴里重新验证一下而已。他只是想找个陌生人,毫无压力,而且十分投机地说一会儿话。
六
这几天齐自新不再出去逛街了。天太热,他一个人赤身裸体躺在客厅的地板上。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什么都不去想,思考都会令他产生不必要的热量。心静自然凉,他想也许安静才能使自己感觉凉快一些。但他还是热,汗水涔涔地在皮肤上爬,像无数条蠕动的毛毛虫。皮肤和地板接触的地方奇痒无比,他于是挪了挪身子,吱吱的声音响了几下,肉皮本来已经被汗水牢牢地粘在了光滑的地板上了,他一挪身子,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像一种撕裂,但没有疼痛。人真的有点像冰雕,一点点在炎热中消失,看着时间从身体里渗出来,滴落尘埃。
这些日子,王雪莓一直没领女儿来看齐自新,齐自新也打消了去看女儿的念头。张玉玲打过几次电话,要他去她那儿,但他都借故推脱了。天太热,他总有虚脱的感觉,哪都不愿意去。
齐自新其实无法真正让自己的大脑平静下来。但他不愿意想未来,在他看来未来不值当自己费脑力去想。人生如同上好弦的钟,只是盲目地走,一切只能听命于生存意志的摆布,追求人生目的和价值是无意义的。
齐自新把自己从小到大的许多事情,一件件地在脑海里像电影一样回放着。就这样,他忽然想起了一个人,是他高中时候的一个女笔友。那时他喜欢文学,在一张小报上发表了几首小诗,于是认识了这个女笔友。他们惺惺相惜,每一周都要写一两封信探讨文学和人生,他们甚至可以毫无隐讳地谈论自己的隐私。那时齐自新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对她产生了一丝爱慕之情。他从她的来信中也隐隐地读出了她对他的好感。但他们的通信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中断了,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应该去看看她!齐自新的内心忽然生出了这个想法,不是生出,是跳出,势不可挡,无法遏制。他急忙爬起来,奔向书房。在书柜的最底层,装着一些很久之前的信件。他急切地翻找着,手忙脚乱,终于找到了那个笔友来的一封信。他记下了上面的寄信地址。
齐自新奔向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往笔友所在城市的火车票。
在火车上,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后,齐自新忽然惊醒了,他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时隔二十多年,一个未曾谋面的笔友,只靠从前的这个旧地址,还能找得到吗?也许她已经嫁到了别的城市,亦或许她已经不在了都有可能。就算费尽周折找到了她,可她也许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能和自己畅谈的朋友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什么都有可能。这一刻,他想起了高中同学曹波。
齐自新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这一行动滑稽可笑,像自己对自己搞的一个恶作剧。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他赶紧站起身,挤过熙攘的乘客,下了车。
出站口,这个城市参加省夏季运动会的运动员正手捧着鲜花鱼贯向外走,出站口外是欢迎的人群。头上的大屏幕上赫然打着一行字:热烈祝贺我市参加省运会的健儿胜利凯旋而归。齐自新骂了一句,凯旋本来就是胜利归来的意思,不知道谁又画蛇添足地加了“胜利”和“而归”。骂完了,他又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人可能都是这样,总想努力地把人生修饰得尽善尽美,其实都是多余徒劳的,都是在自作多情。
天真热,齐自新的影子被晒化了似的,又矮又小,也不那么黑。他拖着自己的影子,盲目地走在街上。
为什么不下一场暴雨呢?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