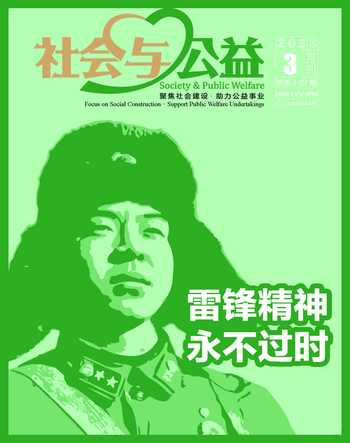“三步走”:失独群体会变得有希望、有能量
2023-06-07张宇迪林依倩贾若楠
张宇迪 林依倩 贾若楠
“失独”是失去独生子女这种社会现象的简称,失独群体是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只生育了一个孩子,但孩子因为各种原因去世的当事人。根据人口学家的估计,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几十年来,我国失独群体的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万人。虽然国家已经结束一胎政策,人口学家仍然预估失独群体的规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会减小,而是会持续增加。在失独群体中,大部分是不具备再生育能力的老年人。
在针对失独群体“开展社会关怀活动”这一扶助要点中,卫健委等部门提到“以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为重点,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关怀活动”,即精神关怀是社会关怀的重点。但是,由于精神关怀属于柔性服务,其开展并不像经济扶助工作那样有章可循,因此有必要结合相关理论、总结实践经验,为各地开展失独群体的精神关怀提供借鉴。笔者最近数年一直关注失独群体的精神健康及关怀工作,与失独群体及为其提供服务的人员有诸多接触,因此尝试总结出关于做好失独群体精神关怀工作“三步走”的思路。
第一步:尊重共情建立信任关系
由于痛失爱子所致的心理创伤,失独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心态较为敏感。即使是丧子前活泼开朗的人,子女去世后也很可能变得既警觉又脆弱,尽量回避与人的接触和交流。有一对失独父母,孩子去世后的前几十天里,他们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关上窗户、拉上窗帘,躲在暗处静静地舔舐伤口。如果电话铃响了,他们经常还会吓一跳,并且觉得铃声异常刺耳。还有一对失独父母,在孩子去世后的前几个月里,跑到所在城市郊区的一个宾馆中长住,每天到附近的山里不停地走路,对着大山呐喊、宣泄,不愿接触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从上述两个案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部分失独者的强烈自我封闭倾向。那么,如何叩开他们的心扉,和他们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呢?尊重和共情是关键。
首先,尊重主要是指尊重失独者的哀伤步调,不試图“强迫”他们从悲伤的心情中迅速走出来。例如,社区工作者逢年过节慰问辖区内的失独者,不宜在失独者不愿意开门的情况下强烈要求进入其家中发放慰问品,甚至为了宣传工作效果“迫使”对方配合拍照。不对他们反复说类似“孩子已经走了,你一定要坚强!要尽快站起来!”的话,而应对他们表示“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记得打我的电话。”
其次,共情是建立信任关系的润滑剂。所谓共情,是指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体会对方的情绪,并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自己被理解了。如果要劝说失独者,最好建立在共情性表达的基础上。例如,“我看您已经两个月没怎么出门了,您是不是觉得不想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我想,您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转折,想自己安静一段时间特别正常。如果您什么时候做好准备了,我愿意陪着您出门转转。”“您经常说,如果您当时能及时发现孩子的病情,孩子可能不会走得那么快。我能体会到您的自责和内疚。但是孩子的病情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我相信孩子不希望看到妈妈陷入自责无法自拔。”
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对失独者表示完全理解其丧子之痛,因为大部分失独者的感受是“失独之痛痛彻心扉,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无法体会。”所以,如果有失独者询问提供关怀服务的人员:“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比较恰当的回答是:“失独之痛太痛了,我没有亲身经历,无法百分之百地理解。但是,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体会您的心情,尊重您的心情。”这样说,绝大部分失独者都能接受,并对关怀者尽力去理解的努力心生感激。
第二步:基于需要提供多种照顾
与失独群体建立信任关系后,关怀者就能够走近他们身边,或者邀请他们到某一场域中,为他们提供多样的照顾服务。需要注意的是,精神关怀绝不仅仅是在精神层面对失独者进行疏导和慰藉,而是把对他们的精神关怀渗透到所有社会关怀服务中,以发挥出“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以北京市为例,许多街道都建立了专门开展失独关怀服务的“心灵家园”。这些心灵家园有大有小,小的能提供唱歌、跳舞、乐器演奏、棋牌、手工、书画等文娱活动的场所,大的具备不同的功能分区,如文娱区域、展示区域、健康小厨房、心理咨询室等。在“心灵家园”中,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失独者的心灵创伤能够得到一定的恢复。
随着政府对失独群体的遭遇越来越重视,丰富多彩的失独服务活动也在各地开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失独服务的提供应建立在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上,而绝不能从主观出发,想当然地组织活动,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例如,某机构为某社区的失独者开展了一场名为“清明节追思会”的小组活动,事先没有了解到参与活动的多名失独者的丧子时间都仅有几个月,正处于强烈的哀伤情绪中。活动时,带领者拉上窗帘,在漆黑的环境中为每个失独者发了一根蜡烛,想通过点燃蜡烛的形式帮助失独者寄托对孩子的追思,并帮助他们宣泄积压的负面情绪。但让带领者没想到的是,蜡烛一点燃,场面瞬间失控,多位失独者捶胸顿足、痛哭失声,一时间场面极度混乱,而带领者由于缺乏经验也不知如何处理。活动的组织者由于没有考虑到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心理帮助,甚至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服务提供者可以事先通过问卷、访谈等方式开展调研,摸清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再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
此外,最了解失独群体需要的是失独者本身,因此,关怀人员可以搭建桥梁,帮助失独者认识其他失独者,使得他们有机会抱团取暖、相互慰藉。实践证明,许多失独者在“同命人”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第三步:增能赋权促进价值发挥
“痛苦”“无力”“绝望”“阴影”“悲惨”这些词是许多人提到失独者时的联想。不得不说的是,这些联想虽不是空穴来风,但也并非完全准确。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失独者,在亲友和社工的帮助下走出了痛苦的阴霾,回到相对积极的生活状态中,还能够发挥自我价值,帮助其他困难群体,为社会做出贡献。笔者访谈过一位已经从国营单位退休的失独者,从失独的伤痛中走出来之后,他在经济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双重动机下,借助在之前数十年的工作中掌握的过硬技术,应聘到某私营单位继续工作了十年。这十年间,他通过发挥自身的技术,不仅服务了单位,并间接服务了社会,而且为自己和配偶的晚年生活积攒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这位失独者正准备找一家好一点的养老院,在里面交一些朋友,安度晚年。此外,还有失独父母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并组织成员赴灾区慰问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每每了解到相关情况,笔者总是觉得很感动。这些事例反映出失独者们“心中有爱、眼中有光”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他们绝不仅仅是等待帮助的被动的个体,还是奉献价值的能动的主体。
上述事例对失独群体提供精神关怀服务人员深具启发性,它与社会工作理论中“增能赋权”的理念相符合。从增能赋权的视角出发,关怀者要看到失独群体因为社会的污名化带来的无力感,例如社会上有部分人对失独群体持“失独者是不吉利的”“子女都去世了就应该安安分分呆着”等消极观念,导致了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失独者产生出无力感。关怀者应该了解到,自我计划、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部分失独者从哀伤中恢复的现实需要,相关工作者应当尽己所能来满足失独群体这方面的需要,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帮助失独者破除社会偏见,通过鼓励他们并链接各方资源以促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计划、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这样做不仅仅对失独者的身心健康有所助益,还能为社会增光添彩,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对失独者的精神关怀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尊重其哀伤步调、在共情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然后将精神关怀渗透到多方面的照顾和服务中,最后以增能赋权的视角,着力促进一部分恢复得比较好的失独者的价值发挥,使他们不再是社会大众眼中消极无力的群体,而是有希望、有能量的人。
(作者简介:张宇迪,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林依倩,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贾若楠,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情感视角提升失独老人生活质量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21BSH1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