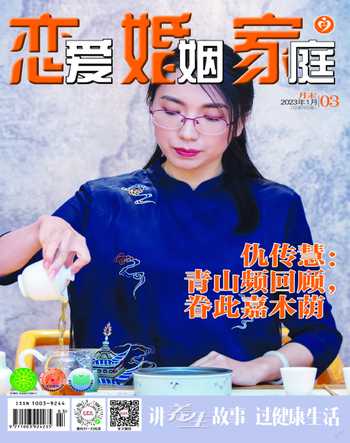苏东坡:一生坎坷三段真情,足以慰平生
2023-06-06汪小年
汪小年
苏东坡的一生中,有几位女性的身影挥之不去:“不思量,自难忘”的王弗,“惟有同穴”的王闰之,“每逢暮雨倍思卿”的王朝云。
这三位女性,出现在苏东坡不同的人生阶段,陪伴他迎接动荡多舛的命运,但她们都早于苏东坡而亡逝。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苏东坡和她们的故事。
不思量,自难忘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苏东坡十八岁,在父母的安排下,娶了青神乡贡进士王方的爱女——十五岁的王弗。第二年,苏东坡十六岁的弟弟子由成婚,妻子只有十四岁。
苏家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两个儿子完婚呢?原来他们准备随父亲苏洵进京应试,按照当时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考试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苏家兄弟若是未婚并且一考而中,必然有京中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而在苏家父母看来,让儿子娶本地的姑娘,对姑娘家知根知底,日后要好相处得多。
子由婚后不久,苏洵便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趕考去了,留下苏母和两个年轻的儿媳妇相伴度日。王弗帮着苏母打理眉山城西纱縠行的布帛生意,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家中事务都调理得当。苏轼后来称赞她“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
后来,苏家兄弟都考中了进士,刚刚二十岁的苏东坡以名列第二的成绩享誉天下。不幸的是,苏母还没来得及听到这个喜讯就病故了,父子三人仓促返家,料理后事,居丧守礼。
这段为母守孝的蛰居生活是苏东坡兄弟一生中难得的悠闲时光,他们和年轻的妻子一起,侍奉父亲,纵情山水。也就是在这段心无旁骛的日子里,苏东坡和妻子王弗之间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王弗敏而静,性格沉静、不外露。苏轼每每读书,王弗便站在他身旁,苏轼不解,回头望着王弗:“夫人有什么事吗?”王弗也不答,只是笑笑,依旧是陪着他。苏轼接着看,遇到某个难解之处,挠挠脑袋。王弗便动动嘴,稍微提醒他一下,苏轼这才醒悟:“夫人真不简单啊。”
居丧日满,苏东坡父子又该启程入京了。这一次是举家东迁,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还有苏东坡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到京之后,父子三人都被授予官职,苏东坡被放了外任,到陕西凤翔就职,子由陪父亲留在京中。
苏轼做了凤翔签判,官不大,名气却不小。毕竟他在京城风光无限,受到仁宗皇帝的夸奖,深得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如今到哪儿都像一坨金子,很吸引人。家里常有来客,客人们素质参差不齐,有素心人、有识之士,当然也有阿谀奉承的小人,大家气氛融洽。王弗隐在苏轼身后,脸上也挂着笑,但那眯起的双眼,仔细打量着堂下每一位来客。没办法,倒不是她有多少防备之心,只因苏轼性太直、心太善、涉世太浅,对谁都不设防,这样是容易吃亏的。事实上苏轼一生为此吃了大亏。
客人们笑过,散了。回到屋里,王弗免不了要提醒苏轼几句:“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就是说有些客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迎合你的意向,你何必同这等人说太多呢?糖衣炮弹最容易迷惑人,更何况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王弗每每如此,“幕后听言”,像一道屏障,隔开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人。有些人与苏轼本是初识,便如老朋友一般黏上来,马屁拍得响亮。王弗又告诫:“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交情套得太快,去得也会很快,这样的朋友不会长久。诸如这般劝言,苏轼很赞同,也很佩服夫人的眼光。
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东坡在凤翔三年任满,举家返回汴京南园。2月,苏轼应试学士院,考了第一,有了新的官职。本是前路美好,然而五月二十八日,王弗突然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苏轼悲痛万分,近乎茫然。东坡的父亲苏洵在王弗去世后,对苏东坡感慨道:“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茔旁葬之。”
十年之后,苏东坡任密州太守,一日夜里,梦回眉山,恍惚间看到王弗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梦中人还是十年前的模样,自己却早已尘满面,鬓如霜,惊醒后是夜里,四下无人,只有一轮孤月影影绰绰地空挂在老树后,东坡不禁悲从中来,对世事的感慨、对王弗的思念,成就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一阙千古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读懂它的人没有不为之悲戚的,他用笔墨喷发出积压在心里的剧痛。
我实少恩,惟有同穴
苏轼的续弦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从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她与苏轼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那是他的人生最大起大伏的岁月。
苏轼涉及王闰之的文字,不像写给王弗和朝云的那么广为人知,却饱含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比如苏轼的《小儿》诗就描述了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小儿子前前后后黏着父亲,后者被缠得烦了,想要嗔怪孩子。闰之一边哄儿子一边责备丈夫:莫非你比小孩还不懂事吗,好端端的,“不乐愁何为?”苏轼一向很听得进劝告,此时被妻子轻轻敲打一番,顿觉有愧,顺从地默默坐下。闰之随即将酒杯洗好,放在他面前。他饮得心满意足:晋代名士刘伶嗜酒如命,夫人想方设法劝他戒酒。闰之不禁止苏轼饮酒,显然让他很受用。当然,他也不贪杯。或者说他虽然好酒,酒量又实在太浅。
王闰之为苏轼提供酒的事例,还有更著名的一次。这就是《后赤壁赋》中,苏轼与两位友人想乘月而游,惋惜无酒,他“归而谋诸妇”。结果妻子说:“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那个月白风清的良宵,有朋辈,有鲜鱼,假如缺了闰之细心收藏、以备不时之需的美酒,不晓得会减色多少。东坡他们的赤壁之游,兴致肯定会大打折扣。
也许,王闰之不像王弗那么富于灵智之妙,但她给予丈夫的温暖和支撑同样不容忽略。很多时候,闰之还显示出她充满生活能力的那一面。在贬谪地黄州,苏轼写给章惇(字子厚)的信中说,一家人居于东坡,靠几十亩田种稻谋生,自己参与耕种,妻子养蚕。他告诉章惇,昨天一头牛差点病死,牛医不知道是什么病症,而老妻却晓得是牛得了豆斑疮,应当喂它青蒿粥。这办法果然很奏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犹解接黑牡丹(牛的戏称)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妻子的博闻、能干让东坡很佩服,忍不住在信里对千里之外的老友津津乐道。
其实,王闰之的贤惠岂止于此?她陪伴丈夫从密州到湖州,从黄州到汴京,随着苏轼仕途的跌宕起伏,时而尽享敬慕荣耀,时而饱尝颠沛流离,但始终“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闰之对堂姐王弗的儿子苏迈与自己亲生的苏迨、苏过都一视同仁,苏轼特别感念她深厚的爱心。
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八月一日,王闰之在东坡任礼部尚书时于京师去世,年仅四十六岁。1098年上元,东坡在儋州梦见已经去世五年的闰之,“灯花结尽吾犹梦,香篆消时汝欲归。”梦中情景,还是在京师的时节。
蘇轼为王闰之写的祭文里有这样几句:“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王闰之逝后,苏轼不再娶妻,唯留王朝云相伴。九年后,苏轼与王闰之被合葬在河南汝州郏县。
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进苏府的时候年方十二,苏东坡在杭州任判官时,常常游湖宴饮,请来擅长丝竹歌舞的名妓助兴。
据《燕石斋补》记载,朝云原是名妓,苏东坡后将她引进府里纳为妾室。朝云原本不识字,但悟性颇高,在苏东坡身边耳濡目染,读书识字,成了他心灵上的知己。
毛晋的《东坡笔记》中,载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天东坡退朝回家,饭后走路消食,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周围人:“你们说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有人说是一肚子诗词歌赋,有人说是一肚子墨水才华,东坡都不置可否,一旁的朝云却笑解其意,答道:“学士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听罢,捧腹大笑,称赞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他们曾有过一个儿子,生下三天举行洗礼的时候,苏东坡写了一首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首诗充满自嘲之意,但也透着喜得幼子的欢欣。可是,这个孩子福薄,在十个月的时候患病夭折。这对苏东坡和朝云都是莫大的打击,尤其是朝云,她终日躺在床上,精神恍惚,东坡曾有诗云:“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可以想见那是怎样的痛彻心扉。后来,朝云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
王闰之死后,苏东坡便只留朝云在侧,苏东坡晚年在惠州的生活,和朝云紧密相关,苏东坡被贬惠州时,朝云常常吟唱他填词的《蝶恋花·花褪残红》,为东坡消愁解闷,王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苏东坡“诘其故”,朝云答曰:“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王朝云之所以凄然不成歌,全因她体悟到了苏东坡旷达之余的苍凉。
人人都只赞苏轼是有大气象、大格局的,唯有王朝云温柔可人地替他伤怀,为他不值。彼时年近花甲的苏轼运势转下,身边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唯有王朝云追随苏轼长途跋涉到了惠州。“不似杨枝别乐天”,苏轼欣然于自己不是年老体弱被爱妾樊素“抛弃”的白居易,其对朝云这一知己的珍视与感激宛然可见。
在惠州的时候,苏东坡大概也觉得有生之年没有返京的可能了,便与朝云决定盖一座房子长久居住。这栋房子盖在一座小山上,设计十分精雅,房前屋后种满了果树。可是,命运从来不会眷顾有情人,新房子尚未竣工,王朝云就因瘟疫被夺去了生命,年仅三十四岁,卒于惠州。这座房子被后人称为“朝云堂”。苏东坡在朝云墓址所在的惠州西湖建过一个六如亭,亭子上有他亲笔写下的一幅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朝云死后,苏东坡已年近六十,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在儿子的陪伴下继续被流放,到了海南,后来死于返京途中,享年六十四岁。
苏东坡一生坎坷多舛,但有这三位女子相伴,他将“一生一世”过成了“三生三世”,让后世之人感慨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