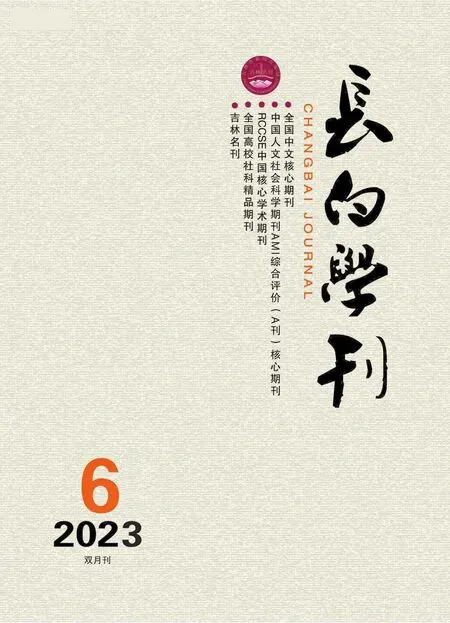数字劳动:概念厘定、权力关系与主体性问题
——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
2023-06-05平成涛
平成涛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无论从社会生活的经验,还是学术话语的时代反应来看,我们正无可避免地处在一个数字化生存世界之中。1995 年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就宣布了:“从原子到比特的飞跃已是势不可挡、无法逆转。”[1]13书中描绘了日常阅读、产业变革、新闻与媒介、多媒体与娱乐等种种数字化生活场景,并以一种乐观的态度直视数字化的未来,预言“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272。几乎在同一历史节点,1999 年由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在全球各地陆续上映,当第一部结尾处男主人公尼奥告诫“要让芸芸众生见到真实世界,一个没有电脑的世界”时,电影便将系统虚拟世界与感性现实世界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摆在了即将迈入21世纪数字化时代的人类面前。《数字化生存》和《黑客帝国》,一个是关于数字化生存的乐观未来,一个是对人与机器关系的现实忧虑,反映出数字化生存世界内在的矛盾性质。实际上,书和电影所揭示的数字化主题及其特征有其现实的社会历史基础。同样是世纪之交的1999 年,美国学者丹·希勒发表了《数字资本主义》一书,该书针对信息技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提出数字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简称ICTs)的发展使得各种生产要素重新得到配置,并实质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无所不在的计算机网络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相结合”,带动了政治经济的所谓“数字资本主义”转变[2]xiv。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是数字化生存世界得以建立起来的社会存在基础。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理解当下数字化生存境遇的真正开端就在于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马克思在19世纪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以产业劳动普遍化为历史前提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对机器大工业生产下雇佣劳动的分析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现实条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前提。同马克思对产业资本主义的批判一致,在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的作用下形成的新型劳资关系,构成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核心要件,其中,对数字劳动的批判又必然是前提性的问题。
围绕数字劳动这一主题,西方学者较早展开了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路径。其一,人本学路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ir)试图在“非物质劳动”概念基础上重建适合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的新革命主体,他们关注“发起信息交流、产出文化产品或服务的劳动”[3]294,提出正是这些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导致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和异化形式的变化。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劳动时间的模糊性,已不能再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分析数字劳动的剥削和异化状况。其二,传播学路径,其中代表人物是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方法对数字劳动进行分析,揭示了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以及数字资本通过无偿占有互联网用户劳动创造的产品与价值来实现资本剥削的过程,并提出了“数字劳动异化及其克服”的问题[4]371-372,其中涉及的问题较为全面,是基于传统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动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对数字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还远远不够,对数字劳动与资本关系等此类关键问题缺乏深入讨论。对此笔者认为,数字劳动批判仍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原理,进而在经济学、政治学与哲学三者融合的整体主义视角中探析数字劳动问题。其中,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厘定是讨论数字劳动异化这一新型劳动异化的基础,因为数字劳动同样需要在与一种新的资本形态的关系中来理解;而对数字劳动异化的解析是进一步讨论数字劳动主体性及其解放的基础,正是因为产生了数字劳动异化这一新的劳动异化形式,劳动的主体生产才呈现出新的形式,从而对劳动解放提出新的可能。
一、重新理解“数字劳动”概念
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存在一个基础性问题亟待解决,即如何准确理解数字劳动的概念。目前的研究中,围绕数字经济活动形成了诸如“知识劳工”“非物质劳动”“线上劳动”等一系列相关概念,且经常与“数字劳动”相互替代,由此出现了一种相对混乱的概念使用。仔细考察这个概念群体可以发现,这里存在一个方法论层面的不当,即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对数字劳动概念作了抽象泛化的理解,其直接表现即将与ICTs 有产业关联的劳动皆称为“数字劳动”。因此,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介入对数字经济的分析,重新理解数字劳动这一核心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专门讨论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每一个在抽象中上升到具体的经济范畴,不仅要在思维逻辑上是合理的,而且一定是在社会历史运动中获得现实规定性的。“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5]28这个“发达的总体”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物质力量,只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机器工业化生产组织体系中,“‘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5]29。这里的研究方法表明,抽象的经济范畴要想成为真正有意义并发挥作用的范畴,就必须获得其具体的历史规定性,马克思称之为经济范畴获得“一定的社会形式”[5]219的过程。因此,当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来言说“产业劳动”这一概念的时候,它首先是能够进入“发达的总体”的劳动,因而不包括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资本主义社会中偶然出现的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给自足的劳动。这是一般劳动在产业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因此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即取得了价值形式的劳动。同样,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当我们在数字化革命背景下来使用“数字劳动”这一概念的时候,首先仍然指的是“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指的是一种“有价值的劳动”,这是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谈论劳动概念的基础。同时,这种劳动之所以不能被涵盖在产业劳动概念之中,或者说区别于产业劳动的地方,在于它在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普遍化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一种新的“一定社会形式”,并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抽象,没有这个新的抽象过程,它就无法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生产的“发达的总体”之中。
如果说在产业劳动中个人的具体劳动只有同时转化为“抽象劳动”才能被社会所认可,那么,在数字劳动中,个人的具体劳动只有能够同时转化为“抽象数据”①与“抽象劳动”相对应,“抽象数据”是数字化生产方式中产生的所有具体零散数据的抽象化。,才能成为“有价值的劳动”,才能进入资本增殖体系并被认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劳动与产业劳动之间是既有重叠又有错位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原先在产业劳动中为交换而从事的劳动,已经由于价值形式化而获得了抽象性质,并因此表现为一定的交换价值。现在,这种具有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只有同时转化成为抽象数据,才能进入普遍的交换体系之中,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看作“价值形式的再形式化”。比如,当出租车司机一直是在物理空间中通过偶然性来与乘客相遇并按照自己的经验路线完成运输时,他的驾驶劳动仍属于传统的产业劳动(服从于特定资本的雇佣制度),但当他进入抢单派单的用车平台系统时,他的驾驶劳动就成为数字劳动,因为这时他的劳动同时形成为抽象数据而与资本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原先存在一些不能被作为抽象劳动的活动,比如在实体商店里挑选衣服的活动只是为了完成最终的商品交换并随着交换的完成而消失,这些活动无法被价值形式所统摄,因而对资本增殖没有任何用处。但是现在,当我们使用智能手机在各大平台挑选衣服时,每一次点击、浏览、评论等活动在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介入下都会形成能够被收集整理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这些活动也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由社会生产关系普遍化带来的抽象形式而“被吸纳到商品化的过程中”[6]了,并因此可以叫作数字劳动。
综上所述,依循马克思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或许可以尝试回答一下数字劳动的概念问题,以便适当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数字劳动,可以说是那些在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普遍化的社会条件下,能够留下数据痕迹,并在价值形式的统摄下形成抽象数据,从而能够被纳入资本增值体系中的各种劳动。这个回答表明,“数字劳动”同样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其依赖且适用于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条件发生的变革。
按照上述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分析和理解,可以发现,那种将数字劳动概念泛化的观点是不甚恰当的。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其《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中将数字媒体背景下与ICTs 行业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劳动统称为数字劳动,然而与ICTs相关的矿物开采中的奴隶劳动以及硅谷为谷歌装配硬件的流水线劳动等制造业和服务业中的各式劳动,并不能直接转化为能够增殖的抽象数据,其性质也无法与马克思笔下19世纪英国煤矿工人的劳动区分开来。同样,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凯瑟琳·麦克切尔(Mckercher,C.)和文森特·莫斯可(Mosco,V.)关注信息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产业领域的“知识劳工”[7]8-19,这一讨论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的“一般智力”范畴出发,聚焦信息、知识和情感在资本主义生产积累中的中心位置,与意大利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提出的“非物质劳动”具有同样的视野。然而,不管是“知识劳工”还是“非物质劳动”,都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不同于实在物体生产的劳动形态,其现实基础仍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总体,而不是脱离物质生产的劳动。因此,它们仍属于传统产业劳动价值生产和流通体系,与前述数字劳动的定义有着本质区别。
通过对数字劳动概念的讨论可以发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研究劳动问题,应当坚持一个基本方法,即要把劳动概念始终置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来界定,而不能仅从单纯技术维度理解劳动外在形态的演变。同时,在马克思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分析中进一步考察数字劳动,必然涉及对数字平台的讨论。只有在数字平台上,人的活动才能形成数据;也只有通过数字平台,大量数据才能得到收集、处理和分配,进而形成价值增殖的新的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劳动正是依赖各种具有资本性质的数字平台而产生,并因此受到数字平台的统治。
二、数字劳动异化与平台资本的权力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的现实形式是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8]374资本主义现代工厂的第一个使命就是消灭手工业生产中独立的分工,让个性化的生产者和分散的生产资料汇集到一起,从而通过对生产过程的一种时空整合形成劳动社会化和抽象化的现实条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数量的社会财富的形态,……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5]316在这里,工厂不仅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空间,它实现了抽象劳动的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发达总体”的一种感性时空载体,各类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只有以不同形式汇集到工厂,才能实现价值形式化而成为商品。
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平台”越来越取得像工厂一样的社会化生产功能。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将平台看作“数字化的基础设施”[9]50、数字化时代的“一种强大的企业形式”,它最基本的定位在于将包括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在内的各类经济主体(网络“用户”)聚合在一起,并提供一系列工具以便各类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从而形成各个用户之间的互动。平台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聚合效应,原因在于它有着相对于传统产业模式的“数据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平台之所以能够为各类用户提供数字空间的互动,在于它同时是一种“数据的提取装置”[9]55。这意味着,正像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如果一担棉花和某个劳动力不进入工厂的生产过程,就不能商品化从而无法取得价值形式一样,今天人们的各种活动通过数字技术和智能媒介所产生的大量零碎数据,如果不进入数字平台的生产系统,也没有任何意义。
但这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考察数字劳动在平台上产生的更深入结果。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工厂及其机器体系和制度操作看作独立于工人活劳动之外的形式统一体,这是一种由“过去劳动”所凝结的客观物质力量,它形成对工人活劳动的支配关系。“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挤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5]354作为一种生产总体的工厂,成了一台吮吸工人活劳动的庞大机器,马克思将此看作“工人劳动受资本支配”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固有关系在“工艺”上的表现。今天,这种工艺表现同样发生在数字平台上。平台运用算法等生产工具对来自用户的海量数据进行开采、聚合、分析和加工,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算法系统。由于数字平台对这些私人数据的占有,这个庞大的数据算法系统与每一个用户之间是分离的,并由此进一步产生对用户活动的支配。于是,这个数据算法系统作为积累起来的“过去数据”,不断地吮吸着平台上每一个用户的“活数据”,用户与平台之间形成越来越两极化的力量。数据算法系统的目的是不断为平台带来利润,从而进一步实现资本增殖的要求,可以称之为平台资本。于是,数字平台就成为“多样化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一种典型和集中地”[10]。这样,产业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就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的关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也呈现出一种新形态:“数字劳动异化”。
马克思将资本看作与劳动相对立的社会权力,如其所说:“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纯粹主体的贫困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5]101由此可以说,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间也是一种权力关系,本质上仍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权。不过相对于传统雇佣制的劳资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有新特征,其更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两种具体数字劳动形式来窥探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新型统治,以便更加具体和深入地考察数字劳动异化。
(一)“零工工作”中数字劳动的流散与控制
伴随着智能手机、便携电脑等移动终端的生活化使用和数字平台的崛起,零工工作成为全球范围广泛流行的工作方式。零工工作的最大特征在于平台将劳动力、企业和消费者等多元经济主体聚合在一起,建立起一种灵活的劳动供需关系。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大量零工工作中的数字劳动成为自我雇佣者,劳动的时空限制也得到极大突破,并且似乎还可以按照自身特长和兴趣来自由选择劳动种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和减弱劳动者受资本统治的局面。在这里,平台解构了雇主、雇员和客户的角色,成为横在各方之间的一道“无知之幕”。作为自雇者的零工工作者与作为“请求者”的客户之间如果不经过平台的分配就不能直接地发生交换,且他们都不知道下一个发生交换的对象是谁。由于对数据拥有占有权和支配权,平台像攥着成千上万条细线一样操控着流散在各个时区和空间里的零工工作者。传统雇佣制生产关系的解体还意味着零工工作者与平台之间处于一种隐蔽雇佣关系之中,就像我们每次在手机上更新APP 软件时遇到的“同意”和“拒绝”的对话框一样,零工工作者只有在点击“同意”或“接受”协议条款按钮后才能进入平台获得工作。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数字劳动形态,它抹杀了传统雇佣生产关系下劳动者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和保障机制。美国学者玛丽·L.格雷(Mary L.Gray)和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将这种隐藏在平台后面的工作关系称为“幽灵工作”,并清楚地表明:“这一就业市场的特点就是临时工作人员的频繁更替。”[11]19在这种不稳定的数字劳动形态中,一个零工工作者能不能找到匹配的请求者发生交换、与什么等级的请求者发生交换以及报酬多少,都要受到平台为他所作的评级打分的控制。各个劳动者奔命的对象不再是原先产业劳动中的交易数量和货币额,而是平台上不断增长的数据以及由数据积累形成的量化积分。没有亮眼的积分,平台就不会派发订单,也就没有劳动的机会。这是隐藏在零工工作中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间新型的不平等权力关系。
(二)“产消合一者”数字劳动的剥削与异化
早在20 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中就提出了“产消合一者”(Prosumer)[12]171的概念。该书以一种历史眼光考察了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出现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界限趋于模糊”的劳动现象。到了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产消合一者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劳动群体。当平台用户耗费体力和创意拍摄、制作、剪辑了一段健身视频,并将其上传至某视频平台获得了数万点赞、关注和转发时,用户(包括视频制作和点赞转发)既是数据的生产者,也是数据的消费者。不过,托夫勒将产消合一的出现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性质的终结,认为这种新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趋势所代表的“第三次浪潮”会带来历史上第一个“超越市场”的文明。托夫勒由此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传统经济思想已经与这样一种文明变革脱节了,因为其仍迷失在第二次浪潮的争论中[12]183-185。实际上,这既是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误解。
在产消合一者的数字劳动过程中,由平台所支配的权力关系是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的异化表现。Snapchat、Fcebook、bilibili和微信等平台以创意和表达工具的形式为平台用户提供“免费”内容制作和社交分享的空间。但实际上,作为交换,用户不仅要放弃个人数据,还要默认支持作为这些平台商业模式的广告和营销逻辑。因此,产消合一者数字劳动中包含的自我创造及与他人的交互性关系形成的所谓“去异化”(de-alienation)[13]144过程仅仅是形式上的,并没有改变这一劳动在根本上受平台资本剥削的状况,“去异化”形式和体验恰恰塑造了平台用户持续生产的“自愿”,也进一步形成了平台对用户的虹吸效应。由于平台资本对数据的私有和支配权,产消合一者数字劳动最终形成了一个劳动闭环,即产销合一者成为劳动活动(内容生产)、劳动工具(传播载体)和劳动产品(被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的有机统一体。这一劳动闭环同时是一个剥削闭环。产消合一者数字劳动的最终产品是用户的注意力,注意力的生产过程同时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因此,产消合一者的出现及数字化时代的蔓延并非意味着市场化的结束,而恰恰是市场化进一步扩大的现实表现。这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连接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一直在线”状态,也时刻处于生产和消费的状态。
通过上述关于两种数字劳动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到,数字劳动异化与平台介入资本主义再生产体系密切关联。当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抽象数据成为最重要的交换价值时,各种数字平台作为数据聚合和使用的空间,运用算法和智能分析等生产工具生产出注意力和流量这种数字产品,也生产出数字劳动与平台资本之间的新的剥削形式。平台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聚合各类劳动与重塑劳资关系的经济空间,成为社会权力再分配的经济空间。
三、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及其解放:从资本主体性到劳动主体性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劳动异化意味着确立人之主体的本质成为一种抽象且对立的客观力量,打破这种对立意味着在存在论根基上通过辩证的否定来找回劳动的主体性本质。沿着马克思思考的方向,对数字劳动的进一步考察需引向数字劳动的主体性。而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追问数字劳动的主体性,不仅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深刻理解数字劳动问题的理论需要,也是寻找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获得解放可能性的一种努力。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阐明主体性问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499。这里的“主体方面”即人的主体性本质,同时,这一主体性与对象、现实、感性的关系,只有在“实践”或“感性的活动”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这是马克思在主体性问题上对包括旧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哲学的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感性活动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进一步被阐释为“物质生活的生产”,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则是马克思在物质生活生产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所确立的历史主体性,这一主体性并非表征为人的种种生理特征的自然性,而是为解决吃喝住穿等一切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性。在马克思不断深入推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在《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中进一步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创造一切价值的“劳动”。“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5]65“现实个人”也进一步具体化为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着商品生产的“劳动主体”。“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5]146在这段以经济学话语表达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劳动”即“现实个人”之主体性的本质规定。从这一规定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中劳动主体与其自身生产生活条件相分离的状态,并将处于这种分离状态中丧失了物质实体的活劳动能力称为“主体的贫穷”[5]106。马克思对主体性的思考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断科学化和具体化而逐步深入,并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建立起与劳动之间的本质关联。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主体性的思考,不在于将劳动者身旁庞大的机器换成了随身携带的数字智能设备,而是在新的劳动形态中发现一个更为复杂的主体结构。与产业劳动下“现实个人”这一主体形态相对应,我们或许可以把数字劳动下的主体形态称为“虚拟个人”。应当清楚,这并非是与“现实个人”相对立的概念,不是对“现实个人”的唯心主义颠倒。这意味着,“虚拟个人”并非“现实个人”被倒回笛卡尔“我思”主体意义上的虚幻的意识内在性,因为后者依循的是主-客体结构中表现的自我意识的绝对优先性,是被马克思称为“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14]499主体性。与此不同,沿着马克思对劳动主体的思考,“虚拟个人”仍起始于“现实个人”,它产生的关键是“现实个人”感性的生产活动的数据化,本质上是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对“现实个人”的欲望和偏好的提取与聚合。只不过,由于数字技术和智能算法的加持,“虚拟个人”对作为数据的欲望和偏好的记忆存储能力要远超“现实个人”的生理性记忆存储能力,它装载了“现实个人”在互联网上几乎一切的数字痕迹;同时,它不需遵守生理自然规律,可以始终保持24小时的活跃,当肉身进入睡眠或发呆状态,“虚拟个人”依然在开采和存储数据,并能够从大量零碎数据中析出有价值的部分,进而将无规则的数据群形塑为与肉身的欲望结构相对应的“数据身体”。这里的“对应”仅仅是从起始的意义上来说,而并非一种镜像复制,因为数字技术已经形成对日常生活的全时空座架,肉身在某一瞬间出于好奇而即兴点击的某个网页,以及可能早已忘记的偶然产生的冲动消费和下意识点赞等各种数字活动,都会被大数据忠实地抓取保存下来,并经过算法形成“数据身体”的拼图,这是一个“被拓展和延伸的身体经验”[15]137。因此,“虚拟个人”是关于“现实个人”更为精细,也更为真实的数字肖像,而并非所谓现实肉身的“数字孪生体”,相比后者,它要庞大且强大得多。这是数字化时代以数字劳动为存在论基础的一种新的主体概念。由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自启蒙以来建立在理性或知识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概念,“虚拟个人”所包含的内容要远超于经过理性中介或筛选过的主体形象。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主体活动痕迹占有的这种不对等性,经过对大量数据进行整合与计算所生成的“虚拟个人”是一个笼罩在现实生命体之上的庞大身躯,其主体性总是表现为能动地对“现实个人”进行“反向生产”。今天人们在各类平台上获取的种种信息,以及完成的“关注”和“下单”已在很大程度上分不清是真实的需要,还是被平台资本运用算法所生产出来的需要。也就是说,“虚拟个人”作为一种他者性的存在不断地激发、牵引着现实生活中的理性主体,使得后者不需要过多地思考就能够完成消费、交往、娱乐等种种生命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建基于“我思”的主体被耗散为“无思”的肉身载体。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肉身毫无压抑之感,因为激发和牵引着我们需要和欲望的正是我们自身。现实世界中原本构成“我”的流动的、受压抑的、无规则冲撞着的情感、欲望、想象、无意识等非理性的质料,在数据算法这一“形式因”的作用下获得了能动性。由此,“虚拟个人”成为比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对我们的认识都更清晰的主体力量,在它面前,建立在感性活动中承载着社会形式的鲜活“现实个人”被还原为一个个机械生命。这是数字化时代人的主体本质最重要的异化表现。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虚拟个人”对“现实个人”的“反向生产”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劳动异化之间的区别:数字劳动者表面上不再有产业劳动者痛苦、压抑、被动的生命体验,相反,数字劳动者更多的是在由数据算法所制造的舒适、无感,甚至愉悦的状态中从事自我生产的。这是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剥削和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全新异化形式。
我们发现,“虚拟个人”这一主体存在形态,不是虚构的想象的结果,而是现实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是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态的主体表现。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从劳动-资本关系角度将这种具有主体性并因此表现为对自身拥有反向支配权的劳动称为“活动的物的躯体”[5]207。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这一“活动的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与工人直接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因此是扭曲的和颠倒的。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将这一颠倒看作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历史性就表现为克服这种颠倒生产关系的暂时性。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内在目的就是要对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劳动主体性的真正占有。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体会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动的哲学革命中关于主体性的论述:“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14]209这里的“非主体的主体性”,是在批判形而上学思辨主体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存在论主张,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向度中又深刻地表现为在批判“资本主体性”的基础上对“劳动主体性”的回归。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路,数字劳动的真正价值,即应该在辩证的社会运动中实现这种非主体的主体性,成为劳动自身对象化的本质力量。这一劳动的解放首先意味着在哲学存在论层面回归由于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权力而丧失了一切自然力的“感性主体”。当然,这并非对数字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完全拒绝,并非卢梭田园诗般的浪漫主义批判,而是对负载于肉体生命上种种数字形式的现实改造,其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向进一步表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现实生产关系的积极变革。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应体现在对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数据——的处理上。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数据共享将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变革。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实取向出发,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根本路径。数据作为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其生产和分配制约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同时,数据相对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资料有其自身特殊的现实特征和行为规律,它有着强烈的虚拟性和流动性,并因此不具有绝对私人产权意义上的可规定性。可以打一个比方,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像是仓库里的一颗颗“苹果”,生产关系解放的第一步即把本该属于每个劳动者的苹果悉数归还;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触角延伸至日常生活的全时空领域,整个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赖以进行的数据像是池子中的“水”,它无法在完全意义上被清晰地分割为私人占有的状况,而只能在社会共有的意义上被重新生产和分配。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在数字化社会的历史表现,数字资本主义作为数字技术这一全新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形态,其内在地要求着自身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辩证运动,是推动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并且“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16]68-69,这一经济性质最核心的体现即要求对生产资料进行“私有占有”转向“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就此而言,在对数字劳动和平台资本这一劳动-资本关系的批判中,从数据共享的要求出发,推动数据这一生产资料逐渐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它意味着,数据的生产和分配不再遵循自发性市场条件下单一的货币增殖原则,数据共享不是资本力量的再次集中,而是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意义上对资本逻辑的一种超越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指向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扬弃。当然,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首先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在一种整体主义视野中从法律、观念、技术、政治等方面对数据共享形成理性的制度安排,这应当是一个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整体性的政治化进程”[17]。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在此基础上关于未来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研判仍具有巨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