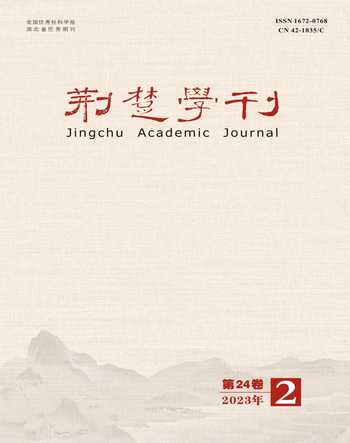教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路径:方法论和立场
2023-06-03杨润东张妍宇
杨润东 张妍宇
摘要: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是史学和人类学的“联姻”,它源于各自学科的研究局限和困境,是学科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诉求。该路径下的教育研究基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融合的研究视角,聚焦于教育中人的日常生活研究,在资料搜集上海纳百川,在资料分析上不拘一格。历史人类学路径下的教育研究的基本立场应是教育学立场——以关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初衷和思维审视天下的教育世界观,以影响个体身心发展及人类发展为宗旨的教育目的观和价值观,以契合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以多元开放、兼收并蓄为依托的教育研究方法。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教育研究;方法论;视角;立场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3)02-0074-06
一、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的形成背景
历史人类学,顾名思义离不开其两大母体学科:历史学和人类学。
考究“史”之词源,histor演化出history和historein,前者最初强调的是实地观察(autopsy),用目击证据来讲述某件事情并为之担保作证[ 1 ]。《说文解字》解“史”:“记事者也。”故历史,初义为从实记事也。记事乃史家之主要活动,从实为史学立家之本。从实则有趋近客观的意蕴,“有若绘画人物,须各还其本来面目,以存其真。……然纯客观之史,实际未必作到,故又谓之近于客观”[ 2 ]。
“历史者,人类留存之重要活动记录,足以参酌而资以了解过去与未来者也”[ 3 ] 85。梁启超亦有言:“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4 ]。历史不仅仅是埋没于时间中的一堆文字、物件、故事……史家也不单单沉迷于过去,还要挖掘历史的价值,让历史发声,让历史彰显出为当下作镜和为未来作估的作用。历史之用显现为:“人们需要从历史知识中汲取必要的文化素质,社会需要历史科学作为它活动的向导,人类需要从自身的历史中认识自身”[ 5 ]。故史家所为,不仅需从实记事,还应梳历史变迁、究历史因果、探历史之用。
史學研究本应涉及过去之全部领域,然而过去在消逝,“过去”流逝至史家的时代已所剩不多,加之史家之精力有限,兴趣有所指,任务有所向,则研究历史时,只能有所侧重。这使得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在史学史的长河中表征为:主流研究长期将目光聚之于重大历史事实,对人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精英阶层,对因果的追寻痴迷于事态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致使微观的历史叙事被漠视,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边缘,历史“冰山”外体下的巨大文化根基长期隐而不彰。
随着法国年鉴学派兴起,政治史对历史的长期统摄被撼动,欧洲大陆的整体史观得到重振,并被推崇到新的高度。计量史、微观史、生活史百花齐放,新史学浪潮开始席卷西方学界。新史学一反长期主宰史界的偏精英远大众、重政治经济轻精神文化的风气,不论是在史观史料上,还是在方法和对象上,史学研究都被空前地开放。这种变化突出地呈现在近当代的一些历史著作中,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屠猫记》中对法国民间故事的关注、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王氏之死》中对小人物的描写、王笛的《茶馆》中关于四川民众及其日常生活的叙事。史学对文化由冷淡转为热心、对大众由不屑变为重视,这种转向正与文化人类学传统对文化与边缘群体的关注不谋而合,“对于很多做历史工作的人类学家来说,过去好比另外一个‘外国,另一个社会或文化”[ 6 ]。就此,史学不仅仅是书斋和文物堆里的史学,还多了些许的烟火气息,史学的人类学化也就自然而然了。
人类学在西方滥觞之时,重在对异国他乡的他者生活进行记述。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时代,民族志的科学价值得到空前提升,但在他和许多田野研究者的田野日志及反思陆续出版后,田野研究者暗藏的主观面被暴露,学界一片哗然,对田野方法的攻击之声不绝于耳,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就在田野研究快被批得一无是处之际,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文化阐释的观点,化解了田野研究无路可走的尴尬,使得田野研究的价值和地位得以重新受到重视和确立(甚至可以说是加固)。人类学诞生以来,不管时代如何变幻,流派有多纷呈,田野研究始终作为该学科研究者的立家之本延续着。只不过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时代,推崇研究者保持绝对客观的立场被消解,人类学也不再以此为傲,反而促发了该学科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客位与主位等核心概念及关系的反思。
随着人文社科的学科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人类学在与其它学科融合过程中,尤其在与史学的互鉴上,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无时间感”(timeless)、相对定格或静态、囿于当下的局限,进而认识到“文化或社会‘碎片,都只有放在整体的历史实践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 7 ]”。1961年,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在曼切斯特所作的著名报告中提倡,人类学要以历史学家为师,因为历史学家在分析历史文献上较有经验,能把握时间和变化[ 8 ] 7。人类学的历史化自然也就成为学科方法发展困境下的新生之路。
史学和人类学各自的反思促成了各自的开放,这种开放使得两个有共同关注点(人、文化、大众、日常等)的学科必定走向“联姻”,在各自学科面临发展困局或危机的背景下,在互化的过程中,狭隘的学科本位观被打破,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
在西方,历史一开始由那些游走四方的行者所记述,是当下所见及所闻,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便是一部记述西亚、北非及希腊等地的一本史书,它不仅记录当地政治和经济,还可看作一部描写地方人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起初也包含对大众及日常的书写。以上古史书《世本》为例,虽原本佚失,但可于后世史书中见其相关的零星散语,由其可知该书中有对人民生活的记述,而不限于对政治的关注。史为官职时,由史官记录或国家大事、或王侯将相起居、或祭祀典礼等等之事,这与人类学的关注也颇为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和历史学是合一的。只不过由于“理性发达过甚,使充满怪诞玄奇的浪漫史诗遭到严重的毁灭驱逐”[ 3 ] 70,历史文献中大量与历史结构、逻辑、规律、事件等无关的记述被看作“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部分被后世所剔除。
再如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史学兴起后,一反中世纪史学对神的仰望和对人的贬斥,使“人”重新回到历史研究的中心舞台,以及当时对殖民地的研究热潮、对自身学科的批判和反思,都与人类学异曲同工。就此来说,人类学与历史学重新融合不仅是学术在研究对象、视角等方面“重回”前学科时代,也是受研究的问题、目的、价值等的时代需要所牵引。
这种“重回”和“牵引”让史学和人类学都一致关注着“人”和“事”,到新史学发端后,加上人类学反思热潮的兴起,史学开始人类学化,人类学也开始向史学靠拢。历史学强调回溯过去,人类学扎根当下,前者看重历史“事实”,后者着重当前的空间(田野)“证据”。二者都重视从实求知,都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同情”,史学通过想象进入历史空间达成,人类学通过身体力行进入田野而实现。前者长期关注重大事件、历史精英,聚焦政治经济史,偏重宏大叙事,忽视人类的日常生活,后者长期固步于人们当下生活的横切面,缺乏对故事的历史审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通价值,便“体现为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 9 ]。
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先贤们力求将二者联通,便是见其长短相形,故求互通有无,“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 10 ] 57。简言之,历史人类学便是要将过去与当下相连,将时间与空间并视,不仅去叙说故事如此发生,还去探寻为何如此、从何而来。
中国学术传统向来强调文史哲不“分家”,先贤们早已洞察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内在交融。西方学者也同样看到人文社会科学间的联系以及综合的价值,“当这些科学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各种相互联系的时候,人们必定能清楚地看到,社会学、精神哲学和历史哲学具有的那些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逐渐在精神科学的体系之中找到它们的解答”[ 11 ]。不同学科方法、视角的融合在近代学术世界早已屡见不鲜,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便在学科走向融合这一大背景下得以开辟。
二、历史人类学路径下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是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的理论假定、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 12-13 ],“所描述的是整个研究所采取的知识论路径”[ 14 ],所研究的对象是“方法整体与对象特性的适宜性问题”[ 15 ]。
宏观来看,教育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对与人有关的教育活动或教育现象的研究。因此,处于固定时空中的人、教育活动、教育事实、教育现象等,都应被置于时空维度中来进行探究。时间性和空间性便是历史人类学路径下教育研究的主要视角。历史人类学对时空的关注内在地要求研究者应将教育场域作为教育历史田野的场域,尤其是学校历史田野。即历史人类学路径下的教育研究应有两大关注点,一是研究对象或问题的历史研究,二是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田野研究,田野空间就是学校或其它“教育场”。
传统教育人类学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总是更青睐“非主流”的教育,如少数族群、偏远农村、特殊群体的研究问题。在当下,这种偏爱需要被扭转,让制度化教育的发生场所——学校作为人类学研究主要的田野之一,与“非主流”平分秋色。教育史的研究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则长期集中于宏大叙事,痴迷于教育大事件、教育的歷史阶段性和规律演变等,和传统教育人类学相反,他们更关注“主流”的教育现象或问题的历史性,对“非主流”的教育历史大多置若罔闻。因此,将历史田野引入教育场,是对以往不同学科各自为战现象的纠偏,通过不同学科的历史性和当下感的融合,让教育问题在时空中得以合并考察,可以让教育研究既冷峻又鲜活,在抽象与饱满、理论与叙事、结构与意义之间获得平衡,从而凸显教育研究的复杂性和张力。
以关于学校的研究为例,学校在一定空间中,但也同时是在一个流变的时间中的学校。在固定空间里的学校具有自身特殊性,也有与其它空间里学校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同样,在时间中的学校具有某一时间点上的特殊性,以及与其它时间学校比较所具有的差异性。对学校的研究应考量学校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时间的连续性和沉淀造就此刻的学校,以及空间的差异性彰显此地的学校。因此,只有将学校置于历史田野之中,方能得到更完整的考察。
“日常生活史是历史人类学的重要出发点”[ 16]。教育往往离不开对“教育中的人”的研究,人是活在生活之中的人,因而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是研究教育中的人的最重要的历史田野聚焦点。教育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地“生活着”。“人是什么……只有当人自己处于活动中,即无论以何种方式——这样或那样成为他所可能是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能经验到”[ 17 ]。因此,要研究“教育中的人”,就需要看他们“如何活着”,尤其在教育场中如何活着。这一方面要求教育研究聚焦于与教育问题相关的当下教育中人的日常生活,做立足当下的田野。另一方面,“教育中的人”作为“人”,是当下的,也是历史的。“当个人进入社会时,他已被社会所塑造了,也就是说已被先于他的历史所塑造了”[ 8 ] 96。这就引导研究者要做“历史的田野”,即通过史料和想象“回到”过去,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构历史日常,去探究背后的历史结构和意义。
简言之,以历史人类学之“眼”去看“教育中的人”,就是要将研究对象的所行所思放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聚焦于这些人在固定时空中的日常,从历史和情境中去探寻他们何以如此,“如果我们只有一个立足于社会之外的抽象的个人的概念而企图进行工作,那我们是既不可能真正理解过去,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在的”[ 10 ] 33。
对于“运用何种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方法”这一具体问题,历史人类学路径下的教育研究应博采众长,根据研究问题来确定资料搜集和使用的方法。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搜集上,历史人类学对研究材料采取“整体观”。它用官方、权威的资料引证,也参考野史、文学、诗歌、器物等任何可能、适合的“证据”,既重视客观的物理事实,也不忽视客观的心理事实。其次,在资料分析的方法上不拘一格,在对材料的分析、阐释、理解和批判上包容开放。量化统计可用,阐释批判也可,外证(external criticism)与内证(internal criticism)结合,事实与想象合用。重视外在事实,也不忽视研究者自身对研究的影响,移情、直觉等都可以用来作为面对史料和田野资料的一种方法。它有独特的历史观,一是“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来研究,而不单把历史视作一种过程来研究。”[ 18 ]二是“强调文化的历史向度,强调历史的多元特征、历史的文化解释和记忆对于历史制作的重要性”[ 19 ]。
三、历史人类学路径下教育研究的基本立场
将教育置于“时空”中来考察的典型是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它“将‘文化与‘历史结合起来,拓展对‘人类形象复杂性的研究范围,将教育人类学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中”[ 20 ]。该流派的代表是克里斯托夫·伍尔夫(Christoph Wulf),他是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的提出者,“主张以‘历时和‘瞬时视角结合的方式看待人类学问题,体现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旨趣”[ 21 ]。
如果说“历史”和“文化”是历史文化人类学的两只“眼睛”,那么“教育学”则是历史文化人类学在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立场”。“历史”和“文化”的“双眼”因为处于教育学的立场而变得特别,拥有了教育学的意蕴和灵魂。
何为教育学的立場?虽然教育学长期以来被其它学科所“殖民”,加上长期被质疑没有专门的研究对象、方法等问题,致使其学科特性被一些研究者判定为模糊的。但是,许多教育学研究者并没有停止对教育学学科身份的寻找和确证,如90年代中国学界对教育学的元研究浪潮。在2005年中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上,专门就“教育学的学科立场”进行了讨论,会上百花齐放,出现了诸多关于教育学学科立场的观点:无立场、责任伦理立场、哲学立场、科学立场、场域立场、实践立场、经验立场、问题立场、生命立场、教育研究者立场、中国的立场、人学的立场、跨学科的立场、多元化的立场等[ 22 ]。这些立场是不同研究者认为教育学何以立于学科之林的“法宝”或“根本”,但仔细审而辨之,大多立场并不是教育学所独有,并不是这里要强调的基于教育学“本身特性”的立场,即教育学与其它学科研究问题相比其特殊性是什么?
教育学的性质是多重的,它“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哲学的成分,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文化的成分”[ 23 ]。王北生提出教育学应坚持“三维一体”的立场,包括:“原点·基础”维度的人之生存与发展;“指向·目的”维度的具体生命与自觉;“方式·方法”维度的生命实践与律动[ 24 ]。这“三维一体”的组合很好地阐明了教育学研究的独特性,因为它基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特殊关注、教育的特殊目的、教育影响人类的特殊方法。虽然研究者们对教育的基础、目的、方法看法不同,但可以进而将这三维看作教育学立场的方法论层面、目的论(价值论)层面、方法或路径层面。这“三维一体”可视为教育学的核心立场,是教育学看问题的出发点、对待问题的最终归旨、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此处并不是要在这里进一步论证教育学的学科性,而是要说明其它学科在与教育学的交叉和融合中,研究者们在强调“教育学”的什么特质?
丁钢提出教育学研究“建立在每个个体发展的基础之上,存在于对社会与文化情境的理解之中;理论概念与经验研究相结合是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内在机制;教育作为实践精神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体”[ 25 ]。从这种观点来看,教育学的独特性彰显为“个体发展”,与社会学、人类学等的内在联系则体现于“社会和文化情境的理解”“理论和经验研究”“实践精神”上。就此,教育学与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的区别与联系便得以凸显,教育学的立场便显露出来。
李政涛倡导教育人类学的“教育学立场”“教育学眼光”。在“教育田野”研究上,他认为“教育田野”和人类学家传统上的田野的差异在于:人类学只关心“找事”和“说事”,“只有当文化与成人、成事联系起来时,才具有教育学意义”;人类学家以“打捞者”“纳凉者”的心态对待田野,教育学家则要进一步关注“实践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单向和松散的,教育学家和实践者则是双向、制度化、合作研究、“互为主体”的。总的来说,“改变被研究者的文化及其生活在文化中的人本身,这就是教育人类学的基本立场”[ 26 ]。在他看来,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不是纯粹科学,也不是纯粹人文”,而是“有关人生的事理之学。”[ 27 ]这一立场便是教育学立场之根本。
不管是教育学的元研究对学科性问题的反思,还是教育学与其他研究交叉融合过程中对自身学科立场的反思,主要体现的教育学立场为这几点的综合与统一:以关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初衷与思维来审视天下的教育世界观,以影响个体身心发展及人类发展为宗旨的教育目的观和价值观,以适用研究问题和对象为导向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以多元开放、兼收并蓄为依托的教育研究方法。其中,教育世界观、价值观是教育学立场独特性的表征,方法论和方法虽不是教育学学科所独有,但是它们与教育世界观、价值观相结合,使得在具体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方法论和方法内含了教育(学)性,如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注意“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对象”“教育生活”等具有教育内涵的特殊性。因此,这几点的统一便可看作教育学研究,以及教育人类学、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等交叉学科研究的教育学立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人类学路径还需强调研究者立场和“教育中人”的立场的融合。“教育中人”的立场,主要指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问题所关涉的人,如研究教师应有教师立场,研究学生应有学生立场。虽然这个立场本身就在人类学视角之中,即人类学的“主位立场”或“他者立场”。简言之就是要求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的位置,通过田野、个体经历等以经验、想象、回忆等方式去“同情”教师,以“他们”的眼、耳、心、情、思去看待研究问题,与教育研究者的立场形成互补。两种立场的融合的达成表现在具体研究中,一方面是在研究资料的搜集上,要有两种视角的资料,另一方面,在研究资料的分析上,要从研究者和他者的立场来把握和处理。最终达成研究者(我)与研究对象(他者)思维、身体、情感等一定程度上的“通达”。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3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3.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04.
[3]王尔敏.史学方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
[5]李振宏,刘克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
[6]西佛曼.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168.
[7]张佩国.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報(人文社科版),2013,34(4):1-9.
[8]勒高夫.新史学[M].姚蒙,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9]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418.
[10]卡尔.历史是什么?[M].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狄尔泰.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M].艾彦,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155.
[12]王积超.人类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
[13]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
[14]格雷.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M].许梦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5.
[15]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14.
[16]常建华.历史人类学应从日常生活史出发[J].青海民族研究,2013,24(4):17-22.
[17]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M].赵卫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74.
[18]王铭铭.我所了解的历史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07(2):78-95.
[19]蓝达居.历史人类学简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1):4-9.
[20]孙丽丽.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的形成与方法论突破[J].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7(2):6-12.
[21]李存金.论德国教育历史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传统[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8(1):30-36.
[22]宋剑,董标.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年会综述[J].教育研究,2006(1):93-95.
[23]刘庆昌.教育知识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246.
[24]王北生.教育学立场的多维度分析[J].教育科学,2012,28(1):13-16.
[25]丁钢.教育学学科问题的可能性解释[J].教育研究,2008(2):3-6.
[26]李政涛.论“教育田野”研究的特质——兼论田野工作中人类学立场与教育学立场的差异[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7(6):6-11.
[27]李政涛.教育学的边界与教育科学的未来——走向独特且独立的“教育科学”[J].教育研究,2018(4):6-17.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2-02-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梳理与‘中国经验研究”(BAA200023)和贵州师范大学2022年度校级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教育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润东(1990-),男,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
张妍宇(1998-),女,贵州遵义人,贵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