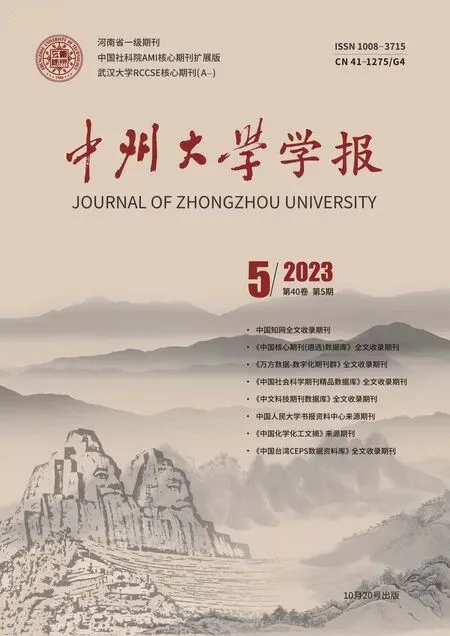五四运动与道德转型
——以传统“忠”德的转化为中心
2023-06-02崔海亮徐燕子
崔海亮,徐燕子
(1.延安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陕西延安 716000;2.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一、引言
“道德革命”是五四时期一个鲜明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始于1902年梁启超的《新民说·论公德》:“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1]22其后章太炎也提出了“革命之道德”。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可以看作是道德革命的宣言书[2]。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促进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型。国内学界对五四道德革命的研究成果丰硕。张锡勤、张岂之等学者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阐述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意义[3],还有一些学者围绕道德革命的主题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吴虞、鲁迅等五四代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在对道德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认为五四道德革命具有理性精神,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第二,认为五四道德革命是全面反传统的,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和“道德危机”;第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的某些方面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普世价值”,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道德的当代价值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支持[5]。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对五四道德转型的过程及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较多,对五四道德革命的意义有充分的阐发,但传统道德的内涵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传统道德如何转变为现代道德、传统道德具有哪些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以传统“忠”德的转化为中心,来说明五四时期思想家对忠德内涵的探讨如何促进了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以及当今时代的忠德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内涵。
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忠德现代性内涵的阐发
对于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学界习惯以“东方文化派”和“西化派”来区分。前者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后者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代表[6]193。至于具体某一人物划入何派,则尚无定论。笔者认为,无论当时的“东方文化派”还是“西化派”,都是认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也都有某种程度的西化倾向。区别在于“东方文化派”是“东学”的底子,西学的面子,而“西化派”则连“东学”的底子都不要了[7]。笔者更愿意以“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来取代“东方文化派”和“西化派”。前者主张吸收西方文化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后者主张以西学为根基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倒重建。前者以梁启超、杜亚泉等人为代表,后者以胡适、陈独秀、吴虞等人为代表。
在近代,梁启超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深入反思的一个思想启蒙者。在吸收西方伦理政治学说的基础上,他主张对国民性进行改造。他的《新民说》一书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命题,其中的《论国家思想》一文,围绕忠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说:
“吾中国相传天经地义,曰忠曰孝,尚矣!虽然,言忠国则其义完,言忠君则其义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件也。二者缺一,时曰非人。使忠而仅以施诸君也,则天下之为君主者,岂不绝其尽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则如今日、美、法等国之民,无君可忠者,岂不永见屏于此德之外,而不复得列于人类耶?……君之当忠,更甚于民,何也?民之忠也,仅在报国之一义务耳。君之忠也,又兼有不负付托之义务,安在其忠德之可以已耶?”[1]26
梁氏认为忠孝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道德品质,是人格的基本条件。此忠德指的是忠于国家而非忠君。那些实行民主制的无君主的国家之民也应该具有忠德。而且君主也应该具备比一般民众要求更高的忠德。一般民众的忠是指报国的义务,而君主的忠则不仅要有报国的义务,还有为人民负责的义务。梁启超所谓的“君”不仅指传统社会的君主,也包括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都应该具有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义务。梁启超对忠德的诠释已经包含了对忠德进行现代转化的意义。
后来,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对忠德的认识又有了发展。他认为,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君主个人尽忠,是因为君主代表国家。如果君主对国家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就不能代表国家,人民也就没有忠君之义务。梁启超这种忠君的本质是忠国的观点,比《新民说》更进了一步。这比五四时期批评古代忠臣对君主只是忠于个人的说法,更有说服力[8]5-14。
辛亥革命后,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由总统制取代了君主制。无君可忠的现实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传统忠德的内涵及现代转化。
1913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国民今后之道德》一文,创造性地提出了“忠之客体”“忠之主体”的概念。他说:“即如忠之一义,就君臣关系之狭义而言,固已根本破坏,然人民当效忠于其国及他事之宜用其忠,是忠之客体变,而忠之主体固未尝或变也。”[9]168杜亚泉认为随着君主制的废除,“忠之客体”发生改变,在过去指的是君主,现在指的是国家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忠之主体”指的是人民,人民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所以,忠之主体“固未尝或变也”。杜亚泉还把人们的职业列入了“忠之客体”当中,这表明公民的职业道德也成为其关注的重要问题。
孙中山不仅对传统忠君思想有深刻批判,对忠德的现代内涵也有新的阐发。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忠德还要不要讲?忠德是不是只对君主一个人效忠?对于这些问题,孙中山明确阐明了他的看法。他说:
“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10]650
孙中山对忠德的阐发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他认为忠君观念要被抛弃,但传统忠德中积极的方面还是要继承下来的。他认为,“为四万万人效忠”是更高尚的道德,随着时代的发展,还需要倡导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自己职守的新道德。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皇帝被赶跑促使了传统忠君道德的转变,忠的客体不再是君主。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进一步促使当时思想家探讨忠德的现代内涵。这一时期忠德观念的转变表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向先秦时期忠的本义回归。一些思想家通过对“忠”的字义学考证,认为忠的本义就是要忠于国事,忠于民利。二是抛弃了忠德不合时代的忠君内涵,增加了忠德新的时代内涵。梁启超、孙中山则主要从民主国家国民资格和国民道德的角度来论证忠德存在之必要,忠君实际上是忠于国家而非忠于个人。孙中山认为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在现代社会还是应该提倡的。值得注意的是杜亚泉提出的“人民当效忠于其国及他事”,柳诒徴考证忠的本义为“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11]80,这些观念已经接近当今“忠于职守”的道德要求,是结合当时时代要求对忠德内涵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传统忠德的批判及其影响
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努力挖掘传统忠德的现代内涵不同,激进民主主义者主要立足于对传统忠德的激烈批判。
陈独秀认为“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12],而中国的“三纲之说”违背自由平等之义,“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3]。陈独秀认为,忠君道德,使民成为君的附属品,导致国人无独立自主之人格。
李大钊主要应用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从压制个性的角度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批判。他认为封建纲常的本质在于“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14]178-179。李大钊吸收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认为纲常名教是对卑下者、被治者个性的压制。忠孝本为一体,都牺牲了人的个性,使臣子成为君父的牺牲品。可见,马克思的学说不仅在建国方案方面直接影响了中国,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也有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当时思想家对纲常伦理的批判主要针对君为臣纲。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废除,忠的客体发生改变,君主不再是效忠的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对三纲的批判由忠转向了孝和节,传统家庭伦理的孝亲和贞节观也遭受很大冲击。
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结构使“移孝作忠”成为可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孝本为一体,孝亲成为忠君的伦理基础。因此,在批判忠君道德的同时必须批判孝亲。民国初年曾出现两次短暂的帝制复辟,虽然赶跑了形式上的皇帝,但人们头脑中还残存有忠君的旧观念。这种忠君的观念和家庭伦理中孝亲的观念紧密相连,因此,必须批判孝亲的思想才能彻底批判忠君的奴隶道德。吴虞就是批判家庭伦理的急先锋。
吴虞认为,我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而不能进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家族制度的阻碍。家族制度限制了人们的独立自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在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中,孝为仁之本,百行孝为先的观念往往体现为“忠孝并用、君父并尊”的特点,“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15]99-101。吴虞认为这种家国不分、忠孝一体的家族制度是国家专制的基础,要想从根本上否定忠,就必须在家庭里废除父对子的专制。
陈独秀也认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而孔教的精华是礼教,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忠、孝、贞节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三纲之义,乃起于礼别尊卑,始于夫妇,终于君臣,共贯同条,不可偏废者也。今人欲偏废君臣,根本已摧,其余二纲,焉能存在?”[16]146-147陈独秀认为随着帝制的废除,不仅忠德无存在之必要,且孝、贞节这些旧道德也无存在之价值。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忠孝的原初涵义与当代价值。
李大钊也将忠孝道德的社会基础归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14]178。因此,批判忠君道德自然连同孝道一起批判。
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特别是批判忠君和忠孝道德都是为了批判“孔教”,是“除恶务尽”的“扫毒”。在激进民主主义者看来,传统儒教中所宣扬的都是维护专制旧道德和培养奴隶性的陈腐说教。他们对传统旧道德的批判不免失之偏激,矫枉过正。如对忠德的批判就有偏颇之处,他们习惯于将忠德等同于忠君,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忠的超越时代价值[17]218。虽然新文化运动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但陈独秀、吴虞等人对传统忠孝道德的认识显然是偏颇的,其批判方式是极端的,其流弊也是深远的。他们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否定复古尊孔,进而否定孔教的忠孝节义,进而对传统忠孝道德进行激烈而片面的批判,这样的思路和做法影响了当时人们对家庭伦理的持守,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下面以吴虞为例来说明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消极影响。
吴虞早年在成都尊经书院师从经学大师廖平研读儒家经典,可以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戊戌变法后,开始学习新学,思想观念大变,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孔的旗手。胡适称他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然这样的评价未必确切。吴虞在思想上激烈地反孔,主张“家庭革命”,反对家族制度和家庭伦理对个性的压制和束缚,在行动上也把他思想上的这种认识付诸实践。吴虞和他父亲关系非常不好,以打官司和他父亲争夺家产,以致成为仇敌。在《吴虞日记》中,对其父亲,不仅无尊称,而且冠以“魔鬼”“老魔头”等污辱性的称呼,字里行间透露其对父亲的痛恨之情。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他和父亲打官司胜诉后,在日记中写道:“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自己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却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为了生儿子59岁还纳妾。吴虞性格偏执,自私专制。无论从新道德还是从旧道德的视角看,吴虞都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倡导新道德的人却是不道德的人,这显然是个悖论。反映了人性本身的复杂性,反映了个性自由、人格平等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张力和冲突。
新文化运动时期,像吴虞这样思想极端的人只是特例,但和吴虞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却不在少数。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许多新青年,高举“家庭革命” 的旗帜,以背叛家庭、离家出走为思想解放的表现,家庭伦理受到严重冲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被削弱,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纯朴的道德风俗也受到消极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那些激进派,因反袁而否定孔子进而否定忠孝节义。这种思想和行为,乃是“因噎废食”。“即如忠孝节义四德者,原非我国所可独专,又岂外国所能独弃?古昔固尊为典彝,来兹亦焉能泯蔑?夫以忠孝节义与复古并为一谈,揆诸论理,既已不辞,以厌恶复古故,而致疑于忠孝节义,其瞀缪又岂仅因噎废食之比云尔。”[18]243梁启超认为,忠孝节义四德,古今中外通用,具有“普世价值”,未来仍然需要。把忠孝节义与复古复辟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由反对复辟而怀疑忠孝节义更是不对的。梁启超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力求进取值得提倡的,而诵法孔子对国民进取毫无障碍,将改革进取与诵法孔子对立起来也是错误的。[8]5-14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今天如何继承和创新传统道德有重大启示。
四、当代社会忠德的合理性内涵
忠德的合理性内涵是什么?这涉及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的常与变之关系。
梁启超对道德的常与变有过深入探讨。在1902年《新民说》中,梁启超认为:“德也者,非一成不变者也(吾此言颇骇俗,但所言之者德之条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万古而无变者也。读者幸勿误会。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数千年前之古人所立一定格式以范围天下万世者也。”[1]21数千年前的道德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做出改变,改变的是道德的具体内容,而道德的本原则是不变的。道德的本原就是“利群”。在其后来所著《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他认为报恩、明分、虑后这三种观念“为一切道德所从出,而社会赖之以维持不敝者”[19]14。“有报恩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过去社会相联属;有虑后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将来社会相联属;有明分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至赜而不可乱。”[19]20梁启超认为报恩观念是履行道德义务的心理动因,而明分则是安于本分,尽职尽责。人人明其本分,尽其职责,社会则繁荣发展。虑后,指的是为未来考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促使人民考虑后果,改过迁善。
梁启超从影响风俗道德的社会心理观念层面来论述中国道德之大原,其分析未必都正确,但却为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变革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注重报恩的自觉履行义务观念,明确职分尽职尽责的观念,都进一步丰富了忠德的时代内涵。
杜亚泉认为,道德有体有用,体不可变而用不能不变。考虑当时形势,应该改变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改服从命令之习惯而为服从法律之习惯;第二,推家族之观念而为国家之观念;第三,移权利之竞争而为服务之竞争。[9]166-168杜亚泉有与梁启超类似的观点,比如注重对国家履行义务,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服务。特别是针对当时社会争权逐利、漠视责任的现状而提出的服务社会的观念,比梁启超又进了一步。他说:“自物竞论输入以来,更引之以为重。利己主义,金钱主义,日益磅礴,而责在人先、利在人后之古训,转荡焉无存。革命以还,此风尤炽。……其在位者,则又尸位素餐,不知责任为何物。循此以往,必至全国上下,无一勤务负责之人,而国将安赖?为今之计,亟宜改此争点。不为权利之角逐,而为职务之服勤。必使农奋于野,工勉于肆,商振于廛,士励于校,而从政之百执事,亦因其责之所在而各尽所长,则国是庶有豸也。”[9]168能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氛围中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以争相做好本职工作为荣耀,则或许能解决好当时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杜亚泉的这种观点对于如何增强我们当今时代的职业道德有重大启发意义。
在现当代思想家里面,贺麟是兼通中西的大家,他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有精深的研究。他所说的新道德不同于新文化时期提倡的新道德,是在继承儒家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创新。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他认为五伦观念是中国礼教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群体的纲纪。必须从检讨旧传统观念里面,才能产生真正的新道德。五伦观念有优点也有缺点,不能全部丢掉。他还认为,五伦观念的核心“三纲说”的真正意义与柏拉图的理念说有一致的地方,和康德的“道德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观点相符合,与基督教伦理尽单方面爱的义务也颇的相同地方。他认为旧礼教中有不可毁灭的基石,通过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可以在这个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20]141-150
梁启超、杜亚泉、贺麟等人都主张,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础上,通过吸收西洋文化进行改造,赋予传统道德以新的时代内涵,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今社会。我们不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但是经过五四至今百年来的思想运动和社会变革,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包括政府层面也在积极倡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十九大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口号,而且把“文化自信”提高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倡导。
当今社会科技高度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分化,社会流动性加大,人格独立性增强,人的寿命延长,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都在不断改变,这些都对传统忠德的内涵提出了挑战。不过传统忠德内涵中忠于社稷、忠于民、忠于事、忠信、忠诚、忠恕这些优秀品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高度契合,传统忠德中的合理内核仍然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道德基因,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当今时代的新变化,当代忠德的合理性内涵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忠于国家。传统忠德中有“忠于社稷”“忠于民”的涵义,具有爱国利民的当代价值,可以转换为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左传》中有“忠,社稷之固也。”(《左传·成公二年》)“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忠,民之望也。”(《左传·襄公十四年》)春秋时代的“忠”是所有人都应该具有的品质,无论国君将臣还是庶民百姓,都应该具备忠德。保卫社稷,利国利民,都是忠的表现,忠的对象最终指向了社稷和国民。即使秦汉以后,忠的对象转向君主个人,但君主是社稷国家的代表,君主要以社稷黎民百姓为念,忠君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仍然是忠于国家。某种程度而言,今天的忠于祖国、爱国利民实际上就是古代忠于社稷精神的传承。罗国杰曾提倡:“我们应当把中华民族的‘公忠’这一优良道德传统,加以发扬,赋予它新的意义。”也就是说,要对集体、民族和国家的事业,“抱着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坚韧勇敢、不屈不挠并为之奋斗到底的精神”[21]403。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作为公民,都要有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的义务,要有忠于国家、热爱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忠于职守。传统忠德中的“忠于职事”具有忠于职守的当代价值,可转换为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左传》中有“违命不孝,弃事不忠”(《左传·闵公二年》),把放弃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视为不忠。孔子也有忠于职事的思想。孔子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对这句话,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敬吾之事”,也就是忠于职守,用今天的话来讲,上班不是为了混工资,不要总想着能得到多少报酬,要先把老板安排的事干好。只有工作干好了,享受的待遇才能心安理得。古代对从事公务的人员也有很高的道德要求,主张“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仕而废其事,罪也”(《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要尽心竭力对待自己的职事,对于不敬业、玩忽职守的官员要治罪。历代统治者都把忠、勤、廉当作衡量官员品德的重要标准。公忠为国、忠于职守、清正廉洁乃是敬业精神的重要标准。在当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的时代,在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自由的同时,尤其需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认真工作,忠于职守,仍然是当今时代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具备的职业道德。
第三,忠于家庭。在儒家传统伦理中,家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儒家认为人伦关系起源于家庭,由家庭推及家族,由家族扩展到社会中的君臣、师友诸关系,由此构成整个社会的政治伦理关系。其中家庭家族关系是整个封建伦常关系的基础。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22]也都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也正因此,家庭被看作是私有制和封建纲常伦理的最后一个堡垒,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激烈的批判。时过境迁,我国古代的大家族变成了当今“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彻底解体,个人对家庭的依赖性也明显降低。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在协调人际关系、改善道德风尚、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夫妻要相互忠诚,否则既是对家庭的伤害,也是对爱情本身的伤害。当今我国的离婚率在不断上升,必须引起警惕。离婚率上升一方面说明社会不断开放和进步,另一方面,如果离婚率过高,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婚姻双方对婚姻本身的轻率,是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表现,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注意自身忠德修养的提升,在金钱、权利和色欲面前失去控制,必然会破坏夫妻感情,影响家庭的稳定,对子女的健康成长也极为有害。因此,当今社会特别需要提倡忠于家庭的传统美德。
第四,忠恕待人。传统忠德中的“忠恕待人”具有友善的当代价值,可转换为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友善精神。传统伦理非常重视忠恕之道。“忠恕”被看作是孔子学说“一以贯之”之道。后人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看作“忠”的内涵,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作“恕”的内涵。其实,“忠恕”乃孔子的一贯之道,本不可分。孔子主张,人不仅要忠于君主和朋友,还应以忠诚的态度对待一切人。当弟子樊迟向他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与人忠”,这里的“人”包括君主、朋友但又不限于君主、朋友,而是泛指一切与自己发生交往的人,甚至对于未开化的夷狄,也要忠诚相待。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在人际交往中通过伦理角度的换位思考来体悟他者的感受,从而导出“推己及人”“以己度人”的宽容恕道。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这种将心比心、以情度情、换位思考的待人原则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可发挥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友善,就是植根于“仁爱”和“忠恕”的道德心理,它要求人们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将传统儒家的忠恕之道进行当代转换,可以更好地在全社会中营造宽容理解、守望相助的和谐人际环境。[17]235
第五,诚实守信。忠德中的“忠信诚实”可转换为市场经济中的诚信原则。忠信观念具有深刻的伦理价值意义,它既是人际关系中每一个体的美德表现,同时也是个体之间相互承诺的责任伦理,即诚实守信的道义要求。[23]107这种责任伦理和诚信道义对于弥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诚信缺失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当今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有很大不同,但对忠信的价值追求和道德自觉则是一致的。在忠信价值的情感因素中增加诚信原则的理性因素,将诚信精神化作人的内在美德和外在制度的结合,就可以转化为规范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诚信道德。
五、结语
五四以来,思想家对传统忠德内涵的阐发表现出向先秦回归的趋势。强调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不仅是忠德本义的突显,也是当今社会对传统优秀道德的一种内在呼唤。虽然五四时期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扬弃,但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然表现出复兴的趋势。这表明,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廉耻等传统优秀道德仍然具有永恒的价值。剥去历史的遮蔽,挖掘其核心要义,结合时代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进行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是传统道德获得新生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