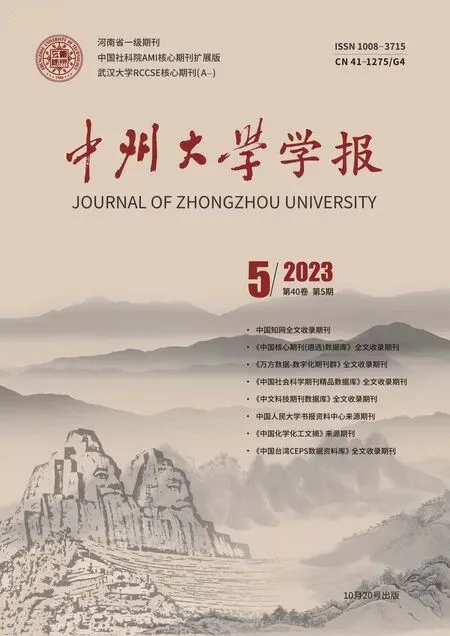《现代人》最后阶段的办刊方针和策略
——《怎么办?》的发表对于《现代人》的意义
2023-06-02耿海英
耿海英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我们知道,《现代人》约在1855—1861年间迎来自己最辉煌的也最激进的七年,他们积极介入俄国的农奴制改革进程,在《现代人》上开辟专栏,引领舆论公开讨论改革中的各种问题。然而,改革后,俄国社会出现了各种极端事件,如射杀农民,镇压大学生,关闭彼得堡大学。在这种局势下,《现代人》激进的倾向也引起了第三厅的注意。1861年9月14日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米·拉·米哈依洛夫因参与编写传单而被捕,到处传言说1862年《现代人》将不再出版。编辑部不得不出面向读者解释,驳斥这种传闻。但是1862年6月杂志“因有害倾向”被勒令暂停出版八个月;而到了7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被捕的原因是他寄往国外给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的信被截获,信中建议在伦敦或日内瓦出版《现代人》。
这样,《现代人》的暂停出版,1861年,米哈依洛夫被捕,杜勃罗留波夫去世;1862年,巴纳耶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和随后被流放,这些重大事件合在一起,给杂志带来了沉重打击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到1863年初涅克拉索夫才恢复了杂志的出版。不过,整个1862至1866年间,书刊审查的严厉,发行量的降低,使得杂志渐渐失去影响,到1866年,《现代人》出版第11期后被彻底关闭。而后,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共同主办的《祖国纪事》,继续完成《现代人》杂志的事业。这样,1862—1866阶段,我们称之为《现代人》最后的艰难阶段。
1863年《现代人》恢复出版后,涅克拉索夫重新组织杂志领导成员,除了他本人,新加入的有谢德林、米·阿·安东诺维奇、叶利谢耶夫、阿·尼·佩平。编辑部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内部的分歧,降低了《现代人》内容的影响力,但是在已经到来的黑暗环境中,它依然是最好的民主主义杂志。1863年至1866年间,杂志发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及谢德林大量的政论文和其他作品,还有安东诺维奇、叶利谢耶夫、阿·尼·佩平的文章,瓦·阿·斯列普佐夫、费·米·列舍特尼科夫、格·伊·乌斯宾斯基等作家的作品。因而就这一阶段,我们关注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这一时期《现代人》最重要的批评家谢德林与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其二是,这时《现代人》为什么还要发表作为被关押政治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一、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与涅克拉索夫
这一时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成为《现代人》最主要的批评家。他与涅克拉索夫在60 年代(以及 70 年代)有着密切的杂志经营和个人方面的关系,他们共同执掌一份杂志,先是《现代人》,而后是 《祖国纪事》。但在此前的十年(在50年代)他们之间并没有这份联系,甚至他们的关系并不和睦,尽管涅克拉索夫在 1857 年提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文学处女作《外省散记》时,还是相当友好的: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谢德林与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相提并论,称《外省散记》不仅是一种奇妙的文学现象,而且记载了俄国生活的历史事实,是一本珍贵而出色的书,俄国文学现在和将来都会为它的《外省散记》感到自豪;在俄罗斯大地上它将会有众多的崇拜者、颂歌者。涅克拉索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外省散记》的评价予以赞赏,称其与众不同。
但几个月后,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养病回来,由于他将近一年不在国内,远离俄国,回来后还没有弄明白俄国生活新出现的现象,他就抱怨起俄国文学的状况,特别是责难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片面性”,称谢德林这个“时代的天才”是一个愚蠢、粗鲁和非常傲慢的绅士。这些措辞严重、实际上并不公平的话,显然是受到了与谢德林个人交往的不愉快印象的影响,谢德林在举止和待人接物上的棱角是众所周知的,它不只对涅克拉索夫一人造成了恶劣印象。不过,有足够的理由推断,涅克拉索夫是带了有色眼镜,从而改变了他原来对谢德林作为作家的良好看法。但不管怎样,1857年底涅克拉索夫在《现代人》上(第10期)还是刊登了谢德林的短篇《新郎》,1859年发表了他的短篇《快乐生活》(第 2 期),从1860年起,他几乎成为《现代人》的重量级作者,1862年底他进入杂志编辑圈。
从谢德林这方面来看,在他50年代末、60 年代初的通信中提到涅克拉索夫时,对涅克拉索夫的态度也不友好。他虽然知道涅克拉索夫对他的《快乐生活》有溢美之词,但却说:“我不知何故不相信他的赞美,因为他嗅到了空气中的一切,只关心公众的印象。”[1]213(1859年2月3日给安年科夫的信)这是指责涅克拉索夫为了经营杂志,只顾投读者所好;在另一封给安年科夫的信(1860年1月27日)中,谢德林称“很难与涅克拉索夫合作”[1]226,并表达了要去德鲁日宁的《读者文库》的愿望。然而,最终这事情并没有发生。谢德林当然不必为此后悔,留在《现代人》,就留在了那个时代俄国文学的主流中,将自己的名字与 60 年代公认的“思想统治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他在信中所指的涅克拉索夫的缺点,在他们密切接触后,证明并不像他早些时候看起来那么重要。再后来,谢德林觉得涅克拉索夫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心理上与自己相似的作家——这也许是谢德林与涅克拉索夫最终能和解的主要原因。在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的创作中,共同贯穿着一种对祖国自然、对祖国人民难以抑制的热烈的爱。可以说,这种有机的内在的爱,是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的“民粹主义”的核心。1875年,涅克拉索夫为即将出国的谢德林作诗一首,送别老友——“在异国他乡不要忘记,/我们忧郁的祖国……”[2]169可以肯定,这不会发生,因为谢德林在1857年就已经在他的《外省散记》中写道:“即使把我送到瑞士、印度、巴西,无论怎样绚丽多姿的自然包围我,无论到处是怎样透明的蓝天——我仍然会找到家乡甜美的灰色,因为我随身携带着它们,永远在心中,因为我的灵魂把它们作为我最好的财富。”[3]152同样在1857年,涅克拉索夫在诗歌《沉默》中写出了类似的心声:“在遥远的地中海之外,/在你更明亮的天空下, /我寻求与悲伤的和解,/ 而且在那里我什么也没找到:/ 无论异国的大海多么温暖,/ 无论别人的天边多么红艳,/ 也无法修复我们的悲伤,/ 抚平俄罗斯的悲伤。”[4]51
他们能够这样相互呼应的例子很多,因而足以判断,早在 1857 年,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彼此之间还知之甚少,正如我们提到的,甚至不太认同彼此,但在信念上就已经很接近,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心绪,同样的火焰在他们的心中燃烧。正是这种信念和心绪使得谢德林在1862 年初放弃了公职,将自己停泊在《现代人》这艘大船上,尽管这时正是该杂志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现代人》被禁八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这次车氏的被禁和被捕是政府希望通过一系列严厉措施对付可恨的“虚无主义者”的结果。但就在这种情形下谢德林加盟《现代人》,并且不害怕在《现代人》编辑部中占据最显眼的位置,这也就不能不看作是他对杂志方向的声援,同时也是某种公民勇气行为。另一方面,这也说明,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之间的关系已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得到稳固。从叶利谢耶夫的回忆录来看,在 1862 年底,涅克拉索夫与《现代人》最亲密的合作者安东诺维奇和叶利谢耶夫的关系开始冷淡,他们怀疑涅克拉索夫(而在不久的将来事实证明,这怀疑并不合理)几乎是叛徒,并打算停止他们的合作。显然,谢德林不同意这些怀疑,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进入了《现代人》编辑部。谢德林 1862 年 12 月 29 日给涅克拉索夫的信表明,涅克拉索夫委托给谢德林一些事务,这些事务相当于行使主编的职权,至少是助理主编的职权:谢德林与审查机关和当局进行周旋,接收作者文章并评估它们的文学价值,在确定杂志排版和印刷方面有发言权;另一方面,1863—1864年他自己与《现代人》的合作异常繁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时他是《现代人》最多产的作者。例如,1863年他在《现代人》上发表文章、随笔29篇,评论19篇,共计627页,而这仅是谢德林合作一年的成果。
显然,涅克拉索夫不仅信任他,还非常欣赏他,他在《现代人》上给了他如此多的空间。而且涅克拉索夫的眼光也没有错,谢德林不仅用自己的作品填满了《现代人》的版面,他还做了一件重要而必要的事情:他在1863—1864年的政论文中充满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愿望,即拒绝日益增长的“反动”风气(指温和派的“和解”“联合”等思想),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实现了《现代人》的目标。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在他们共同活动的这个时期,在意识形态上的亲和,比以前更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由于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倾向存在根本分歧,两者分裂,涅克拉索夫与屠格涅夫分道扬镳了;而谢德林也毫不犹豫地宣称,屠格涅夫为俄国进步事业提供的是“可怕的服务”,因为屠格涅夫称年轻一代的代表为“虚无主义者”。这样表明了他与涅克拉索夫共进退。
虽然在此后谢德林有段时间离开《现代人》又返回公职,但他与涅克拉索夫保持了密切的通信。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与涅克拉索夫的通信中,表达了对那些试图取代被流放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去世的杜勃罗留波夫的地位的人的怀疑,特别是对米·安东诺维奇的怀疑。在1867年秋天和整个1868年,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之间的通信特别频繁,因为在《现代人》被彻底停刊(1866年5月)一年多之后,涅克拉索夫依然无所作为,于是决定重返期刊活动,并决定租用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涅克拉索夫的计划被接受,但在谁应该担任《祖国纪事》的执行编辑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由于不能指望任命《现代人》的任何前成员为主编,因此涅克拉索夫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认为可行的是让克拉耶夫斯基继续留任,担任主编,哪怕是虚设的;谢德林和叶利谢耶夫强烈反对这一决定,认为这将是对涅克拉索夫方向的背叛。涅克拉索夫不得不发挥自己辩才的所有力量使他们让步。等到与克拉耶夫斯基的谈判圆满结束之后,涅克拉索夫立即就给谢德林所在的供职地发了一封电报,让他返回参加《祖国纪事》。这是后话。这足以证明谢德林和涅克拉索夫的密切关系,因而在《现代人》的最后艰难阶段,谢德林发挥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二、《怎么办?》的发表对《现代人》的意义
1863年初涅克拉索夫几经周折恢复了杂志的出版,而且发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样,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政治犯被捕之后,《现代人》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863年初《怎么办?》发表在第3—5期《现代人》上(且第3期是头版头条)。而这是个怎样的年份呢?正如克鲁泡特金在其《俄国文学史》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经过了一个时期相当自由以后,1863年的大残害便来了,而由这残害便开始了对文学、艺术、科学以至于各个大学无有间断的迫害时代,这时代延长着下去,一直到1905年。这些年代之中,几乎每一个青年的著作家(即青年作家——引者注)都要尝一尝监狱或者流放的生活,而且在这个时代里,每一个智识者的家庭中,几乎总有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属是坐在牢狱中或者流放在外面的。”[5]4而车尔尼雪夫斯基1862年7月被捕,正是这场大残害的开始,他正是无数被流放者之一,而且他长达21年的流放与苦役①,足以证明官方对其“危险性”的恐惧程度。就是这样一名在押政治犯作者的小说出现在杂志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意义;尤其具有意义的是,在《现代人》上发表《怎么办?》的决定不是由作者本人而是由杂志编辑作出的。这也许可以窥见这一时期杂志的某种编辑方针和策略?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怎么办?》发表时整本刊物的内容和基调。
车氏的小说《怎么办?》发表在《现代人》最困难的时期,我们前面说过,在此之前,杂志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不过,尽管遭遇了如此大的变故,《现代人》还是“活过来”了:涅克拉索夫使杂志复刊,并组织了新的编辑部。出版活动获得许可后,《现代人》重新“投入战斗”。我们说是“战斗”,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时期发表的大部分内容所具有的那种充满力量的声调(当然就是谢德林的大量文字)。像以前一样,杂志的主要方法原则依然是具有明显的争论性,有时甚至是冲突性。《现代人》的政论家们在自己的文章中与其他刊物、媒体人、著名的作家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展开激烈争论。不过,应当指出《现代人》很少首先挑起争论。进行争论的理由,往往是其他杂志或作家针对《现代人》本身的出版策略,或针对《现代人》基于本身的社会政治立场或文学传统所发表的言论而进行攻击和挑战,《现代人》作出回应。例如:谢德林在自己的栏目《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认为,有必要对费特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札记《来自农村》作出回应,这位著名诗人指责当代俄国文学过于“民主化、大众化”了,这其中暗中指向《现代人》。在自己的回应文章中,谢德林给予费特的诗歌天才以应有的尊重,同时,指责他在自己的创作中远离了现实生活。[6]387
我们发现,在长时间被禁、沉默之后,《现代人》尽一切方式宣传自己的独特性,强调杂志的关闭和恢复对于俄国新闻业的意义。在1863年1—2月合刊中,两次阐明那样一种思想,即《现代人》在俄国文学舞台上占有完全独特的位置,其他刊物全部围绕在它周围,或高声或低声地都企图与之争论。在文章《过去八个月的杂志短评》中,作者米·安东诺维奇以讽刺的口吻描写了《俄国导报》《祖国纪事》《时代》——《现代人》的这些主要对手——的特点,试图捕捉在《现代人》沉默的这八个月中他们的纲领里有没有什么新东西。[7]228-256
《国内观察》栏目的作者们同样向读者宣称,被迫的暂停反而有助于《现代人》更加确切地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和文学的独特意义。在强调了《现代人》在文学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后,作者也没有无视其他刊物的政论事业,将它们与《现代人》进行比较,借此展开“虚无主义”和“渐进主义”问题的讨论,把它们作为两种对立的社会伦理倾向和与之相关的两种社会行为原则。此时《现代人》体现了自己正面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认为自己为社会思想提供了某种新东西,它倡导发展、激发某种新思想和新情感。结果《现代人》成为被围攻的对象。而其他杂志坚持“渐进主义”策略,努力使自己不被注意,以沉默避开热门问题,与官方学说讲和。[8]257-328应当指出,在这几年关于“沉默”“克制”“适应”的思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并不陌生。
我们知道,这时《现代人》的主要批评家是谢德林。他主持的《我们的社会生活》栏目成为杂志立场的主要表达者。思想问题,精神问题,俄国社会主流大众的惯性问题,成为谢德林的专栏的主要内容。他提炼了一个重要概念“善意”,用以描述当时俄国社会的“沉默、克制、适应”之类的现象,认为“善意”其实“就是缺乏一种意味,这种意味使得区分善与恶成为可能”[9]361。而“虚无主义”或“孩子义气”再一次(相对于40年代和50年代上半期)构成了“善意”的对立面。按照谢德林的说法,虚无主义者“应当像屠格涅夫那样轻而易举地一肩担起这个世界的罪恶”,同时,正是这些“小男孩”是当代俄国生活中所有新东西、进步的东西的倡导者[9]370、374。借鉴历史经验,谢德林推断,现在被称为“虚无主义”的、被社会绞杀的,将来某个时候可能会得到社会舆论应有的评价,并且是很高的评价。在讨论那些以自己的“善意”而著称的政论刊物时,谢德林还使用了更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词——“母鸡的善意”[10]191,用于指称那些把一切当代生活中的事件都弄成粉红色的刊物。谢德林还引入一些词汇——“宽容”“温情主义”“纵容”“傲慢”等,这是他从所批评的刊物及其同盟日常使用的语汇中得来的。那些“善意”的人们指责“小男孩”缺乏“宽容”和“不公”,恶意批评社会制度,包括文学。但是谢德林宣称,真正的文学和新闻业是不应该恭维和讳言,做“宽容”样,“绕开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问题”——这不在他们的规则里。[11]387
其实,这种具有论战性的话语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主要针对6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归来后与其兄一起主办的《时代》与《时世》杂志。
在图书出版事务委员会成员伊·冈察洛夫②的《1864年报刊阅读报告》中指出:“《现代人》去年与其他刊物的争论,也就是与《时代》《俄国言论》的争论尤其引人注目。”[12]这就是指1863年《现代人》与《时代》等杂志之间的一场公开论争。这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陷入危机,《现代人》期望的农民革命的前景破灭。陀氏此时提出自己的“根基主义”,以抵制与消除革命民主主义对公众的影响。这场争论长达一年半。
该争论的起因是由《时代》杂志1862年第9期刊登的下一年度杂志征订启事引发的。启事以激烈的口吻抨击“夸夸其谈的饶舌家,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13]538。当然是指向《现代人》的副刊《口哨》及其他刊物。时值《现代人》自1862年6月起被政府勒令停刊八个月,杜勃罗留波夫1861年11月去世,车氏1862年7月被捕入狱,《现代人》无法与《时代》论辩。但《祖国纪事》做出了回应,一位署名“列尼弗采夫”的批评家在1862年第10—11期《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攻击《时代》说:“根基是什么,你们并不清楚……”[13]538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各派对自己在1863年征订启事中的立场和宗旨作出的反应,在1863年第1期《时代》上发表了《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反击包括《现代人》在内的(还有《祖国纪事》《火星》周刊、《俄国导报》《读者文库》等)报刊的攻击,“你们攻击我们,因为我们维护根基,维护人民的本原,主张联合与和解”[13]550。该文加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矛盾。1863年初《现代人》一复刊便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栏目刊发了一篇匿名短文(当然我们知道作者是谢德林),公开抨击和嘲笑《时代》杂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就在同时,《现代人》的一个副刊《随笔》登出一封信,署名“吹口哨者”,批评《时代》编辑部别有用心,自相矛盾。《匿名短文》和《吹口哨者》的信便引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评论》两篇,即1863年第2期《时代》上的《杂志评论》两篇:《答“口哨作者”》 和《年轻的笔杆子》,直指《现代人》。论战双方剑拔弩张,誓不两立,而且嘲弄挖苦,不遗余力,甚至难免人身攻击之嫌。之前的温情脉脉与策略不复存在。
谢德林针对陀氏《时代》的一系列责难做出答复,在1863年第3期《现代人》上发文《〈时代〉的担心》。这是他详尽反驳《时代》杂志的第一篇长文,同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不少诘问。不仅如此,其他一些革命民主派刊物也纷纷著文支持《现代人》,抨击《时代》杂志。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写论辩文章《又是“年轻的笔杆子”——答〈现代人〉的文章:〈时代〉的担心》,发表在1863年第3期《时代》上。他集中力量剖析谢德林其人,不点名地评判谢德林,论辩的语言也更为尖刻。
自1863年5月起,《时代》由于斯特拉霍夫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当然作为编辑的陀氏对文章的发表也有责任)被彻底停刊。1864年陀氏重新创办《时世》,论战得以继续。
谢德林则在1864年5月的《现代人》上刊出《文学琐谈》一文,围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发表的《地下室手记》展开论辩,锋芒直指《时世》杂志及其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在数日内完成《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发表在1864年第5期《时世》杂志上作为回答。文中指责谢德林在信念上模棱两可,缺乏真诚。《现代人》则在1864年第7期上由米·安东诺维奇发表了两篇文章《是非小人的胜利》《致老雨燕》,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他言辞尖刻,几近谩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9月上旬撰写短文《必要的声明》(1864年第7期《时世》,1864年9月出版),表示坚决不与《现代人》进行这种人身攻击式的唇枪舌剑。“为回答《必要的声明》,米·安东诺维奇发表了《文学琐事》,共含五篇文章,长达四十八页。”[13]651为了结束这种混战,1864年第9期《时世》发表《为了结束。给〈现代人〉的最后一次解释》。他在文章一开始就写到:
《现代人》诸君,在我们的《时世》7月号上,我刊的同事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你们评我们杂志的两篇文章写了一篇最必要的三页长的声明。而你们却以整整四十八页的论战文字作答!在此之前就已经惊讶于你们无法控制的冗长废话,而现在我们简直陷入了困惑,因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问:如果我们写的不是三页,而是六页或八页,后果又会如何呢?或者我们冒险也写上四十八页,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做的后果,我们连设想一下都觉得恐怖。……以四十八页对付区区三页!难道诸位就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仅不知分寸,而且显得平庸无能吗?[13]652
这确实是陀氏从《年轻的笔杆子》到《必要的声明》等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章。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与无能之辈继续论战下去。至此长达一年半的争论告一段落。
实质上,双方的争论焦点,正是在对待现实社会问题上,谢德林主张的“不宽容”的、“孩子义气”的、正面意义的“虚无主义”态度,与陀氏所倡导的“善意”的、“温情主义”的(当然都是谢德林给的界定)“和解”态度之间的对立。《现代人》认为,所谓的“和解”,就意味着取消了民主主义刊物发声和存在的可能。
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现代人》,几经停刊的威胁,希望保住自己作为民主主义刊物的生存。对它来说,民主新闻和民主文学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的生存问题是迫切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现代人》上讨论《奥地利新闻业的诉讼案》系列文章中曲折地触及。该文作者阿·尼·佩平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受制于国家政治割据的奥地利的新闻业的历史和特点。尽管几个“历史国家”联合在一个政权下,但国家的每一个单独的民族部分,包括捷克共和国,都渴望建立自己的文学和新闻,表达自己的民族利益。一方面,奥地利宪政政府似乎没有实行禁止言论自由,但是,大部分捷克语报纸因积极的社会和政治活动而遭到迫害。作者细数近期较为有影响的对出版物的所有诉讼案,尤其是对捷克共和国最知名的报纸《人民通讯》的诉讼,其主编格里格利被判四个月监禁和相应罚款,尽管他在出版工作中完全是依法行事。将惩罚言论罪犯与刑事罪犯并列的荒谬的法律条文,在作者那里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作家和新闻人成了自己天才和信仰的人质。因而,“无辜的受害者”的问题不止一次在《现代人》上被提出来。如,1863年第1—2期合刊发表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最后一幕,对俄国现实的批判以及期待现实很快改变,都回响在这幕剧中。讲述《人民通讯》主编格里格利被判罪的悲伤命运的《奥地利新闻业的诉讼案》一文后,《现代人》接着刊登科瓦列夫斯基的诗歌《仁者得福》[14]626,其中也呼吁对被判罪者宽大仁爱,这被视为《现代人》对无论是在奥地利还是在俄国以法律之名行不公惩罚事件的独特回应。读者对诗歌的领会与文章的声音发生共振,极大地加强了批判效应。另外,《现代人》还发表了谢·杜罗夫的译诗《译自雨果——“除了永恒的谎言,谁是自由真理的使者”》[15]312,其中呈现了一个独特的个性在俄国的命运;而阿·普列谢耶夫的译诗《译自海涅——在森林中》歌颂一位为自由而战的年轻斗士[16]155。——这些曲笔的呼声当然都与米哈依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政治犯被捕有关。
与此同时,《现代人》像以往一样,日常主题依然是对当代俄国的批评。尽管有官方密切监视的审查,《现代人》继续引导读者关注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足,特别关注俄国社会低水平的精神和审美发展。
《现代人》上的文学家们积极批评当代生活。瓦·阿·斯列普佐夫在《现代人》发表系列文学随笔《关于奥斯塔什科夫的书信》(第一批信件是在杂志被暂停前的1862年刊登的,其余的是在杂志重启后)。在信中作者以寓言的形式书写当代社会高、低阶层代表的日常生活、习俗,官僚机构的工作日程,试图照亮国家机关的秘密。杂志编辑部赋予斯列普佐夫的随笔以重大意义,尽可能发表它们;1863年第4期刊登斯列普佐夫的《致〈现代人〉编辑部的信》,其中透露了这些《书信》发表的情况:载有最初三封信的1862年5月的《现代人》被禁了,作者们被调查,并针对他们采取了措施,《现代人》命运未卜。斯列普佐夫认为有责任为自己和那些作者辩护[17]404。
谢德林在系列短篇小说《无辜的故事》中,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农奴制俄国的悲剧。第一个故事“村庄的沉默”的主人公——过去的一个地主,在自己的庄园里因无所事事,无聊得悄悄地发了疯。第二个故事名为“为那些少不更事的人而写”,它再现了一个年轻的秘书和诗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他爱上了自己老板的女儿。尽管表面叙事看起来幼稚(恋人在圣诞晚会上相遇,柔情和嫉妒交替发作,几次争吵,几次和解),却也不失批判性的悲哀。他的主人公成为自己的真诚和缺乏经验的受害者:一种年轻、温柔的感觉与世界上公认的惯例发生碰撞。第三个故事“米莎和万尼亚”呈现了农奴日常生活的悲惨画面。故事的主人公,男孩米莎和万尼亚——一个残忍而好斗的女地主家里的农奴——试图自杀,其中一个成功了。
费·伯格的中篇小说《角落》描述了士官武备学校学生的艰难生活。尼·波缅洛夫斯基中篇小说《宗教寄宿学校的新郎》则揭示了神职人员生活中不愉快的一面。惰性的外省环境,被压抑的年轻人的力量、才能和机会,成为短篇《布奇洛夫市》中的主题。伊·布奇洛夫取自平民生活的戏剧,写一些善良的人却成了大路上猖獗的强盗的牺牲品。斯列普佐夫在中篇小说《医院的故事》中再现了县医院的氛围:玩忽职守、不负责任、对人的病痛漠不关心。而维·布列尼的诗歌《童年中有很多可怕的童话故事……》将作者小时候从保姆那里听到的吓唬他的可怕的童话故事与现代生活及其痛苦、社会不公和压迫进行了类比。
《现代人》的政论家们也像小说作家们一样,在他们的文章中谈到了俄国现实的危机。 同时,“问题式文章”体裁(正像“问题式小说”,如《怎么办?》《谁之罪?》等)使他们不仅可以批评,还可以提出建议;因此他们的文章更具建设性,而不是像艺术作品那样令人沮丧。杂志的许多政论家试图在他们的文章中对所进行的改革进行评估,主要是农民问题和司法改革。尤·茹科夫斯基③在系列文章《农民事务和社会活力》中以真实事例表明,农民改革的实施伴随着极大的混乱、无序,结果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8]
在阿·温可夫斯基的文章《司法程序的新基础》中,从公众对司法改革的态度来描述司法改革的结果和程序,指出,司法改革起初经历了“孩童般盲目信仰”及“不切实际的希望”阶段,现在社会对形势的评估变得更加清醒,因此目前对改革变得或多或少有些冷淡。[19]
《现代人》的政论家们也非常关注一般的艺术问题,特别是文学问题,并且是以批评的视角,影射社会发展问题。 米·安东诺维奇在《国内观察》栏目中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的危机》的文章[20]81-110。“危机”——这就是他对当代文学状况的评价,由于虚无主义的影响而造成了文学的分裂;此前,文学一致寻求进步。虚无主义给理解“进步”概念带来了混乱,结果一些作家被过度的激进主义吓坏了,宁愿回头。
但是,应当说,政论家们对未来艺术和整个社会逐步的发展并没有失去希望。尽管《现代人》杂志的基本态度是批评和质疑,不过光明未来的形象也出现在发表的作品中,这表明杂志的编委会相信,其主张的民主政治最终将取得成功,如果不是在这一代,那么就在下一代。在谢·杜罗夫的诗中就有类似的主题:
然而,我们将躺在坟墓里,
带着对地球未来的希望,
意识到人民中蕴含着力量
创造一切我们无法创造的。[21]297
就是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出现在了《现代人》上。小说的总体调子与《现代人》杂志的立场接近:对俄国的社会制度加以批评,寻找通往新的、公平和幸福生活的道路,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希望。此前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该杂志意识形态的定调者,因而这种接近是很自然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涅克拉索夫在小说一经允许就立即刊登在《现代人》上,要知道,这时《现代人》一方面是公众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是审查的重点对象。这表明,一方面,如果说在1863年刚恢复出版的第1—2期合刊中大谈特谈《现代人》的独特性及其对俄国新闻业的重要性,是出于编辑部推测在杂志被迫关闭期间《现代人》失去了部分读者,而意在重新吸引读者,那么作为政治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的发表就可以看作是杂志意在引起舆论注目,是其“康复”杂志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也表明,杂志公开宣示自己没有放弃原来的信仰,也不怕公开宣布这些信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在方法论上接近《现代人》的论战文章,这样,无论是杂志的小说还是杂志的文章,都是极富表现力的、饱满的新闻人的风格。因而,我们可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也是被作为这一时期《现代人》继续倡导民主政治的行动之一。这样,在该杂志沉默八个月后恢复出版,它借《怎么办?》试图积极恢复读者群,维护其在新闻出版物中的地位,并公开宣示其社会和政治信仰,可以说,这是《现代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行动。
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1862至1866年间,官方一系列对政治异见的打压,致使《现代人》杂志很快彻底关闭。然而,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又转战《祖国纪事》,继续他们的杂志事业,不久《祖国纪事》就成为《现代人》的接替者。
注释:
①1862年《现代人》被关停8个月,1863年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即被捕。两年拘留后,沙皇政府找不到任何罪证,只好采取伪证方法,强行判处他7年苦役,剥夺一切财产,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864年5月被押至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示众,处以假死刑。7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盐场服苦役,8月被转送到卡达亚矿山。两年后,又被押到亚历山大工场。7年苦役期满后,又延长其苦役期,转押到荒无人烟的亚库特和维留伊斯克,继续流放,前后达21年之久。
②即《奥勃洛摩夫》的作者冈察洛夫,曾任书报审查官员。
③尤·茹科夫斯基(Ю. Жуковский,1833—1907),俄国文学家、经济学家。俄国国家银行总领(1889—1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