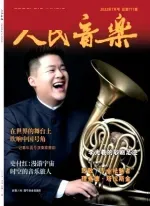“礼俗”之间的天津大乐
2023-05-30沈学英
“天津大乐”,亦称“津门大乐”,是天津古老的民间器乐乐种之一。虽然根据调查发现,天津大乐已经消亡,但是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间礼俗音乐,它见证了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向民间“礼俗”仪式用乐的历史演变过程。运用礼乐范式的研究模式,通过“大乐”名称的辨析,寻踪天津大乐的历史渊源,会发现它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和“前部大乐”融入到天津民间的鼓吹乐种;同时,从“礼制”用乐角度,溯源天津大乐的礼乐功能,会发现它延续了清代卤簿鼓吹具有的“道路依仗”功能。
一、天津大乐的研究述评
天津大乐,属鼓吹乐类,诞生在1799年(乾隆殡天)以后,距今约有二百二十年的历史。清朝年间,天津大乐不仅是天津皇会中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清代皇帝南巡迎来送往过程中“陪王伴驾”的依仗乐;天津大乐还被更多的用于婚嫁和丧葬,在当时,“红白事”请大乐吹奏,是天津人时尚和身份的象征。辛亥革命后,传统的鼓吹乐被西洋传入的铜管乐队所替代,天津大乐完全走入民间,成为地道的民俗音乐。20世纪初,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听到大乐的演奏,尤其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厢区不绝于耳。1908年,百代公司出版了天津最早的一张大乐钻针唱片。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乐受到国际音乐界的重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专程来天津录制了天后宫大乐班演奏的《津门大乐》唱片。1941—1942年,胜利唱片公司请“邹福泰全班”灌制了一套大乐唱片“大乐亚尔洛”(【雁儿落】的谐音)。这张唱片被用作天津婚礼音乐,并成为了天津民间的热门货,行销全国。总之,在天津大乐的历史发展和演变中,它曾经与天津普通百姓的生活习俗、娱乐文化,甚至是精神信仰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大乐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根据调查发现,天津大乐目前已經消亡。
关于“天津大乐”的研究,将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成果几乎没有。它通常作为条目,以传统史志的笔法简要地记录在三类文献中,有的仅寥寥数字。第一类是作为“民间器乐”条目,被记录在民间音乐、民族器乐的书籍中,如《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天津卷》《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中国民族音乐之旅》《天津民间打击乐曲初探》等;第二类是作为“风物特产”“民间花会”条目,被记录在关于天津地方历史与文化的书籍中,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话说天津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民俗》《天津城市民间文化之韵》等;第三类是作为“民间花会”条目,被简要记录在天津“皇会”的相关文献中,如《天津皇会考》《天津皇会考纪》《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以及一系列立足学术田野调查、以文化档案形式对天津皇会传承状态进行记录的课题成果。
总之,“天津大乐”被简单地理解成了天津“民俗”中的民间器乐种类之一。其实,作为天津民间礼俗音乐的天津大乐,见证了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向民间“礼俗”仪式用乐的历史演变过程。项阳认为:中国的民间音乐文化并非就是“俗文化”,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过程。他进一步指出:“宫廷和官府用乐中的大乐在当下民间用乐中同样也有,例如天津皇会大乐等。”因此,应该将天津大乐与清代宫廷大乐、卤簿鼓吹进行历史“接通”,探寻其文化根脉。也就是说,既对国家礼制仪式用乐(清代卤簿鼓吹)与民间礼俗仪式用乐(天津皇会大乐)之间的转化进行认知,又比较其相通性和差异性。
二、天津大乐的名称辨析
关于我国传统音乐的名称问题,自古以来就不统一,从无标准。天津大乐的名称中有“大乐”一词,若以中原礼乐文化背景解释“大乐”之涵义,会发现逐渐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天津大乐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和“前部大乐”融入到天津民间的鼓吹乐种。
(一)“大乐”的三种涵义
“大乐”的称呼由来已久,但是它并不只是指代一个具体音乐形态的名称。它作为音乐的词语有三种涵义。
其一,指代一种至高、至大、至广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音乐审美观念。“大乐与天地同和”这一音乐审美命题十分古老。早在《吕氏春秋·大乐》篇中,就早已经提出了“大乐”的概念:“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其中,“和”与“适”是建立在天道自然观基础上的音乐观念,最早体现了中国古代“乐和天人”的思想。这说明,“大乐”是和于道的礼乐,在礼乐制度中代表着音乐中的至高至大者。
其二,指代一种音乐形态,即以“大乐”为名的辽代宫廷音乐。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说,“大乐”一词在辽、宋时期具有三种意义。与此观点相对照,以《辽代·乐志》中与“大乐”相关的音乐史料为基本线索,可以发现辽代“大乐”承继于唐,具有隋唐“燕乐”之功用。辽代大乐的内容为《景云河清歌》,是契丹族传承中原大乐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和认同的产物,体现了契丹族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
其三,指代一种音乐机构或乐官。“大”是“太”的古字,“大乐”同“太乐”,由此“太乐”之名一指音乐机构,二指乐官。作为音乐机构,“太乐”是古代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太常寺的下属机构。作为乐官,一般称太(大)乐令。
(二)“大乐”到“天津大乐”的历史衍变
“大乐”一词不仅具有多义性和丰富性,而且在不同时期内涵有着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其与雅乐、鼓吹乐关系的漫长衍变之中,并最终完成了“大乐”到“天津大乐”的历史转化。
北宋与辽、金时期是“大乐的雅乐阶段”。在北宋,宫廷称雅乐为大乐。而在辽代,大乐不是雅乐,也不等同于鼓吹乐,而是具有隋唐“燕乐”之功用。金代大乐与北宋大乐同为雅乐之属,所不同的是,鼓吹乐进入了教坊,是大乐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前奏”。南宋与元时期,是大乐与鼓吹乐的“合流”阶段。在南宋,民间称宫廷中教坊所奏的燕乐为“大乐”,鼓吹乐成为了大乐的一部分,属于俗乐范畴。元代大乐虽然在太常、教坊中具有,但是用途各异、性质不同。太常大乐属于雅乐,而教坊大乐是“俗乐化”的大乐。由此,大乐与鼓吹乐实现了“合流”,最终成为了一种俗乐化的音乐形态。明清以来是大乐的“俗乐化”阶段。在明代,“大乐”泛指宫廷中所有的典雅庄重之乐,既指雅乐,又指俗乐,也被称为“郊庙大乐”和“丹陛大乐”。明代中后期,朱载堉“借今明古”,向往古代儒家“大乐与天地同和”“乐由天作”的观念,提出了“夫雅者,美之至也”的音乐审美理想。明晚期,徐上瀛也提出超越于雅与俗的“大雅”命题。在清代,“大乐”之名被用于宫廷音乐中的某些类别,如在祭祀、朝会、宴飨时皇帝出入用到的仪仗乐——“卤薄大乐”;承袭于明制,“凡御殿受贺及宫中行礼之用”的“丹陛大乐”以及皇帝乘舆出入时所使用的仪仗礼乐——“饶歌大乐”和“前部大乐”等。由此,大乐完全脱离雅乐,完成了俗乐化。
民国至新中国后,“大乐部分失传,部分融入民间音乐的鼓吹俗乐”。而逐渐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天津大乐,就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与前部大乐现实存在与历史的“接通”,延续了清代卤簿鼓吹所具有的“道路依仗”功能,完成了“大乐”到“天津大乐”的历史转化。
三、天津大乐是清代卤簿鼓吹之“遗绪”
清代文献对卤簿鼓吹的记载,存在乐部间同类异名、同名异类的混淆情况。但自乾隆以来,清代卤簿鼓吹乐的用乐等级和功能是固定的,可分为“二署三门五类七部”。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清代卤簿鼓吹的两个乐部——“饶歌大乐”与“前部大乐”的乐器配置与功能,并将其与天津皇会大乐的乐器配置与功能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天津大乐是清代卤簿鼓吹之“遗绪”。
(一)清代卤簿鼓吹
“卤簿”自秦、汉以来始有其名,并早在先秦古籍《周礼》中就有记载。据晋朝孙毓《东宫鼓吹议》记载:“鼓吹者,古之军声,振旅献捷之乐。后稍用之朝会焉,用之道路焉。”可见,自汉代以来,鼓吹最重要的功能有二,一是“殿庭鼓吹”,用于朝会宴享和殿庭献捷的仪式仪仗之乐;二是“卤簿鼓吹”,用于道路的车驾仪仗之乐。
最初“卤簿”本是天子或皇帝的专属物,目的是为了安全和彰显威仪。伴随着卤薄礼仪制度的发展,“卤簿”一词被理解为一种礼仪制度,是皇权与礼制的一种象征,更是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的象征与产物。发展至清代,“卤簿”是皇帝所用仪仗的专属称谓,具有明制度、示等威、保安全的功能。据清史资料记载,卤簿仪制正式建立于太宗朝天聪六年。随着卤簿仪制的日益完善,顺治三年(1646)开始有了大驾卤簿、行驾仪仗和行幸仪仗三个等级之分。至乾隆十三年(1748),清朝卤簿制度终臻成熟,定为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和骑驾卤簿四级。
在此需要厘清的史实是,清代文献中,关于宫廷礼乐的分类,相关史料及研究者的划分标准不一,并且存在“卤簿”与“仪仗”两个词语混淆使用的情况。但是,纵观清代“卤簿”与“仪仗”制度,“卤簿鼓吹”和“仪仗鼓吹”的功能和分类相同,可以共称。本文从历史沿革和清代人的表述习惯,使用“卤簿鼓吹”一词。
(二)天津皇会大乐与饶歌大乐、前部大乐的比较分析
饶歌大乐与前部大乐属于卤簿鼓吹,是以鼓和角类乐器为特色乐器而构成的“鼓角乐”宫廷乐队。从乐器配置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天津皇会大乐由清代宫廷卤簿鼓吹之“饶歌大乐”与“前部大乐”相融合而成,这是溯源天津皇会大乐所具有的礼乐功能的基础。
自乾隆以来,清代的礼乐建设最为盛大而完备此后无所增益,使用至清末。因此,本文选取乾隆时期(1736—1795)的御制修纂乐书——《钦定大清会典·乐部》和记载清代宫廷音乐的重要史料——《清史稿·乐志》,来考察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与前部大乐的乐器配置,并将其与天津皇会大乐的乐器配置进行比较分析。列表如下:
在此基础上,对天津皇会大乐与饶歌大乐、前部大乐的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其中,从乾隆朝至清末的相关文献中,关于“饶歌大乐”记载竟有四种乐器配置,具有多层指向。但实际上,饶歌大乐是构成“行幸乐”的一个乐部,使用的场合有两个:一是列于骑驾卤簿,用于皇帝“巡幸及大阅”的仪式中“驾出”;二是与饶歌鼓吹、前部大乐组成大驾卤簿乐队,用于“大祭圜求、祈谷和常雩”三大祀中。“前部大乐”又名“前部乐”或“大罕波”,一般没有专门的乐章,而是与“卤簿乐”并列,“亦曰金鼓饶歌大乐”。使用的场合有三个:一是与卤簿乐构成“金鼓饶歌大乐”,用于“御楼受俘”的法驾卤簿中;二是与饶歌鼓吹组成法驾卤簿,用于“方泽”仪式中;三是与饶歌大乐、饶歌鼓吹组成大驾卤簿乐队,用于“大祭圜求、祈谷和常雩”三大祀。总之,饶歌大乐和前部大作为清代卤簿鼓吹的两个乐部,虽然使用场合不同,但是都属于扈从皇室出行的“车马仪仗”鼓吹乐,都具有“道路依仗”的功能。
作为天津民间礼俗仪式用乐的天津大乐,首先它延续了清代卤簿所具有的“道路依仗”功能,被使用于两种场合中。它是天津皇会中“接驾”“送驾”“巡香散福”的重要环节;同时,天津既是首都的门户,又是商贾聚地、交通要冲,清代皇帝南巡迎来送往的过程中,天津大乐是“陪王伴驾”的必列依仗乐。但同时,天津大乐还衍生出两个新的功能:一是曾作为军乐随军演奏;二是被更多地应用于婚嫁及丧葬之中。
(三)天津大乐的乐器配置
天津大乐属鼓吹乐类,是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相结合的演奏乐。据《天津皇会考纪》记载,天津大乐的乐队配置是“喇叭一对、号筒一对、唢呐一对、金锣一对、钹一对、铜鼓一个、大鼓一个,共十二件”。
天津大乐的吹管乐器包括唢呐、号筒和喇叭。天津大乐中的唢呐就是清代宫廷“前部大乐”之“金口角”,只是数量由“四”缩减为“一对”。清朝年间,宫廷中所有形式的仪仗乐队都离不开唢呐,这与天津大乐所具有“道路仪仗”功能相一致。并且,天津大乐中所使用的是大唢呐,基本构造由“哨”“唚子”“杆”“碗儿”四个部分组成。天津大乐中也使用“双唢呐”,调高无须统一,只要两支唢呐音高一致就可以,吹奏的旋律也基本一样。天津大乐中的号筒是清代宫廷“前部大乐”之“大铜角”,数量上缩减了一半。号筒在吹奏时号口朝地,声音低沉浑厚,在天津大乐的演奏过程中起着烘托和营造气氛的作用。天津大乐中的喇叭就是清代宫廷“前部大乐”之“小铜角”,数量由“四”缩减为“一对”,在演奏过程中起着烘托和营造气氛的作用。
天津大乐的打击乐器包括金锣、钹、铜鼓、大鼓(扁鼓或堂鼓)和铜点。关于天津大乐中锣使用情况,相关文献中分别被记录为“金锣”“笨锣”“小锣”(俗称“点子”)、还有“乳锣”(俗称“疙瘩锣”)、“小乳锣”等。“金锣”的记载,是依据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之“金”,只是数量由“一”变为“一对”。“笨锣”,是“两面云锣”。天津大乐中使用的是两面云锣,没有固定音高,故被称为“笨锣”。笨锣被悬挂在锣架上演奏,上下各挂一面,左手扶架,右手用锣锤敲击。“小锣”,锣面较小,直径约22厘米,锣面中心稍突起,锣边无孔不系绳。演奏时,左手食指关节处提锣内缘,右手执薄木片敲击。天津大乐中所使用的钹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之“钹”,数量不变。为铜制,构造简单。钹呈圆片形,两面为一副,钹的中心鼓起,叫做“碗”或“帽”。“帽”的顶部钻有小孔,穿系绒条,叫做“钹巾”,以便双手持握。演奏时,左右手各执一面,互击而发声。钹是非固定音高樂器,音响洪亮、穿透力强,属于色彩性乐器,在天津大乐的乐曲演奏中常击板位。“锣”在天津大乐中处于从属地位。天津大乐中的铜鼓,就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之“铜鼓”,且数量一致。铜鼓又称“大乳锣”,鼓的中央有一个突起的乳状“锣脐”,边上有两个孔,穿系黄绒条,演奏时悬而击之,常出现在乐句、乐段或曲终等处。天津大乐中的大鼓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之“行鼓”,且数量都是一个。大鼓分为“坐鼓”和“行鼓”两种。“坐鼓”,也称为“堂鼓”,坐着演奏时敲击;“行鼓”,也称为“扁鼓”,行进演奏时敲击。天津大乐中的铜点是清代宫廷“饶歌大乐”之“铜点”,且数量一致。铜点的形状与铜鼓一样,但体型较小,演奏时与铜鼓应和敲击。
综上所述,作为礼乐文化衍生下的民间礼俗仪式用乐,以“礼俗”观“乐”,是理解天津大乐的重要维度。“礼俗”是中国音乐传统与之依附共生的载体。
参见高惠军、陈克整理《天后宫行会图校注》(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21页。
据《津门杂咏》记载,“不论商贾与平民,每遇婚丧百事陈。箫鼓喧阗车马盛,衣冠职事一時新。” [清]王韫徽《津门杂咏》,载潘超、丘良任、孙忠铨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天津市文化局编著《天津通志·文化艺术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据《弥足珍贵的大乐·鹤龄唱片》一文介绍,这张唱片现由王家胤收藏,一面是“雁落大乐”,另一面是“鹤龄”。被称为“雁落大乐”是因为天津大乐正统名称为“天津雁落大乐”,后来才称为“天津大乐”或“大乐”。李恩璞《弥足珍贵的大乐·鹤龄唱片》,《音响技术》2009年第2期,第74-75页。
据《天后宫行会图校注》考证,1994年,天津大乐已经失传。此外,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史静,2012年进行了天津皇会的田野调查。其中,天津大乐的传承现状为“消亡”。参见张礼敏《社会转型于文化积淀——以天津皇会为例》,天津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177-184页。
高惠军、陈克整理《天后宫行会图校注》(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项阳《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天津音乐学
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3-10页。
关于“乐种”的界定,“历史传承于某一地域(或宫廷、寺院、道观)内的,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典型的音乐形态架构,规范化的序列表演程式,并以音乐(主要是器乐)为其表现主体的各种艺术形式,均可称为乐种。”参见袁静芳《乐种学》,北京:华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萧友梅《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上),
《音乐艺术》1989年第2期,第3页。
沈学英《辽代大乐与礼乐制度探微》,《中国音乐》2020年第7期,60-63页。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第421-422页。
太常寺有太乐、鼓吹两个音乐机构。大(太)乐作为音乐机构,常有变化,西汉称大(太)乐,东汉永平三年(公元60年)改称大(太)予乐官,晋代称太乐乐府,北齐称大乐署,隋唐元沿用此名,宋代称大(太)乐局。参见褚历《西安鼓乐中的大乐》,《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第94页。
大(太)乐作为乐官,其职能也常有变化。宋代以前,太乐兼管宫廷雅乐和燕乐。宋代以后,太乐职能发生萎缩,专管雅乐,燕乐由教坊所掌。参见黎国韬《先秦至两宋官司制度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张咏春《制度视角下辽、宋、金、元的大乐》,《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6页。
褚历《西安鼓乐中的大乐》,《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第100页。
谭玉龙《“雅者,美之至也”:朱载堉与明代中后期音乐雅俗观》,《音乐研究》2016年第4期。
刘桂腾《清代乾隆朝宫廷礼乐探微》,《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3期,第54-55页。
史凯敏《清代卤簿鼓吹乐队的命名与分类辩证》,《中国音乐》2021年第1期,第193页。
鼓吹之名始于汉代。但是据史载,鼓吹之源当始于上古。如《周礼·大司马》云:“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执钺,以先凯乐献于社。”参见李石根《宫廷鼓吹与民俗鼓吹》,《音乐研究》
1999年第2期,第23页。
[唐]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卷一百八·乐部·鼓吹八),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第414-415页。
束霞平《清代皇家依仗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页。
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探微——第一届清代宫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石光伟、刘桂腾、凌瑞兰《满族音乐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3页。
温显贵《清史稿·乐志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8年版,第150页。
曾遂今《中国乐器志·气鸣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
黄致萍、唐晋渝《天津大乐述略》,载《中国民族民间器乐 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天津卷》(上),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8年版,第601页。
同,第147页。
来新夏主编《天津皇会考·天津皇会考纪·津门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9页。
刘昕蓉《天津城市民间文化之韵》(汉英对照),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5页。
[民国]望云居士、津沽闲人撰《天津皇会考纪》,张格点校,载来新夏主编《天津皇会考·天津皇会考纪·津门考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
刘勇《中国唢呐艺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天津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族 民间器乐集成·天津卷》(上),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8年版,第604页。
同,第76-77页。
“笨锣”同,第604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页。
来新夏主编《天津历史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项阳《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载项阳《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阈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2018年度天津市艺术规划项目“天津大乐的传承与变迁研究”(项目编号:B18052)阶段性成果]
沈学英 博士,天津师范大学音乐与影视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