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够爱一人
2023-05-30王优
王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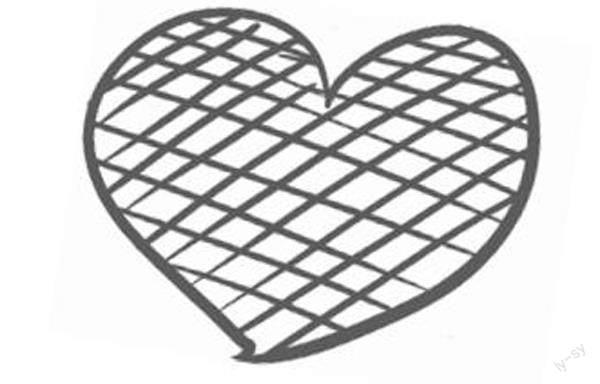
“你那个石榴,好像切开有些日子了啊,”父亲微微一笑,“怎么还没吃完?”掰开的石榴,边缘已经有些脱水泛黄。露出来的石榴籽大部分被吃掉了,剩下的颗粒,紫红中透出黑来,再无刚刚切开时玛瑙般的艳丽晶莹。我答道:“哦,不甜,正准备扔了呢。”父亲说:“怎么不甜,很好吃的呀,我刚才吃了一颗。这么好的果子,又好看又好吃,丢了多可惜——给我吧,你妈喜欢吃。”我一下子尴尬得不得了,说:“啊,放了这么久了,怎么吃!妈喜欢吃,我以后给她买新鲜的吧。”“哪里用得着买,就这半个,刚刚好,买多了也难吃完。”父亲边说边走回来,拿起那半个石榴,找了个塑料袋装好,放在他的包里,心满意足下了楼。
我问:“爸爸,你和妈结婚多少年了?”父亲愣了一下,说:“结婚?”父亲有些茫然,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力。得到证实后,父亲说:“我们1964年结的婚哇。”语气缓慢低沉,好像突然陷入一摊软泥,不知道该从何处着力。
1964年,父亲与母亲刚刚二十岁出头。他们的婚姻遵循的是父母之命,媒人就是他们各自的父亲。我的祖父与外祖父,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祖父的字写得极好,外祖父的接骨技术远近闻名。两人在镇上的小酒馆里,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闲聊中得知双方各有一儿一女,年龄相近,酒兴与谈兴的双重效力下,便定下了儿女亲家。
父亲十二三岁跟着外祖父学医:读医书,记药方,背汤头。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下有兄弟三人;母亲是家里的老幺,上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家里,父亲当家做主,母亲基本唯命是从。夫唱妇随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记忆中,他们常常抱怨、争吵,但似乎从未动过手,在勤俭持家这一点上,两人倒是高度契合。他们同心协力,没日没夜地干活,生活的小舟才得以驶出一穷二白的漩涡。对母亲的辛劳与付出,父亲心怀感激,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妈像牛一样,出了一辈子力。”
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父親忽然谈起他第一次去外祖父家的情形。那是夏天,天气特别热。饭也吃过了,和母亲面也见过了,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父亲知道自己该走了。自始至终,母亲没说一句话。父亲说:“你妈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没有底。”他觉得母亲肯定不会答应这门婚事。外祖父在村里很有威望,家里条件不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祖父家境贫寒,吃穿用度捉襟见肘。凭条件,母亲完全可以找一个好人家,怎么可能跟着一个穷小子去过苦日子呢。父亲很沮丧,他走出了堂屋,走下台阶,步子沉重,身体僵硬,浑身燥热不安。已经走到院坝旁的柴垛边了,母亲从灶房里出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么晚了,就在这里歇嘛。”父亲说:“听了你妈那句话,我的心一下子就落下来了,也不觉得热了。”
父亲一直嫌母亲话多,唠唠叨叨,又口无遮拦,不该说的也脱口而出,这也常常成为两人争吵的导火索之一。但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句话,父亲却记得如此清晰,牢牢记了半个世纪。
父亲是慢性子,从来不急不躁,雷打在脑壳上都是慢条斯理的。母亲恰恰相反,性情急躁,最是沉不住气,大事小事,总想立马解决。一个慢性子,一个急脾气,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争争吵吵中,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一晃而过。
对母亲的急性子,父亲一生都在试图改变。母亲也一样,总在催促着父亲“快点快点”。他们彼此埋汰,相互抱怨。结果母亲依然是急性子,风风火火;父亲还是老一套,慢吞吞的。
父亲宽厚,很有耐性。他对母亲的呵护包容,总是体现在细枝末节上。无论什么时候,母亲要喝水,父亲都会给她倒好水,放好糖,送到母亲手上。即使寒冬腊月,半夜三更,母亲渴了,说一句:“哎呀,嗓子好干啊,都冒烟了。”父亲也会披衣起床,洗锅掺水,点火烧水。屋外寒风呼啸,灶膛里柴火熊熊,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糖水就端到母亲面前了。那时,家里没有暖水瓶,喝水都是现喝现烧,又是土灶,需要烧柴,但父亲从不嫌麻烦,也不会抱怨。如今有了烧水壶,倒是方便多了,但母亲还是很少自己烧水,几乎都是父亲烧好,把糖或者奶粉兑好,端上桌去。
母亲喜欢喝糖水,红糖也好,白糖也罢,只要水是甜的,母亲就喜欢喝。白开水太寡淡了,她喝不下去,薄荷水、紫苏水气味太浓了,母亲也喝不下去。早年,家里太穷,买不起多少糖,父亲就买点糖精,蒸馍放一点,母亲喝的开水里放一点。后来条件渐渐好了,父亲上街仍不忘买糖,红糖也买,白糖也买,用大玻璃瓶子存起来,一年四季不缺糖。遇到卖蜂蜜的,省吃俭用的父亲也不嫌贵,总会买一些来给母亲泡水喝。
每到夏天,母亲顶着烈日,稍不注意就会中暑。父亲一看母亲不对劲,赶快找出“十滴水”,用小勺子倒几滴药水,再兑点开水,喂到母亲嘴里。待她缓过来,又拿些冲剂,煎些草药给母亲服下。这么些年来,薄荷、紫苏、竹叶青、过路黄,屋前屋后,田边地头,那些并不起眼的人间草木,赶走了入侵的风湿邪气,抚慰着父亲母亲的身心。每次喝药时,母亲端起碗,愁眉苦脸:“这个好难喝,苦死人了,我不喝。”“一口就咽下去了,咽下去就好了嘛。”父亲轻言细语,像哄小孩子一样。
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父亲总是先给母亲夹。“够了!够了!”母亲边说边夹回父亲碗里,“你没长嘴巴呀,光晓得给我夹?”有时母亲心情不好,父亲把菜夹给她,她啥话不说,夹起菜啪地扔回碗里。这时,母亲脸色不好看,父亲也黑着个脸。黑着脸的父亲吧嗒吧嗒吃饭,吃着吃着,又把好吃的往母亲碗里夹。母亲胃口不好,吃不了肥肉,只吃一点点瘦肉。父亲笑她:“嗨,没口福。你看你起了多少早,摸了多少黑,才把猪喂得这么肥。这肥肉糯糯的,好吃得很呢。来,尝一块嘛。”
母亲呢,她好像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她对父亲的好,就是拼命干活,什么重活都揽过来自己干,尽量不让父亲去干。集体劳动搞组合,“慢先生”(父亲识文断字,学过医,有手艺,只是身单力薄,动作慢,被村人戏称为“慢先生”)和他的“急娘子”(母亲性急,又有眼疾)常常落单。母亲一声不响,背上大背篼,爬最高的山,走最远的路,掰玉米,挖红薯,割麦收豆。玉米砌成墙,红薯堆成山,豆麦倒下一大片,母亲大汗淋漓,一声不吭。村里人戏谑父亲:“你这个‘慢先生’还不如你的‘急娘子’。”这么多年,收稻谷,掰包谷,挖红苕,母亲既要忙地里又要忙运输。家里堆成山的玉米、红苕、南瓜,基本上都是母亲一肩一肩背回来的。每每说起往事,父亲无限感慨:“你妈像头牛一样,这辈子,吃了好多苦。”
如今,父母已耄耋之年,依然不辍劳作,养猪养牛,种菜种粮,很少有闲暇之时。他们忙碌着,也争吵着。母亲嫌父亲动作慢了,父亲说母亲急匆匆的烦人。
回望父母的一生,生在农村,活在农村。平平淡淡的生活,琐琐碎碎的日子,我的父亲和母亲,吵吵闹闹,不紧不慢,有滋有味,相牵相念,一过就是一生。
编辑|龙轲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