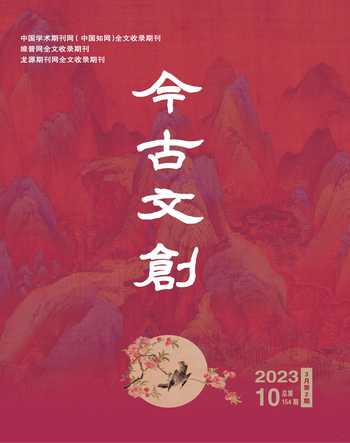江陵失陷与荆雍一体防御格局
2023-05-30王杰
【摘要】 江陵失陷是梁末影响深远的一次政治剧变,江陵政权存续时间的短促与萧绎的政治决策密不可分。对于这次事件,史家多着眼于其影响及此时间段出现的关键历史人物的决策、宗室斗争进行分析解读。萧绎在平叛过程中的消极表现和其非嫡子的身份使其政权合法性遭受质疑,而他在处理宗室问题的措施不当使得荆雍一体防御格局解体,导致了江陵失陷。
【关键词】江陵;荆雍;萧绎;宗室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5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19
对于江陵失陷的研究史学界对其原因的解析已有相应成果,李耀将江陵政权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萧绎构建政权合法性和联魏政治投机举措的失败;王光照从阶级变动出发,解析江陵失陷对江南士族群体的毁灭性影响;陈寅恪从宏观视角解读江陵失陷与南北朝政治角力的联系;还有从宗族势力的斗争解释此次事件的。本文主要以军事视角切入,旨在分析江陵失陷中荆雍一体防御格局破裂的体制性因素。通过解读武帝废除典签、废嫡立庶的政治决策对荆雍一体防御格局的影响,则这一导致新生江陵政权迅速崩塌的直接原因的来龙去脉或许能更加清晰。
一、江陵失陷前南北军事割据格局
在太清之乱爆发前,南北朝在军事层面的割据基本上呈现出对峙状态,南梁萧衍一朝前期基本上处于北魏后期内乱时期,但武帝萧衍对于北伐一直表现得比较谨慎,仅有天监、普通年间两次大规模北伐,南北朝各自控制土地范围总体变化不大。北魏后期与南梁多次交手,互有胜负,在两淮地区梁军通过北伐取得了对钟离、合肥地区的控制权,将国土防御线向北移動,这是自薛安都北投、宋失淮北以来南朝对两淮地区的再次稳定控制。总的来说,南梁在军事上的建树有限。例如,天监四年,萧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①率军兵临洛口,由于萧宏怯懦,梁军先胜后败,被击溃于洛口。所幸在名将韦睿指挥下扭转颓势,获得了钟离之战的胜利。在北魏内乱分化之际,南梁也进行过北伐尝试,尤其以陈庆之北伐战绩最为出众,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②只是由于梁军缺乏准备,援军行动迟滞而招致失利。在长江上游地区南梁因政局相对稳定,趁北魏内乱收复了益州之地。中部防线上西魏与东魏在经历数次大战后,国界线趋于稳定,基本沿黄河一线为国境线。但是双方的军事攻势并没有减缓趋向,这使得南梁在国土防御上整体面临的压力相较于萧齐时代有所减轻。东魏高欢在开始时完全占据主动,西魏宇文泰在整合关中士族和实行府兵制后艰难生存,取得了一些关键战役的胜利,但始终没能真正对东魏形成致命一击,双方在国力层面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在短时间改变。在外交层面,东魏频繁地遣使来聘,与南梁保持密切的邦交,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侯景降梁,这让北魏后期与南朝对峙的基本状态在后三国时代得以延续下来。
二、南梁荆雍一体防御的格局的形成
汉末襄宛地区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对周边地区商业起到辐射作用。荆州地区的核心城市江陵为“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取代王莽时期“五都”之一的宛城成为南朝中部地区的财税要地和国防战略支点。纵观东晋一朝,荆州一直是以西境强藩的姿态参与南朝政局的角逐。江陵之于荆州是心脏之于肢体的存在,谈江陵失陷则无法绕过荆州与周边各州关系的分析,在江陵失陷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中,荆襄一体防御的破裂无疑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围绕荆州局势,“荆扬之争”一直都是史学热点,可见荆州实力对于南朝的影响。王敦、桓玄、刘骏、刘义宣、沈攸之等都凭借荆州军力对下游建康朝局产生威胁。在刘宋一朝开始实施侨置雍州实土化方案,扶植雍州势力之前,武帝、文帝两代君主就已开始致力于分荆事务,从荆州控制的区域分割出湘、郢二州,分湘州而减其财源;立郢州分荆楚之势,扼控长江航道。雍州本地的宗族和南渡北方中下士族在社会结构上都具有相当程度上的独立性,其宗族关系下稳定的社会联系使得他们可以独立团体力量的形式依附于更大的统治集团,对一个较大范围区域乃至中央朝局产生影响。在刘裕时代的义熙土断中,刘裕对侨置郡县中暂时未能实土化的采用取缔的手段,精简机构,“于是依界土断……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④是时,“诸旧郡县以北为名者,悉除。”⑤但雍州在两次行政调整中并未被剔除,表明刘宋政权已有意扶植雍州势力。
孝武帝刘骏在雍州地方势力的助力下讨平刘劭入主建康,随后便着手雍州人士的安置工作,柳元景、沈庆之等襄阳本土低等士族凭借军功跃居上第。襄阳地区开始向中央输送人员参与核心政务,他们的政治地位提升推动了雍州本土势力的强势崛起。最后凭借实土化成功跻身边境大州,雍州作为边境以军事为主的战略要州,在文帝以前包括东晋均未以皇子出镇,直到宋文帝企图经营北伐事务才以皇子刘骏出任雍州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壬辰,抚军将军、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改为雍州刺史” ⑥,这改变了“自晋室江左以来,襄阳未有皇子重镇” ⑦的局面,其中固然有宋文帝经略关河、锐意北伐的原因,也难免包含文帝希望宗室控制军权,避免出现景平年间辅政大臣把持军政威胁皇权局面的愿景。简而言之,随着皇子出镇雍州,襄阳的地位较之于江陵已趋于平级,加之雍州地区“士流肮脏,有关辅余风,黔首扞格,但知重剑轻死。降胡惟尚贪婪,边蛮不知敬让,怀抱不可皁白,法律无所用施” ⑧的剽悍民风,使得雍州本土的军事实力得以充分释放,多次对南朝政局产生决定性影响。依靠雍州军力,刘骏、张敬儿、萧衍均得以实现其政治抱负。
除了雍州独立发挥其军事实力之外,它与荆州军镇的合作是南朝中部区域根基巩固的保障,田余庆先生在《北府兵始末》中提到,东晋一朝国防的稳固不仅只有北府兵一支军事力量做保证,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西府豫州的军事力量与北府的遥相配合才是保证江左安全的坚实屏障。⑨在南梁中部亦是如此,已经成势的雍州和被削弱后的荆州间的密切配合才是稳定南梁中部国土防线的先决条件。荆雍虽分为二州,雍州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独立于荆州,荆州一般督荆、湘、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两者之防区时有重叠,安成王萧秀曾任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梁南北秦州九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还在一定程度上负担雍州物资保障的义务。所以一般战时由一个军事长官统领二州军队总揽全局,例如太清之乱中的萧绎以荆州刺史之位都督湘州、雍州之兵勤王,共同应对来自其他区域的威胁。进,则荆州雍州作为中路军队的集结地,出宛洛逐鹿中原;退,可凭借荆雍一体化防御固守。对雍州的扶植虽在事实上给荆州树立了一个潜在的军事或政治对手,但这无疑达到了有效助推雍州军事实力壮大和有效管控错综复杂的汉沔地区社会的效果,使得北朝无法以雍州的流民汇集的复杂性特征为弱点,突破南朝中部防线威胁江陵。
基于宗王出镇制度,梁武帝萧衍使得皇室成员控制了江左各战略要地,但有宋以来宗室出镇随镇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导致“本枝虽茂而端良甚寡”的出现。武帝废除了一直以来用以加强皇权的典签制度,扭转了典签制度下诸王受制于典签无法全权掌管军政事务的局面,重新由上下级关系变为亲属关系,意图达到宗室和睦相处,“广树藩屏,崇固维城”的局面,避免发生刘宋和南齐末期“枝叶微弱,宗祜孤危”的情况,以求加强各地区对中央的拱衛。在南梁时期,中央一般采用宗室出镇荆、雍二州的方式,雍、荆、湘三州之中,雍、荆二州大多数时候为宗王镇守,少数时间由中央委派熟悉边州军事、民情的官员出任刺史以轮换宗王,例如两度出镇雍州的本地人士代表柳庆远。在梁末中西部主要大州已形成了宗王全面控制上游大州的格局,各宗王实际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太清之乱前夕,湘东王萧绎镇荆州,岳阳王萧詧镇雍州,其兄萧誉镇湘州。武帝试图通过血缘纽带保持荆雍关系的稳定和谐,取代传统的以质任方式任用边州长官,拱卫中央的布局已十分清晰。不过,完全放弃控制宗王的典签制度使得隶属于中央的军队在战时呈现强烈的私兵化倾向,沦为宗室成员政治投机的工具,这是江陵失陷中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三、江陵失陷与荆雍关系
对此,我们不妨尝试分析一下江陵政权的先天不足,即宗室关系紧张让政权合法性遭受质疑,其在荆雍一体防御的关系瓦解中起到的决定性影响,探究江陵政权速亡的原因。
宗室问题产生于梁武帝时期,萧衍在登基之初致力于政权合法性的建立,因而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周代礼制的措施,“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蒨、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 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⑩在南梁境内创设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完成了对荆雍东进集团势力的政治安置后开始政治转型,萧衍的政治重心逐渐转向文治,在政治上给予高门大族相当程度的尊重,使其家门不坠。萧衍本人在文治上的投入虽大有成效,但宽松过度的法治使得本已占据统治阶级上层的士族缺乏约束,与日益士族化的宗室成员结合,形成政治取向趋同的文人集团,给南梁宗室的凝聚力造成极大削弱。加之梁武帝早年身居雍州而无子,随后萧统出生,但好景不长,昭明太子萧统未及继统而早逝。萧纲以非嫡长子身份登太子之位,这一放弃昭明太子嫡系改立庶子为储副的决策对萧梁政权的统治核心层产生了深层次的冲击。“初,高祖未有男,养之为子。及高祖践极,便希储贰,后立昭明太子,封正德为西豊侯,邑五百户。自此怨望,恒怀不轨,睥睨宫扆,觊幸灾变。” ?以萧正德为首的的野心家对新任太子萧纲并未有发自内心的认同。加之武帝中后期佞佛,疏于政事,御下无方,这进一步助长了梁朝各政治团体的暗中争斗,各方势力由此窥伺太子之位。武帝最初尚能镇住局面,萧梁宗室还能保持暂时“兄友弟恭”的局面,但在太清之乱爆发后,这个早已埋下的不安定因素爆发成为建康、江陵失陷的主要原因,文治上对士族与宗室的放纵加上废长立庶,破坏嫡长子继承制,加之典签废除让外任宗室兵权加身,给南梁宗室内斗埋下了伏笔。
太清之乱初起,台城还未失陷前,各方勤王军队云集江左,在柳仲礼的指挥下,“既而四方云合,众号百万,联营相持,已月余日” ?,逡巡不进,坐视台城灭亡。城破之后各军在明知萧衍被侯景控制的情况下奉旨班师,侯景得以进占三吴地区。萧绎在平定太清之乱后未能有效实现南梁宗室的势力整合,太清之乱中,后来称帝的萧纪“使世子圆照帅兵三万受湘东王节度。圆照军至巴水,绎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许东下。” ?由此可见,萧绎个人对于宗室成员是极度不信任的。而且在整个救援台城过程中并未达到萧衍在密诏中的期望。在面对北部边境地区的潜在威胁时,他放在优先级最高的事务是解除身边来自宗室的肘腋之患,对邻近宗室藩王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于昭明太子的后代宗室成员,湘州萧誉与萧詧雍州方向所施加的军事压力恶化了荆雍关系,最终动摇了南梁在整个中部地区的防御基本盘。
四、结语
元帝对战败的萧誉的残忍使得萧詧主动倒向西魏,在率先袭取梁益二州后,西魏对南梁中部区域的觊觎之心陡增,其核心利益为蚕食南梁土地同时巩固业已取得的益州之地,以期在与北齐的后续较量中占得先机。此外,萧绎在外交上的双线并举使得他暂时拥有了一个能让他处理内部反对势力的窗口时间,但这是以益州失陷作为交换代价。双线交好北朝势同水火的两国的决策,使得萧绎并没能真正拥有一个长期可靠的盟友,北部两国在萧绎处理周边威胁的同时蚕食南梁国土,梁益接连失守,江北尽失。一般来说,一个政权合法性的构建有三大来源,它们分别是巨大政绩、群体认同、正当程序。萧绎借外部势力之手铲除异己,在强敌环伺局面下先行“昆弟之诛”的行为,加之其本身并非嫡长子的身份更使得他缺乏南梁宗室群体性的认同,这就招致江陵政权合法性的进一步丧失,周边其他宗室力量也看到了借助外部势力攫取政治利益的契机。因此宗室力量的阻力对萧绎的江陵政权存续是具有挑战性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倾轧使得新生的江陵政权先天的不足的缺点进一步放大,导致萧绎并没有很好的条件妥善处理荆雍关系,使得西魏有了可乘之机。荆、湘、雍、蜀四王的混战最终彻底改变了荆雍连接一体对抗北朝军事威胁的态势,“及武陵王纪称帝于成都,复请于宇文泰使袭纪,而成都又入于周” ?。北齐虽“以湘东王绎为梁相国,建梁台,总百揆,承制” ?,但并未在西魏进军江陵时做出有效的牵制军事行动。雍州萧詧的关键政治转变反而让江陵政权遭遇了西魏重兵压境的局面,终使西魏得以耀兵江汉,攻破江陵,彻底打破了南北均势局面。
注释:
①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40页。
②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62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7页。
④沈约:《宋书》卷二《武帝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页。
⑤沈约:《宋书》卷三《武帝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5页。
⑥沈约:《宋书》卷五《文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3页。
⑦沈约:《宋书》卷六《孝武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9页。
⑧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49页。
⑨田余庆:《北府兵始末》,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9页。
⑩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页。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五《临贺王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28页。
?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六《侯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45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简文帝大宝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46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元帝》。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简文帝大宝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63页。
参考文献:
[1](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2]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来琳玲.南朝流寓人士探微[D].南京师范大学,2006.
[5]高赟.北周文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
[6]李浩搏.西魏攻陷江陵前后时局变迁[J].创意城市学刊,2020,(2).
[7]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
[8]唐長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作者简介:
王杰,男,汉族,四川合江人,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