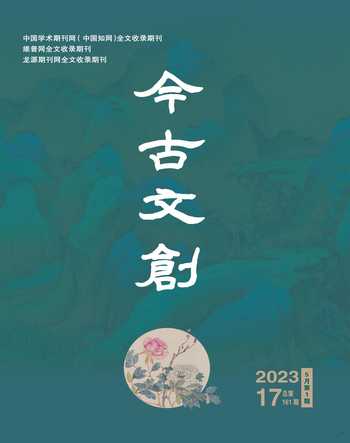蒙古族生态诗学的历史处境与多民族文化因子的结合
2023-05-30徐馨月
徐馨月
【摘要】 在“生态诗学”的概念中,“生态”和“诗学”是互相影响的“二元”,它们在尹湛纳希与满都麦文学中“生态”与“诗学”各有侧重,但各不舍弃,而这种侧重点的偏移是时代的发展导致的结果。本文从“生态诗学”的定义说起,分别对尹湛纳希、满都麦两位蒙古族作家作品中的“生态诗学”特点进行分析,在“民族本持”“民族融合”“人性异化”等话题上通过二人的两相回望以凸显“生态诗学”的意义。
【关键词】 生态诗学;蒙古族;多民族文化;尹湛纳希;满都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7-0044-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7.014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蒙古族作为56个民族中的一支,以其特殊的草原生态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并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凝就了本民族独有的精神内涵,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精神风貌。
别林斯基曾说:“文学是民族的自觉;文学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 ①文学是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民族文学使得读者得以窥见作家无意识流露出的情感与价值观念,背后是该民族自古流传下来的心理倾向,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融入子孙后代的精神基因,使蒙古族的精神文化在代代相传中不至于断流。
尹湛纳希与满都麦同为坚持用蒙语创作的蒙古族优秀作家,他们身处不同时代,以不同的身份背景,在相异的人生经历中,二者笔下文字的侧重发生了二元(“生态”与“诗学”)转换。蒙古族文学那带有浓烈地域性色彩的生态诗学,在新时代向我们展现了转变过后的面貌。
一、生态诗学的定义
文明的发展阶段是从自然生态到精神观念,再从精神观念到文化呈现,最后形成文明这样一个过程。文明在形成之后不是停滞的,它仍旧在发展中丰富其精神观念,拓宽其文化呈现,并且依旧根据自然生态的变化而变动。生态诗学属于这个阶段的文化呈现,蕴含着自然生态赐予人类的原始精神观念,而文学作为文化呈现的一种,承担起了书写精神、留存文化的责任。
在“生态诗学”的概念中,生态和诗学是被拆开的平行的一对,这二者就是上文所说的“二元”,尹湛纳希与满都麦文学中“生态”与“诗学”类似于韦恩图中交叠部分的右偏与左偏。两位作者的作品中都能够体现出这个规律。
“生态”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它于1866年被德国科学家海克尔提出。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从这个释义来看,“生态”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作为文明的始源是生态诗学的基础;社会生态于此作为历史背景。在现代,“社会生态”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社会生物学”,也就是人的社会行为,这揭示了本文的其中一个主题,即时空性变迁与人性异化的关系研究。
“诗学”通常来说有两种解释,但在本文中只取作为作诗论诗的学问,并给诗学添加一层“有关诗意的学问”的释义。于是,“诗学”在本文的概念中,分为“作诗论诗的学问”以及“有关诗意的学问”。它在文本中更详细的内涵,需要结合“蒙古族”这一修饰语来看。“蒙古族生态诗学”是“中华民族生态诗学”大类下的一个分支,其文化部分镶嵌着的是蒙汉文化间的冲撞、包容,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书写的形式之一。故而“蒙古族生态诗学”中的“诗学”主要可以分为“汉文化诗学的融合”以及“蒙古族诗意的本持(来自社会文化本质和规律)”两个部分,其中前者更关注蒙古族文学与汉族诗学的融合,后者更关注蒙古族文学本身的民族特色,这揭示了本文的第二个主题——民族根本的持存与民族融合后一些本文化消泯的冲突研究。
相对于“生态”较强的界限性、可分性以及普遍性,“诗学”的定义显然更复杂、更深广,所以只能够依照题目对其进行“量体裁衣”,使得理论概念与分析更加紧合。
二、尹湛纳希、满都麦二人作品中对“生态诗学”的“阐述”
(一)尹湛纳希的“生态诗学”
本文以尹湛纳希的《泣红亭》《一层楼》为主要研究材料,试图分析这两部作品中的“生态诗学”。
由于所处历史环境的原因,在工业化、现代化尚未发轫之前,有关自然生态的问题在中国实际上并未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尹湛纳希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逝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这段时间属于清朝晚期,在此期间,尹湛纳希的生活时代经历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等巨大的社会变革②。变革的结果是社会的动荡、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当生命安全这一最基本的人权都受到威胁时,生态的不被关心也是能够被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中不存在着“生态诗学”的表现形式,不如从“生态”“诗学”分而看之。
“生态”可分为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在尹湛纳希的作品中,社会生态是其反映的主要方向。据《一层楼》的出版说明以及《泣红亭》的前言,这两部小说俱成书于鸦片战争之后,以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有学者认为“作者从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对清末封建社会的黑暗糜烂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的现实作了尖锐大胆的揭露。” ③鸦片战争洞开了长时间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随之而来的经济入侵,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态格外恶劣。而也正是这样溷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涉及得较少情有可原。
“诗学”主要分为“汉文化诗学的融合”以及“蒙古族诗意的本持”两个部分。“汉文化诗学”也可分为“汉文化”和“诗”两层。“汉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民族认同的过程。丁新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一文中提到了民族認同的三个阶段:一,“最早的民族认同和最牢固的民族认同莫过于血缘关系”;二,“认同更多的是基于文化的,因为学院在流传中会出现模糊,难以考证,并且几乎每个民族都会面临混居杂交的境况”;三,“当有一个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统治或者治理体系,至少共同遵守一个原则时,这个族群就有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就会由民族意识产生出集体诉求,他们就由一个‘共同体进而成为一个‘行为体” ④。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相较之后而言并不太多,部落间的交流与碰撞是这段时期的主要特点。此时的中国于蒙古族而言宛若思想的熔炉,在碰撞、交流中,蒙古族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史传文学名著(如《蒙古秘史》)、民间抒情诗等在此阶段成为主流。在这段时期内,由于蒙古族人民大量下往中原,其文学中草原风情的生态感减弱,人的精神方面更为突出。元朝统治时期,忽必烈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且任用汉臣,主张推行“行汉法”,大大加深了蒙古族的“汉化”程度。“近边诸旗,渐染汉俗” ⑤“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 ⑥等史料将蒙汉的融合作出了结果性的阐释。
“诗”主要体现在作者学习汉族诗歌的严谨格律,大多数诗歌的风格委婉含蓄。以《泣红亭》第一回开篇的三首诗为例:“莫断双缘抑愁情,一番春讯一番新。三千里外客中客,十二年前身外身。”初读入口是“萧萧落叶,漏雨苍苔”,转眼间是凉气散逸、悲感纳收,“双”“一”“三千”“十二”是两主角的时空对望,是轻触即断碎的情缘;“崖上松涛催短景,水底玉魄幻龙珠。应恨彩球将人误,铁石前盟一旦无。”前两句是“神出古异”“月明华屋”,后两句尾字“误”“无”通押仄声,蕴藉充盈;“茅店野舍寒,霜叶马蹄轻。昏鸦啼古树,危楼掷球心。”全诗一句一情,“寒”“霜”“啼”“危”四字有明显的过程性、顺序性,展现了作者诗情的情绪推进,有“徐徐”意,委曲愁肠。可惜它在汉文的翻译下,诗意有所流失。但更值得说道的是,尹湛纳希在学习汉族诗歌格律时仍旧没有放弃本民族的特色,在蒙古诗歌押头韵的传统形式基础上用蒙文对汉民族诗歌进行模仿和创作。而他的所有作品,除却对外译作,也皆由蒙语写成。这体现了尹湛纳希在学习借鉴汉族文化时对蒙古族诗意的本持,其目的在于发展、丰富本民族文化而非对本民族文化的舍弃。
(二)满都麦的“生态诗学”
满都麦的小说对“生态诗学”的阐述更具有现实意义。
“生态”在这里依然分作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两个方面,与尹湛纳希不同的是,满都麦的作品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当一部分的阐述。由于作品创作时间不同,其社会背景也有所区别。从作品的主题上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分为四类:一是美德的书写,二是破坏的生发,三是此间与返回,四是失落与追寻。
“美德的书写”以《瑞兆之源》《雅玛特老人》《春天的回声》最为典型,并且它们皆创作于1981年至1983年,属于满都麦较早时期的作品。在这三篇文章中,女性形象兼具善良、淳朴、坦率等性格特征。《瑞兆之源》中的苏布达额吉为失路的马匹提供食住等待其主人的寻觅与认领,也不计较因此而消耗的钱财,坚持不要“我”(即艾德布)想要还给她的报酬;她坚守在祖国的边疆,清赶形迹可疑的人。苏布达额吉是“勤劳朴实”“仁爱慈祥”的,而这些品质“正是草原母亲的品格”“是蒙古民族的性格” ⑦。《雅玛特老人》中的雅玛特同动物一起生活在琼古勒峡谷,过着恬静、朴素且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日子,然而这样的日子却因为被强行“割尾”而丧失了原来的氛围。“聊以为生的山羊被抢走了”“牧羊狗伙伴离家出走了”,如此孤单凄凉的境地是“割尾”的结果。那些戴帽子的人对雅玛特进行身心的欺辱,突然出现的猎人又割断了山羊宝日的脖子,雅玛特不再放牧,与她“有罪”的儿子拉木日夜相伴,直到一切结束,她才恢复了原来的生活。而《春天的回声》中其其格虽然不是额吉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个女性,她依然拥有草原母亲的品质,是“青春时期的额吉”,她热烈、坦率、敢爱敢恨,展现了草原女子独有的风采。
“破坏的生发”,代表作品有《夜茫茫,他在荒原上》。《夜茫茫,他在荒原上》体现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未卜前路。
“此间与返回”是指在中华民族大背景下,返回到原始的精神与情感。在这种类型下,典型作品是“三火”(《圣火》《元火》《祭火》)系列。“三火”系列发生的场域是元草原,满都麦凭意象构建出一个圣洁的原始自然生存世界。无论是《圣火》中老人坚守对爱人誓言的等待,《元火》中的“毡包”“男女”“婴孩”,还是《祭火》中从相反方向讲到新一代人信仰的逐渐缺失。
“失落与追寻”讲到生态在现代化浪潮下被破坏,蒙古精神文明的失落,这种现象的揭露也是追寻解决方法的一个阶段。代表作品有《在那遥远的草地》《巴图的发财梦》等。
在“诗学”方面,由于满都麦与尹湛纳希写作目的的不同,他更偏向表达一种诉求,敲响了现代化浪潮下人类中心主义给人类本身带来精神伤害的警钟。故而“汉文化诗学的融合”这一方面体现得不多,更多的是一種对汉民族复杂的情感流变过程,这与满都麦的身份背景紧密相关。“蒙古族诗意的本持”是他作品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诗意”在这里可以看作一种纯粹的主观美感。
三、两相回望
在尹湛纳希的作品中,“诗学”意义大于“生态”意义,“生态”仅作为一种背景;在满都麦的作品中,“生态”意义又超过了“诗学”意义,是从“诗学”形式表现“生态”内容,并以“诗学”表达了对“生态”及其以上的诉求。而从尹湛纳希到满都麦的时代大约经历了百年,两者作品之间“生态”与“诗学”二元侧重的流动体现了蒙古族生态诗学的不同历史处境。
二者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成为影响他们二者创作侧重不同的原因,大约可概括成三个部分:一是时代(历史境遇、身份背景)不同;二是写作内容方面的不同;三是作品主题上的不同。
从时代看,二者的历史境遇以及身份背景都不尽相同。尹湛纳希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第二十八代嫡孙,生于清代土默特一个世袭四等台吉家庭(忠信府)。而忠信府则以“忠孝传世钟鸣鼎食之家,武义勤尚书画千载之户”而远近闻名。⑧他的青年时代饮酒赏花,充满文人诗性。满都麦则与之相异,他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赤峰市,是精通蒙、汉、俄、日语言的锡兀达氏恩克布仁的次子,尽管他的父亲惊才绝艳,但其家庭属于没落贵族。满都麦的青年时代在杜尔伯特草原上度过。不同的身份背景造成了不同的生活环境,尹湛纳希的生活环境更偏向于《一层楼》 《泣红亭》中所写的那种诗雅的宅院;而满都麦自幼于草原母亲的怀抱中成长,其对蒙古族精神文化的源泉——草原的情感可见一斑。
从写作内容上看,尹湛纳希更关注蒙古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问题,而满都麦更关注存亡。在尹湛纳希生活的时代,蒙古族的知识阶层中已经出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尹湛纳希以对喇嘛教的批判为起点,逐渐深化民族启蒙思想,形成了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重构民族文化精神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反对民族压迫、追求民族平等的民族关系论。⑨在这一时期,尹湛纳希将民族融合作为蒙古族被认同的手段之一。书中的人物性格以及交往方式,都明显地受到了汉化的影响,如炉梅与璞玉之间诗文传信以及炉梅的“黛玉性格”等。而满都麦的存亡问题分为被剥离与被吞噬这两个过程。《三重祈祷》中阿拜和嘛麦的形象分别象征了圣祖崇拜与佛祖崇拜两种,而嘛麦对阿拜下的死手也表现了神性的最终丧失,文化存在的某一形式被剥离了。而被吞噬则有《“摩托”曾格》,曾格的不骑马改骑摩托车,是被现代化吞噬的结果。文化、文明、精神的存在已呈颓势,保存蒙古族文化、中华文化、人类文化成为满都麦的呼唤与诉求。
从写作主题上来看,尹湛纳希主写“爱恨”,满都麦主写“人性”。尹湛纳希所写的“爱恨”并不低级,它的余味是绵长的。与汉族常见的“才子佳人”式爱情不同,尹湛纳希在这个惯常的模式中实现了解锁,在各自嫁娶的“俗常”中,体现了除爱情外的其他感情存在方式。满都麦主写的“人性”脱不开一个文化的皈依,人性就是其中的一个载体。原始的人性,过去的人性,现在的人性,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在对比中得到反思的空间。原始的人性多有神性的氤氲。而人们对神灵的崇敬,很多时候体现为繁衍。在满都麦的作品中,并无像汉族人那样对男女的情爱以及原始冲动的遮掩。如《元火》中的一段:“在西侧洞壁上刻着的是蒙古包、勒勒车、牲畜,其中有座蒙古包没有毡幪,里边有干活的赤男和哺乳男婴的裸女。” ⑩在满都麦的笔下,这一切都张弛着遥不可及的神性。过去的人性随时间逐渐形成,其主题是“情感的播撒”,是一种宽广博爱的美德,这一点从《瑞兆之源》以及《春天的回声中》两个额吉的形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现在的人性,在满都麦的作品中可以说是“现代化下的人性”,前者有《人与狼》的“人性”“狼性”之间的颠覆,后者有《巴图的发财梦》《四耳狼与猎人》等。
四、结语
生态诗学,是人智与自然融合之下产生的结果,它反映当下、对比过往,给人以享受(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也给人以彻底的警醒。
蒙古族生态诗学的历史处境,单从尹湛纳希到满都麦这二者看来,是“生态”与“诗学”这二元的变化。如果将“生态”与“诗学”比作秤上的两份托盘里的实物,那么尹湛纳希是“诗学”一方更重,满都麦则是“生态”一方更重,也就是他们在二人的作品中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没有舍弃“生态”与“诗学”中的其中一个。
文学反映着民族的精神与生活,而民族文学存在的意义也正是“记录”与“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研究蒙古族文学,将为中华民族之林中蒙古族的大树上添枝加叶,使之更为挺拔与充满活性。
注释:
①(俄)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69页。
②萨仁图娅:《世界文学巨匠尹湛纳希概论》,《满族研究》2017年第03期,第84-89页。
③尹湛纳希著,甲乙木译:《一层楼》,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④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南京大学2015年学位论文。
⑤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下·记实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⑥周铁铮,沈鸣诗等:《朝阳县志·卷二十六·种族》,1930年刻本。
⑦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⑧萨仁图娅:《世界文学巨匠尹湛纳希概论》,《满族研究》2017年第03期,第84-89页。
⑨叶立群:《论辽宁蒙古族作家创作的民族学价值——以尹湛纳希、玛拉沁夫、萨仁图娅为主要考察对象》,《满族研究》2017年第04期,第120-124页。
⑩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
参考文献:
[1]满都麦.满都麦小说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尹湛纳希.一层楼[M].甲乙木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
[3]尹湛纳希.泣红亭(20回)[M].曹都,陈定宇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4]丁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诸夏认同的产生[D].南京大学,2015.
[5]叶立群.民族熔炉与文化高地所锻造的文学巨匠——论尹湛纳希与辽西地域文化[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3).
[6]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蒙务下·记实业[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7]周铁铮,沈鸣诗等.朝阳县志·卷二十六·种族[M].刻本,1930.
[8](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9]萨仁图娅.世界文学巨匠尹湛纳希概论[J].满族研究,2017,(03):84-89.
[10] 葉立群.论辽宁蒙古族作家创作的民族学价值——以尹湛纳希、玛拉沁夫、萨仁图娅为主要考察对象[J].满族研究,2017,(04):1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