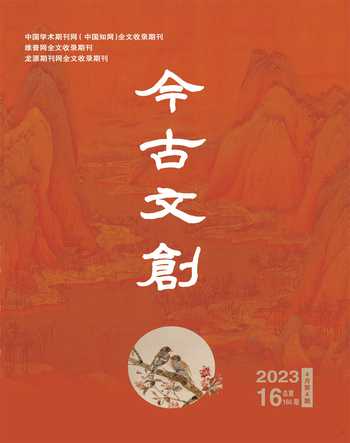再议秦始皇选嗣问题
2023-05-30赵芷若
【摘要】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赵正书》中的许多内容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存在着许多重合,但又多有不同之处。一直以来,围绕着《赵正书》的性质、成书年代等问题,学界颇有争议。本文认为,结合相关传统文献进行关联性的分析,《赵正书》关于秦始皇选嗣等问题的记载应当是不符史实的,很有可能是受到汉初“过秦”思想的影响编纂而出。
【关键词】《赵正书》;扶苏;李斯;出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5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18
《赵正书》是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所获西汉竹简中的一部分,篇名“赵正书”写于第二枚简背面,总字数约一千余字,字迹清晰,连读顺畅,是罕见保存完好的历史文献,其内容主要记载了秦始皇驾崩前和李斯等人的对话与秦二世时期秦二世等人的一些作为,以及李斯被杀前的陈述等。同传统史书的记载相比,《赵正书》的内容书写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尤其是有关秦始皇所立嗣君人选、秦始皇的去世之地、随侍大臣的姓名与职务、秦始皇的形象、李斯的狱中上书等内容更是迥然有异。一直以来,有关《赵正书》的内容及性质,学界讨论颇多。笔者不揣浅陋,就《赵正书》中所载秦始皇选嗣等问题进行浅要的讨论,敬请方家指正。
一、再议《赵正书》载秦始皇选嗣原因的合理性
以《赵正书》所载文字来看,秦二世胡亥的继位乃是秦始皇与大臣共同商议的结果,秦始皇是在清醒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立胡亥为储君,并非是《史记》所记载的为赵高、李斯等人阴谋所致,《赵正书》文曰:
丞相臣斯昧死顿首言曰:“陛下万岁之寿尚未央也。且斯非秦之产也,去故下秦,右主左亲,非有强臣者也。窃善陛下高议,陛下幸以为粪土之臣,使教万民,臣窃幸甚。臣谨奉法令,阴修甲兵,饬政教,官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臣闻不仁者有所尽其财,毋勇者有所尽其死。臣窃幸甚,至死及身不足。然而见疑如此,臣等尽当戮死,以报于天下者也。”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若仅仅从上文来看,秦始皇立胡亥为储君,让李斯等人辅佐胡亥继位是合乎情理的。纵观秦始皇一生,嗣君之位始终悬而未决,即便是长子扶苏,秦始皇也从未明显地表达过以他为继承人的想法,如今秦始皇病入膏肓,为了保证朝局平稳,防止有人趁机作乱,立一个在陪伴身边的也还算受宠的小儿子似乎并不为过,《史记·李斯列传》载:“始皇有二十余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言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余子莫从。”扶苏性格宽厚,处事政策都偏向于儒家的怀柔之道,与秦始皇凌厉肃杀的治国理念极为不同,一直为秦始皇排斥,而胡亥则在表面上极为顺从始皇。秦始皇因此故废扶苏而立胡亥,也存在着一定的道理,以往也正有学者持此意见。不过,若结合当时的政治状况,却会发现其中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据《赵正书》所载,秦始皇想要让李斯等人讨论继位之人的理由是“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哀怜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这句话是在说,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几个儿子不能够像他一样可以操纵群臣,害怕在他死之后、新君未立之前,出现群臣争权的情况,导致自己的儿子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从史料的记载上看,秦王朝内部真正能够引起“争侵主”之争的人,一共只有寥寥几位:在北部上郡地区带兵抗击匈奴的蒙恬以及其身后的蒙氏一族,以王离为代表的王氏一族,镇守岭南的任嚣、赵佗部,以及右丞相冯去疾(《赵正书》称御史去疾),左丞相李斯。是时,任嚣、赵佗虽坐拥大军,但却远在南越,即便是想“争侵主”,也是有心无力。冯去疾留守京师(若以《赵正书》所言,是随侍秦皇左右),更不可能掀起什么祸端。只有王离、蒙恬二人远在上郡,坐拥秦军主力,最有可能趁秦始皇死时作乱,那么所谓“大臣之纷争,争侵主”中的“大臣”,唯一可能指的就是王离、蒙恬二人。明白了这一点,《赵正书》中最大的矛盾就出现了。首先,就扶苏本人来看,秦始皇一生既没有立皇后,也没有明确说明立谁为太子,但是扶苏作为他的长子,而且为人宽厚,深得民心。无论从宗法的角度还是从能力的方面来看,扶苏都无疑是最合适的继承人选,而且虽然扶苏屡次进谏触怒了秦始皇,但是秦始皇本人并不见得就因此否定了以扶苏作为一个继承人的想法。秦王朝为了抵御匈奴,在北部边境布置了三十多万精锐秦军,几乎占据了秦王朝泰半的主力,并以蒙恬作为主帅,扶苏为监军。以往,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以扶苏为监军,是将其外放失宠的表现,但实际却并非如此。秦汉之际的监军一职,职司监督、巡察,拥有庞大的权力,乃是与军队主帅平起平坐的存在,有时甚至能够决定军事战略的实施。故通常而言,担任监军之职的,往往是君主的亲信和宠臣。《史记·司马穰苴传》有:“愿得君之宠臣, 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故而并不能因为扶苏的监军职位就否定了秦始皇对其的信任。同时,由于扶苏身兼皇子与监军的双重身份,能够掌握起相当大的权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九原秦军的行动,加之以扶苏、蒙恬二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可以说,这支精锐秦军主力就是扶苏继位的保障。一旦出现意外,凭借扶苏、蒙恬手中的权势,足以调动这支精锐秦军为扶蘇的称帝扫平一切障碍。事实上,在蒙恬接到命令扶苏自杀的“秦始皇遗诏”时,也的的确确产生了类似的想法。而若是秦始皇立他人为嗣,一旦扶苏心生二意,掀起波澜,秦王朝所面临的必然是倾覆之危。毕竟,九原秦军乃是最为善战的主力军队之一(这一事实,从后来王离的战绩中也可窥一二)。这种潜在的风险,作为一个经历过宫廷政变的君主,秦始皇不可能想不到。倘若秦始皇无意立扶苏为嗣君,就不可能让扶苏去“监军”这样一支主力部队,这无疑是为之后他让其他子女继位埋下隐患,也恰恰是这个行为,证明了秦始皇对扶苏还是有着相当的重视的。而在弥留之际,秦始皇既然对之后可能出现的权力斗争产生了焦虑,就更不会冒着扶苏调动大军南下政变的风险而去立胡亥为嗣,明显与初衷背道而驰。笔者猜测,秦始皇派遣扶苏“监军”上郡,极有可能是想让他在战场上磨炼性格,以便在继位后更好地掌控帝国,否则既不想立其为嗣,又赋予其如此庞大的权力,难免有矛盾之嫌。
至于《赵正书》中大臣们议立胡亥的理由“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若加以分析,更是难以成为其立储的关键。从后面胡亥能安稳回到咸阳再继位的情况看,秦始皇的死讯提前泄露的可能性很小,无论是沙丘(《史记》载秦始皇驾崩处)还是平津(《赵正书》载秦始皇病处),都是处于现在的河北邢台附近,而扶苏所在的上郡则是在今陕西一带,距离咸阳并不算远。根据距离进行推算,沙丘距离上郡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60公里左右(今邢台至榆林),上郡距离咸阳是580公里左右(今榆林-咸阳),而邢台至咸阳则是750公里左右(今邢台至咸阳),虽然看似从沙台至上郡、再至咸阳的路程相较于邢台至咸阳更远,但是无论是给扶苏送信的人,还是要赶回咸阳继位的扶苏本人,都必然是快马加鞭赶路的,而秦始皇遗驾一行不仅人员众多,也还需要伪装成无事之状,速度必然很慢,此消彼长,二者回京的时间不会相差多少。
综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赵正书》所言因为害怕扶苏来不及回到咸阳继位而秦始皇死讯传出导致旧的山东贵族发生动乱这一情况并不合理。对比立一个可能会引发一场军事动乱的小儿子,立一个拥有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的,而且这股军事力量还是绝对忠诚于秦王朝的长子无疑更利于稳定朝局。故而《赵正书》中所记载的君臣对话如果联系起当时的背景来看,显得十分不明智,不像是几个成熟的政治家所做出的决定。
二、对《赵正书》所载李斯临终之言辨析
有关李斯临终之言,《赵正书》中的记载虽然与《史记·李斯列传》存在着不少相同之处,但所表达的意思却大相径庭。《赵正书》中载李斯在狱中所上书曰:
先王之所谓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而齐民苦,此之谓夫?”斯且死,故上书曰:“可道其罪足以死乎?臣为秦相卅余岁矣,逮秦之狭而王之约。始时,秦地方不过数百里,兵不过数万人。臣谨悉意一智,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诸侯。而阴修甲兵,饬斗士,尊大臣,盈其爵禄,故终以胁韩而弱魏,又破赵而夷燕代,平齐楚,破屠其民,尽灭其国而虏其王,立秦为天子者,吾罪一矣。地非不足也,北驰胡漠,南入定巴蜀,入南海,击大越,非欲有其王,以见秦之强者,吾罪二矣。尊大臣,盈其爵禄,以固其身者,吾罪三矣。更刻画、平斗桶、正度量、一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者,吾罪四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者,吾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王之得志者,吾罪六矣。缓刑罚而薄赋敛,以见主之德众其惠,故万民戴主,至死不忘者,吾罪七矣。若斯之为人臣者,罪足以死久矣。上幸而尽其能力,以至于今。愿上察视之。秦王胡亥弗听,而遂杀斯。斯且死,故曰:“斯则死矣,见王之今从斯矣,虽然,遂出善言。臣闻之曰:‘变古乱常,不死必亡。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所谓变古而乱常者也,王见病者乎。酒肉之恶,安能食乎。破国亡家,善言之恶,安能用乎。察登高知其危矣,而不知所以自安者;前据白刃自知且死,而不知所以自生者。夫逆天道而背其鬼神,社稷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斯见其殃今至矣。
《史记·李斯列传》的记载与其文存在着较大差异,其文曰:
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
首先,就《李斯列传》的内容来看,李斯表面是在诉说自己的罪行,实际上是在以认罪突出自身的功劳,试图以此来挽回君主的宠信,故其言语恳切,多有歌颂秦王朝的文治武功。即便是在被处死前,李斯也只是用牵犬逐兔来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并无怨言。但《赵正书》则与之不同。纵观《赵正书》载李斯临死之事,虽也是以认罪突出自身功劳,但言语中却不吝贬低秦王朝的文治武功,如“破屠其民,尽灭其国而虏其王”,“夷宗族,坏其社稷”,“逆天道而背其鬼神,社稷之神零福”,“灭其先人及自夷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等等,几乎无不在表达秦王朝的残暴,这与李斯本人的身份是完全不符的。作为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臣之一,秦政衰乱至此,李斯本身就有着相当的责任,如此唾骂,岂不就是在贬低自己的功绩?更何况,此时李斯正为阶下之囚,生死未卜。从其认罪的过程来看,李斯有着很强的求生欲望,并不甘心就此被杀。然而,若其如此贬低秦君及其功绩,其绝无存活的可能,这显然不符他的初衷,故此言不可能是出自李斯之口。
三、再议出土材料的文献价值
综上所述,《赵正书》一文很有可能是西汉初年,时人根据当时所流转的只言片语,外加个人对秦王朝主观的恶意情节所编写而成。从“赵正”“秦王胡亥”等带有贬低性的称谓和对秦政的批判来看,《赵正书》的作者深受西汉初年“过秦”思潮的影响,对秦王朝的君主和政策都极为不满,甚至于对秦王朝正统合法的地位加以否定。而之所以作者要杜撰出秦始皇立胡亥为嗣一事,则极有可能是要以此突出秦始皇晚年的昏庸无能,借此贬低秦始皇的历史成就和地位,从而宣扬汉王朝的天命性。
由此观之,对于出土材料而言,首先要肯定它的文献价值和对文化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一直以来,受限于材料的缺少,对于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宗教崇拜、生活习俗、文化娱乐等内容所知甚少,许多研究都需要凭借后来人所书写的二手资料,准确度与信服力都不高。而随着《日书》、六博棋、家书家信、烽燧传书等简牍文书的出土,越来越多秦汉时期的文化面貌得以被逐渐复原,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提供了材料,揭开了一层又一层笼罩历史的迷雾,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与发展。然而,这并不代表热门就要全盘迷信出土简牍所展现给大家的全部内容,要意识到简牍材料可能存在的缺陷,要清楚文献本身可能会受到当时个人价值观、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与事实出现偏差,从而更好地对出土简牍进行识辨,发挥出土简牍在史学研究中的正作用。中国文化在古代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并且延绵不断传承至今,恰好以秦汉时期作为转折点,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文化基础,极具时代特色。以出土简牍作为参考文献来进行对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进一步探究,有利于人們更为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李锐.《赵正书》研究[J].史学集刊,2020,(3).
[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秦·西汉·东汉卷)[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
[5]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J].文物,2011,(6).
[6]孙家洲.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J].史学集刊,2022,(1).
[7]郭晴.北大汉简《赵正书》与秦之历史[J].简帛研究,2021,(1).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作者简介:
赵芷若,女,白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