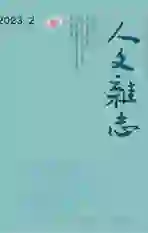什么是物
2023-05-30郑震
郑震
关键词 物 人 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2-0090-08
一、引论
唯物论者认为,物是终极的存在,是前提和基础,它至少也是为精神的自由划定范围的参考框架,因此具有不可还原的真实性。这一观念伴随着现代科学的成功而获得了强化,即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的意识活动的物质世界。它遵循自身的法则,是无可置疑的实在,尽管科学从来也没有证明这一点,它只是一个前提或存在的信仰,不过在现代世界这一信念已经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信念的鼓舞下,实在论者拓展了旧唯物论者对于物质的狭隘理解,进而将某种观念也实在化为一种类似于物的存在,如迪尔凯姆笔下的集体意识,它虽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但却丝毫也不缺少某种外在于并强加于人的物性:“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①他紧接着宣称:“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② 而集体意识正是迪尔凯姆所关切的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他丝毫也不回避将社会事实视做一种自然主义化的理解,以至于他不无赞赏地写道:“不错,孔德说过,社会现象就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自然事实。”③这大概是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加以物化的最为清晰的表述。虽然这一表述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迪尔凯姆所信仰的实证主义原则,将无法被经验的现象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但从实在论的角度看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重要的似乎并不是是否具有物理学意义上的单位,而是是否具有独立于人类个体的客观自在的属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后来的布西亚这样的作者抛弃了实在论信仰的时候,依然可以谈论一种客体的统治,①这里的客体不过是符号或文化的结构,它只是表现为强加与建构个体的历史观念。这个观念的秩序具有一种神话般的存在,②它所依托的仅仅是被支配者的信仰和盲从。尽管布西亚采取了客体的立场,但是他所谈论的客体在唯物论者的眼中依然还是一种观念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事实上,布西亚的这种思路早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哲学人类学中已经埋下了伏笔,③只不过后来的马克思放弃了这一青年时期的思路,转而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地位,从而严格区分了物质实践(现实生活过程或存在)与意识(或观念)。④ 当马克思将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视为具有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以此为主导来探究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的时候,⑤对他而言作为被决定的派生物的意识或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没有发展的。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严格坚持了一种历史唯物论,但这不是机械的关于物质或环境的唯物论,而是关于实际的历史实践的唯物论,对马克思来说观念不过是物质东西的另一种存在而已:“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⑦ 这里的物质当然不仅仅是石头或空气之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的实际的生活过程。这种过程的物质形式完全可以超越个人那直接可感的行动,这在马克思有关异化的讨论中得到了清楚的展现。“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它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⑧本来作为个人力量的生产力异化成了与个人相对立的世界。这是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不再作为个人而与个人交往,个人之间的交往必须以私有制和劳动为条件,而货币就是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源。⑨私有制和劳动通过货币这一媒介而异化为一种客观的条件,这恰恰是私有者的优势所在,而无产阶级则被剥夺了对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的控制,从而无法使生产力成为自己的力量。当财产作为货币来积累,当劳动用货币来购买和出卖,劳动者个人面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也就沦为一个抽象的个人,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
无论是马克思、迪尔凯姆还是布西亚都以不同方式拓展了物的概念和内涵。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心物关系,人与自然物的关系问题已经被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所取代,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解也已经无法再简单地采用笛卡尔之后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框架。但物化的视角却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以至于像布西亚这样摈弃了实在论和自然主义立场的文化主义者,却依然可以在一种相对主义化了的物的隐喻中谈论其所谓的历史性符号秩序。而他对于社会历史存在的理解可谓与影响了他的马克思和迪尔凯姆大相径庭,更不要说和唯物论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做这样的讨论只是想表明,究竟什么是物的问题,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明了,在西方的思想史中(除去主观唯心主义对物的还原论式的消解不谈),也已经包含着各种物的概念和隐喻。
我们姑且抛开西方的论说,进入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之中,那么同样会遭遇到十分复杂的状况。这里固然没有近现代西方的主客体二元论视角主导着问题的讨论,但物的存在却丝毫也不缺少多重的面孔。我们姑且把物质世界虚无化的佛教思想搁置不谈,仅就儒家和道家而言,物似乎就扮演着一种奇妙和多重的角色。一方面,物之作为外物始终构成对人生的一种诱惑与威胁,虽然人的生存不能没有物的支撑,人自己的身体也还是一物,但老子警告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①在老子看来,人的身体是交接外物的欲望根源,物的存在使之难以摆脱感官欲望的纠缠,所以对于人来说便如同大患一样值得重视。也正是因此,庄子才主张:“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②至贵之人是不为外物所役使的(“不可以物”),也就是不流于贪婪和物欲,才能实现一种自由的生存。所以“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③ 你若有心牵挂于物,从而失去了自然的心境,也就无法自由地因应物的往来,从而陷入到物欲的陷阱之中,为物所伤。无独有偶,与道家思想颇有分歧的儒家也同样警惕于外物的诱惑,后者可以说是儒道两家思想所共同具有的问题意识。对儒家而言,物的诱惑是与对私利和私欲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道家主张过分的物欲遮蔽了人的自然天性,儒家则认为不恰当的物欲追求只会使人泯灭了人性中的善良禀赋。所以孟子主张:“养心莫善于寡欲。”④物欲多的人是很少能保存其善良本性的,因此寡欲才是养心、存心的重要方式。这一思路在宋明理学中得到了系统地发挥。所以朱熹说:“心不可有一物。喜怒哀乐固欲得其正,然过后须平了。且如人有喜心,若以此应物,便是不得其正。”⑤心中若有物,就是已经有了先入之见或者说私心,被私心所左右自然也就无法做到公正平实,因此“盖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荡,终不消释。设使此心如太虚然,则应接万务,各止其所,而我无所与,则便视而见,听而闻,食而真知其味矣”。⑥留滞心中不去的就是私,私则遮蔽了本真与恰当的知晓。不过朱熹并不反对人具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好、乐、忧、惧四者,人之所不能无也,但要所好所乐皆中理。合当喜,不得不喜;合当怒,不得不怒”。⑦ 所以這情感若要合理恰当,就不能执着于其中。执着就是滞留于外物而遮蔽了本真的心性。虽然在朱熹看来为物所动也未必为恶,但如果一味滞留于外物的干扰,为各种情绪所左右,就难免会执于一偏。毕竟“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⑧ 如果不考虑立场上的分歧,朱熹的这些言论与前引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这也足以看出,儒家和道家在对待人的私欲和外物的诱惑方面有着高度相似的见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于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而言,物仅仅是一个外在于人的危险角色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儒家和道家对待物的看法还有其截然不同的另一面。这就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思想家们并没有那种西方式的主客二元观,他们即便指出了物质利益对人的困扰构成了人之存在的一大威胁,但这也还是在一种天人合一的语境中来发问的,毕竟物的存在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在人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错失了与物相处的合理之道。所以庄子才会宣称:“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袺然而往,袺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①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的状态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人在本体论上就是与万物通而为一的存在,只有当人沉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与大道相违背的时候,才仿佛陷入到与事物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也就是所谓的患得患失,这种有为的状态被道家视为是一种病理的症候,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道家有关外物的困扰隐含着一种对于人的异化与物化的思考,这一点也获得了儒家思想的回应:“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③天理本来没有将人与物对立起来,是人毫无节制的物欲制造了人与外物之间的超出了自然交往的状态,以至于人反被物化,被物所奴役,这和人肆意的攫取和摆弄事物又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它们不过是同一病理现象的不同说法罢了。所以对儒家来说,天人合一才是自然本真的状态。也正是因此,张载才会宣称:“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鉴物便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己皆见,犹持镜在此,但可见彼,于己莫能见也,以镜居中则尽照。只为天理常在,身与物均见,则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脱去己身则自明。然身与心常相随,无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则举措须要是。”④这里既道出了己身为一物所带来的困扰,又指出了脱去己身而心无一物的无私做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平物我,合内外”,以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做到“君子随物而止”,⑤这个止的立足点就是理,也就是时措之宜,“接物处以时中为是”。⑥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张载才会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⑦这样的物本不该从外部强加于人,人的意志也不是物存在的前提条件,它们都是天地所生,仿佛广义上的一家人(与是同辈、朋友的意思)。这就打破了现代西方二元论的物我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人与物相处的截然不同方案。这一思路的世界观与程颐“理一分殊”的主张可谓相得益彰,而后者则深刻影响了朱熹,“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⑧ 而这个理对朱熹来说就是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这就将整个世界道德化了,后者显然延续了先秦儒学的人文主义视野。因此,物在这里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自然之物,而是从属于一个道德本体论的宇宙观。这也是对儒家而言,为什么万物能够与我一体的关键所在。朱熹主张“性即是理”,⑨而万物皆有其性,这与西方思想中将观念物化的做法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意味,它们都极大地拓展了物的概念内涵。
到此我们已经看到,中西方有关物的思想可谓复杂多样,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总体而言,西方人偏重主客二元的视野,总免不了在精神和物质、主体和客体之间辩出个孰是孰非,虽然由此而产生出众多精致深奥的分析,但却始终难以摆脱各种还原论或平行论的困扰;而中国人则强调物我一体的思路,拒绝那种非此即彼的抽象对立,从而对于将人安顿于这个他本来就归属于的宇宙之中有着一种似乎更加妥帖与深邃的关照,但由于对过分抽象的拒绝,也难免失却了分析的精致与清晰。所以究竟什么是物,似乎还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而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来拷问物之为物呢?
二、从关系出发
对于历史上物之概念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关于什么是物这样一个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解释。现代科学所主张的自然物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它并不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常常只是一个背景或前提,更不要说受到挑战了。事实上物质的绝对客观性也仅仅是一种未经证明的信仰,①自然科学也只是将其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来加以实践,而自然科学关于物质的认识也还经历着认识论范式的历史性变革(如从牛顿—笛卡尔模型向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模型的革命性转换),②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米德的观点,即科学对自然世界的理性主义态度和一致性假设来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而非科学的发现与经验的论证。③ 如果说科学的经验论证也还不能确保真理的绝对客观性,那么实践的信仰就更加难以排除各种局限与偏见,这似乎意味着任何有关物的概念在认识论上都有意或无意地难逃一种人类学的色彩,这大概就是人之存在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即便我们相信存在着客观的物,但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给出一个有关物的绝对定义,更不要说社会科学中那些围绕非自然物质意义上的社会物的争论。
不过这样的状况反倒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如果说有关物的概念难免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建构,那么如何建构也许是帮助我们理解物之为物的重要线索所在。如果建构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创造或意义的赋予,这就进入了观念论的范畴,它认为物之为物的关键在于作为建构者的主体生产,似乎建构仅仅是一种精神性的单方面的支配,这就为各种相对主义乃至不可知论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它的倡导者们并不总是期待这样的结果。然而对于观念论者而言,客观的物即便存在也仅仅是一个无法触及的消极设定(如康德的自在之物、胡塞尔的意识之外的物),这确实助长着一种主观主义的神化。反之唯物论者强调物的优先性和支配性,从而反对一种主观主义的视角,因此物之为物只能是一种物质存在在主观上的反映,否则就会陷入到一种认识论的自相矛盾之中,因为很难想象不能排除主观性困扰的认识是如何能够毫无矛盾地主张物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除非这种困扰是来自物的特殊性的支配,它不像普遍性那样具有绝对真理的价值。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绝对的客观主义也仅仅是一种神化,唯物论者对主观性因素的否定也仅仅是一种信仰的产物;就如同唯心论者对主观性的信仰也全然缺乏一种智识上的充分支撑。可见,当我们停留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中来理解物的建构时,将陷入到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冲突之中,对立的双方各执一词,但却无法彻底否定对方的存在,这使得我们有必要超越二元论的困境。
如果在物的概念建构中既有主观的方面也有客观的方面,那么最容易想到的方案就是主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但这一看似顺理成章的做法其实隐含着巨大的隐患,即一种反噬效用。毕竟二元论最大的問题就在于不能消除二元的逻辑出发点,无法消除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分裂对立的状态,而还原论不过是一种变样的二元论,它依然还是在主观与客观的逻辑中推演。所以主客观的相互作用虽然在表面上提供了一种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解释,但它只是将主观与客观在形式上统一,这一统一并不能够消除对立与分裂的实质。这迫使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不再假定物的概念来自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提法本身就在逻辑上陷入到一种矛盾之中,仿佛在这个关系之前就已经在本体论上存在着所谓的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认识的活动存在,我们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先天的自在存在,之后才使某种关系得以可能,而正是在某种关系之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它们的存在。谈论先于认识的认识者和先于认识的认识对象是同样荒谬的。这种关系导向的本体论思路是颠覆一切实在论的根本策略,因为实在论以及各种实在论的隐喻(非实在论的二元论)正是基于某种实在或非实在的主客观的假设才得以可能,而关系导向恰恰指出了主客观的分野并不具有优先的存在意义,相反它们完全是建构性的衍生物,是对关系的人为割裂或抽象,只有以分析的方式来肢解关系,我们才可能谈论这些看似非关系性的现象,并假定它们彼此对立或彼此遭遇,但这无疑是一种反事实的假设。因此,关于物的建构与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建构是同时一体的,正是在物的概念得以产生的地方,我们才可能以反事实的方式抽象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后者正是这个概念所隐含的抽象可能性。
当我们将物的概念解释为一种关系现象的时候,且这一关系现象隐含着抽象为主客观对立的可能性时,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有关物的主观和客观立场的错觉不过是一种反事实的事实化。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可以在物的概念中既发现主观的方面,也发现客观的方面,但这并不是关于某个事实的发现,而仅仅是一种信念。如果说关于什么是物的问题只能以关系的方式来说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思想历史的语境中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物。因为关系不过是相对性的另一种称呼,这里并不存在客观给定的实在,而是不同关系之间的斗争。当然这也不是要主张一种怀疑论的立场,后者的自相矛盾已经足以表明其不可行性。怀疑论仅仅是对相对性或关系性的一种误读,关系性的实质正在于肯定一种有限的合理化,即相对的合理化。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即便是儒家思想的道德化的宇宙观,也是蕴含着某种合理性,它至少在方法论上避免了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抽象实在论,从而实践了一种拒绝将人与物彼此对立的关系主义的世界观。只不过儒家思想的关系主义世界观经过了一种道德人文主义的中介,包含着将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化的错觉。但由于并不存在一种主观主义式的还原(儒家思想中并不存在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概念,物的道德化也被视为是一种对物的自然主义解释),因此我们不能将儒家思想等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西方还原论式的争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也还是特定关系的建构,只不过它并不是一种关系主义的自觉,相反其关系性的社会历史性特点正在于将关系所蕴含的某种抽象可能性放大成一种片面的合理性,从而掩盖了它的对立面。因此,两种概念策略的差异正是不同社会历史关系之间的差异,关系的建构既可能推动一种关系主义的自觉,也可能推动一种对关系的遗忘。
三、物的建构与物的意义
说清物之概念是关系的建构,并不等于回答了“什么是物”这个问题。但其必要性在于避免了重新陷入到二元论的争论之中,从而意识到我们所谈论的物始终蕴含着某种关系策略,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但认识论上的澄清终究不能回答存在论上的意义,它只是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关于物的概念总免不了一种建构,试图获知绝对客观的物之为物仅仅是一种信仰的抽象,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通过自我反思来减少分析上所谓的主观性干扰,这表明关系主义并不排除分析作为一种反事实的手段的意义。
不过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其实已经隐含了存在论的预设,毕竟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并不能够独立于存在论的判断,认识活动作为一种关系现象不仅仅传递了知识的特性,同时也暗示了存在的意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物之为物是一种关系建构,那正是因为在此种关系中,物始终在实践着或发挥作用,始终在与人打交道,因此这种实践也是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实践(恒星发光与看见光是同一个过程)。所以虽然关于物的概念总有其认识论上的局限性,但物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实践问题,物不可能独立于它的实践,也就是不可能独立于它与人或它物的关系而成其为物,所以概念的关系性不仅包含着歪曲的可能性,同时也完全可能传递着对象本身的信息。所以绝对孤立的东西,完全不实践或不发挥作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存在本身就是关系。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明确物首要的或最为基本的性质就是关系性的存在,存在即在实践或发挥作用,因为绝对的孤立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就是实践,就是关系,是碰撞、挤压、依附、交换、抚摸、吹拂、流淌、漂浮、上升、下降、照亮、遮蔽、吞噬、分解、聚合、静止等等。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将物拟人化,然后给它们冠上诸如行动者之类的名称,并主张它们也在发挥着某种能动性,仿佛它们和人类行动者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体共同投入、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世界关系的网络。这样的讨论看似具有吸引力,但却把问题过度地简单化了。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关系的任何一方都只是对关系的抽象建构,它们并不能够独立于关系而存在,所以不存在所谓的先行存在的各方组建起关系网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关系中发现了一切,而不是一切形成了关系。这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判断,因为任何相反的观点都无法摆脱逻辑上的悖谬。其次,这样的关系并非那种行动者之间可以建立又可以取消的关系,仿佛关系是由行动者所主导和操纵的,恰恰相反,存在的关系是行动者之为行动者的关系,也是物之为物的关系。这并不是说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说那些可以任意缔结或取消的事件仅仅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现象,它们并不改变存在论上的事实,就像我们可以和某个人绝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存在中不再有他人的在场,因为我们的存在是关系性的,这不取决于具体时空中的个别的关系事件。所以谈论某种关系的建立或取消只是对于解释特定的生存事件具有意义,而不能构成一种基础的理论维度。
事实上将物混同于人类行动者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体行动者不啻为对物的取消,从而使物丧失了分析的价值,并且引发了不必要的过度想象。让我们采用分析的口吻来检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会发现在具体时空中的人与物的关系从来就不仅仅是人与物的关系。虽然人类行动者作为总体与自然之物的遭遇的确意味着一种人与物的关系,但这仅仅是就总体而言才具有意义,相反如果我们将视野聚焦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而不是自然环境),人与物的关系就将同时并且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甚至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归根究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主导),当然你也可以发现蕴含着人之中介的物与物的关系。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和倾向、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已经蕴含着他人的在场,这不仅是说那些人造物蕴含着他人的劳动,那些公共设施体现了某种制度的安排,同时也是说,即便是和纯粹的自然物打交道的方式也已經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他人的存在。物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不可能无视物的存在,人首先就是作为一个物存在于物的环境中,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将物一概地视为一个从属的角色。但物的作用中已经中介了人的作用,就如同人的作用中已经中介了物的作用。这种中介作用完全可能包含众多的层次和不同的方式,以至于简单地区分人与物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想象或至少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人不可能绕开物而与他人遭遇,没有物一切都将无法想象,但绝对的非人也只不过是一种信仰,这就是存在的关系性。
所以说在社会世界中严格地区分人与物或人与非人是没有意义的,但将物提升至与人类行动者同样的行动者地位也同样是引人误解的。关系性存在的理论意义在于,将传统意义上的实体(人类行动者、物等)重新理解为关系的建构,从而打破实体之间非此即彼的界限,但这不是将它们混为一谈,反而是通过关系性的差异来重新定位这些只有在关系中才可能被分析出来的要素(人类行动者及其能动性、物及其作用力等)。在同一关系中的分析已经暗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不同的要素,而这种差异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存在论上的,它同时也是伦理学上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以行动者来界定人类个体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了他所具有的广义的感知能力,也就是诸如意识、前意识乃至无意识这样的分析特征,并且主张人类行动者在社会历史关系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分析性角色(这当然不是说物是完全消极的,这里只是相对而言),当我们用能动性这个分析性的名称来描绘人类的作用力的时候就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合乎逻辑地要求人类为生态环境的变化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并且相信改变这一切的关键首要在于人而不是所谓的物,因为物不是行动者,不具有人类甚至生命体意义上的能动性,把物的不可或缺也不可低估的作用力夸大成一种能动作用是毫无意义的,这只会为一种推卸责任的唯物主义打开方便之门。
为了阐明对于物的理解,我们将物与人类行动者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生命体进行了比较。从一种关系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非此即彼地谈论人与物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完全无视一切理论上严格区分的实在都仅仅是对关系的抽象分析和人为的设定,是为了寻找一些分析性的概念所付出的代价。因为关系的事实表明,在我们所谈论的物中已经有人的在场,就如同在我们所谈论的人中也已经不可避免地预设了物的存在,存在的关系性就是这样消解了抽象思维的偏见,只不过它并不是幼稚地向原始存在的复归,而是一种扬弃。
四、结语
物与人一样都是关系性的存在,也正是因此孤立的物或人都仅仅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所以物和人名称的不同只是表明它们具有不尽相同的分析特征,而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完全异质的两种存在者。人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人,就如同物不可能遭遇完全的非物。物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作用力不具有感知的能动性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用机械论和决定论来解释这种物的独特存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即便是自然科学也已经不再痴迷于牛顿—笛卡尔的认识论范式)。但这种作用恰恰可能以某种人的能动性为中介,甚至蕴含着多重的人与物的中介。所以非能动性与能动性的划分仅仅是一种分析的抽象,是一种概念化的策略,因为如果没有非能动性的内在支撑,能动性将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反之如果排除能动性的存在,非能动性也不可能在世界的复杂性中到场。社会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由不同的分析因素彼此关联和交织起来的多样性关系的总体,这种关系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永恒且封闭的实在,而是时空性的存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