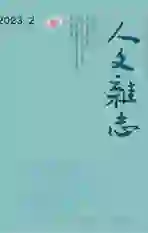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2023-05-30左东岭
左东岭
关键词 玉山雅集 雅正观念 愉悦快适 复杂组合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3)02-0059-08
关于顾瑛的玉山雅集,目前学界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对其雅集性质的认知,也有各自的立场与视角,或以为是元末吴中文人战乱中的“狂欢”,①或以为其体现了当时文人们“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②或以为是雅集文人“风雅浪漫和忧国忧民的双重风貌”之体现,③ 或以为是元末文人所“追求一种文人化、理想化、艺术化的生活”,④或以为是“文士独立品格之形成”的表征⑤ 等等。诸家看法均建立在自己所掌握的文献基础之上,皆有一定依据,提供了对那一历史时段的认知角度。笔者亦曾撰文将玉山雅集之作用与意义概括为四个方面:体现了蒙元特殊历史环境中江南文人的文化优越感,为当时文人提供了躲避祸乱与休憩身心的理想场所,为诗人施展才智、争奇斗胜寻求到有效的方式,成为文人们追求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⑥但经过阅读大量新的文献与长期的学术思考,如今认识到有必要对玉山雅集的内涵与意义进行新的论述。因为以前的研究均有过于笼统的弊端,未能将此一现象的具体历史演进过程及其诗学性质真实完整地予以揭示。
一、玉山文人的诗学理论与顾瑛的台阁情结
就玉山雅集的特点而言,其一是参与人员数量庞大,成分复杂,时间漫长,形式多样;其二是雅集内涵丰富,具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综合文艺色彩。由此,很难概括出单一的属性与意义。但如果认真思考,还是能够进一步揭示其核心要點。一是尽管雅集成员复杂,依然可以将其概括为在任官员与隐逸文人两种类型;二是尽管雅集内容涉及相关文艺领域,但其核心元素乃是诗与酒二项。就其所存留下的《草堂雅集》与《玉山名胜集》二书来看,显然能够充分证实以上的判断。由此,便可将论述的中心聚焦于玉山佳处的景点“可诗斋”的构造特点与活动内容。“可诗斋”的匾额为杜本篆颜,顾瑛本人题为“正声存大雅,古调有遗音”。可谓一出手即有台阁气象。然后是王#所作的《可诗斋记》,其核心在于凸显《诗三百》的雅正传统,所谓:“仲瑛博学好古,尤潜心于诗,故予推本《三百篇》之大要,相与商榷之。”①再次乃是郑元的铭文,其中以大半篇幅强调了诗教的内涵与作用,最后归之于对顾瑛的期待:
顾仲瑛甫,学诗嗜古。邃初是几,本之乐祖。庚歌伊始,如或闻之。猗那商颂,如或陈之。六义迭奏,以?以韶。积力斯久,匪一夕朝。名室可诗,意犹未尽。不有圣师,道何由循。嗟甫于诗,既殚源委。我歌以乐之,几甫其复始。②
后来的几位文人的题诗,也大致围绕此“不有圣师,道何由循”的主旨而落笔,所谓“好稽周大雅,宜咏楚臣骚”(陆仁)、“要共论风雅,先须识性情”(秦约)、“千古再庚周大雅,五言能继汉遗音”(聂镛),其中卢熊的主题最为鲜明:“大雅谁复继,斯人良独工。时时志忧国,仿佛杜陵翁。”③ 从匾额、题词、记文、铭文到诗歌题咏,无不从雅正传统、诗教精神、楚骚主旨、杜甫情怀来论述诗学内涵,与元代台阁诗论如出一辙。从作者身份看,杜本不仅是诗学名家,还是曾经被朝廷征召为翰林学士的台阁名臣,王#则是浙东台阁大臣黄蟳的得意弟子,他们宣扬诗歌的风雅精神应该不是门面话。而顾瑛与其朋友虽为平民文士,也都争相附和杜、王之论,可以说基本体现了“可诗斋”的构造本意。进一步说,也体现了顾瑛玉山雅集的部分诗学追求。这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证实。
一是顾瑛具有明显的崇尚台阁诗人倾向。杜本不仅为“可诗斋”题额,而且还题了“钓月轩”“种玉亭”与“听雪斋”。西域人达兼善(又名泰不华)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也题了“渔庄”“金粟影”“雪巢”“拜石坛”与“寒翠所”,他是和大书法家赵孟瞓作品数量并列第一的台阁大臣。此外,还有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题“玉山草堂”,翰林修撰周伯琦题“春草池”,太常寺典籍鲜于伯机题“秋华亭”,太平路总管回纥人马九霄题“玉山佳处”与“柳塘春”,以及官至翰林待制的赵孟瞓之子赵雍题“读书舍”与“浣花馆”等等,都是具有相当身份的台阁文人的手笔。当然,这些题字不全是专门为玉山草堂所作,比如其中的“芝云堂”“小蓬莱”“碧梧翠竹堂”“君子亭”和“澹香亭”等五处为赵孟瞓题字,但他于1322年即已离世,当时顾瑛年仅12岁,完全不可能请其题字,这些字显然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的。这些匾额题字中,也有少数是由隐逸文人书写的,比如仅在元末任吴县教谕的卢熊所题之“白云楼”,任武康县丞的沈明远所题之“绿波亭”与“春晖楼”,赵孟瞓之孙、赵雍之子赵奕所题之“湖光山色楼”等。至于题写“书画舫”的吴孟思,虽然不明其履历,但也有材料证明其为善书法的隐逸文人。④ 这些题写玉山匾额的文人,无论是身居台阁的官宦还是隐身草野的平民,其共同特点是均为当时的书法名家,因而尽管顾瑛所选题写者多为台阁文人,尤其是曾经任职翰林的台阁重臣,但并不能由此说明他有攀附权贵而寻求干谒的世俗之念。他所需要的是他们书法技艺的高超与台阁重臣的名气,由此为玉山雅集带来高雅的品位与巨大的影响。顾瑛本人曾说:“余家玉山中,亭馆凡二十有四,其匾题书卷皆名公巨卿高人韵士口咏手书以赠予者,故宝爱甚于古玩好。”①这些当时人所题匾额当然不可能都超过古人的水平,之所以“宝爱甚于古玩好”,唯一解释的理由乃是其“名公巨卿高人韵士”的名头与品位。
二是顾瑛竭力邀约台阁文人参与玉山雅集,以增加其高雅华贵气氛。早在元至正八年(1358)玉山大规模进行雅集宴会之前,顾瑛便邀请过多位台阁文人至玉山雅集与题字。如后至元五年(1339)柯九思至顾瑛家题名“拜石”而将其命名为拜石坛,同年三月达兼善至其家,为其作古篆“拜石”与隶书“寒翠”。至正二年(1342)饶介至玉山草堂,顾瑛为其补作《玉山草堂图》。至正三年(1343)顾瑛曾与萨都剌相聚宴饮。至正三年柯九思与姚文奂应邀至顾瑛家相聚,柯九思为于立所藏画题诗。② 至正八年到十二年,是玉山雅集的繁盛期,此时也有昂吉、锁住、张翥、姚文奂、陈旅等高官文士频繁被邀至玉山参与雅集。比如张翥曾于至正十年秋在玉山佳处与钓月轩参与过规模较大的雅集,并形成较大影响。张翥《题钓月轩》诗序曰:“至正十年苍龙庚寅岁秋仲十九日,予以代祀归,至姑苏,顾君仲瑛延于玉山。时郑君明德、李君廷璧、于君彦成、郯君九成、华君伯翔、草堂主人方外友本元、元璞二公,酒半,欢甚,即席以玉山亭馆分题者九人。予以过宾,属为小引。”③ 其实此次张翥至玉山并非顺便路过,而是被顾瑛特意邀请。《寄题玉山诗》序曰:“至正九年秋,海道粮舶毕达京师,皇上嘉天妃之灵,封香命祀。中书以翥值省舍人彰实,遍礼祠所。卒事于漳,还次泉南,卧病度岁。乃仲春至杭,遂以驿符送上官,而往卜山于武康,克襄先藏。秋过吴门,顾君仲瑛留宴。”④张翥代表朝廷祭祀保佑海道运粮船舶安全抵达京师之“天妃”,在一年多内奔波于福建、浙江一带,最后到了武康。元代武康属湖州管辖,距昆山尚有400里左右,因而他到吴门赴宴并不轻松。既然张翥来自数百里之外,又系朝廷重臣,当然要给足面子,故而请他做了此次雅集的主持,即所谓“予以过宾,属为小引”。张翥也颇为尽力,不仅为“钓月轩”题了诗,而且在回去途中又赋五古五十韵寄给顾瑛。意犹未尽,在回程舟中又撰百韵长篇五古《寄题玉山诗》。并一再表示:“他日或游昆墅,当为一亭一馆赋之也。”⑤ “他日过玉山,当为一亭一馆赋之。”⑥ 可见张翥参与玉山雅集并非空走过场应付了事,而是态度认真且感受真切,尤其是他那两首五十韵与百韵的长篇五古诗作,具有足够的分量拉高雅集的品位。
三是顾瑛特意请黄蟳与李祁两位台阁重臣为其《玉山名胜集》作序,以提升雅集的地位与声誉。黄蟳序曰:
中吴多游宴之胜,而顾君仲瑛之玉山佳处其一也。顾氏自辟疆以来,好治园池。而仲瑛又以能诗好礼乐,与四方贤士大夫游。其凉台燠馆,华轩美榭,卉木秀而云日幽,皆足以发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诗,间见层出。而凡气序之推迁,品汇之回薄,阴晴晦明之变幻叵测,悉牢笼摹状于赓唱迭和之顷。虽复体制不同,风格异致,然皆如文缯贝锦,各出机杼,无不纯丽莹缛,酷令人爱。……今仲瑛以世族贵介,雅有器局,不屑仕进,而力之所及,独喜与贤士大夫尽其欢。⑦
此序署时为至正十年,可知是黄蟳对玉山雅集早期特点的理解,而且是以士大夫的眼光看待此事的,其要在于从台阁创作的角度予以评价,这无论是其一再强调顾瑛的“与四方之贤士大夫游”“独喜与贤士大夫尽其欢”,还是“能诗好礼乐”的趣味,以及内容之“悉牢笼摹状于赓唱迭和之顷”,以及体貌之“文缯贝锦”,均以雅正华美之台阁特征予以概括。李祁之序表达了大致相近的意思:“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洽。随兴所至,罗樽俎,陈砚席,列坐而赋,分题布韵,无问宾主。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于是裒而第之,以为集,题之曰《草堂名胜》。凡当时之名卿贤士所为记、序、赞、引等篇,皆以类附焉。间尝取而读之,高者跌宕夷旷,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丽洒脱,远去流俗。琅琅炳炳,无不可爱。”①尽管他在聚会成员内加入了“仙翁释子”,但依然以“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当时之名卿贤士”为主体,这显然并不符合雅集之实情,而是进行了自我的选择,放大了台阁文人的比重。尤其是他对雅集诗文体貌的概括,“高者跌宕夷旷,上追古人。下者亦不失清丽洒脱,远去流俗。”完全符合元代中期以来台阁体平和清丽的雅正品味。顾瑛虽然对杨维桢、郑元等人在诗学水平上甚为倾倒,但并没把作序的权力交给他们,而是恭恭敬敬地请来两位台阁重臣担此重任。这除了用顾瑛具有浓厚的台阁情结解释外,实在找不出其他的理由。
二、玉山雅集的诗歌创作实践与诗学旨趣
如果认真阅读玉山雅集的前期诗文,显然难以得出其诗学主张与诗歌创作完全符合儒家传统诗教之雅正观念。参与雅集的成员相当驳杂,有为友情交流而至者,有为解闷求乐而至者,有为休憩身心而至者,有为口福之乐而至者,甚至不排除部分文人是为生计而至玉山谋食者,所以很难用统一集中的诗学观念将其概括出来。如果勉强求其大致倾向,则追求诗酒之乐或可庶几近之,具体讲也就是追求身心兼而有之的人生快乐。最能代表此种状况的莫过于至正八年二月的一次雅集。对此,杨维桢《雅集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右《玉山雅集图》一卷,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所作也。……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视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俊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用也。②
此处所言“雅”之内涵,不在于道德教训之情理之正,更不在于忧国忧民之儒者情怀,甚至不在于装束齐整之行为检束,而是体现为环境之优雅,侍伎之妍整,童隶之驯雅,饮酒之有序,音乐之流畅,文思之敏捷,尤其在于在场参与者行为之自由无拘,仪态之娴雅从容。这些内容都通過张渥的妙笔与杨维桢的妙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他们的理想是能够与古人的兰亭、西园雅集相媲美。而且“兰亭过于清则隘,西园过于华则靡”,只有眼下的玉山雅集,“清而不隘”“华而不靡”,真正达到了雅之品格。当日的分体赋诗的主题乃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中之诗句“爱汝玉山草堂静”,其中主人顾瑛诗曰:“兰风荡丛薄,高宇日色静。林回泛春声,帘疏散清影。褰裳石萝古,濯英水花冷。于焉奉华觞,聊以娱昼永。”③ 格调清丽,境界幽静,可称雅致。其他如“采英延清酌,揽芳结幽佩。”(于立)“众客各雅兴,辞适忘尔汝。”(姚文奂)“乐哉君子游,于以寄高躅。”(郯韶)“清文引佳酌,玄览穷幽讨。”(顾晋)④亦大致围绕清丽雅致体貌而组织落笔。从至正十二年之前玉山雅集分韵赋诗所选择的诗句,即可大致看出其主题、格调以及雅集气氛所发生的变化。如至正九年六月碧梧翠竹堂宴集以杜甫《夜宴左氏庄》之“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分韵赋诗,⑤同年十二月听雪斋以顾瑛自作之“夜色飞花合,春声度竹深”分韵赋诗,⑥至正十年正月碧梧翠竹堂以杜甫《秋兴八首》之“碧梧栖老凤凰枝”分韵赋诗,①同年五月玉山佳处以苏轼《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之“炯如流水涵青苹”分韵赋诗,② 同年七月湖光山色楼以李白《夜宿山寺》之“危楼高百尺”分韵赋诗,③同年七月芝云堂以杜甫《夜宴左氏庄》之“风林纤月落”分韵赋诗,④ 并以李商隐《无题》之“蓝田日暖玉生烟”分韵赋诗,⑤同年七月秋华亭以杜甫《月》之“天上秋期近”分韵赋诗,⑥同年七月金粟影以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之“荷净纳凉时”分韵赋诗,⑦ 同年七月渔庄以许浑《寄桐江隐者》之“解钓鲈鱼有几人”分韵赋诗,⑧ 同年七月钓月轩以陈师道《秦少章见过》之“旧雨不来新雨来”分韵赋诗,⑨同年七月芝云堂以李商隐《无题》“蓝田日暖玉生烟”分韵赋诗,⑩ 同年七月玉山草堂以杜甫《崔氏东山草堂》之“高秋爽气相新鲜”分韵赋诗,⑾同年七月玉山佳处以杜甫《寄裴施州》之“冰壶玉衡悬清秋”分韵赋诗,⑿同年七月玉山佳处以冯道《赠窦十》之“丹桂五枝芳”分韵赋诗,⒀同年十二月芝云堂以曹操《短歌行》之“对酒当歌”分韵赋诗,瑏瑤同年十二月湖光山色楼以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之“冻合玉楼寒起粟”分韵赋诗,⒁同年十二月听雪斋以杜甫《和裴迪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之“东阁观梅动诗兴”分韵赋诗,⒃至正十一年八月以苏轼《阳关曲·中秋月》之“银汉无声转玉盘”分韵赋诗,⒄同年九月玉山佳处以杜甫《羌村》之“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分韵赋诗,⒅同年十月玉山佳处以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分韵赋诗,⒆至正十二年八月春晖楼以杜甫《八月十五日夜月二首》之“攀桂仰天高”分韵赋诗,⒇同年九月碧梧翠竹堂以韩膞《风雨中诵潘邠老诗》之“满城风雨近重阳”分韵赋诗,(21)同年九月可诗斋以曹操《短歌行》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分韵赋诗,(22)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书画舫以杜甫《小寒食舟中作》之“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分韵赋诗(23)等等。
在这二十余次的分韵赋诗中,作为主人的顾瑛当然是所拈诗句的主要人物,因而尽管参与雅集倡和的是性情才气各不相同的文人,但因为有了所选诗句的限制,也就大致规定了诗歌写作的范围、内涵、情绪、格调与审美指向。其中内容基本可分为对于景物时令的歌咏与雅集快适的抒写。比如“碧梧栖老凤凰枝”实际是咏碧梧翠竹堂的,“危楼高百尺”是咏湖光山色楼的,“攀桂仰天高”是咏中秋的,“东阁观梅动诗兴”是咏冬日赏梅的,“解钓鲈鱼有几人”是抒发隐逸之情的,“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是倾诉思念之感的。尤可注意的是,曹操的短歌行被征引三次,分别以“对酒当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分韵赋诗,包含了及时行乐、重视友情与饮酒助兴的主题。古人曾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难并,但玉山雅集则是要力求四美兼有,所以会成为后世文人们所艳羡的风流韵事。因此,说追求身心快适乃是玉山雅集前期的主调应该是确然无疑的。其实,当时秦约在《嘉宴序》中就感叹:“生熙洽之世,际文明之运,出无跋涉之劳,居有宴赏之适。从容言笑,樽俎%浃,日得以享亲戚故旧者,不其幸乎!”(24)这也难怪,在至正十二年之前,尽管元末的战乱已经在江淮等地兴起,但尚未波及富庶繁荣的吴中地区,因而雅集的主调自然以游乐观赏、饮酒赋诗为内容。从至正十二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诗句选择看,文人们已经明显感受到祸乱的临近,可以视为一种内涵深远的隐喻。不过,玉山雅集的文人们似乎尚未意识到形势的严重程度,而认为战乱仅为一时的烽火,朝廷可以旋即扑灭。萧元泰对此的判断在此次分韵赋诗的序文里有明确的表述:
夫天下之理,未有往而不复。器之久不用者朽,人之久不用者怠。国家至隆极治,几及百年,当圣明之世,而不靖于四方,或者天将以武德训定#乱,大启有元无疆之休。诸君有文有才,将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且有日。予老矣,尚拭目以观太平之盛,何暇作愁叹语耶?(25)
顾瑛听后赞曰“子诚知言哉”,然后便又“饮酒乐甚”。顾瑛及其宾客们之所以有如此通达的胸怀,并非是真的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是与元代江南文人的旁观者心态密切相关。在他们眼中,朝政大事乃是达官权贵所当虑,既然自己走不进权力中心,又何必去越俎代庖操闲心。同年到玉山参与雅集的熊梦祥也淡定地说:“于斯时也,弛张系乎理不系乎时,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其所谓得失安危,又何足滞碍于衷耶?”①战乱的烟尘丝毫不影响他们“张筵设席,女乐杂沓,纵酒尽欢”,而且更将此种超然情怀视之为难得的人生境界,所谓“于是时能以诗酒为乐,傲睨物表者几希?能不以汲汲戚戚于世故者,又几希?”②
顾瑛本人当然也是如此。如至正十二年秋,秦约《可诗斋分韵诗序》中记载:“酒既半,玉山作而言曰:古人驱驰戎马间,览物兴怀,未尝不讬之赋咏。每读周公东征、宣王、六月、江汉、常武,下迨两汉六朝、唐人诸诗,其有及于乱离者,切有感焉。昔则见于诗,今则身践之。风景艰棘,山川险阻,诸君相会良不易得,可无赋咏以纪兴乎?遂以《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分韵。”③顾瑛历览古今“及于乱离”之诗而“切有感焉”,但他既没有叹政权之兴替,亦未能哀民生之多艰,而是深感“诸君相会良不易得,可无赋咏以纪兴乎?”然后顺手拈来“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以分韵赋诗。顾瑛得“宾”字,其诗曰:“玉山茅斋溪水滨,日日舟楫往来频。行厨酒熟更留客,当槛花开殊可人。看云听雨意自适,分韵赋诗情亦真。风尘贐洞罕相见,尽醉忘形谁主宾。”④ 他所感兴趣的,依然是看云听雨,分韵赋诗,尽管身处“风尘贐洞”之际,但遗憾的是不能与诗酒朋友频繁聚会,如今相逢不易,自然要“尽醉忘形谁主宾”了。周砥是当时参与者之一,他专门为此次雅集作后序曰:
夫诗发乎性情,止乎礼义,非矫情而饰伪也。嗟夫,王者迹熄而诗亡,然后春秋作矣。寥寥数千载下,晋有陶处士焉。盖靖节于优游恬澹之中,有道存焉,所谓得其性情之正者矣。玉山顾君仲瑛,慕靖节之为人,居处好修,行义好洁,故其诗清绝冲澹,得之靖节者为多。仲瑛开可诗斋,延四方之文人才士与讲论其中,故海内之士慕仲瑛而来者,日相继不绝也。⑤
此段文字跳跃性很大。发乎情止乎礼义而不矫情饰伪,乃是《诗大序》所提出的儒家诗教观念,但其落脚点则是“以一人之事而系一国之本”,以达成主文而谲谏的兴观群怨效果。而周砥完全忽视汉儒论诗传统,直接过渡到晋之陶渊明,其特点是“优游恬澹之中,有道存焉”,并将其归之为“得其性情之正”。此种坚持自我操守而超然于世外的“性情之正”显然与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诗教精神并无直接关联。随后又过渡到顾瑛“慕靖节之为人”,其“居处好修,行义好洁”大致可以理解为重操守而“得性情之正”,所以其诗才能“清绝冲澹”。最后顾瑛又“延四方之文人才士与讲论其中”,所讲当然也是性情之正与清绝冲淡的诗学之道了。周砥的诗学观念与论述策略极具代表性,他将讲究重教化、正人伦的正统儒家诗学传统巧妙地转换为坚持自我操守而超然物外的隱逸闲适境界,可谓一种创造性的诠释。这当然与宋代以来理学的内转直接相关,更与元代江南文人的隐逸追求密不可分,同时也要考虑到元末文人于乱世中以求自保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助推作用。不过,周砥的概括依然是不准确的,因为顾瑛做不到陶潜“心远地自偏”的冲澹,玉山雅集也难以用闲逸的格调来评价。在玉山雅集中,豪华的馆场,幽雅的景致,丰盛的宴席,醉人的伎乐,乃至古玩书画的陈设,均具有鲜明的世俗享乐色彩,是陶渊明所不敢奢望也不屑享有的。如果较为全面归纳玉山雅集的诗学观念内涵,则可作如是表述:它是以元代中期以来的台阁诗学理论作为倡导的口号,追求一种潇洒随意的创作形态,以达到愉悦自我的人生目的,并通过文人雅集的诗酒唱和而构成令人向往的诗情画意境界。对于顾瑛本人来说,还渴望通过雅集创作活动造成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将众人的诗文作品搜集刊刻以达名垂不朽的目的。
三、玉山文人群体构成之基础:共同的隐逸倾向
以顾瑛为首的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此种理论主张与写作实践相脱节的情形可谓显而易见,那么以黄蟳、李祁、张翥、柯九思、李孝光等出身翰林的台阁文人也绝不会视而不见,否则他们又何以会乐于参与雅集并为之撰写大量序言?这就牵涉到元代文坛的特殊状况,也就是多数台阁文人都兼具隐逸之情结,落实在创作与理论上则体现为台阁与山林并举兼备的特征。尤其是到了朝政混乱、战火四起的元末,台阁文人向往山林而隐逸的倾向日益浓厚,则玉山雅集的生活情调与创作模式便拥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台阁重臣虞集曾说:“诗之为教,存乎性情,苟无得于斯,则其道谓之几绝可也。皇元近时作者迭起,庶几风雅之遗,无愧《骚》、《选》。然而朝廷之制作,或不尽传于民间;山林之高风,或不俯谐于流俗。以咏歌为乐者,固尝病其不备见也。”①如果说强调诗教须重性情尚未溢出儒家正统传统的话,则“朝廷之制作”与“山林之高风”并举便拥有了元人的色彩,至于最后不经意间“以咏歌为乐”的目的,则显然是玉山雅集的话头了。正因为具有如此的看法,所以虞集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如下题“钓鱼轩”的诗作:“方池积雨收,新水三四尺。风定文已消,云行影无迹。渊鱼既深潜,水华晚还出。幽人无所为,持竿坐磐石。”②景物清新,心静如水,把竿而坐,尘虑全消,可谓典型的山林之作。柯九思也挥笔而作:“谈笑从吾乐,相过罢送迎。凭栏看月出,倚钓待云生。蝶化人间梦,鸥寻海上盟。轩居总适意,何物更关情。”③他径直将玉山之行归为快乐适意,而且将此处的随意轻松与官场的迎来送往相对举。此处的“轩居”并非官场的轩车之意,而是那个月好水清的“钓月轩”,有了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值得牵挂于心!张翥的《题钓月轩》为长篇七言歌行,其后段曰:“一丝涵影秋??,待到月来花上时。苦吟忘却鱼与我,但觉两袖风飔飔。引竿钓破广寒碧,乘兴搅碎青玻璃。不知今夕草堂醉,笑领洛神张水嬉。明朝回首越来道,独看月华多所思。”④忘我吟诗而飘飘欲仙,于是驰骋想象超越时空,引竿广寒而嬉戏洛神。直到次日依然难以释怀,余味可思。其实,这些台阁文人并非在玉山宴会上受到现场气氛感染才有了此种享乐倾向,他们即使在平时也大多有此种及时行乐的末世情怀,张翥曾有《独酌谣》曰:“有酒且一醉,有歌且一谣。杯尽当再沽,瑟罢须重调。生足意自适,身荣心苦焦。所以黎首人,多在于渔樵。一谣仍一酌,且复永今朝。明朝未可料,况乃百岁遥。所愿花长开,美酒长满瓢。静疑太古调,散觉神理超。近识南郭叟,得酒时见招。尽醉时高卧,谁能慕松乔。”⑤上述这些例证充分说明,参与玉山雅集的台阁文人在观赏美景、饮酒赋诗、享受生活、及时行乐诸方面,与主人顾瑛及其隐逸文人具有相同的爱好与情趣,所以能够和睦相处,其乐融融。顾瑛友人释克新曾有《题暮云集后》一文论及顾瑛与张翥的交情:
吴郡仲瑛与余、翰林承旨张先生为布衣交。先生居京师,相悬数千里,而诗筒书札无虚月。仲瑛以为近有一旦致身权要者,视父兄为路人,况朋友乎?自以结客三十年,惟于先生得之。于是,辑其倡和篇什、往来尺牍为一编,曰《暮云集》,既又求书先生与予酢酬者附集尾。予辱交先生二十余载,故知之深,举莫予若也。先生平昔与人子言必曰孝,与人臣言必曰忠,与人朋友言必曰信而不可忘。今观其所以拳拳于仲瑛者,尤足以见其素所操存矣。抑夫仲瑛志高尚而泥涂轩冕;先生又薄功名,视富贵如浮云。盖所谓志同道合者,其愈久益敬而不忘也宜矣!《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公以之。予故书其诗而又系其说,以为势利交者之劝云。①
该题跋文所提供的信息量十分丰富:一是根据释克新的说法,顾瑛与张翥乃是布衣时即为朋友,绝非雅集时临时邀请。二是张翥具有忠孝诚信的君子品格,由其富贵而不轻视旧交可见其一贯操守。三是二人交往的基础是都拥有泥涂轩冕、轻视功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情操,可谓志同而道合。四是正是由于有此深厚友谊,顾瑛将自己与张翥往来唱和的诗作、尺牍合编为《暮云集》,并将释克新的作品也附于集后。最后将所有这些情况概括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以赞美之。《暮云集》今已不可得见,但由此令人感受到元代文坛状况的立体样貌与诗学观念的丰富内涵。并可进一步推测,如今存留的纸面文献十分有限,难以充分体现玉山雅集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多重面相。但即使如此,已足以说明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关系的繁富复杂与观念的叠合交错。
四、结论
就玉山雅集的发起动机与前期情况看,昆山文人顾瑛依托其丰厚殷实的家庭财力,交游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自身的文艺才华与浓厚诗学情趣,纠合了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方面的优秀作家,构建起玉山草堂这一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文艺沙龙。其根本目的在于愉悦自我、展现文采、联络感情与扩展影响。他在理论上借助了儒家传统诗论的宗旨与口号,获得了当时诸多重要台阁文人的支持与参与,而实际上是以吴中隐逸文人为主体的诗酒雅集,以满足其追求娱乐快适的人生目的。而参与雅集的台阁文人虽有儒家的观念与经世的责任,但同时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与江南生活的影响,也拥有浓厚的隐逸情结与求乐倾向,他们参与玉山雅集也满足了自我的人生理想与文学诉求。可以说,玉山雅集是在元末的特殊环境中,由顾瑛所倡导的一种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所共同组成的文艺盛会,体现了江南文人诗酒风雅的风气与快乐自适的审美旨趣。自至正十六年到至正二十年,是玉山雅集的转型期,其主要特征是由追求娱乐快适转向感伤低沉再到绝望空幻,其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感伤凄凉的體貌,展现了元末诗学观念由轻快闲适向深沉哀婉的过渡,对此则须另外撰文论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翼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