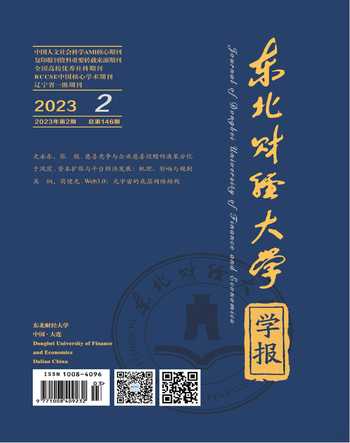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的特征、问题及路径
2023-05-30唐志勇陈林
唐志勇 陈林
〔摘要〕乡村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治理要与时俱进,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使其成为更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区域和市场主体。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伴随城市群、都市圈的高速发展,经济高度发达但社会治理滞后而出现系列治理困境。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城乡融合的实践,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管理民主”向“有效治理”的治理理念转变,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也应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为抓手,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重构以有效治理为目标导向的特色治理体制机制。
〔关键词〕超级村庄;有效治理;治理理念;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F3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3)02-0073-12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自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以来,就一直是以村民自治占据着主要的制度政策设计、社会实践和学术话语体系。从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刘义强[1]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源阶段(1980—1987年)、试行阶段(1987—1998年)、全面推行阶段(1998—2003年)和深化发展阶段(2003年之后)。徐勇和赵德健[2]概括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然村为基础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三个自我”;第二阶段是以建制村为基础规范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四个民主”;第三阶段是建制村以下内生外动的村民自治,主要贡献是有效实现形式。然而,村民自治作为党和政府着力推进的基层民主治理实践,其有效运行的难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魏晨和李华胤[3]指出,早期村民自治的实践因为强调农民的自主管理,所以将保障民主权利放在更为核心的位置,这导致了对有效治理重视不够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已成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4];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5]。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乡村治理的“管理民主”总要求被“有效治理”所替代。同时吸收浙江省等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经验,把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方式作为指导全国乡村建设的重要原则,意味着乡村治理的目标和手段已经发生转向。自此之后,“有效治理”“三治融合”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乡村振兴的重要学术增长点,并产出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江必新[6]指出,在向基层治理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要认识政治、自治、法治、德治的各自优势和局限,注重“四治融合”。以自治为根本,以政治为支撑,以德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加强“四治”建设,构建“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邓大才[7]指出,自治、法治、德治是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三者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三者不是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基础。三种治理方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可以实现善治,而两两组合、三者组合也可以实现善治,在实践中不应该追求“最优善治”“最佳善治”,而应该追求“最适宜的善治”。胡洪彬[8]指出,浙江省桐乡地区乡镇社会治理的“三治合一”模式在理论上契合了人民主权理论、善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也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对现有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突破性创新,但“三治合一”在实践运作中亦存在一定的现实缺憾,如相关理论研究滞后、民众思想认识有待提升及制度建设相对短缺等。张文显等[9]指出,“三治”是方式方法,自治、法治、德治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自治以其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而凝聚共识,实施共治;法治以其规则刚性、程序透明、准则有效而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德治以其核心价值、公序良俗、社会贤达而弘扬正气、引领风尚。自治、法治、德治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三者融合必将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王春光[10]指出,乡村治理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乡村现代化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匹配关系。新农村建设目标之一是“民主管理”,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目标则改为“有效治理”。
以上梳理了乡村治理理念转变后学者进行的理论探索,背后是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出现困局后,理论界对治理理念的反思和扬弃。因此,笔者尝试从具体案例分析,指出都市型超级村庄这种城市化了的农村在传统体制错配[11]的情况下,所面临的治理困局和转型方向,为其他都市型超级村庄的有效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笔者认为,在国家整体政策取向和治理理念发生转变之时,都市型超级村庄在面临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动、治理基础变迁时,城市化了的农村社区治理转型需要从村庄内部的治理机制和现有的治理体制入手,进行治理创新,基层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也应该根据村庄的发展变化情况,实现基层组织体系重组和再造,从而激活其内部活力,实现村庄内部的有效治理。
二、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
都市型超级村庄因地理位置邻近城市,在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从普通村庄原来简单的组织框架之内,生长出结构复杂、不断增生功能的庞大行政和经济组织。改革开放以后,部分体量较大的农村在城市文明冲击和内部现代化要素的雙重因素加持之下,主动吸纳外部企业,积极发展非农经济模式,发展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经济结构的超级村庄。折晓叶和陈婴婴[12]把都市型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一是已经形成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农经济结构,工业产值和非农产值已占村庄全部产值的绝大多数,成为产值过亿乃至十几亿元的发达村庄。二是已经形成稳定的可用于村政和公益事业的收入,具有初步“准政府”村政结构和职能,如经济、村政和福利保障的结构和职能。三是村社区的经济组织开始采用现代集团公司的模式,迅速向村庄以外扩展,经济的触角已经伸向城市和海外,甚至以参股的方式渗透到大中型国营企业。四是村社区的人口成倍增长,聚集大量外来人员,有些村社区的外来劳动力已超过本村人口数倍乃至十几倍。五是社区内部已形成以职业多元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分层结构。六是村政设施和公益事业发展迅速,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在形成。
本文选择广州市D村作为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转型的案例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案例的适用性。D村的经济社会状况符合都市型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在改造前具有“拟城聚落”形态,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中介社区。二是案例的完整性。2018年8月,D村党支部被列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由市区镇三级书记挂点,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队驻村开展3年综合整治,目前已经历了完整的政策执行周期,治理效果明显,具备较好的分析价值。三是案例的典型性。D村是广州市最大的城中村,反映了广州市同类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转型的共同特征,其转型路径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本文的资料搜集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访谈数据。对区、镇、村三个层面的党政干部和村民进行了座谈、访谈。二是调查数据。针对广州市D村的基本状况进行了不同的问卷调查,分别发放问卷4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3 900份。三是其他数据。笔者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课题组一同参与实地调研,收集了相关政策文件、讲话、通知、总结、简报、会议纪要等材料,共计30余万字。
三、案例呈现与治理困境
(一)D村简况
D村地处广州市BY区东部、TH镇南端,总面积为25平方千米,户籍人口为9 816人,外来人员超过16.50万人,与一些小型的县城人口相当。外来人员众多,远超出本村户籍人口,是典型的城乡结合型社区。被民众称为广州市最大的城中村,2018年被广州市列为重点整治改造对象。现有1个经济联社、23个经济社。村“两委”干部共6人,交叉任职率100%,村党委下设23个经济社党支部,共有党员294名,2018年村社两级集体经济收入为3 874.70万元。
⒈ 党支部与党建情况
D村党支部成员共6人,村委会成员共5人,村委会主任一职空缺。此外,除了村支书没有兼任村委会主任,其余成员同时兼任党支部和村委会职务。党支部成员的年龄平均值为54.83岁,中位数为57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党支部委员贺某46岁,最大的是党支部副书记谢某60岁。《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周岁,女性为55周岁。可见,D村的党支部成员年龄偏大,接近法定退休年龄,受教育程度偏低,缺少中青年党支部干部。
在D村党支部建设上,2014—2018年连续5年都有村民申请入党,2014—2017年每年都有2名村民申请入党,2018年则有5名村民申请入党,村民入党积极性呈上升趋势。D村党支部严格把控党员的准入门槛,除2016年之外,每年只发展一名党员。2018年的正式党员总数为294人,占全村村民的3.17%。尽管村民申请入党人数呈增长之势,但该村的党建工作总体上不容乐观。D村党组织的领导力、把控力不强,各类组织涣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
⒉ 村民自治情况
2018年D村因“村集体物业出租”和“村级超过10万元支付”等重大事项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共有71名村民代表出席,占全村人数的0.76%,其中,党员有16人,占村民代表的22.53%;群众有55人,占村民代表的77.46%。至于全村的村民大会,D村近5年来,分别在2014年和2017年因换届选举召开了两次,全村村民参加。
⒊ 产业情况
D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大部分耕地被征用或被建设(包括大量没有报建的“两违”建设)而演变成城乡结合型社区。目前,D村的支柱产业是电商和交通运输业,基本没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主要发展制衣业,第三产业则充分利用广州市近郊的区位优势,发展物流、电商等服务业。
D村现有企业为3 173家,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尤其突出,其中,第二产业为481家,占比15.16%,主要为服装加工业、生活用品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为2 692家,占比84.84%,是D村的主要经济支柱,主要为零售批发业和道路运输业。尽管村域内经济活动活跃发达,但D村的村社两级收入均不高。据村干部介绍,2017、2018年村社两级收入均约为4 000万元,其中,村级收入为800万元,社级收入不足4 000万元。
⒋ 土地资源情况
D村土地面积为18.58平方千米,其中,现有耕地面积为0.17平方千米,占全村面积的0.91%;现有宅基地面积为1.71平方千米,占全村面积的9.20%;现有建设用地面积为6.40平方千米,占全村面积的34.45%。D村社区服务机构办公场所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休闲场地、医疗场所用地、社区养老服务用地和托幼服务用地,面积分别为5 700平方米、22 290平方米、9 258平方米和22 390平方米,其中,休闲场地面积最小,占全村面积的0.02%,其次是社区养老服务用地,占全村面积的0.04%。而医疗场所用地和托幼服务用地均占全村面积的0.09%。可见,休闲场所用地和社区养老服务用地供应不足。
(二)D村的治理困境
从D村的现状数据来看,该村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经济体量、经济活跃程度等指标都已完全超出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在两个方面问题突出、急待解决。一是村内的企业基本上是在缺乏区域规划的情况下无序、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因而散、小、弱的特征非常明显,目前的无序状态影响了空间区域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村内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虽明显多于其他城乡结合型社区,但由于建筑多为村民自建民宅,整体缺乏科学规划,目前的公共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常住人口之所需,造成了基层治理上的明显短板。
⒈ 人口严重倒挂,极易引发“土客”矛盾
D村共有7个物流园、3 173家企业,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员。村内本地户籍人口不足万人,但外来人员超过16.50万人,户籍人口占本村实有人口为5.71%,属于典型的“人口倒挂村”,而公共服务设备配套仍按户籍人口配备,造成资源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尤其是教育资源,D村只有1所公办幼儿园、4所在册民办幼儿园,1所公办小学、4所民办小學,1所民办初中,因而外来人员与本地村民的小孩上学难问题突出。同时地缘性聚居特征显著,外来人员中广东省户籍人口为3.30万人,其他都是外省户籍人口,主要为湖南省、江西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江西省3万多人从事的是服装加工业,福建省1.30万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相互之间以及与当地村民之间融合发展困难。
⒉ 产业发展方式低端,抗风险能力较差
整治前,D村企业中90%以上是个体工商户,其中,从事电商活动的企业或个体超过1 000户,从业人员3万多人,电商快递件日平均为180万件,高峰时超过200万件,年销售额达300亿元。但是,D村电商存在散乱、无序生长状态,电商分布在村内各个角落、出租屋,集聚效应发挥不明显,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超过2 000家中小型企业几乎没有网上销售的能力,企业管理、交易方式传统落后。除电商外,D村还有服装加工业、轮胎业、建筑土木工程业,以及与之配套的商业和服务业。D村的网商从事“线上销售—线下发货—线上收款”的简单运作模式,其他相关的品牌经营、包装设计、摄影美工、培训咨询、客服、管理、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等服务体系都未成型,进行现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困难,产品低端抗风险能力差,且易产生劳资纠纷。
⒊ “城中村”问题集中突出,人居环境改善难度大
一是违章建筑多。D村区域面积大,但村内土地管理混乱,村民在集体土地上毫无规划地建房出租,“两违”建设禁而不绝,违法建设林立、抢建现象突出,整治初期发现,村内建筑物为8 777栋,建筑密度高达45%,其中,村民住宅以7—8层为主,占村总建设量的73.20%,人居环境差,散乱污企业落地生根。二是交通拥堵。D村对外交通主要依靠两条市政道路,村内道路狭窄、断头路多,道路之间连通少,系统性差,每天至少有上千辆货车进出D村,由于车流多,客货混杂,道路拥堵常态化,停车位不足,导致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更加突出,挤占村内道路,影响消防车通行。三是环境脏乱差。村内原来只有76名环卫工人,垃圾收集依靠露天垃圾斗,保洁标准低,截污管网建设滞后,流经D村内的沙坑涌原为黑臭河涌,村内污水横流。同时村内“路无名、楼无牌”、城市“六乱”现象突出,人居环境亟待改善。
⒋ 社会治安管理混乱,风险防范能力薄弱
整治前,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低端,主要依赖出租经济,衍生出大量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问题,致使违建底数大、涉及面广,集体“三资”问题突出,加之外来人员多,缺乏本地认同感,容易滋生黄赌毒、盗抢骗、打架斗殴、矛盾纠纷等系列治安问题,D村警情及案件数均占当地派出所的55%以上。在2018年整治之前,D村社區民警只有7名,治保人员52名,村安管员5名,与管理辖区面积、人口及高发警情的现实严重不匹配,导致D村社会治安管理混乱长期得不到根治,在2018年5月被BY区禁毒委列为区毒品问题通报警示地区。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D村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大环境原因,也有基层自身原因。综合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⒈ 地区发展现状超出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基层组织,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都应由村民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然而,事实证明,D村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实际管理超过20万人的大型社区,却只拥有村级组织资源和管理权限,没有行政执法权限,难以遏止巨大经济利益刺激下的本村“两违”建设涌现。同时外来人员涌入导致“城中村”人员来源不清、社会结构复杂,加大了治安管理和环境治理难度,也让村级治理组织措手不及。村两委干部的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理念、治理技术手段等都严重滞后于超级村庄的经济社会结构带来的治理要求,凸显了基层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不足。地方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后,于2020年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以D村为主体,将原D村与邻近的2个村庄和3个社区合并为街道,辖区人口约21万人。同时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完善区域党组织设置,在23个经济社全覆盖建立党支部,搭建村级党建联席会,将辖内28个“两新”组织党组织和3个社区党组织全部纳入村党委代管,推动辖内3个大中专院校党组织与村党委共建管理。落实“令行禁止、有呼必应”基层党建工作要求,赋予D村向镇、区部门呼叫权。向村派驻10名干部组建D村管理服务办,成立工作队开展党建工作专项指导,村党委新成立党建办,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
⒉ 治理制度供给匮乏,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单一
一是乡村治理制度顶层设计缺位。由于村级的乡村治理制度顶层设计缺失或不到位,部分地方政府在开展乡镇(街道)、行政村(居委)一级的乡村治理制度设计时,对国家的政策、人口转移流动情况、产业发展情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没有综合考量,没有选优配强,致使欠缺各类组织带头人、外来人员管理不足。二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仍未形成。作为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成为各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配”。而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方式和机制缺失,是造成乡村治理无序的源头。部分乡村缺少民主协商机制,村中重要事项或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没有发挥村党组织、自治组织、群众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没有形成“村党组织提事—村民代表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决事—村民自治组织执事—村务监督委员会执事”的协同治理机制,是造成乡村治理失序、缺位的重要因素。三是乡村治理方式传统且较为单一。当前,部分超级村庄普遍存在处理违建房、治安混乱等问题,主要依靠村支书、村主任的“家长作风”来开展形而上的“村庄治理”。“村中有利大家抢,村中出事无人管”的乱象,根源在于没有开创多元共治、协同治理、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能力不强,加上法治缺位,乡村治理混乱在所难免。调研了解到,D村经过整治后,创新“党建+社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推动组织联合、优势综合、资源整合、工作融合。针对流动党员多、单位机构多、外来人员多,大力实施流入党员“安家工程”,常态化开展流入党员登记;充分发挥党组织牵引作用、单位机构和商(协)会基础作用,搭建党建联席会议、共治议事会的“党”“群”议事平台,畅通各类组织、外来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及时传达信息、协调事务、破解矛盾,有效解决治理难题。
⒊ 农村基层监管及惩戒机制缺失
在乡村治理全链条中,农村基层监管机制是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国内部分农村基层监管机制在治理链条中均有缺失,无论是从领导层面、操作层面、财政保障层面还是村务管理层面,都不同程度存在监管机制缺失的现象。惩戒机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缺失尤其严重。惩戒机制既包括法律法规层面的约束与处置,又包括村庄内部的约束与处置规则,如村规民约、村德家训条例等。一方面,部分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加上部分村支书和村干部本身就是“村老大”“村霸”,在推进村庄新农村示范片建设项目、产业园建设时,在工程招投标和财务管理上很大程度存在“监守自盗”“有家法无执行”的现象。另一方面,村庄基层组织在处置村干部贪腐等问题上,普遍存在“碍于情面、网开一面”的做法,如对于违反村务管理、“两违”建设贪污扶贫救济款等问题,要不熟视无睹,要不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作为做法,毫无法治意义上的惩戒机制可言。针对这个问题,BY区全力铲除违建“潜规则”,对控制水、电资源的利益链和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进行彻底打击,重点查处了收受贿赂、违规办理报建手续,向村社干部行贿、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巨额获利,垄断供水、供电并为违建违规供水供电三个系列案。全面开展“三资”管理专项检查,每年增加集体收入近千万元。
⒋ 部分村干部價值观人生观腐化堕落
部分村干部价值观人生观腐化堕落是导致农村基础性、源头性问题的根源。由于村干部存在严重的自我逐利、小农经济的短视行为,把集体资源作为自我牟利的工具,“三资”管理不善,存在合同管理优亲厚友、利益输送,垄断供水、供电等行为,由此,村民无序抢建宅基地,大面积违建,导致治理失效、无序。对此问题,BY区2018年成立专案组,以违建利益链作为切入点,从违建的审批报建、土地使用、“三资”管理、水电供应等方面全面调查,对历任村社干部、违法建筑所有者、经营者、租赁者等200多人进行全覆盖摸查,彻底查清违建利益关系网。成立专案组一年内,共查处D村违纪违法人员103人,其中,公职人员38人(含村社干部30人);移送司法机关29人,已逮捕16人,党纪、监察立案19人,追缴赃款459.70万元、冻结资金4 200余万元。重点查处了收受贿赂、违规办理报建手续系列案,向村社干部行贿、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巨额获利系列案,垄断供水、供电并为违建违规供水供电系列案。
四、创新治理理念与治理路径
乡村有效治理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3]以“三治融合”为抓手,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都市型超级村庄的治理提供了创新的治理理念和明确的治理路径。
(一)治理理念
⒈ 共建
共建即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在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如就业、住房、医疗、教育、托幼、治安和社区服务等,应本着政府主导和政社合作原则,通过一系列政策安排,为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团体创造更多机会,特别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领域。都市型超级村庄需要综合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和村庄、村民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政府主导,科学设计社区空间,从长远发展来看,选择产业定位,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供给的共建。在城乡融合的共建进程中,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导,发挥市场效率、社会能动,以改造空间物质环境为切入点,分片推动、逐层深化。
基层地方政府在超级村庄转型改造过程中,不仅要扮演好“效率+公平”的维护者、监管者、仲裁者的角色,也要成为改造的主导者、规划者、设计者,主要负责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协商制定空间规划,通过区域发展与空间创新来妥善处理大量历史性遗留的“两违”建设,平衡村民之间、社会与市场之间的利益,规范和监管村民及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
基层地方政府要根据城市整体功能规划和布局对超级村庄的城市功能类型进行个性化空间规划设计,实行“一村一策”“一村一模式”。空间规划既要保护村民合法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又要兼顾市场收益。D村的空间规划,就是BY区政府为主导的,在坚决遏制“两违”建设的同时,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编制《BY区D村片区提升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一全村域的系统性空间规划,采用“产、城、居”三融合的用地布局,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新型智能社区,利用后发优势创建“城乡融合示范性街区”。
市场的介入、社会的参与是共建的必然内涵,在超级村庄的改造过程中,市场参与的第一类主体就是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改造主体的开发商和被改造主体的村集体及村民均应当是受益主体,从空间规划全面参与进来,就能促进后续拆迁、建造、回迁、维护等多方面的集体性行动与共同性妥协。
⒉ 共治
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治理的参与权是人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从城乡基层社区来看,就是在基层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基层地方政府的主持,不断改革现行社区管理办法、创造社区信息分享平台,将“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应用于基层治理,让每一个居民都具有话语权、及时表达意见,并参与决策表决,以治理技术与沟通技术的发展推动共同参与社会治理。都市型超级村庄这类城乡融合型社区,尤其在公共事务制度层面要尊重与纳入外来人员的社区发展话语权与表决权。
都市型超级村庄普遍存在本村居民与外来人员倒挂的问题,因而在治理中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传统本村宗亲关系联结的纽带逐步瓦解,村落内部以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整合功能受到挑战。二是当外来人员显著超过本村居民之后,原本建立在“村籍”基础上的自治制度边界就受到挑战,两类人共居一地的新社会联合体,需要合作探寻现代社会意义上的地方性共同治理的制度机制与社会基础。超级村庄的治理转型,其本质是城乡融合类村庄在物理边界(以建筑表达)、制度边界(以自治资格表达)、精神边界(以身份认同表达)的重塑过程,只有三者融合,才能最大程度上达到有效治理的效果。2013年,民政部印发《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明确“除拥有本村户籍的村民外,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也可参加选举”[14]。但是,居住关系仅是构成村民选举资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村民利益方面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土地所有权关系,涉及宅基地、村集体土地资源、耕地的分配,也就涉及住宅租赁收益、村集体经济分红、耕地销售补偿与分红等。对尚保留村委会建制的超级村庄而言,外来人员一旦准入村委会选举,就意味着获得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如果正式落户,就同时获取经济合作社的组织成员资格与公共资源共享资格,这个方面如果缺乏科学管理,空间规划的权利关系就会更加复杂。
因此,解决外来人员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村庄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如果仅仅依靠村集体收入来提供公共服务,难免会触碰到原有村民利益而受到村民和村集体的阻挠,因为“经济组织的边界联系着产权所有者,社区公共福利以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边界联系着社区成员权的获取”[15],所以从产权与治权的关系上,都市型超级村庄的共治,必须要理清社区成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村籍等多领域不同标准而产生的社区内多重群落边界,并在此基礎上重新构建新型的治理结构与组织结构,而要完成这个任务,仅仅依靠基层自治组织的村居委是难以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地方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和提供引导,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相应的财政资源,以保障城乡融合过程中的城乡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与基础设施投入实现同城同待遇和逐步一体化,并在不打破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封闭性的背景下,增强资源投入以切实解决超级村庄村域治理的资金来源,为外来人员参与村庄治理提供正式的组织通道与制度保障,使两类人共同合作,真正走向可持续的共治之道。
⒊ 共享
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效率优先的路径导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存在各种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6]因此,共享治理成果,一是靠党保障民生的决心,二是靠政府有改善民生的思路,三是国家建立共享的制度保障,这是“共享”的第一层认知境界。更进一步的第二层境界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共享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基层治理的成果,形成协同治理、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治理格局,即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通过共担治理责任、共行治理之举、共用治理职权而共享治理之果。从城乡基层社区来看,就是在社区空间之内,实现全体社区成员对社区治理的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的收益分享——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安全、发展、空间、审美等所有方面的收益分享。都市型超级村庄由于“本地村民—外来人员”属于不同所有权主体,以土地房屋的租赁契约为关系纽带,将村庄内部的经济与面向全区、全市的经济连接起来,通过大量外来人员聚居,都市型超级村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次生经济圈和低层次生活链。一些规模较大的外来人员聚居村,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功能齐全、自我供给、自我服务的小社会,但“本村居民—外来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薄弱。
在人际关系上,一方面,融合本村居民和外来人员,需要进行新时期下“新居民”的培育,稳步推进外来人员在身份认同方面对城市社区的融入,增加外来人员因居住所形成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需要在社区内构建良好的“本村居民—外来人员”的沟通交往氛围,可以通过传统风俗搭桥、新时代风尚铺路,兼容并蓄打造新型社区文化、社区公共参与等活动,并在社区公共领域构建可供沟通交往的空间,保证两类居民之间的沟通渠道顺畅、相互信任建立,从而实现不同居民在社区内的融合。
在福利保障上,由于生活福利主要通过村集体经济资产来分配,因而外来人员被排除在社区生活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今后,需要结合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优化外来人员的生存居住空间,如在集体产业用地上建设公租房,既可以保障本村居民的长期收益,又为外来人员提供安居乐业的空间。同时可以通过加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稳步推进外来人员在当地的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平等分享,逐步消除福利保障供给上的差别。
(二)治理路径
⒈ 提高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一是提高行政执行能力。借鉴珠三角其他地区“村改居”经验,以“党建+”的方式,加强党政行政力量介入,推进超级村庄的整体转型。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把都市型超级村庄逐步升格为乡镇(街道),从而在行政管理体制源头上理顺村庄的管理体制。依法赋予乡镇(街道)的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应急处置权和行政执法权。二是提高为民服务能力。规范乡镇(街道)政务、商务、民生、公共安全等事项,将直接面向村居委会、街道能够承接的服务事项有序平稳下放,既保证放得下,也保证能接得住。三是提高基层议事协商能力。完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咨询会等民主协商方式,注重发挥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街道)有关会议制度,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内容。四是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立与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完善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建立应急管理队伍和合理配备应急资源。五是提高平安建设能力。重点推进现代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创新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强心理疏导服务和危机干预机制建设,完善乡镇(街道)综合治理智能化指挥中心的规范化建设。
⒉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动员能力,完善和加强党组织对村域治理的统一领导。一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领导,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全覆盖建立党支部,推进村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实行集体经济组织党组织负责人与法定代表人的交叉任职,把村干部的组织任命权牢牢掌握在上级党组织手中。二是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完善区域党组织设置,除了在集体经济组织内全覆盖党支部外,也要在外来人员较为集中的“两新”组织和社区中加强党建,成立相应党组织,搭建村级党建联席会,并由上级派驻干部开展党建工作专项指导,从党内民主建设的路径解决本村居民和外来人员的融合问题,推动辖区内党员干部率先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表率作用。三是强化阵地建设。通过建设主题党群文化广场等,推进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融合建设,统筹打造党建办、党校分教点、“两代表一委员联络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进集体经济组织、村党支部阵地规范化建设,强化党组织服务功能。
⒊ 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
一是丰富村(居)民自治实践内容。把村(居)民自治实践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纳入全过程人民民主中,不断丰富和规范基层民主实践,拓展村(居)民自治内容和形式。借鉴山东省青岛市“德育银行”的经验,建立积分制,把纷繁复杂的村级事务化解为标准化、具象化的积分指标,让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从而全面激活村(居)民自治。二是提高村庄治理法治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强“一村(居)一法律顾问”推广示范建设,发挥法律在基层社会矛盾中的预防和处理功能。创新社区村(居)民法治教育模式,建立智慧法治教育平台,提升村(居)民的法治意识,夯实依法治理的群众基础。三是加强德治教化建设。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在村域全力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程,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治理内涵,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强化德治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
⒋ 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
一是推动网格化管理向智慧网格化管理升级,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开发“德育银行”APP系统,构建“镇、行政村、网格村”三级后台管理体系,以户为单位建立需求上传和办理反馈的渠道,为分析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的问题点、需求点提供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二是构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数据库,依法实现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享,探索打造“市民码”,拓展作为电子凭证、信息关联载体功能,并连接各大政务平台,构建先进的便民服务体系。三是开展数字化乡村治理。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通过平台提供、技术扩散和场景改造等方式,将数字技术嵌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切实为建设乡风文明、改进乡村治理注入智慧动能。
⒌ 推动治理资源与基层治理事务相匹配
一是推動社会治理体制扁平化,提升治理效率。根据村域面积、地理特征、人口规模和产业规模,科学设置街道规模,探索街道、社区合并,将村部分行政管理职能逐步转移和融入到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并按照需求在街道设置分拨、网格、民生、企业服务等新型职能部门。二是按照“事、权、责、人、财”对应原则推动基层减负。实行人力、权限等资源与事项同步下沉,完善农村社区事项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严格修订事项清单的程序,完善基层资金项目预算制度,确保农村社区具备完成所承担清单事项的能力。稳步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按照市场原则向社会组织和专业公司有序转移。三是建立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持续稳定增加农村基层党建经费,探索设立农村基层党建引领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专项行动经费,如乡村“三治融合”试点专项、乡村法治公益基金专项、乡村道德模范体系建设专项等。
五、结 语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时期城乡融合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地的实践探索也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制约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也不断凸显,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都市圈城乡融合地带农村发展情况、契合农村集体资产发展和社区治理的体系。乡村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17]。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大批伴随城市群、都市圈崛起而成长起来的都市型超级村庄,这些村庄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自身也快速发展,村庄资产保值升值,但不可避免出现经济发展已进入现代化,而社会治理仍停留在传统农耕社会的模式和水平,导致一系列的治理困境。本文通过厘清都市型超级村庄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超级村庄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路径,为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农村治理联动机制提供学理支撑,从而为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新时代的中国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参考文献:
[1] 刘义强.村民自治发展的历程、经验与机制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7(6):2-7.
[2] 徐勇,赵德健.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3(4):1-8.
[3] 魏晨,李华胤.基层党建引领民主与治理有效互联的创新机制研究[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0,22(6):27-36.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EB/OL].(2014-01-19)[2022-03-13].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4/content_2574736.htm.
[5]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
[6] 江必新.构建“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J].人民法治,2018(15):32-37.
[7] 邓大才.走向善治之路:自治、法治与德治的选择与组合——以乡村治理体系为研究对象[J].社会科学研究,2018(4):32-38.
[8] 胡洪彬.乡镇社会治理中的“混合模式”:突破与局限——来自浙江桐乡的“三治合一”案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7(12):64-72,157.
[9] 张文显,徐勇,何显明,等.推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J].治理研究,2018,34(6):5-16.
[10] 王春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民主”与“有效”治理的匹配问题[J].社会学评论,2020 (6):34-45.
[11] 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254.
[12] 折晓叶,陈婴婴.超级村庄的基本特征及“中间形态”[J].社会学研究, 1997(6):37-45.
[1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EB/OL].(2019-06-23)[2022-03-13].http://www.gov.cn/zhengce/2019-06/23/content_5402625.htm.
[14] 民政部关于印发《村民委员会选举规程》的通知[EB/OL].(2013-05-08)[2022-03-12].http://www.mca.gov.cn/article/gk/wj/201901/20190100014530.shtml.
[15] 郎晓波.“人口倒挂”混居村的自治组织边界重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9):43-48.
[16]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31(1).
[17] 阳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9:1.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Pathways of Urban-Style Super Villages'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D in Guangzhou City
TANG Zhi-yong1,CHEN Lin2,3
(1.Academic Affairs Office,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50,China;
2.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3. Institut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ance model of rural areas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democratic governance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and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of management democracy has been replaced by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e governance model that integrates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main way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urban-style super villages, demonstrate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transition of these two governance models,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next step. However,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ance models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and lacks in-depth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comparative analysi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to obtain a large amount of first-hand data through discussions,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access to relevant policies, laws and documents, thus helping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nd pathways of urban-style super villag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urban-style super villages face a series of governance difficulties due to rapid urbanization. They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far exceeds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primary-level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ance model still relies on self-management,
self-service, and self-supervision of grassroots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which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social governance needs of urban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urbanized rural commun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restructure and rebuild the primary-level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to activate the internal vitality of the governance subjec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expands in the following area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primary-level political power. Specifically, we can gradually upgrade urban-style villages to towns and stree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djustments, so as to straighten out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villages at the sour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Second, in order to achieve effectiv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re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in village governance. Third,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villagers' autonomy practice. Specifically, we can fully incorporate democratic elections, democratic consultations,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Fourth,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basic support rol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embed digital technology into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combines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Fifth, it is necessary to match governance resources with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affairs, and empower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affairs, power, responsibility, personnel, and finance'.
By clarifying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urban-style super village governance, and proposing a governance
pathway,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to actively construct a
rural governance linkage mechanism of 'Party leadership,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farmer main body,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ollaboration'. This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ing a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ntegrates
self-governance, rule of law, and mo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ng a soci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exploring a path of socialist rur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uper villages; effective governance; idea of governance; governance pathway
(責任编辑:尚培培)
收稿日期:2022-06-09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广东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治理体系研究”(GD18XFX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广东农村村民自治的法社会学研究——以清远市村民自治重心下移为例”(GD17XFX15)
作者简介:唐志勇(1984—),男,广东清远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法社会学、基层社会治理和智库等方面的研究。E-mail:nfzkzb@163.com
陈林(1981—),男,广东河源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企改革和反垄断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char
lielinchen@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