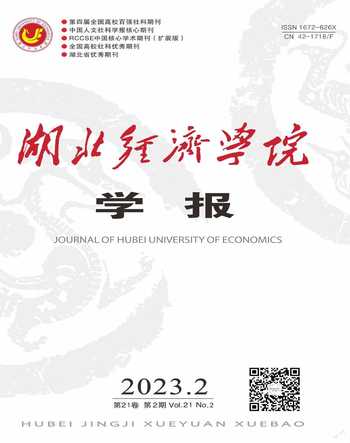强互惠的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
2023-05-30王覃刚,冀红梅
摘要:古典形态的强互惠在面对复杂社会系统时,不能实现有效回应以及获得合法性认同,强互惠的社会形态经由二阶演化分离出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并以结构性的方式嵌入社会系统,与古典形态共存,各自依据不同的模式和步骤完成强互惠的古典演化和现代演化的进程。强互惠的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尽管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演化机制,但二者事实上却能实现相互渗透式的动态结合和统一。
关键词:强互惠;古典演化;现代演化
一、引言
“強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是Gintis(2000)提出的概念[1],意指那些自愿合作并不惜付出成本以惩罚不合作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维持人类族群合作从而实现群体成功演化的必要条件[2~3]。Fehr等(2002)将强互惠直接表达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的行为,并通过实验证明其广泛存在[4]。也有学者认为,Fehr的实验只是验证了人类强互惠或者强利他本能以及行为倾向的存在而已[5]。我们注意到,“强互惠”本意是从被观察到的那些社会行为以及行为实施之后可辨识的社会状态等行为学层面来表达的。同时,在Santa Fe经济学家的文献中也通常将“强互惠”当作一种个体性质素的描述使用,其意近乎“强互惠主义(Strong-Reciprocism)”[1,6~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更偏向于本能或者行为倾向的理解。因此,强互惠的行为本身或者行为结果也可以被简单表述为强互惠。正因如此,在相关研究中,强互惠一词事实上既被用作表征一种内在质素,又被用作表征一种外在行为呈现,在内外两个层面上,该名词的使用是相通的[8~10],甚至还可被用作指代某个具体或者抽象的具有强互惠行为倾向的个体或群体[3,11~12]。以上对概念的梳理,使得将会以多种词性以及涵义出现在我们研究中的“强互惠”这一表达,不再需要对此分别作出说明和解释。于是,我们的研究主题——强互惠演化(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也就至少分离出两个方向。其一,是强互惠作为一种质素或者偏好的演化,由于这样的质素或者偏好是以个体为载体来呈现,因此,也可视为强互惠个体的演化;其二,是强互惠作为社会行为以及行为后的社会状态的结构演化,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演化是从零散的不确定的强互惠行为被一种社会系统方式设置的强互惠结构(the structure of strong reciprocity)取代以后,其系统设置的复杂性演化的社会过程。前者正是Santa Fe经典文献的主流研究方向;而后者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开创并不断探索的研究方向[13~16]。为了研究便利,我们将前者界说为强互惠的古典演化,而将后者界说为强互惠的现代演化。
二、强互惠社会形态的分离
Santa Fe经典文献中的博弈实验说明人类行为存在显著的亲社会(prosociality)偏好以及追求平等性的本能。然而,Filed(2001)[17]、Wael(2009)[18]等都质疑这样的实验结果在现实中的真实性以及强互惠的存在性。我们认为,这样的质疑是有意义的,至少为我们研究的严谨性提供了思维路径。因为客观上是否存在诱发强互惠的环境条件,即就算大多数个体具有强互惠行为倾向,但环境阈值是否足够将这样的心理激发至现实行动化,这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
(一)强互惠古典形态的理论困境
首先,什么条件会触发强互惠心理?多数文献仅单方面从卸责者的不合作行为考察,认为此时与激励相关的脑区会被启动,尾核(caudate nucleus)的血流峰值显示出其活跃程度远超平均水平,个体表现出强烈的利他惩罚愿望[7]。然而,我们从Gintis等(2003)的田野调查结果中发现[2],不同群体在合作中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市场整合程度越高,合作剩余越高,群体中的合作水平从而惩罚不合作的愿望才会越高。那么,在缺乏合作剩余体验的文化中,对卸责者利他惩罚的强互惠心理倾向并不必然产生。
其次,什么条件会触发强互惠心理行动化?即使个体存在行动意图、心理倾向,但并不必然外化为真实的行动,因为并非每一个强互惠心理高涨的个体都具备有效实施利他惩罚的资源禀赋。尽管在Gintis(2000)的研究理路中[1],强互惠者应该不计成本地惩罚卸责者,然而,正如当交易费用高到抑制某些交易,使其难以发生从而无法计量交易费用总额一样,当利他惩罚成本高到具有强互惠倾向的个体无法承受时,强互惠行为也就不会真实发生,自然也就无从讨论需要克服的成本。这意味着,即使存在强互惠心理,实际实施强互惠行为能力的欠缺以及实施过程中和后续可预见的成本过于高昂,强互惠行为可能不会以能被观察到的方式发生。
第三,基于社会学层面的顾虑也会阻碍强互惠行动化。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最大的不同是,行为个体是原子式的,在零交易费用的环境下,个体的行为决策孤立地取决于狭隘的私人成本-收益比较。然而,现实中的个体却是典型的社会性存在,其行为的发出需要考虑群体或者社会的认同,并由此获取合法性基础。具体而言,个体的强互惠心理究竟是私人情绪还是社会共同心理倾向,决定了强互惠行动化以后能否得到群体乃至社会的认同及支持,否则可能会招致群体的抵制或者反向强互惠行动。因此,在个体缺乏相关知识的条件下,强互惠心理也并不必然行动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强互惠心理并不必然被激发、外化为行动,至少没有机制确保在所有必须的场合下,所有个体的利他惩罚动机都能实现。这样的理路是在经济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关照到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而形成的。事实上,更多可被观察到的社会情形是,即使心存惩罚卸责者的冲动,但由于缺乏实际行动力,只能坐等其他具备利他惩罚行为能力的个体出手实施实际的强互惠行动,从而免费获取合作秩序恢复后的剩余[13],或者在针对卸责者的惩罚行为数量甚众、群情汹涌之时,强互惠行为才得以低成本生发。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能期待有助于合作维系和人类演化的强互惠行为在总量以及时机上持续稳定存在,社会系统可能陷入二阶社会困境[19]。所以,在社会生存延续的演化压力之下,基于个体主义、自我利益假说的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强互惠行为,并不足以单独支撑社会演化的宏大动态体系,强互惠社会形态的理论层面面临必要的分离,在古典形态之外,须引入新的现代形态。或者依据演化论的叙事逻辑,古典形态的强互惠自发演化出自我的分离形态,以适应社会系统的复杂化进程。
(二)强互惠现代形态的出现
针对上述强互惠个体缺乏现实行动能力的问题,我们曾提出过一个补救步骤,即强互惠锻炼(Exercise of Strong Reciprocity)[13,15]。这是一个强互惠个体选择的演化过程,当具备足够行动能力的个体被选择充当群体中合作秩序的强互惠行为者时,他们表现出来的能力成为群体中具备强互惠心理的个体的锻炼方向而流行起来。这样的锻炼主要朝向两个目标,第一,辨识有效合作秩序的能力,这为强互惠行为提供理性基础;第二,实施利他惩罚的行动能力,这为强互惠行为提供低成本保障。强互惠锻炼明显改善了强互惠个体的行动效率,提升了群体合作水平,促进了强互惠个体的涌现,我们把这一有效率的过程称为一阶演化。
然而,我们注意到,一阶演化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强互惠的古典形态,也没有实质改善强互惠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意味着无论是简单多数,还是权力强制,都需要获得稳定的足够比例的自愿一致或者被迫一致的表示,显然,古典意义的单个个体不能被有效赋予任何合法性依据,合法性是基于群体意义上的社会性概念。在缺少合法性基础的情况下,强互惠行为的社会合作效果是不足的。G?chter等(2011)的实验表明,反社会惩罚与合作水平负相关,当存在报复性反社会惩罚时,利他惩罚的威胁甚至是不可置信的[11]。于是,群体面临二阶演化。在丛林状态下经由暴力获得的合法性,开始被制度结构以无知之幕的形态所取代,社会也就从蒙昧进入现代化进程。强互惠行为不再由不确定个体临时激情式的生发来供给,而是在制度化的结构中确定性地实施,其合法性已经被这样的制度化结构事先对外标识,同时,利他惩罚的具体步骤也被事先约定。二阶演化以后,产生强互惠利他惩罚社会结果的行为事实发出者并不必须是具备强互惠心理冲动的个体,而只是一个制度性的强互惠过程的实际完成者而已,于是,在制度结构中强互惠个体的私人性质被隐去了,强互惠获得了现代形态。在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形态存在为强互惠结构。
我们之所以以社会形态的分离视之,是因为强互惠现代形态的出现并没有完全取代其古典形态,而只是演化分离出并行却更具效率的存在。当强互惠取得现代形态以后,利他惩罚的手段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从个体层面迅速上升到群体、社会的制度层面,不再简单依靠个体对个体的简单暴力,而是呈现出更多群体层面的诸如隔离、驱逐等剥夺卸责者社会性的有效率的机制。同时,古典形态强互惠者依然零散地存在于社会系统中,然而,由于制度化的强互惠结构基于合法性的约束,其强互惠行为的暴力倾向得以控制,社会系统整体获得了更有秩序的安排。顯然,这样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演化效率。
三、强互惠演化方式的转向
按照我们的界定,Santa Fe研究中的强互惠表现为一种古典形态,因此其经典文献中关于强互惠演化的研究大多可以视为强互惠的古典演化研究。
(一)强互惠的古典演化
Gintis(2000)的演化研究表明[1],强互惠可以通过群体选择在互惠利他中自发产生,群体选择的压力使得强互惠者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合作更容易发生,进而引发协作力量、产生合作剩余,并由此示范整个群体。Calderón等(2006)的模型证明,强互惠也可以由个体选择引发[10]。Sánchez和 Cuesta(2005)的研究表明,即使整个群体在初始时刻都是自私的,但只要存在产生突变的概率,强互惠者就有可能经由漫长的自然演化过程而稳定生存[9]。Bowles和Gintis(2004)的狩猎采集时代的仿真模型起始设定20个相对独立且规模较小的原始族群,其成员100%是自私者,即个体选择的古典范式[3]。初始阶段,自私者占绝对多数,卸责比率(shirking rate)近乎100%;而当强互惠者出现后,合作者数量增加,平均卸责比率显著降低;在大约500代,卸责比率降至10%,而强互惠者和合作者在群体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大约2500代内,群体中三类特征人群的比例以及平均卸责比率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即自私者占38.2%,合作者占24.6%,强互惠者占37.2%,卸责比率为11.1%。作为经济学起点假设的自我利益行为范式,在群体乃至社会的复杂性增强后,明显趋于社会偏好发展[20]。
然而,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中有效执行强互惠规范的利他惩罚效果开始与执行主体的身份表现出明显相关性[21]。在Nikiforakis等(2011)的重复多期的双边惩罚实验中,私人个体的惩罚可能引发个体间的持续仇恨,甚至会成为合作障碍,如果允许私人间相互惩罚,人人都将成为自然法的执法者,纠纷根本得不到妥善解决,社会结构面临深刻恶化[22]。因此,上文述及的二阶演化进而分离出强互惠的现代形态,正是有效克服古典形态下缺乏足够合法性基础的社会矛盾的有效步骤。于是,强互惠的演化方式部分转向为现代演化。
(二)强互惠的现代演化
当强互惠获得现代形态以后,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再附着于一个具体生物性的道德个体,而是转向一个社会性的制度存在,个体性被隐去了。这意味着其现代形态表现为一种制度结构,包括什么样的行为被视为非合作卸责状态、其突破什么阈值将会触发利他惩罚的制度安排、如何执行适用的惩罚手段等等,并且各个实施环节的个体只是完成制度性行为,并不必然具备强互惠质素,但制度结构整体却有效地完成了强互惠的社会效果。这样的强互惠结构进一步构成更大的社会系统,或者说嵌置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之中。如此理路见诸于我们的前期研究,将社会系统表述为一个复杂的以制度为基础单位的制度结构[16]。我们认为,强互惠结构作为社会系统制度结构的构成组件,其功能结构设置就是实现社会系统的均衡稳定。一方面,其具备足够合法性基础、以强互惠为特征、可识别性的制度设置,抑制可能威胁到系统稳定运行的不合作卸责行为的实际发生;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实施利他惩罚及时纠正系统的失衡,并有效维持社会多数成员对于系统稳定的良性预期。
强互惠从古典形态中分离出现代形态以后,其演化方式也就形成了区别于古典演化的现代演化。严格来说,任何演化都要从复制单位开始。强互惠的现代演化的复制单位十分明确,就是构成制度结构基础单位,即制度本身。这样的复制是在一个制度系统结构中,以制度化的自创生方式实现,即以制度复制制度,同样表现为去个体性。在制度的社会系统中,强互惠结构的作用方向是有助于达成复杂制度结构的均衡并持续维系、保守这样的均衡。正如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在选择机制的压力并不足以推动变异的情况下,得以稳定复制一样,强互惠结构也在这个过程中稳定复制自身。然而,我们注意到,对系统而言的非压力环境的形成可能存在另一种情形,即系统结构缺乏对环境压力的感知灵敏性,实际环境压力本应迫使系统的部分或者整体制度结构面临调整,但强互惠结构对旧系统的保守力量过于强大,于是整体上社会系统将持续稳定复制自身而并不会转向变异,最终可能被拖入制度内卷,我们将这一情形界定为强互惠内卷[14]。
事实上,远离现代文明的丛林部落或者封闭小族群,基于古典演化逻辑,给定一个相对稳定的自然环境起点和初始动力,这样的演化将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管道中持续进行下去,更容易陷入强互惠内卷。正如当初Clifford Geertz(1970)提出“内卷”概念时,在印尼爪哇岛所观察到的那样[23]。然而,社会系统中强互惠结构的现代演化,在组织闭合、结构开放的条件下,实现了系统内外的能量交换,从而有可能达成拉马克式的获得性遗传。这意味着,在达成针对既有社会系统的均衡态的制度性守护,甚至可能固执地将其拖至内卷境地的同时,强互惠结构从制度安排的结构性功能来看,也最有可能获得环境的演化压力信息,进而在触发制度创生程序后得以成功演化。
一般认为,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思想可概括为选择、遗传和变异三个机制,而正统的达尔文主义却更强调前两种机制,变异机制作为一种演化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选择和遗传机制的[24]。因此,达尔文主义事实上无法像拉马克主义那样彰显获得性遗传。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制度演化在机制上更偏向拉马克主义,强互惠结构就表现为基于一种外部环境压力的获得性演化遗传。从其结构的社会系统功能来看,由于其制度性的保守原则,当现有制度结构与环境耦合度下降,系统的租被迫耗散于各种摩擦环节,强互惠结构就成为最真实感受到外部生成的这种演化压力对系统形成冲击的最前沿的制度存在。在耗散的租突破某个阈值时,系统提示强互惠结构放弃保守原则,转而实施制度系统的调整,事实上,这一切并非出自某个具体的精明的个体的敏感,而是事先制度结构的设置,这样新的制度被创生。并且这个过程同样是制度的预设以及制度运动的结果,是制度在创造制度,表现为一种自创生。然后,强互惠结构再度成为演化后的新的制度结构的守护者,当然如此之制度演化也包括了强互惠结构自身的调整变迁。事实上,我们能这般轻松流畅地表述其演化过程,是预设了社会系统具有相对完备的制度构成,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几乎也是其社会系统及其强互惠结构的制度演化的目标方向。通常情況下,以上自创生的演化需要面临类似自然选择的筛选过程,并由此获得制度演化的合法性认定。这种试错逻辑的程序也许会持续进行直至获得系统最大限度的认同,具体表现为需要强互惠结构强制推进的实施成本不断递减,甚至达到归零的最优状态,即制度安排的社会习惯化、习俗化。而另一方面,若以上试错过程无法获取有效认同,其实施成本高企不下,便再度作用于强互惠结构,形成新的制度演化压力,进而重复上述过程。于是,整体过程表现为制度形态的现代演化。
四、现代演化与古典演化的统一
强互惠的古典演化是一种基于生物演化的表述,而当其演化分离出现代形态的结构后,现代演化在存在和识别意义上就表现出有别于古典演化但又交互统一的特征。
(一)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的特征
我们认为,社会系统中的强互惠以制度结构形式实现的演化过程之所以被视为现代演化,正是因为其演化主体已经超越了古典演化的纯生物性特征,而获得了一种去个体性的制度结构的演化逻辑。其间,建构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强互惠结构的制度安排,以及具体到强互惠结构的作用方式、行动程序等都实现了适应环境压力指向的演化变迁。当然,强互惠结构的现代演化并不落实到具体的人员构成上,其过程也是去个体性的,最终以制度的演化、新的制度格局生成来对外呈现。我们认为,这样的演化并不必然代表效率,而可能仅仅指向针对系统环境的适应性,这种类似生物生存本能诉求的强制适应性嬗变过程,在其环境突变不具备连续性特征的情形下,也就不必然表现为单向度的线性特征。正如,基于古典演化的强互惠个体以及基于现代演化的强互惠结构本质上都只对现有的制度结构的秩序保守,而不必然对其秩序的运行效率负责,除非环境演化压力被感知到。
我们注意到,在保守式的行为特征上,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方向其实是一致的,同时二者都不排斥对方而是以不同的结构层次共同嵌合于社会系统之中。我们的研究已然实现了对社会系统的结构重述[16],获得了对其新的两分法认知,即非功能性社会系统以及功能性社会系统。在这样的语境下,基于古典演化的强互惠个体多以相对零散的方式分布于非功能性系统之中,而基于现代演化的强互惠结构则以系统性的制度安排结构化于功能性系统中。二者在共同将社会系统整体保守于既有的制度结构中从而维持系统的稳定均衡上实现了统一。
(二)古典演化和现代演化的交互关系
强互惠的古典演化和现代演化在社会系统结构上的统一,实际上还表现出两个层面的矛盾性的交互关系。
第一个层面,生物性的古典演化是在个性上塑造强互惠个体,而制度性的现代演化则是在系统中输出强互惠制度结构,因此古典形态的强互惠难免有个性和感性的一面,而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则有排斥个体性而追求纯理性的一面。这样,二者的交互关系就表现出静态倾向,即两种形态的强互惠都倾向于排他性地坚守各自的规范领域。首先,从个体性的古典形态强互惠相对于现代形态可能介入的两种方式来看,其一,古典形态强互惠个体以制度具体实施的制度性角色的方式介入,会被制度安排屏蔽掉个体感性层面的因素,以确保制度结构的严格效率,例如,一些制度明确规定了回避规则;其二,古典形态强互惠个体试图以其社会角色的方式介入,一般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管道,这样的形式相对更困难一些,例如,一些家族式的或者社团式的私人惩罚被制度明确视为非法而被严格禁止。其次,从制度性的现代形态强互惠相对于古典形态可能介入的方式来看,古典形态往往会以道德律令等习惯、习俗方式坚守其生活世界的行为范式,我们注意到越是封闭的独立的小社群,越排斥现代形态的介入,例如,曾经坚守于九龙旺角北的城寨。但因为现代形态毕竟具备合法性地位,事实上,并无可能完全被排斥。于是,在两种演化方式上被各自预设了某种标志其排他性的特质或安排,其中古典演化更倾向于风俗习俗等文化的保守形式,而现代演化则往往在其结构上植入杜绝人为干涉的制度。
第二个层面,在二者交互关系中也表现出动态倾向的一面,即两种形态的强互惠总在试图向对方规范的社会系统领域渗透。一方面,古典演化意义的强互惠个体更愿意介入制度化的强互惠结构,充当社会系统中强互惠的制度角色,因为其自然行为取向与制度行为取向具有趋同性特征。尽管在制度角色的实践上是去个体性的,但我们认为,具有强互惠利他惩罚行为倾向的古典个体在具体实施制度性的强互惠行为时,能更有利于实施结果的有效达成,例如,具备利他惩罚倾向的个体在践行制度职责时更能认真到位。同时,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古典强互惠个体也会有机会利用其制度角色优势为制度演化引领有利的方向,例如,对社会演化进程起到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然而,从反面来看,古典演化意义的强互惠个体对于制度结构的过度渗透,有可能会打破其去个体性的结构特征,进而弱化制度功能,现实中就可以观察到某些特殊行为能力个体的干预影响制度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现代演化意义的强互惠结构也会介入古典形态规范的非功能性社会系统。我们认为,古典形态的强互惠由于其行为的合法约束更多表现在道德训教层面的非强制性利他惩罚,而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其合法性行为优势能更有力地引导社会习俗方向,移风易俗,加快现代化进程,例如,城市禁鞭制度实施后春节期间人们已经开始习惯更清洁环保更有意义的民俗活动。同时,由于社会演化的进程而出现新的行为模式可能超越传统价值观的有效辨别能力,此时制度结构的有效介入既能制度性呵护新生事物的生机,又能基于规范性要求抑制可能危及社会和谐的事物蔓延,例如,近年来随着城市扩建,城乡结合部出现了由拆迁致富带来的赌博盛行,随后治安措施的加强以及拆迁方式的改进等制度安排有效抑制了这一势头。然而,从反面来看,一旦现代形态过度介入,也可能出现生活世界殖民化倾向,那些制度身份会被带出其制度规范的系统外,从而产生功能性系统秩序的无限延展趋势并伴随着利益导向。
(三)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的矛盾统一
强互惠作为社会行为规范性机制,以其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的两种动态方式,矛盾統一于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结构之中,并外化为宏观的社会系统的演化从而被观察到。任何一个系统首先是寻求在环境约束下的生存延续,其次是在生存延续中尽可能实现稳定均衡及和谐。无论是古典形态还是现代形态,这样的诉求恰恰与强互惠行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强互惠形态为系统锁定有利于群体、社群乃至社会存续的制度安排集合,并结构化构建起社会系统;另一方面,保守着这样的社会系统制度结构的稳定态,利他惩罚有悖于此的行为以及行为个体。我们认为,当系统环境处于一种稳定态时,古典演化的生物个体以及现代演化的制度结构都表现为相对简单的同型复制和继承,或者最低限度的异变。而当社会系统被迫置于一种强大且持续冲击的环境下,最初基于保守式的维系逐渐失去抵抗后,强互惠形态会转为以系统存续为方向的演变,直至再度实现静态均衡,并获得新的可用作保守的系统的制度结构,从而完成一个被外在观察到的社会演化进程。历史经验提示我们,这样的进程对于相对封闭、尽可能隔绝外在影响的社会系统而言是迟缓的,甚至促成内卷的发生;而对于暴露于外在环境的多频次冲击下的社会系统而言,其进程则要显得活跃得多,即强互惠演化也更易发生。概言之,相对于封闭系统而言,开放条件下的社会系统更易实现强互惠演化。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尽管同处在一个统一体的社会系统的制度结构中,古典形态的强互惠与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在演化速率上也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社会系统的划分来看,功能性系统的制度安排较之非功能性系统即生活世界的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分别,而正式制度较之以习俗、道德等文化层面因素来对外呈现的非正式制度而言,其调整具有更多灵活性,后者则相对稳定得多。那么,进一步推论可以发现,规范于不同系统中的两种形态的强互惠,现代形态在演化速度上快于古典形态。概言之,相对于强互惠的古典演化而言,强互惠的现代演化更易实现。
五、结束语:理论思考的现实延展
基于以上复杂的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的基本理路:由于古典形态的强互惠在面对复杂社会系统时,不能实现有效回应以及获得合法性认同,强互惠的社会形态经由二阶演化分离出现代形态的强互惠,并以结构性的方式嵌入社会系统,与古典形态共存,各自依据不同的模式和步骤完成强互惠的古典演化和现代演化的进程。我们认为,强互惠的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尽管表达两种完全不同的演化机制,但二者事实上却能实现相互渗透式的动态结合和统一。这样的理论思考可以在解说现实态势和问题时获得更开阔且更有益的延展,实现从经验角度完善思辨的思想架构。
强互惠的古典演化是以具体个体为中心的生物塑造和社会塑造过程,最终也是以生物性个体及其行为对外呈现;而强互惠的现代演化则是以抽象的制度结构为中心的自创生过程,最终是以制度的实施对外呈现。我们注意到,制度的实施在现实社会中需要借助具体的个体行为来完成,尽管这一过程本身可以完全去个体性,该个体行为可以并非出自其私人的情感伦理或者价值观本意,而纯粹只是一种制度性操作。这意味着,强互惠现代演化中的制度结构设置重点应在于制度本身,排除制度实施对具体行为人的依赖,以去个体性作为制度建构的基本逻辑。同时,强互惠利他惩罚的实施程序的制度化,也是制度演化的重要方面,不仅能增强现代形态强互惠的合法性认同,还经过去个体性排除对实施行为的可能扰动。在这个逻辑方向上,人工智能成果的广泛运用可以有效推进现代形态强互惠结构制度化、程序化的社会实践,这会成为其现代演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然而基于古典演化与现代演化的统一性,我们也认为,强互惠制度结构并不排除其利他惩罚执行节点上的具体行为人同时是古典形态的强互惠者的可能性,尽管不是必须,但这仍然意味着去个体性框架设置并不抵触个体性的同向度有意识地结合与参与,并且这样的结合模式事实上形成了更有力的强互惠制度结构。
我们可以考察一个特殊的近似古典演化逻辑的强互惠形态结构,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单纯的政治参与型政党,首先是一个社会中先进分子集合的团体,其先进性正是在于这些个体能自觉地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维护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制度安排的强烈的强互惠倾向。之所以可以将其视同为古典形态的强互惠来研究,是因为其在组织特征之外还表现出明显的个体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选择培养和发展对象上,设定的是其群体中凸显的初步具备先进性的强互惠倾向个体,并在其后的组织过程中以先进性强互惠性为方向不断塑造该个体。我们注意到,尽管组织中的个体被制度化群体整合,并且以群体的方式对外标识,但作为具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在社会系统的制度行为中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个体性特征,在此过程中组织性仍是一种团结意志统一认知的结构性力量。基于这样的逻辑,我们几乎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将中国社会中的强互惠倾向的自然个体组织起来,并以先进的思想不断锻炼提升其强互惠品质,使其能更好服务于社会的一个制度化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表现为严密的系统性结构,但在社会系统中,并非直接以其自身结构对外发生作用,其特殊性恰恰在于,将其培养的党员同志广泛置于从功能性系统到非功能性系统的整个社会系统结构中,包括现代形态的强互惠结构,以这些个体的先进性特征更有效率完成制度性强互惠行为,同时也依托系统结构获得自身组织性体系。各种经验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凡是存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系统结构,都能因其认真负责以及引领担当的个体性影响而成功实现制度性系统功能,形成更有力的强互惠制度结构。在特殊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结构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在一个开放系统中,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的强互惠由于承受环境压力的差异,表现出来的演化节奏速率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结构错置的社会问题,即现代演化的强互惠对内可能遭遇古典演化的强互惠力量的摩擦。基于观察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古典演化的强互惠个体的组织集合体,至少具备两大制度优势藉以有效弥合社会的错置结构。其一,分布的广泛性。能最大限度地根植于社会系统的各个结构,有效实现结构性认知协调,避免类似西方社会的撕裂发生。其二,组织的有序性。能逐次向上层强互惠结构的制度设计输送信息,确保各个社会系统结构中的诉求在制度演化中得到足够关照。由此,我们可以用两个加强获得两个实现作为未来这一研究方向的目标,即加强现代强互惠结构演化的制度协调、加强古典强互惠演化的组织化建设,从而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同时有效传承文化传统、实现现代形态的强互惠结构的强制最低限度化,进而达到和谐境界。
参考文献:
[1] GINTIS, HERBERT. Strong Reciprocity and Human Sociality[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0,206(2):169-179.
[2] GINTIS,HERBERT,SAMUEL BOWLES,ROBERT BOYD,ERNST FEHR. Explaining Altruistic Behavior in Humans[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3,24(3):153-172.
[3] BOWLES,SAMUEL,HERBERT GINTIS.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J].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2004,65(1):17-28.
[4] FEHR,ERNST,SIMON G?CHTER.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umans[J].Nature,2002,415(1):137-140.
[5] 李建德.制度及其演化——方法與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64.
[6] BOWLES,SAMUEL,ERNST FEHR,HERBERT GINTIS . Strong Reciprocity may Evolve with or without Group Selection[R].Santa F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2003.
[7] FEHR, ERNS,DOMINIQUE J.-F. DE QUERVAIN,et al. The Neural Basis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J].Science,2004,305(5688):1254-1258.
[8] GINTIS,SMITH,BOWLES. Costly Signaling and Cooperation[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2001,213(1):103-119.
[9] S?NCHEZ,ANGEL,JOSE A. CUESTA. Altruism may Arise from Individual Selection[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05,235(3):233-240.
[10] CALDER?N,JUAN PABLO,ROBERTO ZARAMA. How Learning Affects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J].Adaptive Behavior,2006,14(3):211-221.
[11] G?CHTER S.,HERRMANN B. The Limits of Self-Governance When Cooperators Get Punished: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Urban and Rural Russia[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11,55(2):193-210.
[12] WEERD,HARMEN,RINEKE VERBRUGG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J].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2011,290:88-103.
[13] 王覃刚.关于强互惠及政府型强互惠理论的研究[J].经济问题,2007(1):10-12.
[14] 王覃刚.制度演化:政府型强互惠模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153.
[15] 王覃刚.强互惠理论扩展中的核心概念界说[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4):24-30.
[16] 王覃刚,冀红梅.基于强互惠理论的自创生社会系统研究框架探讨[J].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9(1):115-127.
[17] FILED,ALEXANDER. Altruistially Inclind[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152.
[18] WAEL,FRANS. The Age of Empathy:Natures Lessons for a Kinder Society[M].Harmony Press,2009:274.
[19] 叶航.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J].经济研究,2012(8):132-145.
[20] 费尔.社会偏好和大脑. 格莱姆齐,费尔,凯莫勒,波达瑞克.神经经济学:决策与大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13-314.
[21] MARLOWE F.,BERBESQUE J. C. More 'Altruistic' Punishment in Larger Societies[J]. The Royal Society:Biological Sciences,2008,275(1634):587-590.
[22] NIKIFORAKIS N.,ENGELMANN D. Altruistic and the Threat of Feud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2011,78(3):319-332.
[23] GEERTZ,CLIFFORD.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27.
[24] VROMAN,JACK J. Economic Evolution:An E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M]. London:Routledge,1995:128.
(责任编辑:彭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