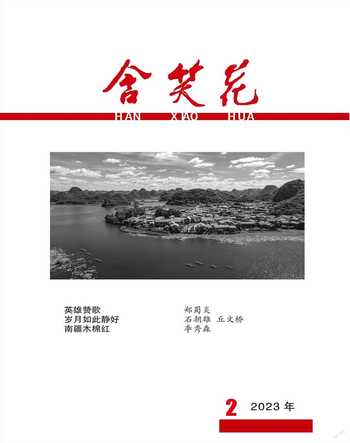忆母亲
2023-05-30汤和云
汤和云
我从来没有给母亲过上一次生日,更不用说什么“母亲节”的。
我母亲是广西靖西县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十六岁的她嫁到富宁县胡家为妻,生得二子(长我十多岁的大哥、二哥),五十年代胡家开始没落,母亲被遗弃后独自携二子在富宁西街务农艰难地生活,后经人撮合改嫁南下富宁干部——我的父亲。
母亲是个勤劳、贤惠、温顺而朗爽的壮家妇女,这是街坊邻居所公认的,唯一缺憾的就是没文化,但在他们那个艰难的年代里这并不妨碍日常生活。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乐观开朗的性格,面对生活的重压,社会现实的残酷,她都是以笑脸应对。她就像一头任劳任怨憨厚的牛,无怨无悔、甘心情愿、忍辱负重、竭尽全力地去维系着这个家。
我的母亲没有华丽的服装,从来没有穿过一双凉鞋更不用说什么球鞋和皮鞋的了,连袜子都没穿过一双。一年四季两套典型自织的壮族土布姊妹装,便是她唯一修饰自己的衣着,夏天头上裹着花叶相间的针织毛巾,算是遮阳挡酷,入冬一件自己缝制的土棉袄捂住身子,算是驱寒保暖,一双自己做的千层底布鞋,是她最为得意的杰作了。
母亲个子不高,身子瘦弱且很早就佝偻驼背了,一双满是老茧褶皱变形的手见证着她的辛苦劳累,脸上棕色的皱褶里是饱经风霜和苦难的印证,皱皱的嘴唇中牙齿已是残缺不齐了,一双眼睛已模糊不清,戴着一副没有耳挂的老花眼镜,大凡闲余她都在麻线兜旁穿针引线,为子女们增添和缝补衣物,那双已被生活压弯了的腿支撑着那弯拱的背,当她累到需要起身时,只见她双手掐住腰部很吃力地慢慢撑起整个身子,然后仰天长呼一口气悲腔地叹道:“喔咩呦!”(壮语,我妈呀)有时我偶然会看到她那两眼饱含着盈盈泪水……
母亲不知疲倦勤于劳作的作风和不屈不挠刻力奋发的精神,常常使我不自觉中暗露出一种无力的担忧。“这样活法不会累死的吗?”我常常望着她的身影疑问,她就像一部机器开了闸就拼命地疯转着不会停歇那样令我心弦。
儿多母苦啊!全家六姊妹八口人,就靠我父亲一人的工资过日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的,后来稍有改变,大哥小學还没毕业遇上富宁段323国道开工,未满十三岁的他就自告奋勇地去参加公路建设工程队的了,能有饭吃还得一定的生活补贴。二哥初中毕业,就在本县团结街生产队兼任一名会计工作。我姐毕业被招到富宁木央公社道班当上一名养路工人,直到1963年初我开始步入学堂后,家里才总算缓过常年挨饿的窘迫的困惑。
母亲很勤快,地地道道的壮族传统造就了她朴实勤劳的本性,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具有本民族传统勤奋基因的传承和熏染,她自然就能掌握许多生活的基本常识及生存技巧。
我母亲的手艺不错,从她手下酿出的那豆腐雪白、鲜嫩、饱满、均匀透体,让人垂涎三尺。母亲的豆腐经常才挑到街上不一会儿就卖完了,甚至还没挑到街上,路途中就被人们抢光了,就连供销社食堂都专门订她的豆腐。这下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从每天生产两槽豆腐,增加到四槽再到六槽。
当时家里的燃料来源都是我和父亲去落实,一般上山砍柴和到煤厂捡煤,那是我分内的事。家里若有钱偶尔会到市场和煤厂买一些,可是父亲老舍不得掏钱,母亲卖豆腐收入那点钱,精打细算下来也没多少利润。母亲不太会做生意,她只知道我买了三块钱的黄豆,做了一槽豆腐,卖了五块钱,反正赚了两块钱就行啦,却不知人工费、燃料费、水电费等等之类成本要开支。其结果我给她细算下来,她做的豆腐几乎是亏本的,为此父亲大怒几次砸了她的豆腐设备。母亲就是不甘心,父亲砸了她又做,做了又被父亲砸。
母亲的倔强,即便强悍霸道的父亲也只能罢手。接下来往后的日子里,为了母亲我只能默默地付出自己的辛劳,每逢假期或星期六、星期天,我便很自觉的上山砍柴,挑着撮箕到煤厂去捡煤渣,到田边地角、山洼箐沟里去捡拾枯枝、干草,以弥补家中燃料不足。
母亲每天凌晨鸡叫就起,我也不得不早起,怕母亲累垮我得帮她。磨豆、烧火、煮豆浆、起锅、扭浆、摊豆腐模板、压豆腐,这些工序我都学会的了,我是母亲唯一得力助手。每当天蒙蒙亮时,我们的一两槽豆腐就做好了,把它切成见方等同的方块大小,放在有水的两只木桶里,然后母亲挑起两桶满满的豆腐就兴匆匆地出门去的了。
朦胧的清晨,望着渐渐远去的母亲背影,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什么感受,肚里五味杂陈只觉得内心一阵阵酸涩,眼前一片模糊起来……
在那个饿得心慌发昏的年代里,母亲成了家里最坚强得力的“后勤部长”。她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四方寻觅能充饥的食物,田间散谷、山间野菜、河里虾虫、沟里的爬虫、菜园里的地龙、芒棒皮、芭蕉芋等等,大凡只要能吃的她都毫不客气、也不嫌弃地整背整背地搬回家里。
这样一来家里吃的问题是基本解决了,可餐餐清一色的野菜苞谷饭、野菜芭蕉稀饭,这就是我家当时的一天两顿的正餐伙食标准了。菜只是一碗无油的汤,常常都是南瓜老苞谷汤,要么就是萝卜老青菜汤,再就是干菜红薯汤了,能吃上一顿油荤的,还是父亲从单位食堂带回来的不轻易有的别人吃剩的那汤汤水水,一家人最好的那顿饭只能渴望着逢年过节的尽早到来。
那时,街坊邻居只要有哪家偶然冒出一丝油熏肉味时,谁都突然嗅觉灵敏般的一惊地馋涎欲滴的四周顾盼,你会原地定住,马上闭目养神那般,贪恋的深深深呼着这久违诱人的香味,梦幻式的进入鱼肉满桌大吃大喝的场景。
母亲那瘦弱矮小的身躯,那双压弯变了形的腿,那稀疏苍老的白发,那双坠着严重眼袋已失去神韵的眼框,每每让我想起都痛彻心扉。我没法用语言和文字去准确勾勒出母亲的形象,所以我一直不敢去写,也不敢去画她,因为我那天生就情感脆弱的泪,会情不自禁地滚落出来的,以致会摧毁我本就十分薄弱的点点意志。
母亲,儿子想你、好想你啊!这也是我步入晚年来,常常自我自慰的一种精神寄托与祈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