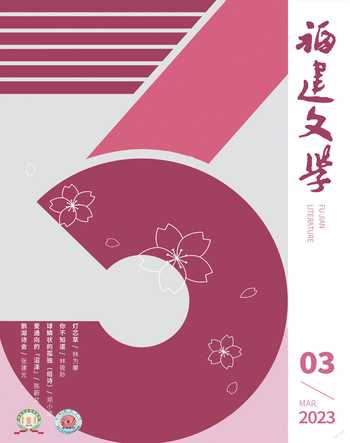朱马的河流
2023-05-30安庆
安庆
斑鸠河岸的向日葵又开了,河水变成了金色,斑鸠掠过河床,在看不见的树上叫,河谷里发出回声。我想起朱马,那个喜欢河滩,走在斑鸠河边的青年。
河水流动着,我仿佛看见站在岸边的朱马,看见了笨重的老木船,船上又长又粗的缆绳。那时候,斑鸠河上还没有那么多桥,从我们这里过河主要靠的就是一条老船。朱马偶尔会早早地到河边去,把那条老木船拽到河的中间,让等船的人在岸上急。认得他的人在岸边喊,朱马,快把船摇过来,你占着一条船干什么?他在船上笑,笑得有些贼,笑够了,才把船悠悠拽过去,自己则走向离船几十米的河滩,“扑通”一声跳进河里。朱马一身好水性,在河床里变换着姿势,然后躺在草地上,浑身白白嫩嫩的,像一个乡村的异类。那些年斑鸠河里还有过鹰船,一个人站在舢板上,两头立着两只鹰,船上的人一个手势,鱼鹰钻进水里,出水时叼着大大小小的鱼。朱马喜欢鹰船,跟着鹰船跑,鹰船快起来,他在河滩上追着,有时会钻进水里,在河水里撵着鹰船。如果长时间看不到鹰船,朱马会坐在河边等,终于等到了一只鹰船,高兴地跳起来,再一次跟着鹰船跑。朱马曾经有一个理想,就是有自己的一只小鹰船,顺水而行,在水上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朱马的父亲是个老师,就在我们村教小学,有一年得了急病,突然不在了。父亲出殡那天,朱马的哭声很凄厉,后来我们又见过朱马独自到父亲的坟上去,坐在父亲的坟前,望着河水,他们家的坟地就在斑鸠河的岸边。父亲不在的第二年,朱马离开了瓦塘,去了城关的机械厂,传说是朱马的母亲去找了朱马的一个表叔,那个表叔当时在城关镇当镇长,朱马那一年就成了一个工人。城关镇离县城近,他差不多就是去了城里,成了半个城里人,我们不能再天天看到朱马了。好在朱马星期天是回来的,他骑一辆加重自行车,走的是从城关到瓦塘的河堤路,河床里汪着明亮的河水,有时他会停下来,瞅着河床,寻找着鹰船。朱马偶尔会穿工作服回到瓦塘,就是那个时代流行的劳动衣,上下都有兜的那种,在村庄里显得洋气。他的头发变得有形了,有几分流气。他给我们讲厂里的事,讲他下班后和厂里的同事去城里逛街,在小酒馆喝酒,喝多了打架。当然也讲厂里的女工,她们身上的脂粉气,下了班换一身漂亮的服装像换了个人,也有跟着男同事出去逛街进小酒馆的。朱马后来回来得越来越少了,可能是两个星期回来一次,也会偶尔在调班后突然回来,这种情况大都是在夜里,河堤上洒满了月光。他在我们家的门口打铃铛,哥哥就带我偷偷地出来,在辽阔的麦场里,他把刚学了几招的摔跤方式教给我们。我说的我们,包括我哥和我、朱马的弟弟朱羊。我们看着夜色里蘑菇样的麦秸垛,麦秸垛顶上糊着一层干泥,月色洒在干泥上。我们听到了叽叽的叫声,麦秸垛上藏着麻雀,往身边的麦秸垛上一捅,麻雀呼啦啦飞起来,翅膀声在夜色里很响,带着风。我们看着另外的麦秸垛,想象着每个麦秸垛里的麻雀,朱马把脚步放慢,挥着手示意我们离开。我们小心翼翼地绕过麦秸垛,走出麦场,各自回家。后来我们去河滩上或野地里,在黄昏的河滩看着朱马施展着手脚,河水在夜色里静静地流淌,偶尔有野鸟飞过河床。朱马望着斑鸠河说,好几年没看到过鹰船了。他的语气里透着期待,也有一种失落。
朱马是两年后回到瓦塘的,也就是说他不再去机械厂,或者被机械厂开除了。那一年朱马的表叔已经不再在城关镇,调到了另一个乡镇工作。据说朱马是因为和一个女孩接触,与另外一个男孩打架被除名的。也有人说朱马离开机械厂,和他的表叔离开城关镇有关,那个厂长和朱马的表叔不是一个阵线,忍气吞声了好几年,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逐渐离开机械厂的,还有另外和镇长有关系的人。朱马对我们说的则是机械厂减员,他因为工作时间短被裁下来。朱马的母亲又去找过那个表叔,表叔答应在他调到的那个镇里为朱马再找一份工作,那个镇里有榨油厂和酒厂,可朱马拒绝了。那一年朱马的弟弟朱羊初中毕业,初中毕业的朱羊不再上学,开始在地里劳动了。
朱马从机械厂回来后变得沉默,他更多的是去斑鸠河边。不知道这条河为什么叫斑鸠河,我们那一带的斑鸠的确很多,除了麻雀多,就是斑鸠了。但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斑鸠的叫声,很少看见斑鸠成群搭伙地飞,斑鸠的性格可能比较内向。不过,我和朱马是在斑鸠河边见到斑鸠的,黑色或灰色的斑鸠排在河滩上,它们在河边喝水,寻觅河滩上的草籽。那几年,斑鸠河上修了不少的桥,那条老船在岸边泊了一阵,被拖上岸,不知最后放到了哪里。离开机械厂的那一阵日子,朱马就在原来站船的地方坐着,望着河,我们去河边找过朱马,在朱马的旁边坐下来。河水在河床里流着,树在岸边摇曳,偶尔也会看见河边喝水的斑鸠。朱马沿着河滩往下游走时,我们也跟着朱马走,河滩上软软的,太软的地方能让脚陷进去,拔出的一束草根带着泥水,草根是白色的。我们把草栽回坑里,再用脚踩实,这样重新栽下的草才可能活过来。
几个月后,朱马又活了过来。
有一天,朱马忽然站起来,说了一句,机械厂,算什么!他手里抓着两团泥,扔进了河里。他还说了一句很时髦的话,让过去的过去吧!那天傍晚他还在河滩上唱了歌,我现在还记得几句:“大雪纷纷扫门外,我和你姐谈恋爱,谁知恁爹知道了,抽了我两皮带……”我还记得他唱的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河水荡漾着,岸上的树摇晃起来。那天傍晚,朱马撇下我们,独自跑向了河的对岸,他在站到桥上时,又吼了几声,然后沿着对岸的河堤,呱嗒呱嗒地跑,他的脚步声我们都能听见,他从另一座桥上跑回了我们的村庄瓦塘。
活过来的朱马,开始经常到县城去,也会在县城里住下来。县城里有了舞厅,有了酒吧,他和城里的朋友到那些地方去,掂着酒瓶,在舞厅里摇晃。朱马说,他其实不喜欢那些地方,更多的时候他和那些城里的年轻人,到一片城边的河滩去,在那里摔跤、练拳。那是一条护城河,河边长满了芦苇。他们也到夜色的体育场里,摔上一阵,而后坐在空荡荡的看台上,抽烟。
那个重新活起来的朱马变得开放或者放荡。朱马家开始热闹,常有从县城里来的青年到朱马家来,他们骑着飞鸽牌或永久牌自行车,有人身上背著乐器,一把吉他或一根笛子。朱马在城里竟有这么多的朋友。当然,我们村里年纪大的人都叫他们混混,甚至说他们都是流氓,不干活,天天流窜。城里人到底不一样,他们穿着新潮,留着各种发型,在朱马家,他们就坐在自行车上,腿支着地,大声地聊天,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那些歌都和爱情、女人以及流浪有关,有一个人喜欢唱《拉兹之歌》,就是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那首:“到处流浪,哈——到处流浪,哈——命运伴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哈——到处流浪,哈——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到处流浪……”几个人和着跟着唱。他们中偶尔会有女孩过来,唱着《流浪者》中的《丽达之歌》,唱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们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的路上飞奔,一起去看斑鸠河,唱着《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夏天的时候扑通跳进河里,河水里游动着年轻的身体。他们在麦场里打拳,甩着长长的头发,好多人都围在麦场里。城里的人走后,我哥,我,朱马和他的弟弟朱羊,继续在麦场里练拳,练摔跤。摔在地上很疼,朱马把我抓起来,要我继续练。所以说,我是练过几套摔跤的,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经忘掉。
那些城里人里来得最多的是二子,二子不但来得勤,还经常在朱马家住下来。我现在还能想起二子的那辆自行车,绿色的,28或者26的车。二子留下来的时间长了,和我们熟络起来。二子吹得一手好口哨,有时候我们正聊着天,二子会忽然吹响悠扬的口哨,有时是模仿小鸟的叫声,婉转嘹亮。我记得我和朱羊赶着驴车,走十几里地,去临县的北阳面粉厂换面,就是用小麦换回面粉。二子跟着我们坐在驴车上,驴车上的人比麦子要重得多。二子一路上吹着口哨,吹得最多的还是《拉兹之歌》,他噘着嘴,口哨从他的嘴里一声一声地溢出来,偶尔会有布谷鸟的叫声。给麦子过磅开票的是一个白净的女孩,二子睁大眼睛看女孩,装作去看她给我们开票,往女孩的身上挤,女孩的身子扭了扭,往里边挪,二子头一歪撞在了女孩乌黑的长发上。我们听见二子夸着女孩,你真好看,头发真滑。声音放低,完全不是平常顽劣的二子。然后,面粉很快换好了,在离开面粉厂时,二子又一次朝开票的女孩看过去,朝人家挥手,喊着拜拜——我们赶着驴车赶紧离开,二子的哨子响起来,这一次不是吹着口哨,是手指弯进嘴里,打出响亮的口哨声,口哨长长的,像一种告别,二子的脸憋得红红的。二子后来说,那个女孩真美,这样说着,他又吹起了口哨,口哨低低的,像对一个人的思念。可我们很少去换面,再次换面大概是一个多月两個月后,二子好像一直在关注着我们换面的这件事。他住在朱马家时又赶上了,依然是我和朱羊赶着驴车,加上吹着口哨的二子。这一次给我们过秤开票的还是那个女孩儿,二子一直直直地盯着人家看,女孩的脸红红的。二子说,你们这里招人吗?我想来你们面粉厂上班。女孩红着脸,低着头。二子好像是认真的,继续说,主要是想天天看到你。二子的话让我们怀疑他一见钟情,真的喜欢上了那个女孩儿。不料那女孩这次回话了,很坚定地说,不招!又补一句,招也不招你们那儿的,我们的人还用不完!这一次女孩甩了一下头发。二子叹了一口气,不服,说,你去过卫城吗?卫城就是我们的县城。女孩又甩了一下头发,不去!朱羊去拉二子,说走吧。又有人来过秤,二子被朱羊拉了出来。
那天离开,二子又吹响了口哨,口哨应该是好多人都听到了,出来了几个人,朝我们看,我看见在人群中,有那个女孩儿。我捅了捅二子,二子从车上站起来,又吹了几声响亮的口哨。驴车嗒嗒地走在回程的路上,二子不说话,偶尔吹起一段口哨,口哨弯弯绕绕的,有些低沉。回想起来,那不过是生活中的一段乐趣,是生活中偶然的,甜蜜又忧伤的回忆或插科打诨,那个姑娘的回忆里或许会保存很多年的口哨声。
我现在还记得朱马的那件风衣,浅绿色的,他敞着怀,走在瓦塘的大街上,骑着车到另一个村庄去。可能是他结交城里朋友的名声,他在周围的村庄也结识了很多的同龄人。他到周围的村庄去,周围村庄的年轻人也开始到朱马家来,那几年朱马家的粮食常常不够吃,有几次家里来了年轻人,朱马的母亲到我们家借面。就是这样,朱马还很慷慨,和他们一起喝酒。朱马手里很拮据,他找人借钱,也会出去几天,回来后把借的钱还了。我们后来才知道,朱马是去外边打了几天零工,有一个朋友在搬运站,他在那里干几天装卸的活儿,手里会挣下一些活钱,他把一些钱缴给母亲,让母亲买油盐酱醋用。冬天来临前,他又去了搬运站,几天后有人送过来几百斤煤,屋里的炉子可以燃起来。这事儿,是哥哥偷偷对我说的,哥哥和他去过搬运站。哥哥说朱马不让别人知道,要替他保密。
可能是又挣了一笔钱,那一年,朱马买了一台录音机,那种带提手的,有两块砖头那样大。他拎着录音机在村街上招摇,带电池的录音机里放着当时流行的歌,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程琳的《黄土高坡》,一个台湾歌手的《新鞋子,旧鞋子》……朱马的身后会跟着几个小孩子,我有时也跟着,他会让我拎一会儿录音机,录音机的喇叭震着我的手,唱歌的声音格外清晰。晚上我们就坐在他家院子里听歌,也拎着录音机到麦场上、到村堤上、到河边去。我们在村外的大路上跟着录音机唱,朱马的身子在夜晚的路上摇起来,朱马告诉我们他摇的是迪斯科,他一边摇一边唱着:“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儿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记着我的情,记着我的爱,记着有我天天在等待,我在等着你回来,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二子还是不断地到我们瓦塘来,他们骑着车去赶附近村庄的庙会,总会有吃饭喝酒的地方。他们出门时喜欢带着那台手提的录音机,二子在录音机上加了长带子,挎在身上,一路走一路唱,一路招摇,特别的另类。他们走在庙会的人群里,录音机会突然响起来,二子的指头弯在嘴里,口哨声从他的头顶绕出来,在天上飞。他们在庙会和集市上格外招眼,二子有时朝身边的女孩吆喝着:妹妹!几个女孩一边回头看,一边躲着他们。其中一个女孩的酒窝很深,穿着时尚,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挥着手表示回应,可她还是被同伴拉着躲开了。那几年,朱马和城里的二子就这样浪荡地生活着,像一股旋风,影响了乡村的风气。
朱马隔一段时间还是会离开村庄一段日子,谁也弄不清他到底去了哪里,去干了什么。我哥说,他不但去搬运站,也去干另外的活儿,那帮城里的伙伴干什么的都有。有人看见朱马在很远的一个乡镇,帮人竖过线杆。他曾想和几个人合伙在城西的一个老厂里办个煤场,没有成功。他其实一直在折腾,或者想折腾点什么。朱马办的一件让村里人服气的正事,是把朱羊送到了部队,在北京当警卫。用我们当地的话说,朱羊是当了“样兵”。朱羊个高,不大爱说话,但符合一个“样兵”的标准,身体特棒,会一点武术,就是朱马教我们的摔跤和拳。那个年代当兵的指标很紧,竞争很激烈,朱马是找城里的朋友帮弟弟弄了一个指标,那个朋友的父亲在县里的武装部,朱马还请了几次客。就这样朱羊去了北京,我们看到了朱羊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前的照片。
那一年,朱马在老塘镇遇到了范葵花,范葵花的目标就是找一个高个白净的男人,朱马完全符合她的标准。朱马不但白净,像一个白面书生,而且身高一米八多。范葵花也瘦瘦高高的,皮肤白皙,眼睛格外有神,嘴唇下有一颗痦子。两个人相遇时都有一种惊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范葵花暗暗窃喜,我心里的白马王子不就是这样的吗?那一天,朱马的头发长长的,穿着风衣,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前,风吹动他的衣襟,有点电视里上海滩的味道。两个人也算是心意相通了,范葵花就住在镇上,朱马去镇里的次数更加频繁,这样来来去去的,他们在那个冬天就择了吉日,办了婚礼。朱马结识的人很多,婚礼那天,热热闹闹的,二子提前过来忙碌着。朱马和范葵花的日子就如此开始了。
朱马游荡的日子有些收敛,不过,朱马还是会隔一段时间离开瓦塘几天,回来时会给范葵花买她喜欢吃的东西,给范葵花一些零花钱。范葵花有些疑惑,问,朱马,你这几天到底去了哪儿,去干了什么?你,你这钱是,是怎么来的?朱马说,你不用问,这钱你该花就花。范葵花摸了一下他的脸,捋了一下他的头发,说,朱马你可千万不要干傻事,我要你干干净净的。朱马伸出手来搂范葵花,说,你放心,我不会的,你不用担心。范葵花去拉他的手,摸到了他手上的一块硬皮,把手放到她的脸上,有些粗粝。她把手拿下来,放在自己的胸前,有些心疼,问,你的手怎么了?朱马没有把手抽出来,任葵花抚摩着,他说,没事,我这几天去给我在厂里时的师傅帮了几天忙,给别人加工了几样东西。葵花长舒了一口气,紧紧地抚着他的手。朱马躺下来,好像很困,一直睡了几个小时。他醒来已是夜半,外边响起沙沙的细雪声。他看着睡着的范葵花,想他这几天在搬运站的生活,他们说,朱马,你如果能坚持,就来搬运站上班吧。朱马没有答应,他不想天天守在搬运站里,不想天天不在葵花的身边,对朋友说,谢谢你们能容许我过来打短工。葵花醒了,把朱马往被窝深处拽,把他的头摁到了自己的胸前。葵花是真喜欢朱马的,朱马不像传说的那么流气,没有那样痞,她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男人,包括他的浑身上下都是白白净净的。
可是,朱马出事了。
朱马出事也是在河边,那是朱马和葵花结婚后的第三年夏天。那个午后,河滩上的向日葵还在黄金般开放着,河水里倒映着杨树柳树的影子,斑鸠河边的斑鸠依然在河边叫着,掠过河床的还是五颜六色的蜻蜓,河也是彩色的。就是这个美好的午后,朱马掉进了河里,永远属于了斑鸠河。他是下河救一个在水边玩耍的女孩,那个女孩才幾岁。他是走在斑鸠河边时听到了一个女孩的求救声,第一声喊过后,第二声隐隐约约地才能听到,紧接着是另一个女孩的喊声,那个女孩一边看着滑下去的女孩一边哭喊着。朱马拼命地寻找着,他看见了河里的小旋涡,两只小手在朝上举着,露出小小的手指。他扑了下去,抓住了正在下沉的女孩,喘息着把女孩托上来。可他被水冲走了,他忽然感到了一阵晕眩,没有了力气,他最后的喘息变成了河面上浑浊的水泡,等人赶到时,他还在水里往下冲,在水里挣扎,渐渐地没有了力气。斑鸠河边的麻雀和斑鸠突然发出惊悚的叫声,大片的麻雀在河面上盘旋,蜻蜓配合着麻雀和斑鸠,紧跟着被冲下去的身体嘶鸣着。他在生命的最后看到了彩色的河流,听到群鸟的哀鸣,任河床把他往下边冲,冲到几百米外的河坝。那天中午,朱马是喝了酒从县城骑车回来的,听到了女孩的喊声,他一个激灵,酒醒了许多,跳下河救出了女孩。葵花是挺着肚子跑到河边的,她在那个午后一边捂着凸起的腹部,一边号啕大哭。麻雀在头顶一圈一圈地盘旋着,叽叽喳喳地鸣叫,朱马离去的地方距当年的渡口很近,只是早没有了那只木船。
朱羊请假匆匆赶回来时,看到的是一方新坟,他在哥哥的坟前悲恸大哭。朱马的坟地就在斑鸠河的附近,他可以天天听着斑鸠河的流水声,可以天天看到陪了他近三十年的斑鸠河了。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关于见义勇为的说法,如果是现在,朱马可能就是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当时县里有一家小报,小报的一个记者听说后,写了一篇报道就过去了。朱马的葬礼和他的婚礼一样来了很多人,那些人一直把朱马的灵柩送到坟地,他们抓着土,把朱马埋到了河岸上那片泥土里。
范葵花是在生过孩子后离开瓦塘的,她给孩子取名叫朱小马,临走时对朱马的母亲说,孩子永远都是你的孙子,他会一直姓朱,一直叫朱小马。范葵花把葵花籽种到了朱马的坟地周围,此后的每年,她都会在朱马的坟地种上葵花。在斑鸠河岸上,如果你看见一片孤独又蓊郁的向日葵,那里就是朱马安葬的地方。
葵花回到了娘家村老塘,老塘镇里依旧隔几天一个集日,日益地繁华着,叫卖声充斥着街道。葵花就站在热闹的街道上,在人群里寻找着一个穿风衣的身影,那个身影迈着大步走在街市上。她喃喃地念叨着朱马的名字,淌着泪,在人群里仿佛又看到了朱马,美好的时光竟然如此的短暂。
范葵花在孩子一岁后,在镇里开了家裁缝店,名字就叫“葵花裁缝铺”。有时她的身边会跟着孩子,孩子慢慢在长,会牙牙学语,会喊妈妈,会说简单的话了。孩子在铺子里蹒跚地走来走去,有一天突然说出了,爸,爸爸,爸……葵花愣住了,蹲下来,看着孩子,你喊,喊,爸爸,爸爸……孩子嘟噜着嘴,嘟噜出爸爸……葵花把孩子搂紧在怀里,眼泪扑簌地流下来。她抱着孩子走到大街。那天又是老塘镇的集日,大街上摆满了摊子,充满了摊贩的吆喝声。她抱着孩子在人缝里寻找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走了个来回。她知道,穿风衣的朱马永远不可能回来了,只是她眼前还常常出现一种幻觉,让她觉得穿风衣的朱马就站在她的眼前。孩子嘟噜嘴再喊爸爸时,她在房间里寻找着,好像朱马就站在房间的某个角落。她问孩子,爸爸在哪里?她握着孩子的手指说,你指指,爸爸在哪里?孩子迷茫地看着母亲,嘟着嘴,喊出的是妈妈,嘴角流着口水。
在无人的夜晚,她守在裁缝铺里,常常陷入对时光的回忆,她的眼前又是那片河滩,耳边是斑鸠河边上斑鸠的叫声。她朝大街看过去,夜晚的老塘镇是沉寂的,清冷的,大街上只有零星的店铺开着,晃动着寥落的人影。她喃喃自语,像在叙述,像在背着刻在记忆里的日记:某一天,我们在老塘镇的集日上认识,我跟着你去见你朋友,和你回家……一天夜晚,我看到了你手上的茧子,实际上我猜到了你去干什么……这样自语着,禁不住又扑簌地流下泪水。
范葵花的裁缝铺渐渐地在镇上有了名气,生意越发地好起来,范葵花天天忙碌着,孩子由她的母亲和家人照顾着。当然也有油头粉面的小青年到店里来,他们的嘴里还带着酒气,他们在葵花店里做服装,在镇里的十字路口的饭馆里吃饭喝酒,邀请过范葵花过去一起吃。葵花每次都威严地拒绝了。
二子经常到老塘镇上来,还是骑着那辆28或26的自行车。他默默地守在裁缝铺里,帮葵花打理一些杂务。二子一直在等葵花,葵花心里明白,只是她在心里解不掉那个结,即使再有一次婚姻,也要等到朱马去世三年之后。她先是拒绝二子到店里来,她不知道该怎样向人介绍,慢慢地,她把抵触变成了沉默或者默认,开始大大咧咧地对人介绍,二子是朱马的老朋友,朱小马的叔叔。他们在夏天会忽然去到斑鸠河边,去看朱马坟地周围盛开的葵花,在灿烂的葵花下,收拾着墓地上的野草,二子也会吹出低低的口哨。一直就这样,二子和葵花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他不想有任何的冒犯。有一次,二子喝了酒,坐在裁缝铺里,借着酒气说,葵花,是朱马让我照顾你!葵花从缝纫机上抬起头,看着二子,他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是有什么预感吗?二子含着泪水,说,他说过,朱马有时候就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心里总好像装着一种愧疚,他每次出去其实都是去外边找地方挣钱,他要让你手头有零花钱,他一直想干点事儿。有一次朱马和我一起喝酒,他喝得太多了,不知道他怎么就对我说,二子,如果我万一怎么了,你,你要照顾好葵花……二子的手和声音颤抖着,低着头。
葵花和二子的婚姻是在朱马去世三周年之后,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范葵花的裁缝铺里撒满了金色葵花,他们在婚礼前,拎着酒去过朱马的墓地,告诉朱马他们要结婚的事。二子经常到镇上来,他愿意和葵花守在裁缝铺里,如果葵花不愿意到城里去,他愿意搬到镇上来。几年后,葵花还是跟二子去了县城。二子的家就在县城里的戏院街,离热闹的马市街很近。老戏院门前有一家有名的饺子馆和一家人气很旺的胡辣汤店,和戏院街相邻的是石榴巷,石榴巷每年都开满了石榴花。葵花把裁缝铺开在饺子店右边的胡同口,离饺子店不远是一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喜欢吃饺子和喝胡辣汤,也到葵花的裁缝铺里去,后来成为裁缝铺里的常客。
那一年,朱羊从部队复员了,有一天他找到了葵花的服装店,这一次,朱羊是带了新婚妻子来。朱小马已经上小学了,学校就在附近的戏院小学,每天放学就会跑到店里来。朱羊是来看孩子的,他抱起侄儿朱小马,新婚妻子把一个红包和玩具放到了孩子手里。那天,二子请朱羊喝了酒,吃了饺子。
二子在罐头厂干了几年下岗了,下岗后的二子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营生,后来他跟着一个皮匠学做皮鞋。学成后,葵花的服装店扩张了,改成了“葵花服装皮鞋店”,夫妻俩认真地经营着,生意如意地火起来。
有一个习惯他们保留着,每年都回一次瓦塘,去看一次斑鸠河,去看河岸上的那片葵花。这一年,他们再去那片葵花地时,看见了一个女孩,手持着一束鲜花站在墓地前,一转眼已经是好多年过去了。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