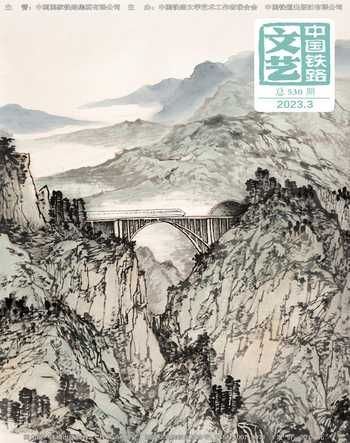在黄土中寻找
2023-05-30李浪浪
作者简介:李浪浪,1994年生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南宁局集团公司柳州工务段。作品散见于《中国铁路文艺》《中国青年作家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文学》等报刊。
没有离开故乡之前,我总想着走出脚下这片土地,去看一眼黄土外面的世界。我老家在渭北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土。父辈们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渭北高原干旱少雨,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光景一直延续到现在。村里人在大自然面前始终都是被动的,风调雨顺是他们一年最大的愿望。很多时候,我觉得故乡是一成不变的。那片黄土塬,那些槐树林,甚至那一道道沟壑都不会变,我回去的时候,它们还是以往的模样。土是黄色的,槐树林在沟壑中沙沙作响,泾河依旧悄无声息地向东流淌着。
故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分量,这取决于一个人对故乡的理解。故乡在我的心中像是一位认识了很久的朋友,是从小陪我长大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谈。在故乡面前,我就是黄土地里长出来的碎娃,皮肤黝黑,脸上挂着高原红,说着关中方言。故乡除了一望无际的黄土,还有满目的沟壑,经过岁月的更迭,一条条沟壑像时间的褶皱一般,记录着故乡的人和事。
渭北高原上,两个人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吃饭了吗?”“我吃了。”“嗯,我也吃了。”这是人们打招呼常用的一句话。直到现在,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依旧是:“你吃饭了没有?”吃饭总是被第一个问到,这与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以前听父亲说过,在他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经常没有饭吃,平时吃的全是高粱面饸饹和馍,到了下半年高粱面都没得吃。白馍细面只有过年那天才能见到,到了冬天实在饿得不行只能吃柿子和萝卜充饥。在渭北,家家户户大多以面食为主,一日三餐基本都是馍和面条,为了养活家里几口人、供孩子读书,日子过得紧,人们只能从嘴里省了又省。
在靠天吃饭的渭北高原,“春雨贵如油”不是一句空话,确确实实如此。春天是耕种的季节,也是一年四季最重要的阶段。对村里人来说,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洋芋、豆角、南瓜、辣椒、黄瓜、茄子、玉米等都是这个时候种的,要是恰好碰上一场春雨,人们可高兴了,远远地在田埂上就能听到有人吼秦腔的声音,浑厚而又洪亮的声音在沟壑里回荡着,这是他们表达喜悦的一种方式。
到了四五月份,正是渭北高原最美的时刻。万物逐渐苏醒的时令,满山的黄土一点点被嫩绿包裹着。苜蓿在荒草底下试探性地发出嫩芽,荠菜已经成了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桃花、杏花在不知晓的夜里已经悄然绽放,花团簇拥,窗台上散落的花瓣定是夜里春风细雨的杰作。泾河东面的杏花林被春风染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远远看去,整座山川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甚是好看。清晨,走在乡间小路上,整片田野上飘着淡淡的杏花香,就连被露水打湿的裤腿上也沾染着野草味的清香。过不了几天,大人、小孩都提着用树枝编成的小笼去北沟里掐苜蓿。苜蓿是春天的馈赠,可以做成麦饭、菜馍,还可以做成拌汤,用苜蓿菜馍蘸着野小蒜配好的辣椒汁是我的最爱,馋得让人直流口水。洋槐花算是开得比较晚了,大约五月中下旬才开花,它和苜蓿不一样,不能一茬一茬地吃个不停。洋槐花的花期比较短,大概两三周之后就会凋谢,洋槐花没有完全盛开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扳花枝了,因为含苞待放的花苞做成的饭菜更加劲道。槐花开满门前的沟壑时,我和奶奶把扳到的洋槐花枝捆成一小捆,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背回去,再一把一把将花苞捋在搪瓷盆里留着第二天做饭用。洋槐花的做法和苜蓿差不多,都能做成菜饼、菜馍、菜疙瘩。不过村里很少有人用洋槐花做拌汤吃,因为它比较甜,做成汤会有些许甜腻。
渭北高原最热的时候是七月份,知了在院里的杏树上能鸣叫一个中午,车前草被太阳晒得软趴趴地躺在地上,燕子在水盆边悄悄地喝几口水后,又忙着去捉小虫子,来喂屋檐下的那一窝幼鸟。小麦一天一个样子,不经意间就由绿变黄了。小时候,到了收麦天,天蒙蒙亮,父亲和奶奶便起床收麦子去了。早晨地里潮湿,镰刀割到麦秆时,麦粒不会轻易脱落,这样就能避免浪费。我也会拿着镰刀学着父亲的样子割麦,父亲总担心我会被镰刀割伤,让我去已收割过的麦地里拾麦穗。拾麦穗是收麦时节我最喜欢做的事,因为拾到的麦穗可以换西瓜吃。下午放学后,我背着碎布做的书包,跳动在一块块收完麦子的麦茬地里,找那些被遗落的麦穗,仿佛我已经品尝到了硕大又甜美的西瓜。“换西瓜!用小麦换西瓜喽!”有一天下午,远远地就听到换瓜人的吆喝声,我背着书包就往家跑。“大大!换西瓜的来了,咱去换西瓜!”“走!去换两个瓜回来吃!”父亲背着小半袋麦子和我去换西瓜。“一斤麦,四斤瓜,一共十斤六两瓜,算你十一斤!两个大瓜还是三个小瓜,你随便挑!”瓜农边说边把称好的麦子倒进自己的蛇皮袋子里。我本来想要三个稍微小点的西瓜,父亲说大点的西瓜甜,在父亲的劝说下,我们最终换了两个大西瓜。
家里的三亩半麦子割完得一周时间,父亲在前面收麦,奶奶在后面捆麦,差不多收到二三十捆的时候,父亲把捆好的麦子装在架子车上,用麻绳捆紧。装完车,我们换着喝几口罐头瓶里的白开水,父亲拉好辕绳,我们姐弟三个用尽全力将架子车艰难地从麦茬地里往外面的土路上推。父亲在前面一边压着架子车辕一边说:“使点劲,再加把劲就到大路上了!”由于年幼力气小,推那几十米的路,我感觉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刚把车子推到大路上,我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喘气。架子车拉到打麦场后,我们将一捆捆麦子整齐地立在打麦场围成一个圆圈,然后等好天气时碾麦。烈日当空,拖拉机拉着麦碾子穿梭在村子里大大小小的打麦场上,这是村里人一年最忙碌的时候。碾麦时,住得近的叔伯都会相互帮忙翻麦、挑麦秆,我站在高高的麦垛上负责踩实麦垛,这样就不怕在大雨天因麦垛被雨水灌透而不经烧。到了晚上,全家人都会睡在打麦场,等深夜的东风吹来时扬麦。由于昼夜温差大,打麦场晚上很凉快,天上的星星看起来很低,似乎伸手就能摘到。起风的时候,父亲会立即起身拿起木锹扬麦,奶奶用扫帚轻轻地扫去麦壳,我和姐姐拿着麦推將父亲扬干净的麦子推成一堆。
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在庄稼人的眼里,粮食就是生命。小时候,全村人每年指望的就是七月的麦子,收成好了,人们这一年的心里才会踏实。若是哪家的麦子因为没及时收割,淋了雨,发了芽,走在路上往往都抬不起头,像霜打了的茄子一般,家里人也只能跟着吃长芽麦。听父亲说,长芽麦做出来的馍面不好吃,不但酸还黏牙,难以下咽。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今收割机替代了人工收麦,天气好的时候,不到两天的时间,村子里的麦子差不多都被收割机收完了,人们只需要在艳阳天里坐在自家门口翻麦、晒麦,吹麦壳的风机也替代了人工扬麦,以前那种家家户户在麦地里收麦的场景成了历史,北上的那群麦客也彻底消失了。
每年九十月份是故乡的连阴雨季节,这两个月的雨水分外多。从下雨那天开始,整个天空就阴沉沉的,雨点不紧不慢地落下来,打在梧桐叶上,嘣嘣地响个不停。打麦场,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游乐场,我们穿着雨鞋在水洼里戏水,玩玻璃弹珠,从这个胡同跑到那个胡同。初秋时节的雨,断断续续,缠缠绵绵,像是专门为了让忙碌了大半年的农人们休憩一阵子。雨水稍空的时候,家家户户便开始烧炕了。奶奶会往火炕里烧两把麦秆,晚上睡觉时,被褥就不会那么潮湿,睡起来也舒服。每当村里烧炕的青烟升起来时,我都会驻足看很久,这是我最喜欢故乡的时刻。我喜欢那一抹青烟的味道,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喜欢看青烟在村庄中游走,一点点升到高处,飘过泾河飘向远处,和天边的云雾融合在了一起。我站在麦碾子上,手里拿着被雨水打湿的马莲枣,欣赏着朦胧的山峦,纵深的沟壑泛起了白雾,这一刻,故乡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把眼前的这一切都记在了心里,似乎注定长大后我会离开故乡一样。
走出渭北高原多年以后,我常常因记不起故乡的某一个时令而自责。有时候为了和自己较劲,我会给父亲打电话,和他验证一下,当下是不是洋槐花开的时候、麦子应该挂絮了、白色桑果能吃了、崖畔的黄花能摘了、花椒树是否还在……总能惹得父亲在电话那头笑一阵子。父亲笑着说:“洋槐花早都落完了,不过今年也吃了好几顿槐花疙瘩;麦子絮刚挂上不久,还没有长出麦瓤;白色桑果绿绿的吃不得;黄花前两天才摘过,晒干了给你姐寄一些过去;花椒还得等一个多月才能红,今年崖畔又出了一棵幼椒树……”
出门在外的日子里,有时某个不知名的瞬间、一场暴雨、路过的一个转角、闻到的一缕青烟、听到的一句乡音都能把我的思绪拉回故乡。记忆重新回到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像翻阅一本书,一页一页寻找着乡土的模樣。那里有数不清的黄土塬,有烟火的味道,有金黄的麦田,有高大的皂荚树,有古老的土城墙,有家人期盼已久的等待……思绪短暂停留片刻后,又很快回到现实。原来,我仍在他乡,些许失落涌上心头,也会无奈叹息。
当我独自走在老家的沟畔时,重新审视着眼前的故乡,发现自己一直在这片黄土塬上默默寻找,这个动作重复了很多年。一道道沟壑在微妙地发生变化,槐树林比往年更加幽深,土城墙倒塌在苜蓿地里,野生柴胡和茼蒿遍布山野,挖药的撅头在房檐下锈迹斑斑。沿着长满蒿草的小路,顺着一阵枣花香,走进儿时住过的老屋。几口窑洞还是那样坚固,只是没有了门窗和烟火气,显得格外凄凉。老院里的核桃树、杏树、花椒树都在,只是水窖里没有了雨水。打麦场旁边的核桃树、枣树、柏树和麦田都在这里,它们和漫无边际的黄土没有一点变化,唯有这片土地上的人,在不经意间变得模糊不清了。
远离乡土的日子里,即便路途遥远,只要有时间,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家的探亲路,回到我生长过的那片黄土地上。陪一陪大半年未见的家人,看一眼小时候住过的窑洞,摘几颗脆甜的马莲枣,坐在被秋风吹过的麦碾子上放空。我看见,麻雀从身边飞过,夕阳落得很慢,天边的云是彩色的,放羊的伙伴们都回来了,打麦场上的荒草也消失了,窑洞里飘出了做饭的香味,巧霞姑来家里借酵头,奶奶在烧炕……我打个盹的工夫,他们都不见了。不久之后,满村的落叶会被北风吹得很远,挂在树上的柿子会风干,人们在黄土上走过的痕迹都会显现出来。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村子里四通八达,有人在这些路上百转千回走完了一生,有人沿着这些小路去了很远的地方。后来才明白,其实不用刻意去寻找,有一天风一吹,时光的掠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那一条条小路是我必须走的路,即使有些小路已经长满了荒草,我也会找到那一条条小路。我清楚地知道,故乡会老去,这里的人会远去,但我相信,生命的接力棒始终会栩栩如生。无论它怎么改变,在故乡面前,我还是那个脸上挂着高原红的碎娃,满身的黄土,说着关中方言,身旁依旧沟壑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