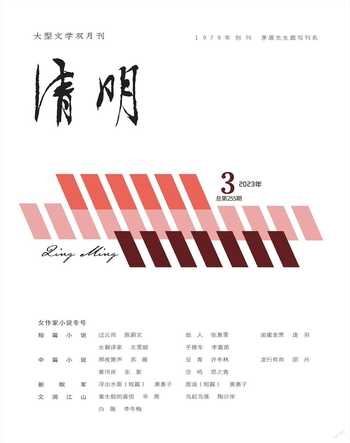手推车
2023-05-30李嘉茵
李嘉茵
老罐五十出头,身穿白衬衫、黑西裤,外罩一件印着华联超市标志的红马甲,一大串钥匙丁零当啷,挂在腰际,拎一只滚圆玻璃杯,盛满热茶,外罩暗红针织杯套,防烫手。老罐倚在超市出口处两个塑料童模旁,一只一只地数顾客抛在扶梯前的手推车。数到三十只,他走上前,将它们交叉折叠,排成一节小型火车车厢,随后驱着那节车厢回到拐角处的手推车停放处。工作轻松,就是没什么意思,常常数着数着,就开始走神,思绪游逛其他地方。愣神时,他曾不止一次被烟头烧烫手指。老俞哼着一支调子低沉的异域民谣,拉拽一辆补货车缓步走过,“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缓缓吐气,“在这迷人的晚上”,尾音戛然止住,指指老罐的手,说,留神,烧燎蹄髈了。
老罐咧嘴想笑,因面部麻痹,表情略僵硬。他对老俞说,晚上聚聚啊。随后上前,将散落四处的手推车慢慢聚拢。右脚围着左腿画圆,两只脚捉迷藏似的,一个追撵一个,两腿始终挨不到一起。
同事悄望卖力工作的老罐,看他僵硬又熟练地将手推车聚集、交叠、排列。若是看得再仔细些,他们便会发现老罐此时不同以往,不再笑容满面,总下意识地低头,满腹心事似的,衣褶里透出沉默。延宕的右脚,在起落间的赘冗节奏中亦踩出叹息的意味。
无论老罐工作多么卖力,被辞退照旧是早晚的事。他们早早预料到这一日。不过,在居委会陈嫂的斡旋下,这个时间被一再推迟。
老罐姓冠,平日爱吃罐头,独身几十年,好事者揶揄,刻意念作老鳏。老罐的过往,人们不便过问,老罐却主动谈及,讲得轻描淡写。先前,父母做水产养殖,假期他与伙伴在江上游泳、戏水、打浮漂。养殖季刚过,江边蟹笼空落,有人提出玩沉船探险。他胆大,水性好,率先下水,下潜几米,钻入蟹笼,探得几枚散落箱笼的蟹钳,仔细掖进口袋,视作胜利勋章,等回转身时,不知何故,笼门卡住,怎么都推不开。他在昏绿的水里挣扎,抓住笼门摇晃,笼内逼仄狭窄,布满水草游藻,重重网格,切开支离的水面。意识跟随摇荡的水波渐趋模糊,身体像是失去重量,脱离地面,徐徐上升,穿云破雾,钻入云端,仿佛伸手便能触到清冷如水的月亮。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岸边,阿妈泪眼婆娑。老罐人救回来了,一双眼却蒙了雾,呆滞如鱼目。说话时,吐字模糊,讲不清爽。去城里看病,医生诊断,困在水里太久,导致缺氧,患上小脑萎缩症。阿妈哭了又哭,城里医生问遍,个个摇头,看不好,治不得。阿妈拖他去找村里的神婆。神婆说他魂落在水里,不好寻,得施法。神婆让阿妈亲手为他缝制一双红布鞋,择一吉日,买下九条红鲤鱼,带去江上放生。阿妈遵照神婆嘱咐,让他饮下符水,怀抱红鞋,跪在岸边,向九条红鱼游散的方向叩九个头。回家后他感到疲惫,沉入睡梦,黄昏时转醒,阿爸阿妈围在床前,殷切望他,他看弟弟手里捧一只午餐肉罐头,眼睛亮了,涎水流下,仍旧咧嘴傻笑。
阿爸阿妈整日叹息,用尽各种法子,终于知道,缠上这种病,便是走上一条单行路,断然没有转圜余地,老罐的脑子只得一天一天萎缩下去。
老罐倒认定眼下所度日脚不差。有员工宿舍住,上下铺铁床,无需缴纳租金,餐食更不必说,每月货架上的临期食品,先打折倾销,实在卖不掉的,陆经理索性散给员工,以极低的内部价抛售,有时甚至让他们随意挑拣,分文不收。老罐从来只拿罐头。
年少时老罐爱吃梅林牌罐头,柜员慵懒,他身量小,总在货架上攀上攀下,搜寻自己喜欢的茄汁沙丁鱼罐头。几十年后,他对罐头的热爱有增无减。那回仓库临期剩余最多的是油焖笋罐头,他拿了几只带回宿舍,撬开罐盖,将浸满油汁的笋片夹起,尝了一口,他从笋和油中尝出一种岁月的味道。罐中将熟未熟的春笋,会一直将熟未熟,不再因长久放置而变老。
吃罐头好处多多,最显而易见的是无需每日下厨。员工宿舍功率有限,老罐的炊具只有一只数年前超市打折时买下的小电锅,他用它煮面,热水滚开青菜心,下面,生抽、芝麻油、糖、水調成料汁,浇在面上,直接就锅吃,碗也不必刷。有了茄汁沙丁鱼罐头,早餐配粥,午餐配面,晚餐与临期的排骨鸡肉同煮,浸润酱汁,鲜咸浓郁,日子过得有了些旧时滋味。
罐头保质期长,闷得住时间。就像阿妈为老罐介绍对象,老罐从不积极回应,一拖再拖。老罐虽头脑不灵光,讲话慢半拍,但心里清楚,对方看中的多半是老家的宅基地。更何况,老罐觉得,罐头生产出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顺利售卖掉。老罐总在等待的临期滞销罐头,无人挑选,商品属性降为零,但他细致地将它开启,掏空内里,不浪费丝毫酱汁。再说,有了伴侣,须搬离宿舍,另觅住处,这无疑是笔巨大开销。阿妈给老罐拿钱,要他请媒人介绍的姑娘喝茶,老罐面上答应,转头将这钱拿去买烟。老罐烟龄二十三年,比工龄长,平素烟不离手。阿弟劝他戒烟,同事也都说,老罐的病,须戒烟禁酒,否则明朝只得轮椅上躺。老罐听完笑笑,散烟,一人一根,最后一根,留给自己。
老罐爱烟爱酒。可惜酒能贮存十年,临期货少,老罐只喝超市卖的散酒。老罐不会品酒,哪种好,哪种不好,喝再多也尝不出。倒是越劣的酒越爱喝,醉得快,过会儿便不记得自己生的什么样貌,走路边跑边跳,步子轻盈若飞,恍惚之间,将身体负累全数忘掉。
酒醒后,还是要为往后的日子担忧。往后几十年,这病究竟要恶化成什么样子,老罐心里没谱。他想估算出一个最为适宜的年龄离开,享够烟酒、尝足生活之乐,同时不至于给家人添太多麻烦。至今还未得出结果。老罐上班发呆愣神的时间越来越长。旁人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彼此眼神示意,抛来接去。老罐瞧不着,浸入一片静谧湖沼。久而久之,竟浸出事体。
一辆队末手推车自扶梯滑落,砸中前方一位怀抱孙儿的阿婆,拍了片,医生说是尾椎骨折。老俞站队末,老罐立队头。老俞哼歌,老罐恍神。说不清是谁的错,仿佛手推车生出脚,要活动筋骨,不巧撞上人。好在是空车,滑行速度不快,不然两人非蹲牢房不可。
陆经理提果篮去医院,垫付了医药费,回来摊手,要两人补交医疗费,外加精神损失费。老罐家底无多,且不认为自己应在事故中负担责任。老罐当日站在车队另一端,离老太远隔数米,显然老俞嫌疑更大。老俞却一口咬定是老罐的问题,全怪他那条麻痹的右腿,忽然抽搐,抖动很快通过车头传导至车尾,自己一时恍神,给那辆自由滑动的手推车以可乘之机。老罐满脸涨红,说不出一句整话,声音断断续续,车轮内侧有凹槽,牢牢卡在扶梯锯齿上,怎么可能一抖就滑脱掉!
陆经理说,别吵。讲定车轮半年加油保养一回。讲定一次传送手推车不超过十只,这回看监控,运了十六只。责任你俩都有。陆经理眉毛压得极低,目光如秃鹫,在两人身上扫视巡回。老俞和老罐不再争辩,低下头,听凭发落。最后,两人各自从陆经理那里提前支取了部分工资,老罐额外找做水产生意的阿弟凑了几万块。钱还清,事故潦草翻篇,梁子却就此结下。
日子过得紧巴巴。老罐戒了烟,路过便利店,偶尔买一包,揣进口袋。无人时,拿出一支,低头嗅闻片刻,又搁回。唯有散烟给同事,才舍得往外掏,当然,老俞除外。事故过后,陆经理将老俞调去仓库,做理货员。两人上下班路上碰见,目光闪躲,一个抬头看树,一个低头看裤脚,隔出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
与老俞绝交后,老罐人缘反倒变好,烟酒之外,拓出一片新领地。盛夏时令,雨势阔大,顾客寥寥,多是避雨的老头老太,逛来逛去,只看不买。生鲜肉档的老韩和海鲜区的小蔡随同几人,在超市后门的雨廊下摆好方桌方凳,静坐听雨,兼搓麻将。有事时,招呼声自室内层层传递。老韩,客人要二斤猪五花。老韩唤过一旁观战的老罐替补,匆忙赶回生鲜肉档。老罐麻将牌摸得不好不坏,赢钱不骄,输钱不骂,牌路沉稳,规规矩矩。虽说麻将桌在第二日便被陆经理取缔,老罐却当替补当上瘾。随后,麻将桌营业时间推迟至下班后,位置重新选定在老罐的宿舍里。
麻将搓到后半夜,几人喊饿。老罐开了两只临期罐头,煮两包临期方便面,磕两枚鸡蛋,剥一株小葱,用四只红碗盛了,几人哧溜吞咽下肚。临走前,刻意多輸老罐一局,权当付了夜宵钱。老罐坐定方凳,满心快乐。后来,有人吃腻了罐头配清汤面,便自己动手。老韩拿出肉档卖剩的肥牛卷,摘起宿舍墙角的大白菜,拿电锅炖,抖几勺盐,放几撮味精,洒几粒花椒,而后焖上锅盖,不多时,汤锅咕噜咕噜煮开。人们暂停麻将局,端碗吃净,满足而尽兴。
下回再聚,又添新花样。有人拿了块麻将牌大小的底料,内里裹藏各类香料,花椒、辣椒、大料、牛油,彼此浑融,沉凝如琥珀。先加水,煮沸,化开底料,香气四溢,直将房顶掀开。放入临期肥牛卷、羊肉卷、猪五花,搅弄一番,便被成群筷子捕捞干净。肉类被抢掠一空,牛丸、虾丸扑通扑通滚下热锅,脑花待命,黄喉预备,白菜断后。老罐的存货被一扫而光,众人却余兴未尽。此刻已近凌晨,街上商铺都已打烊,超市虽在眼下,却封锁严密,白日里与他们浑然相融的场所,此刻却顶着一把铜锁,将人群生分隔绝。
老韩思忖着,打个饱嗝,忽然拍了下大腿,说,有了,找老俞。小蔡和老赵纷纷称赞,老罐心里有点咯噔,没好明说,出门点了根烟,不作声。老韩很快拨通手机,老俞的声音隔空传来,没问题,这就来。
老俞在夜色下晃着一把黄铜钥匙,打开仓库门。借着月光,目光点数一番,心里有了数,让众人陆续将堆放墙角的一箱临期存货搬出。老罐腿脚不利索,捧着两颗蔫白菜,走得歪歪斜斜,老俞将袋装泡面换给他,想从他手中接过白菜,老罐不松手,老俞使力,白菜摔在地上,老罐不便蹲身,老俞将白菜拾起,立在原地掸去灰土。老罐甩过两手,越过老俞走掉。老俞加入火锅局后,顿时成了主角,他张罗大家洗菜切肉,亲手剜去冬瓜的溃烂部分,将大白菜发黄蔫坏的菜叶掰开,层层剥下,直至露出最里侧的嫩心。
老俞涮火锅相当讲究。清点仓库调料时,发现一袋受潮的海椒粉,倒一些在碗里,闻了闻,说还好,晚几天就生霉啦。他拦住一只涮肉下锅的手,夹起一片牛肉,在盛满蛋清的碗中转上一转,在海椒粉堆里打滚上浆,这样涮出的牛肉,鲜嫩弹牙。吃饱了肚皮,几人又回麻将桌前酣战,直至天明将晓。
此后,老罐宿舍就成为了聚餐胜地。有人拿来一只卡式炉,一只铁锅,往后便可弄些炒菜。聚会变得小有规模。每人都带些食材饮料,算凑足了份子。老俞食材最全,像揣了半个超市库存在身上。有人夸老俞神通。老俞笑笑,举起杯子,杯中倒满月末过期的青岛啤酒。老俞四川人,自小家境贫寒,却好吃,讲究,精细,手头有一点食材,就能转出花样。
散场后,老罐站在门边送客,老俞帽子忘带,落在最后,一时之间,房中只剩两人,氛围紧涩发僵。老罐开口说,吃掉这么多东西,给陆经理晓得,当真没事?老俞说,嗨,大惊小怪。随后挥手离开,清亮亮的脚步,响彻暗夜中的小巷。
某夜聚会,几人凑钱买了瓶洋河大曲,醉得七零八落,老俞跟老罐碰杯,洒了半杯酒,老俞含混地说,那辆车子,前轮缠了块口香糖,我先前就发现了,一直没清理。那事怪我,但我拿不出什么钱。老俞声音低矮下去。
此后,罅隙算是填补齐整。老俞不再束手束脚,进门坐定后,便要讨酒喝,东翻西找一阵,还特意看了老罐床底下,看有没有传闻中那瓶1982年的茅台。老罐说,有的话,也早喝光了,酒瓶底子也要舔干净。喝不成酒,老俞讨支烟抽,老罐从上了铜锁的抽屉里拿出一盒黄鹤楼,分一支给老俞,自个儿红双喜照旧。老俞走走晃晃,将八平方米的小屋扫描个遍,墙上一处裂纹,蔓延至墙角。
再来时,老俞手里多了张风景画报,用胶水糊了,贴在墙纹裂缝上,似乎视而不见,便可延缓墙壁衰朽。老罐问,画报上的女人是谁。老俞说,民谣歌手,唱过一首《墨绿的夜》。老罐摇头。老俞从柜中掏出老罐的黄鹤楼烟盒,抽出一支,点火,得意地吸上一口,不说话,卖关子。老罐又问画报上的那座颇有年代感尖顶建筑在哪里。老俞说,是上海外滩的西餐厅,焗蜗牛、罗宋汤都是招牌菜,老罐问他是否吃过。老俞摇头,却说自己有位朋友曾在里面做工,等退了休,我们也去尝尝,逛逛外滩,听听歌星唱歌。
老俞在老罐的床边坐下,慢慢将烟抽完。铁架床墙边贴着一张女孩相片。老俞用指间烟头探向女孩,问,你女儿?这么大了。老罐说,侄女。老罐指着女孩身上的浆果色毛线裙说,裙子好看吧,我织的。
成年后,阿弟早早结婚,为了生计,跑东跑西卖水产,老罐住在家中,随母亲织毛衣,赚点零花钱。老罐腿脚不好,手却巧,毛衣棒针用得格外顺。侄女出生后,他织过十几条毛线裙给她,直至她走入青春期,跟同龄女孩一样迷上名牌服饰。如今她在几百公里之外的省城上高中。他想去看她,但腿脚不便,路途又远,每年鲜少会面。
老俞笑他说,你去省城,骑电瓶车去?随之两手平行握拳,将并不存在的车把拧转两下。老罐说,那多没劲,指着开你的新车去了。
听说老俞儿子今年入职投行,大家都讲,老俞转运啦,熬到儿子毕业,苦日子算是到了头,再不用捣腾仓库里的过期烂货。前日连降暴雨,超市附近地势低洼。下班时,众人往马路上一站,发觉水已淹到大腿。后半夜雨势渐弱,众人散出超市,见老俞还蹚着积水在仓库忙进忙出,抢救货品。有人喊,老俞,不搞了,陆经理谈妥了,淹掉的货,厂家给换。接着有人喊,老俞,折腾半晚了,当心高血压啊。老俞挥挥手,照搬不误。几人见状,无法,只得蹚进黑水,七手八脚帮老俞搬货。
搬完后,心里清晓了。原来老俞心疼的不是超市仓库内的新鲜库存,而是那些花钱买来的临期货品。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老俞管公家仓库时没闲着,也顺带将自家的货存在里面。从前聚会上,老俞带去的那些食材调料,都是预备返厂调换的临期货。
老俞的私货去路广阔。过期的薯片、饼干、蜜饯、果冻,卖给城郊养殖场,喂猪喂鸡;一来一去,中间小赚一笔差价。实在不济,还能自己慢慢吃,稳赚不赔。人们没想到,看似憨厚的老俞,心思这样活络,这样会转花样经。
往后可以歇下了,人们都说小俞工资不低。在市中心商业街写字楼工作,月薪八千只是基数,再往上攀攀,一万两万三万,都是可以想见的。美好生活的蓝图,边线已描好,就差兑现了。人们谈着谈着,开始传:老俞儿子给老俞买了辆红色小轿车,一直搁在离超市五十米外的马路上,上下班多走一段路。说老俞低调老实,不爱招摇,父慈子孝。谈着谈着,又开始传:老俞儿子在投行上班没错,但职务是专职司机,那辆红色小轿车是老板座驾。这些传闻,半真半假,隔空打架,但对老俞晚年幸福生活的探讨,人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老俞听旁人说起,笑笑,有时点点头,有时摇摇头,摸摸后脑勺,心里也有点雀跃,他将旁人的客气视作恭维,渐渐主动配合起来,甚至描述起小轿车舒适的真皮座椅和柔软的靠枕,后座中间有个真皮材质的活动板,与真皮座椅连在一处,手一点按钮就自动放下,盛放茶杯纸巾,老俞的玻璃缸子放进去,大小恰好,稳稳当当,哪怕急转弯、急刹车,照样滴水不洒。
老罐也拿这事揶揄。老俞不回避,说,存折拿来,立马给你换辆新车,别说开着上省城,开去上海滩遛弯都没话说。老罐见状,笑笑,不再揪着小汽车的事问,又递了一根烟去。
月末刮了阵台风,超市放假,几人在老罐宿舍搓麻将,听风响。老韩说,听这动静,这嗓门儿,唱得比老俞带劲。
台风走远,超市外一棵树被拦腰折断,压倒两辆电瓶车。雨水将息,街邻出门走动,见超市门前这棵断树,不偏不倚,从正面拦截了超市粉条状的透明塑料门帘。街邻对断树哀悼两句,想起东街那间永辉超市新建不久,开业大酬宾活动不知完结没,消费满三十元送抽纸的活动不知还有没有,便脚步不停地绕开华联超市,走向远处。
陆经理盯着门前残树恍神一阵,不再整日笑眯眯,时常若有所思。人们说,陆经理发起呆来,跟老罐越来越像了。树的断枝在超市门前躺了两天半之后,市政部门才来人清理,树根被刨去,留下一个形状不明的巨大地洞。
台风过境许久,街上路灯仍未亮起。过了晚上七点半,超市周边一片阒寂,陆经理给市政部门拨了好几次电话,总是一个懒散的声音重复说,知道了知道了,天黑前,准给你把路灯修好,耐心等等。
连续三日,都是这般答复。陆经理在第三日挂掉电话前骂了句戆卵。当天夜里,九点半,老罐下班,走着走着,没留神,右脚一滑,歪进树坑。坑中积水,洼水冰冷,不深,但淹没了他歪斜的下身。他站不起来,双手扒牢洞壁,大声呼救。喊声引来了同事,几人合力将他从水坑中拔出,老罐下身沾满污泥,平日无事的左腿也随右腿抖动,不多时,抖动扩散至全身。几人抬他到宿舍,换上干衣,老俞从仓库赶来,守在床边,老罐的脸像一个揉皱的纸团,一层褶叠着另一层。老罐躺在床上,窗外路灯倏尔亮起,时间是十点一刻。暖光铺来,老罐的脸立时被涂抹,变作一张色彩滑稽的脸。
人们心里知道,老罐这一摔,旧疾恶化了。小脑日复一日萎缩,像冬里的稻谷。面部频频抽搐,五官不协,好在暂无口吐涎水、全身瘫痪之类的征兆,生活尚能自理,日后怎样发展,不好讲。
老罐卧床期间,全靠老俞照料。仓库与宿舍相隔不远,他隔几个钟头来一趟。这日下班,老韩从档口带来几根白日里剩下的猪骨,小蔡自海鲜区带来海蜇头和冷冻蟹柳,老赵拎来低价内销的晚间菜蔬,老俞去仓库提了根老葱,剥皮,拿猪骨熬煮高汤,独放葱白。一旁热锅冷油,三成热时,放花椒、八角、香叶,小火,油炸出香,放葱绿,同海蜇头爆炒。随后煎好三只荷包蛋,煮进汤锅,汤色愈加奶白。骨汤煮给老罐,其余几人就着葱爆海蜇头小酌,给老罐讲超市近来的逸闻趣事。老俞立在锅边,不时撇去浮沫。
次日,老俞、老韩和小蔡将那坑一锹一锹填平。老俞踩在填好的地上,跳了几下,将雨后松土踏实。过完周末,上班首日,人们再路过时,踏过光滑地表,很少会想起此处过去曾耸立着一棵树。
下半年,又有两家大型超市陆续开张,华联超市效益不如以往。陆经理被调去其他分店。走之前,陆经理坐在老罐床边,说,会跟新经理洽谈,让他安心。
新经理空降后,先在办公室查对账目,随即喊出全体员工,开誓师大会。二十分钟后,稀稀拉拉凑齊人数。新经理站在讲台中央,拿扩音喇叭喊话,知道为什么业绩这么差吗?都怪姓陆的,把你们骨头缝里的蛆都养肥了。当即颁布数条铁腕政策,譬如,上班期间不准闲聊,不准跨区走动,不准躺在年龄簿上吃老本。此外,增强硬件设施,譬如,逐渐改用带自动锁链的手推车,减少人工成本。又说,超市不养闲人,近期将对员工进行精减。
一时之间,人人自危。老罐清楚,矛头是对准自己的。新经理早已听说老罐摔倒落水的事,心有戚戚,担心这样下去,超市迟早成为老罐的免费养老院,棺材寿衣都要一同包办。新经理明里暗里找他谈话,层层铺垫,要他早做打算。
老罐在超市的日子已经望到头了。超市换上一批新出厂的手推车,前车后车自动以锁链连接。使用前在把手处的卡槽里放入一元硬币,与前车相连的锁链便会弹开,顾客便能将车推走。同样,离开超市前,唯有将手推车放回指定位置,嵌入前车,令前后車锁链连接,后车卡槽内的一元硬币才会自动弹出,顾客将硬币拿走,放回口袋。正是这一元押金的缘故,至此以后,手推车不再像从前那样散落各处,巡回游戏玩到头了。
偶尔,有一两辆手推车仍被遗落在超市门口。老罐走去,将它领回。握住把手,向前推,阻力比以往要大。摩擦力大,行走速度慢,顾客在货架前驻足时间更长久。货品被迅速卖掉,剩在货架上的就会少。老俞理货时,往往会有疏漏,货品临期前没能及时上架,堆在墙角暗自生霉。新经理似是对仓库管理情况有所洞悉,另请了一名专业理货员点数库存,又连续做了半个月的减价清仓。销量迅速增长。老罐他们减少了聚会频次,眼看着这块由临期食物拼凑而成的漂浮大陆逐渐远去。
在老罐被列入清退名单后,新经理调头开始找老俞麻烦。老俞从前与陆经理约定俗成的规则,被逐一推翻。多年来,老俞早已把仓库内的临期商品看作私产,月末交点钱便能换得。新经理却说,依照现代超市管理准则,这些过期货品只能销毁丢弃,不能低价售卖,也不能折价卖给员工,流去外面。老俞瞪起眼睛,说,那这不是浪费?新经理的新皮鞋在地面瓷砖上跺了两下,说,哎呀呀,你们这些人。
老罐即将走人,老俞存货见底。几个老伙计重又聚在老罐宿舍,围着方桌坐定。他们曾在这张桌上彻夜摸牌,也涮过各式火锅,广东骨汤打边炉,重庆牛油锅,四川串串香锅,贵州酸汤鱼火锅,等等。今夜,都晓得是最后的欢宴了。席间话音寥落,不似以往,摆龙门阵,侃大山,只各自低头闷吃,有人暗里流下眼泪,随即悄无声息地抹掉。一喝便喝多了,比往日醉得快,醉得深。不知是谁说了句,吃了这么多年临期货,不如去超市里整点上档次的。反正,过了今朝没明朝。
备用钥匙旋开黄铜门锁,四人歪歪斜斜、连磕带碰地挤进超市后门,想找辆手推车,身上都没硬币,收银台锁得严严实实。好在堆放杂物的工作间里还散落着几辆旧推车,没有自动锁链和硬币卡槽,车轮仍缠覆着未能及时清理的塑料细绳和口香糖。他们各自推走一辆,走向空空荡荡的购物区。老罐走去,推起最后一辆,捏握车把,还是熟悉的感觉,比新车推着轻快,顺滑。
老罐推起车,甚至腾跃了几步,歪斜着身子,直走,左转,他踮脚,撑着把手,身子飘悠起来,被手推车托着向前滑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毫无阻滞,平顺流畅,犹如低空飞行。
本应先左转,后右转,结果手推车滑行得过于顺畅,他没能及时调转方向,慢了一拍,手推车随即撞上货架,他半身栽进车斗,头冲下,起不来身,呜呜喊叫。老俞赶来,见状,酒醒了些,将他从车斗里拔出来,老罐捂着鼻子,哀叫连声。其他人闻之,陆续围拢上来。
老俞问老罐,感觉如何,老罐说不出一句整话,双腿抖得厉害。几人七嘴八舌,议论一通,要带老罐去邻街卫生院看看。老俞和老韩架起老罐的两条胳膊,酒劲未消,身子发软,老罐身体死沉,拖了几步路,三人险些摔叠在地。老俞站起身,环视四周,说,别拖了,这不是有车吗。
老罐在三人的搀扶下,举起哆哆嗦嗦的右腿,试着挪进车斗中,未果,几人半推半抱,才将老罐整个人搁进车斗中。老罐蜷在推车里,莫名地笑了起来。
三人围着那辆手推车,走在一串闪烁不定的街灯下。老罐坐在车里,歪着脑袋,看向天上的月亮,想起多年前在笼中溺水的夜晚,水上漂着一重模糊月影。街上灯柱是新换的,悬在头顶,分外明亮,光里带刺,似一轮骤然放大的月亮。他闭上眼睛,四肢袒在光里,想象自己仍在水底,头一次感到安稳。他在这只敞开的铁笼中满意地睡去。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低缓浑厚的声音响起。多么幽静的晚上,依稀听到有人轻声唱,是老俞。
长夜快过去,天蒙蒙亮。老俞推着车,意识有点飘忽。眼神跟着声线在空寂的街道游荡,没看清眼下一块石头。石头将车轮卡住。他推了两下,没推动,又推两下,还是不动。护在车斗两侧的老韩和小蔡也围上来帮着推,还是推不动。老俞纳闷了。换了只手,轮子动了一下。原来刚才不小心按住了刹车钮。车动了,老俞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说,给上油了,发车,发车。老罐醉眼蒙眬地抬起头,问,去哪儿啊?老俞垂头想了半天,说,走,去外滩。随之挥起两手,在空里划拨,像是在捞水里的月亮,又像是在推开一重看不见的波浪。
责任编辑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