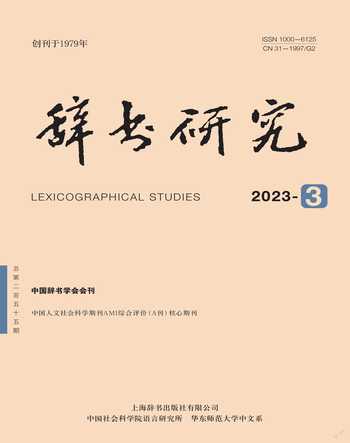从Pleco看外向型汉语词典的语法标注
2023-05-30刘荣艳
刘荣艳



摘 要 Pleco作为当下颇受欢迎的外向型汉语词典类App,其语法标注不区分字头下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对单音节词、单音节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都进行了“无差别的词性标注”。这一标注模式虽肯定了语素在复合词学习中的作用,迎合了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心理,但也存在标注依据不合理、混淆不同层面语法单位等显著不足。因此,文章提出了功能与意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素性标注依据,以及语法标注的区别性原则。在具体操作层面,文章还提出了“分层标注”的新型标注模式,尝试优化外向型汉语词典的语法标注模式。
关键词 Pleco 外向型汉语词典 语法标注 词典编纂 词汇学习
一、 引言
外向型汉语词典是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重要学习工具,其在辅助汉语词汇理解、记忆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汉语词典类App被广泛应用,甚至取代了大量传统纸质版词典。Pleco作为较早面世的外向型汉语词典类App,其使用率和受欢迎程度远超过其他汉语词典类App,(杨玉玲,杨艳艳 2019)但我们在考察Pleco的词性标注时,却发现了一些问题。
现出版的内、外向型汉语词典大都已实现全面词性标注,即将收录的成词条目标注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不同类别,以辅助使用者了解词的位置和搭配。与这些词典不同的是,Pleco中词性标注的对象范围要广得多,其不严格区分汉字字形下的语法单位,为单音节词、单音节不成词语素和部分音节字都进行了无差别的“词性”标注。如图1中Pleco将非语法单位的音节字[1]“猩”标注为名词“NOUN”。
当下的内、外向型词典大多为字头中的单音节词标注了词性,对单音节不成詞语素和音节字则不加标注,如《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等。但也有少量词典对单音节词和单音节不成词语素字都进行了语法性类标注,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规范》)第三版。但像Pleco这种,词性标注范围囊括词、语素、音节字的情况并不多见。由于不成词语素作为复合词的构词成分,其在词内大多是按照构词规则进行组合搭配的,与复合词内的其他组成成分之间也存在主谓、动宾、偏正等关系,如“国营、司机、表哥”等,因此学生在学习这些复合词时也会考虑构成语素的意义及语法性质,形成语素意识。现有研究表明,汉语语素意识能有效帮助学习者从构词语素中提取部分信息,从而辅助整词的理解。(Ke & Koda 2017;Chen 2018;
Chen 2019) Pleco的特殊标注模式凸显了非常规语法单位的语法功能、强调语素和音节字的作用,揭示了汉语学习者追求语言单位的功能、意义、形态“三位一体”完整性的学习习惯,有利于学生培养“自下而上”的词汇学习模式。
另有大量心理语言学研究证明,人类大脑中存在高度组织化的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储存着语言的词项或词条知识,(Terisman 1960;Aitchison 1987;桂诗春 2000;蔡振光,董燕萍 2005)汉语学习也是如此。学习者在学习汉语词汇时,除了“整体接受”,还会采用“拆分理解”的方式记忆、习得汉语复合词。在现代汉语中,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使用的语言单位,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汉语单音节语素作为双音节复合词的构成材料,其与词的关系密不可分。汉语双音节词中的语素与其构成词的功能和意义也互相联系,使汉语词汇域与语素域互相映射。因此,Pleco为不成词语素标注“词性”的做法既揭示了汉语语素域向词汇域的“由低到高”的跨层级映射关系,也体现了词汇学习中语素的重要地位。符合汉语学习者学习规律及学习心理,有一定的合理性。
汉字与单音节词、单音节语素、音节字的复杂关系使得汉语的语法性类标注十分困难,Pleco不区分语法层级的混合标注方式,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容易让使用者混淆不同语法层面的语言单位,造成使用偏误,如将不成词语素当作词来单独使用等。学界对语法标注单位的大小问题也展开过激烈的讨论,认为语素不能进行语法分类的学者指出,语素(特指不成词语素)只有表义功能,只能凭借意义进行分类,不具备语法功能,
(陆志韦 1957;张寿康 1986;金立 1999)给语素标注“词性”,是“混淆了词素平面和词平面,用词性代替了词素的词性”(潘绍典 1986)。而承认语素具有词性的学者则认为,语素可以进行语法分类,语素的语法类别问题基本上就是词类问题,不同结构体的类别跟语素的类别基本相同,如“名”“动”“形”等,(吕叔湘 1962)语素虽不一定是词,但是却明显地具备着词性。(尹斌庸 1984)亦有学者尝试对现代汉语语素进行语法分类,分类结果虽不尽相同,但都肯定了语素的语法功能。(尹斌庸 1984;苑春法,黄昌宁 1998;杨锡彭 2003)
介于当下研究外向型词典词性标注情况的文章不多,且Pleco独特的标注模式鲜有人研究,故本文从Pleco的语法标注出发,探讨外向型汉语词典语法性类标注的依据、原则及意义,即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 通过分析汉字样本在Pleco中的标注结果,研究Pleco不区分语法单位的标注模式的深层原因,分析其合理性与不足。
(2) 结合Pleco语法标注的现状,尝试提出较完整的标注依据和原则。
(3) 探究“分层标注”这一新型标注模式在优化外向型汉语词典编纂、辅助汉语学习过程中的意义。
二、 Pleco中语素及音节字的标注情况
(一) 样本的选择与抽样
汉语字、词、语素三者间的关系纷繁复杂,大多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介于从整字入手进行分类的难度大、出错率高,本文从汉字的义项出发,根据表义与否将样本分为语素字(包括成词语素字和不成词语素字)和音节字,再以语素字的各个语素项为统计基础,以成词与否为标准,将其分为成词语素项和不成词语素项。最后重点对单音不成词语素项和音节字在Pleco中的词性标注情况进行分析。在汉字抽样过程中,本文利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2001,以下简称《大纲》)中抽取了甲级字55个、乙级字55个、丙级字42个、丁级字48个,共计200个汉字。由于同音字(29个)和异形字(1个)的存在,实际抽样所得230个汉字,共计854个语素项,各级样本汉字的成词情况如表1所示。
(二) 样本标注概况
经过对样本的检索,我们发现Pleco对230个样本汉字中的221个进行了分项词性标注,在标注过程中不区分语素和非语素、成词与不成词。Pleco的词性标注与《规范》大致相似,即不做词和不成词语素的区分,字头一律分义项标注词性。但《规范》不标注词缀和音节字的词性,Pleco则不对其做严格区分。Pleco的词类系统基本与《现汉》和《规范》一致,采用的都是目前通行的词类系统,即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拟声词等大类。
(三) 不成词语素项的素性标注
汉语的词类划分以词的语法功能为主要依据,兼顾词的意义和形态,而汉语不成词语素的素类划分依据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现有的关于不成词语素的分类研究大多将意义、在词内的组合关系及对应古语词的词性作为语素标注依据。如《规范》的编者李行健(1997)就指出语素间的关系“未尝不可以按词和词组合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确定其词性”,并对该词典所收录的语素进行了语法标注。而这种语素标注理念在《规范》问世后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指摘,部分学者认为这种标注模式回避了词和语素的区别,混淆了不同语法平面的单位。如孙德金(2004)提到,对于汉语非母语者来说,给不成词语素标注词性会误导学习者把语素当成词来造句。马楠(2009)也指出词典应该以词为单位标注词性,《规范》这种广义的词性标注模糊了语素和词之间的层级关系,增加了离析汉语词、语素和字的困难。可见目前内、外向型汉语词典语法标注的单位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
我们分析了391个不成词语素项在Pleco中的标注情况,从该词典的英文释义、配例、配例翻译着手,分析Pleco中不成词语素项的标注依据。在391个不成词语素项中,依据语素的英文释义及构成词的意义对语素进行语法性类划分的共有334项,占总量的85.4%,如“复”被释为duplicate,标作动词性;“卡”作为card和car的音译外来词缩略音节,按照“卡片”和“卡车”义被标注为名词性;“观”按照其构成词“景观、外观、观念”等意义被标注为名词性。依据语素的组合关系划分语法性类的共有57项,占总量的14.6%,如“旅”在“旅美、旅日”中做动词,后接宾语;“丹”在“丹枫”中做形容词,修饰名词。我们在分析过程中还对照了《古代汉语词典》(2021)的词性标注,发现Pleco中391个不成词语素项的词性标注与《古代汉语词典》重合的有328项,占总量的83.9%,即现代汉语中的不成词语素项在古代汉语中可单用,且意义和词性相同的占绝大多数,故不排除Pleco在标注不成词语素的素性时参考了对应古代汉语单音节词的词性。
(四) 音节字的标注
在本文选取的230个汉字样本中,有10个不表示意义的音节字,即只充当联绵词表音成分的汉字。这10个音节字在Pleco中的标注情况是复杂的,其中“便、估、委、伺、踌、唠”被注解为MEANINGLESS BOUND FORM(无意义黏着形式);“佛、令、氏”的释义中给出了配例;“蜘”作为无意义的音节成分,被标注为名词。我们不难发现,Pleco强行为音节字标注“词性”时存在体例不一致、标注无依据、缺少配例等问题。为进一步探究Pleco对音节字的词性标注模式,我们从《联绵词大辞典》(2013)中随机抽取了50个双音节联绵词,将其拆分为100个汉字,并检索这些样本汉字在Pleco中的标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Pleco对样本中的29个汉字进行了无差别的“词性”标注,且大多数音节字的“词性”与其所在整词的词性一致,如“鹦、醍”等被标注为名词,“拮、蕤”等被标注为动词。
Pleco这种“独特”的标注体例看似缺乏合理性,实际上却迎合了汉语学习者普遍将汉字当成“汉语天然的单位”的心理。汉语将汉字作为书写单位,字与字之间不实行分词连写,汉语非母语者很难从句段中分离出词、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而且汉字的表义性将其从大量表音文字中独立出来,汉语学习者很容易将汉字看成意义与功能的特殊表现单位,即形成“字-义-性”这种一一对应的类推思维。再加上汉字形体本身的理据性很强,音节字可能没有使用上的意义却拥有字形层面的意义。如“猩猩”中的“猩”字是典型的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但我们很难向没有语感的汉语学习者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正常”的汉字却不能单独表义,而只能通过重叠表义。因此Pleco为了避免区分汉字字形下的词、语素、音节成分所带来的麻烦,对大部分汉字都进行了无差别的词性标注,然而这种标注模式却未得到贯彻,仍有部分音节成分因其构成词的意义抽象、字形理据性不强等原因未被标注。
三、 Pleco语法标注的局限与对策
(一) Pleco的语法标注局限
Pleco对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语法性类标注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标注依据不完善、标注体例不科学这两方面。
在研究Pleco语法性类标注的依据方面,我们通过分析样本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的语法性类标注,发现Pleco将语素的释义、在词中的组合关系及对应古语词的词性作为不成词语素项标注的主要依据,将音节字构成的联绵词、音译词的词性作为音节字标注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汉语单音节语素的组合能力强,其意义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Pleco将单音节不成词语素的英语释义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而只有小部分语素项的标注以语素的组合关系为依据的做法未能将语素的意义与功能良好结合,易造成标注不当。例如上文提到的不成词语素“复”,在Pleco中被翻译为duplicate,标注为动词性,例词为“复写”。而“复写”在《现汉》中的释义为“把复写纸夹在两张或几张纸之间书写,一次可以写出若干份”,此时“复”带有明显的副词性,修饰动词“写”,而不是Pleco所标注的动词性。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语素化过程,大量现代不成词语素在古代汉语中是作为独立的词来使用的,因此Pleco将对应古语词的词性作为语素的重要标注依据之一,词典中大量使用古语词和古汉语用法作为配例,未充分考虑释义的通达性和实用性,还造成部分不成词语素项的文言配例与语法标注不符,削弱了语素标注的科学性。例如“考”的不成词语素项用法,在Pleco中被标注为名词性,配例为“《毛诗古音考》《宋元戏曲考》”,而在《古代汉语词典》(1998)中,“考”字除了在表示“旧称已死的父亲”一义时为名词,其余义项均为动词性。Pleco将古籍名作为配例,出现了生拉硬套、標注失当的错误。至于音节字的标注,Pleco倾向于将整词词性作为联绵词音节成分的标注依据,将音译词原词词性作为音译词内部成分的标注依据。如将“葳蕤”的形容词词性直接移植到音节字“蕤”上,又如“卡”作为card和car的音译外来词缩略音节,其按照“卡片”和“卡车”义被标注为名词性。本文认为联绵词和音节词内部的成分具有共同表义性和不可拆分性,成分之间不存在组合关系,也无法体现语法功能。因此Pleco将整词的词性和意义强加在这些成分上的做法是欠考虑的,单纯的音节字不应该被语法标注。
在标注体例方面,Pleco对单音词、单音语素及部分音节字不加以区分,统一标注为“N,V,ADJ”等,这一做法加深了三者间的模糊程度,也增加了离析单音词、语素和汉字的困难,还可能误导汉语学习者,使其将不成词语素或音节字当作词来单独使用,造成偏误。例如Pleco将“旅”的不成词用法解释为travel,并标注为动词,汉语水平不高的学习者很有可能在查阅词典后将不成词语素“旅”当作词语“旅行、旅游”来用,出现“我明天要去旅。”“你喜欢去哪儿旅?”等错误用法。我们在检索暨南大学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后发现,留学生将不成词语素当作词来用的偏误并不是个例,如:
1. 至今、它成为世界惟一的特观。
2. 我去了河原、梅州、福建,观了土楼。
3. 就是当那些动物踩上它时,它的种子就会被带到别的地方生户、发芽,进行繁殖。
4. 老实说,我们小时候的衣服都是穿妈妈用剩下的巾来做给我们衣服。
上述学习者因无法很好地区分意义相近的成词语素项及不成词语素项,将不成词语素“观、户、巾”当作独立的词来用,这引起了我们的反思:当下的汉语词典及词典类App的词性标注是否加剧了这种趋势?我们如何在促使语素素性发挥作用的同时避免学习者混淆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
(二) 优化语法标注的对策
介于Pleco中语素素性标注依据不完善、标注体例不科学,我们提出了功能与意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素性标注依据,以及语法标注的区别性原则和“分层标注”的新型标注模式,在区分同形异层语法单位的基础上,发挥素性的积极作用。
1. 语法标注的“三结合”依据
(1) 功能与意义相结合
“语素的语法类别问题基本上就是词类问题”(吕叔湘 1962),因此我们在进行素性标注时可类比词性标注,将语素的功能与意义结合起来作为标注依据。语素的意义在确定语素同一性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捷径,我们可根据语素项意义关联与否,完成语素的分项与合并,这是素性标注的前提,但根据尹庸斌(1984)的统计,75%的语素都有两个及以上的语素项。语素的多义性造成了语素的多功能性,在不同的组合中,语素可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和功能,反过来说,语素的多义性是通过不同的词法组合实现的,语素的意义需要在组合中显现,自身具有模糊性。因此我们在判断素性时需将语素放进组合形式中去,观察该语素与组合中其他成分的搭配规则,判断其语法功能,做到功能、意义相结合。例如Pleco将“蜂集”中的“蜂”标注为副词性,认为其表示“像蜜蜂一样(聚集)”,然而Pleco如果充分考虑被释词的内部语法组合形式,并类比“云集”“狼吞虎咽”等词,就会发现此类词语都是名词修饰动词用法。因为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蜂”并不因为其临时意义的改变而改变词性,仍做名词。
(2) 共时与历时相结合
从现代汉语的词法出发来判断素性是共时层面的素性标注依据。除了共时层面,我们还可从历时角度出发,从对应的古代汉语单音词的词性入手,推断现代汉语单音节词或单音节语素的语法性类,做到共时、历时相结合。古代汉语单音节词汇占优势,随着汉语的发展,大量古汉语单音词降格为单音节语素,在词法层面发挥作用。虽然由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但词汇的继承性使现代汉语单音词与单音语素和古汉语单音词在意义、功能上都有莫大的聯系。因此古代汉语单音词的词性为我们判断现代汉语语素的素性提供了捷径,很多学者都在研究中肯定或采用了这一方法
(吕叔湘 1979;尹庸斌 1984;李行健 1997;杨锡彭 2003;董秀芳 2008等)。例如“客”的动词性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已丧失独立使用能力,仅在“客居”等词中出现,但在古汉语中做独立动词,因此可据此将其判定为动词性。
(3)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汉语语法分类研究中,学者们选用了不同的理论依据,如董秀芳(2008)利用“中心原则”(Headness Principle)和X标杆理论(X-bar theory)来研究语素的语法类别和名词性半自由语素的独立条件,俞士汶等(2020)运用生成词库理论解决动名兼类问题等。我们认为,理论支撑对词性标注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标注过程中,我们还要充分考虑语素的实际使用情况,即根据其在汉语语料库中的分布来立目、标注。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样既避免了“内省法”的主观性,又解决了理论覆盖之外的条目的标注问题。例如Pleco收录了动词“进”的“使球进”义,而《现汉》第7版并未收录这一义项。我们检索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发现,“进球”的检索结果共有1万余条,使用率很高。因此,根据实际使用频率和使用方式,我们认为词典应该收录这一用法,标注为动词性。
2. 语法标注的区别性原则
许多学者反对在辞书中标注语素素性的原因是将词和语素一股脑儿都标上语法性类,会使原本界限就模糊不清的二者变得更加难以区分。《规范》和Pleco都是如此,对词和语素不加以区分,全面标注词性,如“餐”的释义:
Pleco:1.N. food; meal 西餐 中餐 2.V. eat 饱餐一顿3. MW. [for meals] 一日三餐
《规范》第三版:1.吃;吃饭 |会~ 野~ 2.饭食 |夜~ 快~
“餐”的名词性用法和动词性用法都属于不成词语素项,在现代汉语中不可单独使用,然而Pleco和《规范》的无差别标注模式很容易引起误会,尤其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容易误导他们将“餐”当作名词和动词来使用,形成“吃餐、餐饭”等偏误。对面向汉语学习者编纂的外向型词典来说,语法性类标注的首要目的是让外国学习者明白单位和单位间的搭配关系,即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用对、用准”,强调词和语素的功能及意义,而不是纠结于二者的概念和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外向型汉语词典在进行语法性类标注时应该区别词性标注和素性标注,即从检索层次和标注符号两方面对词项和语素项加以区分,尽量做到一目了然,不涉及过多专业知识。
3. “分层标注”模式
我们在区别性原则下提出“分层标注”模式,具体分为两步:
(1) 区分义项成词与否。从词典字头下的义项出发,根据各义项的成词情况将其分为“成词类”和“不成词类”两类,其中成词类的义项可以单独使用,具备独立性,用“X”表示;不成词类的义项不能单独使用,需与其他成分组合成词,用“-X”表示(X为检索的条目)。
(2) 分类标注词性和素性。将“X”类和“-X”类中的语素项分别标注“N.,V.,ADJ.”或“名、动、形”,凸显其层级差异性。
以上述的“餐”字为例,其在新型标注模式下的体例如图2所示:
我们借鉴英文词典对词缀的注释方式,将同样不能独立使用的不成词语素项归为“-X”类,用“-”表示汉语语素的黏附性质,不具体区分前附与后附,这样既能有效将同形异层单位区分开,防止偏误的产生,又能避免在每一个不成词语素项前面都加注表示语素的区别性符号或者改变素性标注的名称所带来的麻烦。
四、 新型标注模式的意义
(一) 优化外向型词典标注体例
无论是内向型词典还是外向型词典,只要涉及全面词性标注,就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录内容不完善、标注对象不明、兼类情况标注不当、释义及例证中的语法性类与词性标注不一致等。因为外向型词典多是内向型词典的删减本(陆俭明 2007),加之其使用者主要是缺乏汉语语感、极易“迷信”词典权威性的外国学习者,所以这些标注问题在外向型词典中更为突出,造成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像Pleco这种使用率颇高的外向型汉语词典App,其因标注不当带来的负面影响更是巨大。
我们提出的新型标注模式强调语法单位的区别性特征,其对外向型汉语词典标注体例的优化具体表现为:(1) 明确标注对象。新型模式标注的对象是兼具语法功能和意义的词、语素及语素化后的音节字,避免遗漏和过度标注;(2) 区分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当下词典中的词性标注与素性标注大多在名称、方式等方面不做区分,易导致单音词与单音语素的混同。分层标注能有效区分同形异层单位,避免误用;(3) 完善兼类成分的标注。汉字的分类标注使词和语素的语法层级在词典中得以体现,字头下词的兼类和语素的兼类更加明晰。新型标注模式既能发挥词性、素性标注的积极作用,又能避免二者混淆所带来的弊端,还能有效解决收录内容不完善、标注对象不明等词典现存的问题。
(二) 辅助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学习
自从胡炳忠(1987)提到留学生出现将“鸡”描述为“鸡蛋的妈妈”这类错误时,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整词输入”式的汉语词汇教学在某些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因为复合词内部语素的组合具有灵活性和可分解性,“词本位”这种“整存整用”的教学法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虽发挥了一定的优势,但随着学习的深入,留学生了解复合词内部的构成成分及构词规律的需求加强,这就涉及语素的意义、功能和组合规律的教授。白乐桑、张朋朋(1997)等“字本位”倡导者们正是意识到了常用构词成分和构词规则在扩充学习者汉语词汇量教学中的作用,所以提倡“以字带词”的教学原则。这种强调利用词内共同语素进行词汇拓展学习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逐词学习的模式,化“零散式”词汇学习为“網络式”词汇学习。张博(2020)也指出:“语素法词汇教学应当把握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侧重强构词力语素项,二是侧重基于特定语素的能产性词法模式。”前人的实证研究亦证明了处于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就已经开始具备语素意识,这种语素意识对汉语词汇学习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徐晓羽 2004;洪炜 2011;Zhang等2019)
我们提出的新型外向型词典标注模式能培养汉语学习者的语素意识,帮助其了解复合词构词成分的语法性质,掌握复合词内部的构词模式,加快汉语心理词典的构建。使学习者灵活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词汇学习通达模式,提高汉语词汇学习的效率和质量。
五、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汉字样本在外向型汉语词典Pleco中的标注情况,从现象到本质地探讨了Pleco不严格区分单音节词、单音节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的词性标模式,发现这种面向汉语二语学习者标注模式看似毫无道理,但结合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规律以及汉语自身的特点来看,该标注方式意识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与母语学习的区别,重视语素在组词造句中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Pleco的标注模式及其依据不够成熟,不区分单音节词、单音节不成词语素和音节字,统统进行无差别标注的做法容易使汉语学习者混淆不同层级的语法单位,在使用过程中造成偏误。因此,本文在肯定外向型汉语词典对不成词语素标注素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与意义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标注依据,以及语法标注的区别性原则。在操作层面,本文提出了“分层标注”的新型标注模式,并讨论了新型标注模式在优化外向型词典标注体例和辅助汉语词汇学习中的意义。
附 注
[1] 本文的“音节字”指叠音词、联绵词和音译外来词中不能单独表义的单音节成分。例如“猩猩”的“猩”、“葳蕤”中的“葳”和“蕤”、“披萨”的“萨”等。
参考文献
1. 白乐桑,张朋朋.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7.
2. 蔡振光,董燕萍.从表外词语介入看汉语复合词的心理表征.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2).
3. 迟铎主编.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4. 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编写.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 桂诗春.语用和记忆.语言文字应用,2000(1).
7.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编.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修订本).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8. 洪炜.语素因素对留学生近义词学习影响的实证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1).
9. 胡炳忠.基础汉语的词汇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4).
10. 金立.汉语常用字中的不成词语素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3).
11. 李行健.“规范字典”的特点在于“规范”.语文建设,1997(6).
12.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三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13. 陆俭明.词汇教学与词汇研究之管见.江苏大学学报,2007(3).
14.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5. 吕叔湘.说“自由”和“黏着”.中国语文,1962(1).
16.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7. 马楠.词典词性标注的单位问题.辞书研究,2009(3).
18. 潘绍典.词素略论.教学月刊,1986(10).
19.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0. 孙德金.略谈词性标注的目的性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4(2).
21. 徐晓羽.留学生复合词认知中的语素意识.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2. 徐振邦主编.联绵词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3. 杨锡彭.汉语语素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4. 杨玉玲,杨艳艳.汉语学习词典调查分析及编写设想.现代语文,2019(2).
25. 尹斌庸.汉语语素的定量研究.中国语文,1984(5).
26. 俞士汶,朱学锋,刘扬.参照生成词库理论对动名兼类现象再讨论.辞书研究,2020(4).
27. 苑春法,黄昌宁.基于语素数据库的汉语语素及构词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2).
28. 张博.“语素法”“语块法”的要义及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2020(4).
29. 张寿康.略论汉语构词法.中国语文,1986(10).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31. Aitchison J. Words in the Mind: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87.
32. Chen T. The Contribution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Lexical Inferencing in L2 Chinese: Comparing More-Skilled and Less-Skilled Learner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2018 (4).
33. Chen T. The Role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in L2 Chinese Lexical Inference: From a Perspective of Word Semantic Transparency. Reading and Writing,2019(5).
34. Ke S E, Koda K.Contribution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to Adult L2 Chinese Word Meaning Inferencing.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17(101).
35. Terisman A M.Contextual Cues in Selective Listen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60(12).
36. Zhang H M,Koda K,Han Y T, et al. Word-specific and Word-General Knowledge in L2 Chinese Lexical Inference: An Exploration of Word Learning Strategies . System,2019(87).
(澳門科技大学 澳门 999078)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