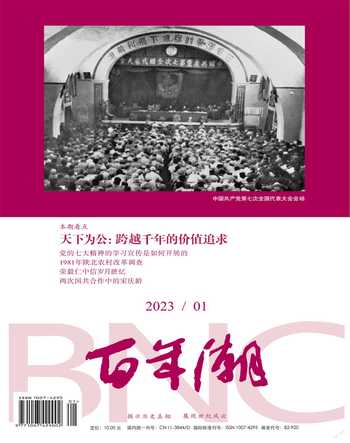张元济:愿留老眼觇新国
2023-05-30宫陈
宫陈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宣布我国正式实施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生产加速发展。卧病在床的张元济有感于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欣荣景象,于1954年初写下两首告存诗篇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心情:
微躯撑拄又三年,弹指光阴境屡迁。
为报亲朋勤问讯,夕阳红好尚依然。
预期计划盈三五,社会主义万般新。
愿留老眼觇新国,我倘能为百岁人。
张元济一生经历丰富,阅尽沧桑,年届垂暮,“及身亲见太平来”。新中国成立后,他献身文教,热忱国是,积极参政议政,“夕阳依旧晚来红”。关于张元济晚年关心时事,建言献策的具体情形,既往研究已有若干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补充一些背景细节,希望通过对晚年张元济形象的侧写,丰富我们对于其人其事的认知。

毛泽东与张元济在交淡
1949年秋,张元济北上进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围亲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皆感意外。刘承幹在日记中便提到:“阅《解放日报》北平开政协会议,皆有张菊生、周孝怀之名,遂以电话去问已否启行,家人回答去已数日,深为讶然。”之所以有此反应,是因为张元济本人向来声称不涉政治;此前在1948年底,潘公展、杜月笙等人集合沪上各界名流发起成立上海自救救国会,将张元济姓名列入“行动委员”名单之中,张元济在得知此事后马上登报声明,以“年力衰迈,凡社会公共事务不克担任,久经谢绝”为由,予以拒绝。并且对身旁友人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平日正以步履维艰为苦,如何还能够跟着他们‘行动’呢”?同为政协会议代表的张难先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即专门指出,“本席这个小组的代表中如张代表元济、周代表善培,都是七八十多岁的人,数十年不愿参加甚么政治性的会议。却是此次所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家都欢欣鼓舞,不顾衰老,毅然参加,这实在是看见解放军军纪之好,政府人员之刻苦努力,以及毛主席、朱总司令之英明领导所感召。就这几位老先生之参加看来,真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之心悦诚服地拥护人民政府。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故本席附带的报告一下”。
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饱受日寇摧残,元气未复国民党又接着发动内战,再加之属于国民党派系的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分割其业务市场,多方打击之下营业状况愈加恶化。张元济希望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环境以利于商务印书馆业务的重振。在写给严景耀的信中他说,“战事延长,遍地烽火,人方救死之不暇,诗书自非所亟。一、二月来,全馆几无营业可言,累卵之危,不堪设想”。有鉴于此,在1948年春,张元济获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后,面对教育部在南京举办院士大会的邀请,张元济称病婉拒;他在给朱家骅和翁文灏的复信中自谓“元济毫无学识,滥厕儒林,枉窃荣名,深惭非分。然得追随海内贤哲,藉资激励,自顾菲材,尤深私幸。复蒙宠召,极□思趋(原文如此,引者注),只因染患感冒,不克远行,只可辞谢”。后经教育部方面再三礼请,他虽最终出席,但在会上发表了不受国民党欢迎的《刍荛之言》,再次表达强烈的反对内战态度,呼吁通过共同协商实现和平稳定。在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以前,张元济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此外还为被捕学生发声,与国民党政府大唱反调。进步报纸评价他“思想先进”,认为“其言论文章,与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志同道合,惟他身未入党籍,不过站在人民立场上说话”。

新政協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张元济等同游天坛
新中国成立前夕,考虑到张元济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其一贯态度,新政协会议在筹备过程中竭力邀请他参与其中。
1949年8月,上海市委统战部交际处负责人梅达君第一次登门拜访并将北平方面有意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告知时,张元济写信谢绝。其后,既是商务董事也是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的陈叔通,告知张元济已将其列入会议特邀代表之列,张很快再次回信予以推辞。为了消除张元济的种种顾虑,8月27日,陈毅与潘汉年联合致书张元济,明确告诉他“昨接我党中央来电,人民政协筹委请先生作为邀请单位代表出席,并望于九月十日前抵平”,由于此前张元济声称自己因病无法远行,陈、潘还“特再派周、梅两同志前来探视,并致慰问之意。如近日贵体转佳,盼能北上”。这次张元济虽然继续坚称“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但既然“一时行止尚难决定”就表明态度已经有所松动,随后,政府方面再度敦请,最终在统战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张元济于9月3日决计接受北上之邀,并将这一消息告知友人。在致张国淦的信中,他曾提到:“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
在北平期间,张元济为化解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窘境而多方联络政学名流,先后拜会了陈云、陈叔通、黄炎培、郭沫若、茅盾、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宦乡等人,希望获得各界的支持。
作为身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传统文人,张元济对于新生政权的接受并非一蹴而就,经过他自己的思想认识的深化和我党积极的思想工作和统战工作,他逐步认同并支持中共的种种政策。譬如,刘承幹在江南解放之初,因政府在家乡征粮而求助于世交张元济、周善培等人,希望他们能够代为向中央反映,以纾民困。张元济借毛泽东设宴招待之机当面进言,有关此事的解决之道,张元济建议“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可以看出此时的张元济的思想依然固守传统,在乡村基层治理中重地方士绅而轻中共干部,对新生政权的治理模式尚未有意识。与之同席的陈毅解释说江南的税赋较之河北、山东等北方省份已不算重,并且没有抽丁,江南地主过于看重自身钱粮,多有抗拒,所以官方要加以惩罚,以儆效尤。对此,毛泽东答复称等军队南下福建之后,江南等地的情况自当好转。随着政权鼎定,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全面展开,张元济的思想也随之转变。随后在他与刘承幹就私人藏书的处置办法商议期间,两人就时局形势有所交流,张元济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极大信心:
此次上海代表大会伊与孝怀皆列席,开一星期,昨日闭幕,即着手组织华东军政委员会,不久即将成立。现在共产已成立,蒋只有台湾、海南、舟山三岛,无能为矣。共党已无敌手,美国亦聪明,决不肯徒然牺牲,是以数年之内共党必无他虑。至于人民,则必艰苦正长云云。
土改期间,张元济对政府政策也颇有微词。负责张元济祖产收租的司账“因受种种压迫,不胜惶惧,业经辞职”,改换他人后亦不奏效,因“各乡农民协会不允田主收租”,张元济因此致函海盐政府,质问“似此租不能收,粮何从纳”。随后又就土地问题与饶漱石在开会时辩论。为了更好地取得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理解,毛泽东先后指示,欢迎他们赴全国各地参观土改成效,并且指出,这样做“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张元济这些文化老人对于土改过程中的一些现象的暂时不理解,毛泽东也认为“让他们议论纷纷,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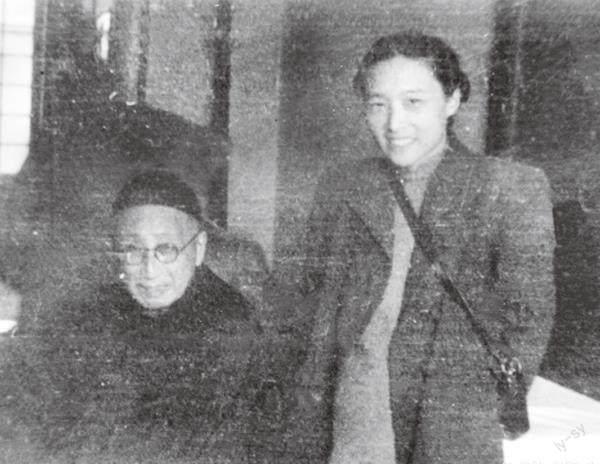
张元济和家人合影
张元济虽然因身体状况没有同参访团亲自前往各地调研,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从报刊和周边亲友处了解到更多关于土改的情况。在土地改革完成之际,张元济特地作诗祝贺,称赞新政施行后“农尽服畴,民罕坐食”的大好局面:
赢来岁月堪矜贵,争说今年胜去年。闻所未闻见未见,史家载笔看空前。
八口之家百亩田,子舆遗意至今传。试看膴膴周原上,旷土游民一例删。
“三反”“五反”运动大规模开展后,张元济对于运动形势非常关注,对于“三反”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等口号,张元济有相反看法。他将中国共产党政策比附为先秦诸子中的墨家学说,认为该主张虽好,但不合人性,张元济主张以儒代墨,高薪养廉。随着认识的深化,张元济逐渐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指示商务印书馆上海方面负责人陈夙之,在商务内部进行裁汰冗余的部署:
陈云君政治报告,亟需厉行节约,渡过经济难关,以俾建设。鄙见本馆容有复沓机构及可省之浪费,可否由董事会提议,仰承政府宗旨,特设一××节约委员会,筹划进行。人选由总管理处及工会推出,是否有当,请代提出讨论。
与此同时,张元济以捐赠祖宅的实际行动支持新政权。位于海盐的张元济祖宅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租借给当地学校作为校舍,1950年海盐中学致信张元济,希望他能将祖宅献出。该处房屋为张元济与同辈宗亲共有,因此捐赠需要获得同宗共允。在与长房儿媳许廷芬商议时,他劝慰同族:“海盐故居现租县立中学,每年租米十二石,为数甚微。托人代收,收到即被人用去,且新章地价税极重,以后无法承担”,因而继续保留祖产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无利可言,是故他告知族人“决定捐与该中学校”。在捐赠正文中,他写道,“本县县立中学赁余室教授生徒,历有年所。比来学者众,苦无力自建校舍。回忆余母在日,汲汲以余兄弟学业为念。今当推余母之志,以及于全邑之学子,思以先人遗产全部赠与本县县立中学,永为校舍之用”。
而对政府为尽快恢复生产,面向社会各界发行折实公债的举措,张元济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闭幕致辞中也极力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不是专用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而且为了全国人民利益的生产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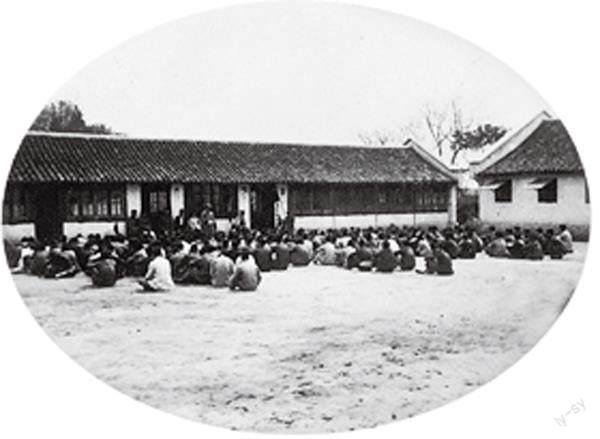
张元济捐作校园的祖宅
对张元济的争取与职务安排,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1954年李维汉在第五次全国统战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既要保证党员加进步力量占显著优势并处于领导地位,又要包含需要包含的民主人士”,要对政治上可靠、有相当的代表性等三类资产阶级人物予以重点安排,李维汉在报告中将张元济作为典型:
还要照顾到各种历史关系,旧政协时提张元济作代表就因为他参加过戊戌政变,这些历史关系第一届政协时都是照顾了的,现在也不能不管。各个社会集团也都要照顾到,不要使人感到我们有偏爱,要全盘考虑,通盘打算,要考虑如何平衡。
上海文史馆筹备期间,在李维汉、周而复亲自登门劝勉下,张元济答应担任馆长职务。在给陈叔通的信中他提到:“闻人言,市府须开会议决,谓觅一资格相类者殊无其人。甚矣,人惟乎名,猪惟乎壮也。如对方提出不必问事,弟意亦祇可勉应从。”在正式就职后,张元济时常通过陈虞孙、江庸等馆内同事了解文史馆工作情况,并嘱咐将馆务记录定期抄送其披阅。此外,张元济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早在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期间,张元济就向冒鹤亭表示,“普选投票,举国若狂……老辈可谓躬逢其盛矣”。在正式当选之后,陈叔通劝告他,“公以东南人望,被选为代表,可以不来京。昨周总理、李部长维汉尚以为言,属传达,如有意见可以书面寄来”。但是张元济立即表态,声称要扶病北上,为国尽忠。之所以垂暮之年依然壮心不已,原因或可从其与友人的通信中窥见一斑,他曾对黄炳元言及自己“民国后却未入仕”,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政府以礼相羅,弟曾到京列席政治协商会议”,原因即是“弟以为今之政府与民国之政府迥不相侔”。毛泽东在了解到张元济来京赴会的意愿后特地委托陈叔通“代为致念”,考虑到“此来不但途中不便,即到京或亦有妨静摄”,故也劝慰其一动不如一静,同时对之关照有加,叮嘱相关部门“文件可以寄去”。宋云彬的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录:
陈叔老接张菊老(元济)自上海来信,谓当选全国人民代表无上荣幸,必当扶病来京出席,死在北京亦所欣然云云。按菊老自参加第一次政协全体会议回沪后,即患半肢风瘫,至今卧床不起,年龄较叔老长九岁,今年为八十八岁(依中国习惯算法),在势万不宜来京出席,叔老已去函婉加劝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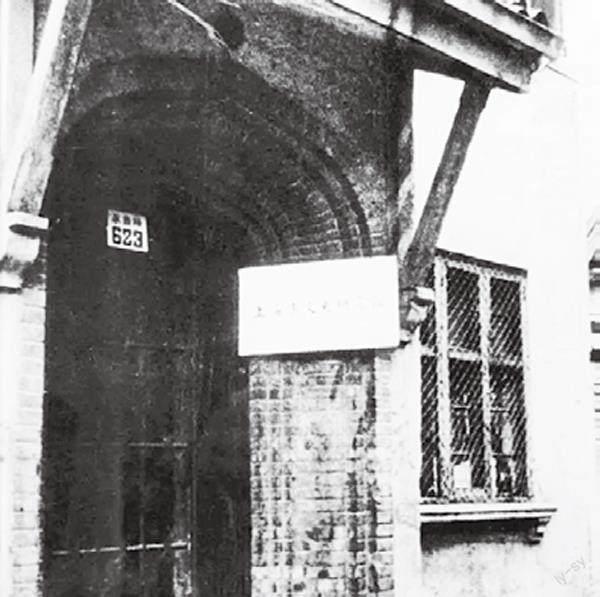
上海文史馆最初馆址永嘉路62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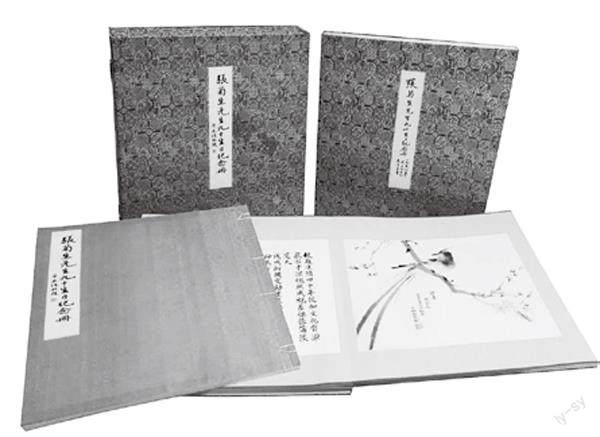
就在张元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同时,其所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也在努力寻求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期间,黄洛峰代表出版总署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谈话时就特别指出,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虽同为老牌出版企业,但中华的董事长吴叔同“在政治地位与出版事业中均不能与张菊生比”。对于这类地位较高的“资方代表”,统战部门在对他们的安排上也作了稳妥的部署。李维汉在谈到对资方的改造问题时,特别指出设立“董事会”的作用:
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历史比较短,但是按个人年龄来讲他们有些人还是相当大的。这里面有一批人在企业中是有地位的,和这个企业有深远的历史关系,但是他们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多少事情了,不是实职人员。这些人我们管不管?要不要把他们安下来?如果不把这些人安下来,那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从清朝以来的那些旧知识分子,至少是光绪皇帝、袁世凯、蒋介石时候的旧知识分子,都把他们安排了,到处设了文史馆,还设了半文半武、文武合流的参事室之类,对这一些人作了安排。那么现在对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怎么办?我看董事会就是安排资产阶级分子的文史馆。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些人安排下来,对资本主义总应该比对封建主义优待一点。
1956年10月30日是张元济的九十寿诞,在此之前上海有关方面领导邀请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张元济故旧蒋维乔、舒新城、江庸等一起筹备为其庆生。据蒋维乔的日记所载,10月25日上海政协开会,“到会后,祝公健,舒新城、龙榆生、沈尹默、江翊云、屠基远等讨论张菊老九十生辰如何为之祝寿”,蒋维乔“与新城等已接商务书馆通知,撰诗祝贺,政协会方面拟送礼物”。张元济生日当天,“党政府为备盛席,在他家祝寿”。此外,中央与上海各级领导陈毅、李维汉、郭沫若、黄炎培、柯庆施等皆发来祝寿电文和信件,并送上诗画礼物,蒋维乔记述其与张元济的会面情形:“我与菊老已年余不见,见面后握手不放,格外亲热。虽半身不遂。耳口皆不便,然兴趣甚好,精神尚不差。欢宴至午后二时方散归”。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病逝。老友陈叔通悼怀故人,撰写挽联概述其一生行状:
通艺开风气之先,钩党归来,殚正文化,乃遂及散材平岁相期知己泪
晚境为病魔所困,绳床偃息,偶咏诗篇,犹不忘國事洪流共济老成心
(责任编辑 杨琳)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