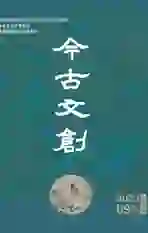浅析《有生》中的苦难叙事
2023-05-18张丽
张丽
【摘要】胡学文在《有生》这部鸿篇巨制中,以深刻细腻的笔触书写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百年间乡村苦难的历史以及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胡学文借助祖奶和宋庄人的一生冷靜、客观地表达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深刻洞察,展示了苦难背后的温暖人性和悲悯情怀,对苦难境遇予以积极的表达。
【关键词】乡土;苦难;人性;悲悯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9-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02
《有生》讲述了百年中国的生命秘史,胡学文以一位出生在晚清时期的贫苦女性乔大梅的故事为主线,把由乔大梅所接生的宋庄几代人的生命历程进行串联,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乡村百姓艰难的生存状态。从鲁迅到余华、莫言、贾平凹,作家在表现乡村底层百姓的生活时,苦难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总是处于叙事的焦点。可以说,苦难一直是乡村叙事的重要母题。正如丹纳所言,“在一切理由中最有力的一个理由,使艺术家倾向于阴暗的题材。作品一朝陈列在群众面前,只有在表现哀伤的时候才受到赏识。” ①在描绘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这段历史时,作家对苦难尤为关注。然而,当代文坛许多作家在书写苦难时常常选择戏谑或尖锐的方式,笔者认为,漠视苦难或为苦难而苦难都使得苦难的本质被消解。胡学文在书写《有生》时,既保留了乡村叙事中记录底层百姓和苦难的共性,同时又发掘了苦难中底层百姓温暖的人性和悲悯的情怀,对苦难境遇予以积极的表达,既体现了历史疼痛感又充满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
一、苦难中的悲悯与人性
洪志刚说:“现代主义小说,由于其本身就一直强调对人性内在的幽暗面进行揭示,强调对存在的潜在状态进行探寻,因此,苦难并不是作家表达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他们审度人性本质和检视存在境域的一个载体。” ②胡学文在书写《有生》时没有选择宏达的历史视角,而是将历史转为普通民众的个人经验,通过对个体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的表达探寻群体的生活状态,达到审视人性的目的。乔大梅与父亲北上之路对应1942年河南大旱之后惨剧人寰的大饥荒,宫廷锯瓷匠梦想破灭源于清政府灭亡,从罗家豆腐家族传说中可以窥见慈禧逃离的一角、关外生活、关税叠加、土匪横行……胡学文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这些历史大事件,但几乎每一场历变都以不同形式在乡土中国的普通百姓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胡学文一以贯之的用小人物的个人化视角和个体经验的叙事方式,把这段时期的历史多元化呈现出来,用乡村接生婆乔大梅以及乔大梅所接生的如花、毛根、钱玉等低视角成就百年中国蝶变的崇高立意,挖掘苦难中的温暖人性和悲悯情怀。
“苦难”是《有生》的底色,也是串起全篇的链条。从乔大梅到宋庄的百姓,无一不是苦难的亲历者。乔大梅出生时,便是“踩地生”,意即出来的不是头,而是脚,并且是一只腿出来。这种情况,给乔大梅母亲接生的接生婆也只遇到过一次,当时结果是母子双亡。如此状况,接生的过程自是一波三折,接生婆三番五次要逃离,母亲昏过去两次,出生后的乔大梅被拍打多次都没哭出来,最终在接生婆即将放弃时咳嗽了两声,算是宣告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用接生婆的话说就是“这孩子命大”,其实接生婆想说的是“这孩子命硬”,一语成谶,母亲、父亲、丈夫、孩子甚至朋友、姊妹先后离自己而去,就连唯一的孙子乔石头也要被死神带走。出生时的苦仅是所有苦难的开始,乔大梅所受的苦却不止这一种。乔大梅四岁时,父亲中了别人的圈套倾家荡产,从此一家三口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纵然父亲一直想买回自家房屋,却因为接连的大旱让一家人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逃亡之路,亦是苦难之路,乔大梅时刻体验着困顿之下生命凄凉的存在。她经历了母亲的死亡——逃荒路上难产而死,其尸体被蚁群吞噬;经历了饥饿——众人为抢一具鸟尸大打出手,父亲的耳垂被咬掉;经历了梦想破灭——清朝灭亡,北上做宫廷锯瓷匠的念头被浇灭。本以为定居宋庄之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却是另一种苦难的开始。父亲被害,自己被土匪强奸,丈夫遭遇狼灾,孩子一个个因意外或疾病死亡。乔大梅在苦难重重的逃难之路上,没有见到新生与希望,却无时无刻不在接触死亡。为了活下去,她只能艰难跋涉。对乔大梅来说,苦难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有心灵上的。饥饿、疾病、匪患、鸦片……不仅仅乔大梅是苦难亲历者,她身边的宋庄人,或者彼时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底层百姓与乔大梅一样都是受难者。这与乔大梅最后思考的一句话是对应的:“当然,有一点是能说明白的,路的开端其实就是结果。”人们从出生开始,就面对着苦难,面临着死亡。
在叙述乔大梅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时,胡学文选择了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叙述,这种“冷静”使得苦难变成了顺理成章的、无法逃避的困境。然而乔大梅却没有被苦难束缚,而是在苦难中激发了灵魂深处的温暖人性,走向了接生婆的道路,使得全篇充满悲悯众生的人性光辉。
年幼的乔大梅作为苦难的被动承受者,对身边的人与事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强烈的情感一直在她的潜意识中存在、积聚,直到她成年之后,因为一个契机突然强烈的爆发出来。乔大梅生产就是这个契机。孩子的顺利出生让乔大梅看到黄师傅头顶上光芒四射,这份光芒就是人性的悲悯。这种新生命带来的光芒与她此前所见到的种种死亡带来的黑暗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这样的契机下,乔大梅没有选择守着安稳的日子生活,而是选择成为一名接生婆,她要用新生命带来的一缕缕光明照耀进童年因为死亡而黑暗的记忆中。在胡学文的笔下,人性最深处的欲望不再是“黑”与“暗”,而变成了“悲悯众生”。
陈思和说:“从生命的本能来看,人是要生存的。生命在一秒秒地消失,在这个消耗过程当中,人类有一种本能的抗衡,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就是生存。生存就成为人类的伦理的第一任务,我们经常讲‘生存第一’,因为它是生命最本原的,明明知道自己生命一天天在消失,但是,他必须要有一种意识把它拉住,其实是拉不住的,那你拉不住,生下来就死掉了,他还是要拉住。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人的生命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人跟自身的消耗之间,一个无情的非常艰巨的斗争,我想这个斗争的张力是人类生命当中的第一因素。” ③在胡学文的笔下,“生育”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能,祖奶一生虽然历经苦洗礼,却始终心怀对生命的敬意,“接生”成了祖奶悲悯众生的方式。苦难不再是底层百姓的孤苦和艰辛的传达,而是激发出温暖人性的引子。苦难从此被赋予了积极的审美冲击力。
二、以乡土为载体的苦难叙事
乡土社会作为苦难叙事的载体,往往因其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而使得苦难的根源更加复杂。
乡土社会聚村而居,人口流动率少,社区间的往来也疏少,因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有地方性的。在生于斯,死于斯的乡土环境中,一个村庄里人与人之间必然会非常熟悉,即每个孩子都是在乡人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村这个固定而稳定的空间中,胡学文得以将乡土小人物的复综错杂的精神世界以祖奶为中心的牵引编织,从而将所有苦难聚集于祖奶面前,用祖奶悲天悯人的情怀冲淡苦难。胡学文并没有否认苦难,但是在他人与祖奶的对比中,祖奶那种坚韧、悲悯、牺牲的情怀使得苦难成了向上的力量,从而完成了人性的升华。
《有生》中,宋庄的每一个人都与周围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有地域之间的联系又有血脉联系,同时他们又是彼此之间情感的支撑者与毁灭者。如花是一个爱哭爱花的农家闺女,好不容易从爹娘的争执中逃离出来嫁给了和自己志同道合的钱玉,钱玉又为了给自己购买烟花而外出打工葬身煤矿。文学作品中,心爱之人被迫分离的场景数不胜数,是作家们常用的悲剧手法,但如此尋常的悲剧情节体现在如花这个自小梦想不被理解的“泪泡”身上,就尤为让人怜惜。当喜好射猎的毛根射杀了乌鸦之后,如花不依不饶,甚至从村里闹到镇长处,坚持要让毛根伏法受惩。不得不说,从脱离世俗和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这种对花和乌鸦的痴迷、执念不免令人为之感动,感叹二人灵魂之契合,感叹如花对钱玉的爱之深沉,然而当这种诗意、动人而浪漫的狂想打乱了理性的步伐时,就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深深的干扰。充满苦难的人生中,爱情是治愈心理的一味良药。可若是这伤疤被治愈后又反复被揭开,所承受的痛苦或许更甚。如花本已经丧失希望,将乌鸦当作丈夫时又燃起希望,这种心灵的自我蒙蔽何尝不是排解苦难的一种方式呢?可生活偏偏将她最后一丝希望都斩杀殆尽,让她永久地承受着与爱人分离的痛苦。罗包是做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慢性子,纵然凭借做豆腐的技艺在镇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是仍然持久的被感情困扰,因为麦香的威胁而日夜不宁。从爱人到仇敌,罗包和麦香的爱情令人唏嘘。毛根追求宋慧求而不得是一种痛苦,自以为得到却又失去的落差感更是将这种求不得的苦再加一层,这种自以为得到心爱之人却又骤然失去的苦痛足以将毛根的心理防线击溃。曾经相爱又沉浸在爱而不得的痛苦中的喜鹊和乔石头,无时无刻不在承受“心魔”的困扰杨一凡,即使祖奶这样有神性光环的中心人物,她也只是一个民间普通的接生婆,会遭遇土匪,会为生计担忧,会被胁迫,会被批斗。这些琐碎的历史,都真实地再现了底层百姓的生命轨迹,描述了苦难对人施加的束缚,增加了苦难的悲剧性力量。
埃里希·弗罗姆说:“社会地位卑微,或拥有获得实际胜利的物质力量小的人们,就必然更多地追求纯想象中的胜利,以作为实际失败的心理补偿。它是社会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 ④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性格,是在一个群体共同参与的经历与生活经验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性格可以说同样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人格,它已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人的无意识中。这种精神上的抗争与接受构成了底层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从而使得苦难有了深长的意蕴。但是苦难最终没有指向苦难本身,而是指向了祖奶。身处苦难中的每个人都选择向祖奶吐露心事以消解苦难,而祖奶此时已经是一个躺于病榻之上,无法动弹的人。祖奶之所以拥有消解苦难的力量正是因为她对众生无差别的爱和灵魂深处的悲悯。
三、超越苦难的意义与价值
在《有生》中,胡学文描述了不少神秘主义的现象。例如乔大梅第一次生产的时候,黄师傅将黄表纸的灰烬冲水喷在她身上时,她瞬间恢复了力气,并且看到了黄师傅头顶的光。当然这类带着神秘色彩的事件也在后续乔大梅接生时予以解答,这不是神佛显灵,而是自己内心的精神力量,是心理安慰,也就是书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方鸿儒老先生所说的:“信仰,特别是坚定的信仰是可以让灵魂安宁。”祖奶的信仰是对生命的敬畏,无差别的爱。
事实上,“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 ⑤祖奶通过生命的追逐和庇佑,抵达了人性至善、至美的深度,最终到达了接近神的位置,散发神性的光辉。这也能解释自从乔大梅成了接生婆之后,她听力更加灵敏的原因。当她成了祖奶,这个人间意义上的“神”的时候,更是可以闻得到四季的气息。这种在祖奶身上的“神性”体现,是对生命本体神智的深度挖掘。“神存在与生命本体”,神性是以美与爱为内置的人性。神性的回归能够让沉沦的人重新“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业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祖奶灵敏的嗅觉和听觉正是神性对人的感官的唤醒。
几千年来,在中国民间有许多的信仰——儒释道,以及药神、灶王神、土地、关公等,但这些信仰都是临时的、急救式的信仰,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就像宋庄人对祖奶的信仰,也是功利的,遇到问题来找祖奶诉说。祖奶,作为一个化解欲望的调节器而存在。但祖奶在历经苦难、多次拜师后,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或者说她的信仰即生命至上,这种真正的信仰推动着祖奶散发神性的光辉。女儿桃儿在婆家受了委屈,她说:“人生在世,大灾大难不能避免,受点儿委屈算什么呢?多拉几下风箱又咋的?多洗几个碗又累不着,怀不上娃的女人有的是。你认为是短,那就是短,你想开,那就没什么。人各有短,只是你不知道别人的。”白礼成因为没钱买地生气,她说:“信命不是好吃懒做,不是怨天怨地,而是不该有杂气和浮气,因为那不但帮不了你,反裹你的脚、锈你的脑。命其实是理,信命就是凡事顺着来,别拧。”面对苦难,乔大梅并非没有怨恨过,当父亲暴尸荒野,她孤寒绝望时,恨不得长出毒蛇的牙齿恶狼的利爪;在接生路上遭遇歹徒时,她祈祷上苍碎其筋骨残其耳目;守着被子弹穿过的骨肉,她想变成利刃穿透凶手的喉咙;她撅在台上,拳脚、唾骂、痛斥如冰雹砸落时,她也生出过愤怒与怨恨,但她最终选择了原谅。她引领了无数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有人记挂着她的恩情,有人没有,但她始终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她说,人活在世上,要感恩的有很多。一滴水、半碗粥,清醒时的夸赞,抑或糊涂时的两个巴掌。她始终感恩,若不是产妇的叫喊,自己早已命丧黄泉。她坚信“什么都不能阻止生命的降世,无论战争还是饥荒瘟疫,响亮的哭声足以刺破阴霾”。
如果把苦难看作一个关乎德性实践的信仰。就不难理解祖奶神明一样的一生,她拯救的对象不分贵贱高下,无论贫穷富贵,不管是土匪还是日本人,所有的生命都有来到世上的权利。这不仅仅蕴涵了颇为重要的价值,蕴涵着强烈的“众生平等”诉求,它的情怀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得失,因此反向消解了世俗的价值观念。
我们的民族不乏奋斗的历史,专注英雄人物描写的史诗性著作往往场面宏大、振奋人心,但在文学史中同样需要一些作品来展现悲悯情怀与人道主义,而《有生》中對于人性的书写则使读者获得共情之时发挥感化效应。正如王达敏所说:“在世俗人道主义中,苦难叙事是启蒙取向逐渐向世俗伦理取向和人性取向的演进,其人道主义思想专注于人的生存与自我确认、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展示人战胜苦难、超越苦难而自我获救的精神。” ⑥
四、结语
胡学文通过乡土呈现,书写底层接连不断的苦难,展现人战胜苦难,自我救赎的精神,呈现温暖的人性和巨大的悲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创作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注释:
①(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第37-38页。
②洪志刚:《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③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④埃里希·弗罗姆著,刘林海译:《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98页。
⑤刘歌:《先锋的幻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页。
⑥王达敏:《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新时期至新世纪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文学评论》2009年5期,第100-104页。
参考文献:
[1](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冯光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3]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4]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J].文艺研究,2005,(8).
[6]洪志刚.底层写作与苦难焦虑症[J].文艺争鸣,2007,(10).
[7]刘歌.先锋的幻想[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