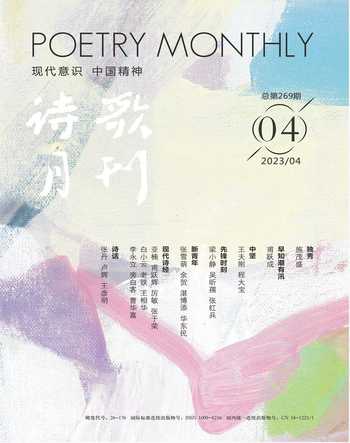老街
2023-05-12杨紫烟
穿过家门前的马路,往南下行约八百米,有条老街,街边皆为有些年头的旧砖房,大多已无人居住,一把把铁锁沉甸甸地挂在门上,显出破败的气息。砖房的前面,各有一排树,中间夹着一条狭窄的马路,一年四季,树下满是露天的菜摊,挨挨挤挤地足足拉了有一里多长,路的尽头,是通往繁华城中的大道,过往的行人经过这儿,大多会顺便拐进去,买一把青菜,一两斤水果或是其他,而后匆匆离去。
起初,我从那个清冷的菜摊经过时,它并未引起我的格外关注,因为它的位置实在不显眼,在老街入口的十字路口偏北,再往下便是人烟稀少的环城路,而大多的菜摊皆沿十字路口向喧嚣的东面延伸。那个菜摊就冷冷地被孤立在繁华之外,一张磨损的油纸铺在地上,几把水灵灵的小白菜,一捆绿油油的空心菜,一小箱红通通的西红柿,一堆油光发亮的青辣椒,还有十来根苦瓜,三五个青瓜,皆为夏天的时令蔬菜,红肥绿瘦地挤成一堆,很是热闹。菜摊的主人我也从未见过,一个蓝格子上衣,脸圆滚滚,梳着马尾巴辫子,大约三十七八岁的女子。
我猜测那菜是女子自家栽种,因为每种菜的数量都不是很多,并且格外新鲜。凭我的经验,小贩的菜通常品种繁多,数量较大,并且皆有专用菜箱整整齐齐地码放,阴晴雨雪,从不失约,一眼便能认出。只有农民的菜,大多是自家种的,并非每天都有,只是隔三差五地摘一些来卖,因此菜摊皆是临时,卖完便撤,并无固定摊位。一切都平平无奇。漫漫老街,熙熙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多一個菜摊,少一个卖菜的人,根本无人在意。我最初路过那个游离于喧嚣之外的菜摊时,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斜睨了一眼,便直奔人声最鼎沸之处而去。是的,一条老街,千般事物——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不疾不徐的家庭主妇,操着南北方言的小摊主,堆在地上或架子上的新鲜和萎蔫的果实,偶尔也会有挤在笼子里瑟瑟发抖的乡下柴鸡,以及杵在它们之间的两排大树——桑树,柳树,银杏,紫槐,和风吹过的它们婆娑的枝叶,那么多纷繁的事物,又有谁会在意路边一个寥落的菜摊呢?
但我一贯钟情于细致地去观察一些被人忽略的朴实事物——我一直认为,凡目光所及处皆有风景,譬如一条坚冰结固的河流,它与近处的河岸、远处的荒滩共处同一视野时,所呈现出的那种冬天独有的凋敝之美,可谓动人心魄;譬如清明前后路边杨柳初萌的芽苞,它们夜以继日的蠢蠢欲动,虽不秀丽,却完美地见证了季节的重生之美;譬如沙漠之中大片死去的胡杨,它们极尽挣扎扭曲的枯枝令人联想到生命的竭尽全力,也可隐喻一种消亡之美。所谓吾之蜜糖,彼之砒霜,一切的定论皆为相对而已。在老街上,我能精准地捕捉到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和各种复杂的声音、气息,所构成的一条街独有的风景或是特质——生动,质朴,以及像粗瓷海碗里盛着的黏稠的苞谷大■子粥那种跌落尘埃的烟火气。
我喜欢这样烟火气的老街,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我不再有“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或是“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的凄零,而是存在感十足;蜿蜒而下的菜摊上一字排开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丰腴而水润,它们背后所呈现出的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盛世气象,使我走路稳当,入眠酣畅,并赋予十足的安全感;而那些衣衫简朴,手臂大多被晒成焦糖色的摊主人,更让打着洋伞穿着精致美丽百褶裙的我产生一种如在云端的优越感。因此,我常常会为了几根小葱或是一块老姜不惜特意去一趟老街,以借此满足我潜意识里蛰伏的虚荣心理。
那天,我兜兜转转地为了买一把鲜嫩的小白菜又转回那个独处繁华之外的菜摊时,我才发现,那个在人迹稀少的十字路口北面,几乎无人光顾的菜摊前,卧着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水泥墩,一盆我叫不出名字的植物,正在漠灰色的水泥墩上开出一枝娇艳的黄花。
那一瞬,我呆了。那盆植物,有着狭长的披针叶,乍看像极了山野兰花,却又没有兰花那么苍绿和坚挺,以及久历幽谷自然而生的那种孤高、冷寂的气质。它更像一个家境优渥的妙龄少女,嫩绿的叶梢如同少女油亮的长发慵懒地垂落,十足一幅昨夜苦思春,通宵不曾安眠的困倦模样,可又自叶丛中心陡然伸出一枝修长的花葶,顶端吐出一朵娇艳的黄花,花萼合拢,花瓣四散张开,状若喇叭,又似爬篱的南瓜花,天真烂漫地盛开在菜摊前。
一枝盛开的黄花,那个清冷的小菜摊,还有菜摊的主人,一个有着一张圆滚滚的脸,梳着一条马尾辫的女子,忽然就成为一条老街的风景。
我蹲在菜摊前,黄花就在我身边盛开,披针叶干净翠绿,花瓣上甚至还有几滴晶莹的水珠,在阳光下清新如玉。我低头,那斜倚过来的花朵几乎就要触到我因长期失眠、多梦导致焦枯的发。我的心情蓦然变得明亮起来,那一瞬间,我甚至遗忘了,在头天,我还深陷在某些恼人的琐事之中,想要逃离这座因为长年不下雨,路边的草、灌木和树皆覆满尘土的小城。
我轻声地和女子说话,想要买一把小白菜,偶尔也微微地偏过头去,让黄花温柔地摩挲我的发。女子用肉乎乎的手递过一把湿漉漉的小白菜,我才望见她脚边立着一个小小的喷壶和一瓶水。暑热的夏日,这个细心的女子,一直在为她的黄花和蔬菜们喷洒清水。和我说话时,我望见她一口洁白的牙齿,像月亮一样皎洁。我将菜装进袋子里,侧过身去,用手小心地扶起那枝黄花,低头嗅了嗅花蕊,并无香味。
一枝惊艳了一整条老街的黄花,竟然没有香味。“它为什么不香呢?它明明应该是香的呀!”我讶异地问。
女子笑了起来,牙齿洁白,闪烁着月亮一样的光彩:“它本来就不香啊!也不是每一朵花都会香。可是,就算不香也没关系呀,你看它开得多美!”
是的,它虽然不香,可并没有影响它盛开时的美丽呀。我再次俯身扶了扶黄花修长的花葶,离去。可走出没几步,那黄花亭亭的样子还总在心里,忍不住回头望,那枝花依然安然地盛开在菜摊前一个漠灰色的水泥墩上,娇艳而又沉静。黄花之外,卖菜女子双手扶腮,正安静地坐在那里。它们的身侧,一条老街正湮没在此起彼伏的长腔短调中。一切,竟出人意外地活色生香,甚至那个漠灰色的水泥墩,也显现出一种原始、朴拙的艺术效果。
我拎着一袋水灵灵的小白菜,朝家的方向走去。我路过一个街角花园,扇形的花园里,蜀葵正开着与牡丹一般硕大的花朵,只不过它暗红的色调比牡丹低调、内敛了许多,但仍不失霸气。我嗅了嗅其中一朵蜀葵花,和菜摊上的那枝黄花一样,并无香味。它们身边,大片的白的、粉的、紫的秋英,正在纖柔的花葶之上卖弄着,风姿绰约。我扶起一枝紫色的秋英,再次嗅了嗅花蕊,亦无香味。可我依然看见三三两两的蜜蜂和蝴蝶落在那些不香的花蕊之上。
晚饭,我打了青菜蛋花汤,几片小白菜绿油油地漂在蛋花之中,浅黄间碧绿,美极。我轻轻地啜一口汤,清香四溢,渗入齿颊,也美极,就仿佛从未喝过那么鲜嫩的青菜蛋花汤。我慢慢地品味着汤,慢慢地想着菜摊前的那枝黄花,它的气质也该是清香的。
那天夜里,子时将过,小区里早已无人游荡,我独倚在一棵垂柳下,听夏风轻轻地呢喃。我一向喜欢在岑寂的深夜仰望星空,无人打扰的夜色干净纯粹,我的脸上也不附铅华,一样的干净纯粹。一枝细柳不动声色地拂过我枯焦的发,也仿佛一枝娇艳的黄花温柔地摩挲。穿过柳的叶隙,一轮圆月遥遥地挂在墨蓝的夜空,将光辉莹莹地洒在人间,几点灯光远远近近,夜色美丽而宁静。
翌日,快近黄昏时,我托辞买一把香菜,又去了老街。我再次经过那个开满了蜀葵和秋英的街角花园,蝴蝶和蜜蜂依然来来往往地穿梭,但我并无意赏花,只是匆匆而过。老街上,我望见那些喧嚷的露天菜摊,正蜿蜒而下,足足占据了一条街,那些新鲜的蔬菜们,依旧如往日一样无声地卧在油纸上,码在架子上,这其中,也有绿油油的香菜,它们的主人,也依旧大声地用长腔短调的南北方言叫卖着。可我却没有心思去挑挑捡捡,只想着一枝盛开在一个菜摊前的黄花。
那里竟空无一人。头天端端正正卧在地上的水泥墩,仍在原处,只是之上已然失去了一盆正在盛开的黄花,曾经的黄花之后,已是一片空地。我转身向喧闹的东面望去,满是菜摊的老街依旧蜿蜒而行。我穿梭在一个个菜摊之中,想要找到一个脸圆滚滚,梳一条马尾辫的女子,我走完了一整条老街,却全然没有她的踪影。
我空着手,惆怅地立在曾经的菜摊前,失落不已。我是想问一问卖菜的女子,那枝娇艳的黄花,叫什么名字,我还想冒昧地探究,它盛开在一个菜摊上的意味深长。可是消失的菜摊,黄花,和它们的主人,一个卖菜的女子,竟仿佛从未与我相遇过。我开始懊恼头天没能拍下一张照片,以此佐证,那里的确曾经有过一枝盛开的黄花。
我拾起一片萎蔫的菜叶,枯黄,像极了我头天买的那把水灵灵的小白菜,只是它已被太阳晒干了水分。我多少踏实下来,至少它证明了,这里的确是曾经有过一枝盛开在水泥墩上的黄花,用它仿佛绸缎一样光洁的花瓣温情地抚慰过一个满腹心事的女子。我将菜叶攥在手中,在心里默默地猜测,那个卖菜的女子,一定是被家事羁绊或是当天地里没有成熟的青菜可摘,才失约了一条老街和一个人。
第三日,忍不住我又去了老街,又找到那个曾经的菜摊,那里依旧空无一人,依旧只卧着一个沉默的水泥墩。失去了黄花的映衬,水泥墩被迫还原成一块被废弃的水泥块,毫无艺术效果。我徘徊在老街之中,怀念一枝没有香味却依然美丽的黄花。后来,我日日经过那里,日日期待一枝盛开在水泥墩上的黄花,可我再也没有遇见它,和它身旁一个脸圆滚滚,梳着马尾巴辫的女子。
后来,那条街上的菜摊逐日消失,我已很少再去,再后来的某日,我去老街之时,竟空无一人,我听闻他们大概是去了一个新的市场。数月之后,整条街被拆迁了。
杨紫烟,本名杨红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作协会员,有作品发表、选载于《厦门文学》《绿洲》《回族文学》《散文诗世界》《海外文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