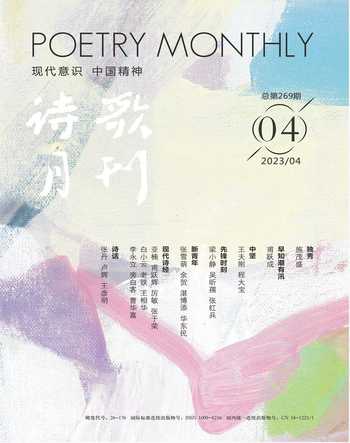时间叠加与语言代谢
2023-05-12王彦明
熊焱的诗集《时间终于让我明白》中,阐述了时间本身的无限性,时间可以打乱清晰的头绪,而其间交叉的经纬———爱、生命、孤独,更紧紧纠缠在一起,形成我们人生的际遇与认识。诗人会寻找诗意的对接点,在疼痛里捕捉内心的“蝴蝶”;而时间会使一切向下,沉淀,达成和解,进而加深生命的韧性和抒情的从容。显然,我在这里说的就是熊焱,他将在时间里获得了更多的馈赠。本文,我将从时间感、写作新范式、亲情书写、生命记游四个方面来解读这本诗集。
时间感
熊焱有清晰的“时间感”,这个概念里隐含了生命的焦虑,同时延展出无限的深情。“时间终于让我明白”,是生命的龙卷风裹挟一切,在降调的节奏里趋于平缓,归于平寂。而这背后,还隐含着时间的叠加进程,这带来了言语和精神的双重代谢。之所以说这里有“焦虑感”,除去“让”的被动性直接作用于主体“我”之上,还在于诗人“我已四十岁,我的祖辈们都死了”(《我们来自哪里》)“我不再幻想未知的命运,只是顺从于时间”(《我已顺从于时间》)一类的自我确认与修正。
“多么愧疚呀,时间终于让我明白/我的乡村有着斑斓的大美,只是作为故乡的叛逃者/我已不配接受这人间丰腴的馈赠/不配献上我廉价的爱与赞美”(《时间终于让我明白》),这首诗不仅是对时间功用的体认,更是对人生际遇和生命情境的省察。“明白”这个动词干脆决绝,以生命的截面和暂时的领悟涵盖全部。如果说因这种感觉过于绝对而否定它,似乎又否定了生命的所有进程,而显得缺乏自信。事实上,秩序中又有着诸多破碎、颠倒、扭曲和不规则。时间、身份和自然的转换,降低了抒情的调性,熊焱以一种仰视的方式转换了精神视角来感受过去的“我的乡村”,以及“我”的精神立场。
时间的概念是单向度的,但是在熊焱这里被交织成了网状,生命、爱与孤独,甚至时间本身都在网中被反复指认和标注。而写作是他命运的年轮,“那是灵魂在沼泽中挣扎,又在时间的包围中/成为精神的琥珀”(《写诗的过程》),写作是在岁月的沉淀中挣脱困境、获取延伸和修习温润的情感。熊焱后来省思:“我所理解的时间,是一个立体、丰富、无尽无穷的概念。如果只把时间理解为年月日,理解为时辰、分秒,那就太片面了。”同时,他指出:“时间让我们似乎明白了许多东西,但似乎又什么都不明白,无穷的困惑便由此产生。”这种反复与不确定感来自对现实和过往的反观,是对人生况味的体味,是内心焦虑的外显。
写作新范式
写作是生命的出神、漫游与溢出,是现实的描摹、对抗和消解,同样也是对理想现实的建构与想象。熊焱在氛围、技艺和精神几个层面,去摹写写作的快意、向光和孤独的特点。诗中同样有对时光的喟叹,“一眨眼就跑进了中年”(《夜航》),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写作就成为滴漏和刻刀,一方面在催生暗夜的花朵,一方面把生命镶进历史的年轮。熊焱在这首诗里,写“远行”“磨砺”“搬”和“开车穿过深夜的长街”,都在有意无意地改变着时间、距离和技艺。
熊焱在《返乡——致博尔赫斯》《比邻而居》等诗篇中,表明自己对于博尔赫斯、米沃什等诗人的欣赏与追慕,并希图在写作中恢复或者秉持他們的诗学传统。这种倾向势必要在这浮躁的写作环境中做出抉择,甚至进行一些具体的“反抗”。“我庆幸还有一所心灵的房子/庇护着人类的永恒”(《比邻而居》),如果有一种痴迷可以引领人的精神向上,那么写作一定处于其中,“修辞被隐藏在背后/精神的力量喷薄在指尖/最后由心灵指引,回到灵魂的沉默或轰鸣”(《手艺——观一次泥碗的拉坯制作》),而写作的终极意义还是获取心灵的震颤。
熊焱在诗歌的抒情传统中形成了他独特的抒情方式,在吸收中外的诗歌传统中观照着现实的生存境遇,使得他的表达总是沉实有力。这种衍生出的气质,可以从中窥见李白、张若虚、博尔赫斯、米沃什、叶芝等人的恍惚的影子,这些斑驳的影迹在熊焱的写作中得到很好的统一,同时也为他的写作催生出一种新的范式。他可以很好地驾驭“光明”“大海”“银河”等大词,使之在具体的细节里恢复生机。
熊焱的美学范式,还在于捡拾了部分别人“丢掉的武器”,来强化他的抒情力度。譬如在句式上,他选择了抒情意味很浓的复沓来延宕语言的气息,以跳跃的韵脚来增强韵律感,以不断扩充空间和时间来增加结尾的无限深情。就像他的诗《我一直在等一封远方的书信》,开篇就以复沓手段来将时光、深情推向空远而又具体的地方,这里有想象力的功效,而句式和音韵也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不可否认熊焱在选词上,都是一些颇具“轻逸”之感的词语,使得深挚的情感,轻轻流淌如溪水,且缀满落花。
亲情书写
亲情书写需要很好的分寸感,因为很容易陷入虚饰、浮夸和不可自抑的洪流之中,随之而来的走样,反而显得矫情而不深情。熊焱将爱、亲情、孤独、愧疚等情感和时间形成经纬,而在伦理层面又形成代际的承续,使得他的表达具有“及物感”——他以“只给了你白发苍苍的暮年和孤独”(《给妈妈的信》),来体认现代亲情的缺失和内心的愧疚;以少年的“夜读”回忆,来尝试缩减地理距离和精神距离;以“原来死去的亲人从未走远”的感叹,去将亲情扩展为对弱小者及人类的普遍爱意。
就像对于故乡,我们越走越远;对于母亲,我们离开她们的身体,就在持续地拉开距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受到委屈、承受不公时,才会想要反身折回,才有痛哭一场的勇气。熊焱多数的表达都非常克制,唯有在和母亲的交流中,才放下写作者的身姿,回归一个孩子的身份,除去《给妈妈的信》,还有《北风正在喊我回家》,都抛开了书面语的他者身份,而是以“妈妈”这个口语直接抒情。
父亲是世界的肩膀,是强力的暗示,是“假想敌”,只有在转述童年记忆中才会出现“爸爸”这样亲近的称呼,现实中则是会在某一天和“我”“分手”的人,是传递给“我”“钢笔”的人,是急匆匆外出借钱的人,是“头发又稀又白,老年斑又多又暗”的人……在诗集开篇的《父亲》中,他选用第二人称“你”来形成一种对峙、对话,然后在跨越了鸿沟之后,又进行了精神的融通——“我们成为父亲,全都用尽了生死”,而这之间的过渡就是一个儿子成了“父亲”,开始关注育儿经,“世界的朽木正在逢春”。这种克制之后的深情,是喷薄的烈焰,是理解后的余烬。
“当爱来到身边”这一辑展示的并不仅仅是亲情,还有爱与生命,甚至还有时间的秩序。那种血脉形成的伦理梯度,衔接父母、“我”与妻子及儿女,而情感的交织使得时间的有效性如鬓角之雪,雪落的层次也是如此紧凑。“是啊,真快,真快,一眨眼他们就老了/新修的高速公路分明是时间的手/要拉着我们,看一看父母的苍老与孤独”(《高速公路经过村庄》),在反复的确认,诗人的表达都加快了速度,语言和情感的节奏形成了一致,而对父母的“苍老与孤独”也就更为深沉。相对于对母亲的愧疚、对父亲的理解,对于妻儿,熊焱表现出的爱意更为直接、温润,所有的语句都仿佛幸福的呢喃。
生命记游
熊焱的诗在调性上是延宕的,余韵悠长,那些近乎民歌的游记诗更是在句式的交错中,与现实的情境形成了音节上的和谐。
古人一直都有登高记游的喜好,而此中好诗又颇多。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精神的松弛度相关联的,纵情山水,所寄情感又颇为繁复。熊焱的记游诗,有对故乡的呼应,有对现实的抽离,有对诗意的人生的触摸,有对古人的缅怀与思念,有内心的畅快,也有内心的苦闷……诗的表达在自在中得以开阔,得以自足。他选择了类似于“甘州八声”“凉州词”“清平乐”这一类词牌名,试图打通古今的情感,而在制式上却并没有太多的钳制与框定,而其中的节奏和所历风景、内心的情感形成了应和。“而我千里奔波,这曲折的旅程/那不断远去的光阴,都是我人生苦寂的修行”(《凉州词:在天祝的途中》),这种荒凉的感觉,有人生羁旅的领悟,也有凉州本身的感觉——这同时是词语本身带来的感受。我将之视为熊焱对于汉语的理解与创见。
王彦明,1981年生于天津,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天津市作协签约作家。曾获《芳草》杂志诗歌新人奖、鲁藜诗歌奖和钨丝诗歌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