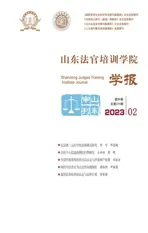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研究
2023-05-08邓昆鹏
李 可 邓昆鹏
引 言
相对于《民法通则》,《民法典》以“习惯”取代“政策”,使之成为仅次于“法律”的法源,从而形成“法律—习惯”的法源格局。①参见《民法通则》第6 条、《民法典》第10 条。民法通则法源格局中的“法律—国家政策”的双层构造,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民法发展的体系化和科学化要求。②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363 页。如哈耶克所言:“文明的发展之所以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类用那些理性不及的习俗(the non-rational customs)约束了自己所具有的先天性动物本能。”③[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哈耶克经济学、历史学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8 页。《民法典》第10 条作为法源条款,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习惯”在民事领域的适用空间,补足了制定法在民事权益救济中的“真空”。
“法的渊源的阐述方式明显反映了相应法律体系的复杂程度,以及该法律体系的社会背景。”①[加]罗杰·赛勒:《法律制度与法律渊源》,项焱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96 页。立法层面对待习惯的态度,由否定转变为肯定。②参见李可、邓昆鹏:《民法典背景下“习惯”的法源地位及可能趋势》,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然而,对于民法典的法源类型及法源的适用模式,民法学界多有争论。早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有学者认为民法法源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制定法、习惯和法理。③参见杨立新:《塑造一个科学、开放的民法法源体系》,载《中国人大》2016 年第14 期。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渊源包括制定法、习惯、判例和法理四种。④参见贾翱:《〈民法总则〉中二元法源结构分析及改进对策》,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2 期。还有学者认为民法典的法源包括制定法、习惯和基本原则。⑤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 页。但最终立法层面并未明确法理为民法典的法律渊源,只确立法律与习惯共同作为民法典的法源。在此背景下,有学者呼吁应明确法理的法源地位,以填补民法典法源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的不足与漏洞。⑥参见杨立新:《论法理作为民事审判之补充法源——以如何创造伟大判决为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 年第4 期。
可见,关于民法典所确立习惯为民法典法源之漏洞补充,及民法典采用何种法源适用模式,在学界尚无定论。为此,应予以思索及追问:一是为何最终只确立法律与习惯为其法源,而将法理排除在外?二是民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又处于何种法源地位?三是针对所确立的法源类型,在司法适用层面应构建何种法源适用模式?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立法层面与司法适用层面解构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的争论及焦点问题,揭示“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的司法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以法律和习惯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源,重构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回应司法实践中倚重制定法、偏废习惯、固化民法典法源适用路径的弊端,以期实现“法律与习惯”法源之间的和谐差序适用。
一、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的争论及焦点
民法法源适用规范,是民法法源理论在民法典上的提炼与表达。⑦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 页。法源适用规范涉及两个层面,即法源的定性与法源的定量。⑧所谓法源的定性和定量,即某事物是否具有法源地位及此事物法源地位的高低或者说在法源谱系中的位置。参见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1 期。前者主要涉及法源的范围,后者则涵盖不同法源之间的关系,即各个法源之间的位阶序列及其互动与转换。⑨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13 页。
民法最终成典,使得民法典的法源类型通过法条的形式得以固定下来。目前关于民法典法源类型的划分,最具争议的是对民法典基本原则的法源定性,即归属于何种法源类型。而关于民法典法源适用的规范,主要包括民法典法源的范围界定、法源之间的位阶关系及法源的适用方法等。
(一)关于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的争论
习惯作为一种不成文的社会规则,形成于初民社会,存续于市民社会,并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具有强大的韧性与生命力。但不成文的特质使其在民事立法与民事司法层面通常作为末位法源而存在,起着填补制定法漏洞的作用。围绕法律与习惯,针对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的争论,学界主要提出两种法源模式,即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与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
其一,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法国19 世纪的传统法,认为成文法是可以自足自满的,而惹尼(Francois Geny)并不认同此种观点,主张有四种形式的法源,且法官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①四种形式的法源分别是成文法、习惯、判例与学说。参见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7 页。惹尼的此种主张,实践层面最早为《瑞士民法典》所吸纳与创制,“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由此逐步形成。②《瑞士民法典》第1 条规定:“任何法律问题,凡依本法文字或其解释有相应规定者,一律适用本法。法律未规定者,法院得依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得依其作为立法者所提出的规则,为裁判。在前款情形,法院应遵从公认的学理和惯例。”参见《瑞士民法典》,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 页。此举也意味着,现代立法者首次在一般规定中承认法官对于立法不可缺少的作用。③参见[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 年版,第323 页。尔后“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为众多国家和地区所移植与效仿。④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 条:“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韩国民法典》第1 条:“民事,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法理。”参见《韩国最新民法典》,崔吉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35 页。我国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也有民法学者持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的观点,例如梁慧星、谢鸿飞。⑤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2 页。
然而,在肯定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的前提下,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民法典是否应当吸纳法理为法源的观点不一,主要表现在: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确立“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将法理的法源地位予以明确,充分发挥法理在司法适用中的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参照法理进行处理,民法典基本原则充当法理进行司法适用。⑥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 页。当制定法与习惯无法适用时,应通过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进行补足,由此构建的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习惯—法理”法源模式,而应该是“法律—习惯—基本原则”法源模式。例如,有学者在论及民法典法源适用规范的设计时,将法律与习惯分别列为第一位阶和第二位阶法源,法官基于民法基本原则创设的规则列为兜底性法源。①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9 页。
其二,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认为,法律规范主要以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构成,二者以能否“全有或全无”适用之标准进行区分,前者满足此标准,后者则无法满足此标准。依据此标准,《民法典》第10 条的法源条款中“法律—习惯”构成民法典法源的第一层次,民法基本原则构成民法典法源的第二层次。②参见刘亚东:《〈民法典〉法源类型的二元化思考——以“规则—原则”的区分为中心》,载《北方法学》2020 年第6 期。
由此可见,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将法律、习惯、民法基本原则划分为两种层次,法律与习惯因可以全有或全无适用为第一层次,基本原则因无法全有或全无适用为第二层次。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层次“法律—习惯”的格局中,依然适用制定法优位、习惯进行补充的惯常思路。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虽然在划分标准上逻辑周延、高度盖然,其实质依然是“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的变体,并未突破法律、习惯、基本原则司法适用层面的次序,背后隐含的依旧是制定法优位、习惯次位补充、民法典基本原则末位殿后的司法适用惯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或是“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又或是“法律—习惯”第一层次和“基本原则”第二层次之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关于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理是否可以为民法典的法源、基本原则的法源地位及法源适用次序三个方面。
(二)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争论的焦点
如前所述,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法理是否可以纳入民法典成为法源;二是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能否充当法理进行司法适用,以及在民法典中的法源类别划分与法源定位如何确立;三是如何克服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下“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惯性,缓解强行适用制定法、习惯难以适用造成的违背民情、权益失衡的情形。
焦点一,法理能否作为民法典的法源。在英美法系,现代社会及其法律体系不再过多依赖习惯和习惯法,而是更多依仗理性原则和理论学说。③See Amanda Perreau - Saussine and James Bernard Murphy, The character of customary law: an int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由此,法理和学说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法源意义,并逐步为法律体系所采纳。综观各国民法典,法理作为法源被纳入民法典,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将高度抽象之法理以“法理”概念的形式纳入民法典,例如韩国民法典;二是将抽象的法理进行分类、转化为具有实质意义的法理纳入民法典,包括自然法原则、公平、合理的要求等,例如阿尔及利亚民法典与俄罗斯民法典;①《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1 条第3 款规定:“必要时,法官也可根据自然法和公平原则作出判决。”参见《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尹田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 页。《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6 条第2 款规定:“如不能使用法律类推,则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民事立法的一般原则和精神及善意、合理、公正的要求予以确定。”参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黄道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7 页。三是将蕴含法理的载体纳入民法典,包括学说、学理、立法者提出的裁判规则等,例如瑞士民法典。可见,法理作为民法典的法源为一些国家所认可。此外,我国大多数学者也持法理应为民法典法源的立场。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当前阶段不可贸然将法理引入民法典法源体系之中。例如,杜涛认为,法理具有不确定性,其内涵与外延难以明确,适用到司法层面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②参见杜涛:《民法总则的诞生:民法总则重要草稿及立法过程背景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10 页。李永军认为,法理的概念不明确,法官引用法理进行判决易造成司法层面的不确定性。③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94 页。此外,从现实层面来讲,囿于当下法官的专业素养,实践过程中适用法理容易损害司法的公正性与案件标准的统一性;④参见梁慧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解读、评论和修改建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 年第5 期。且随着民法典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如与民法典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类推适用等,已将民法典的漏洞填补,无再寻求法理补足漏洞的必要。如谢怀栻认为:“民法的内容、民法的变化发展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如果与社会脱节,就失去了它的价值。”⑤谢怀栻:《关于日本民法的思考》,载渠涛:《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1-102 页。可见,无论从民法典自身层面,还是司法实际适用层面,法理自身的局限及弊端尚难规制。
焦点二,民法典基本原则的法源类别划分及法源定位。有关民法典基本原则属于何种法源类别,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基本原则不同于制定法、习惯与法理,而应独立作为一种法源类别,继制定法、习惯之后作为兜底性法源而存在,从而构建了“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⑥参见李敏:《论法理与学说的民法法源地位》,载《法学》2018 年第6 期。第二种观点也认为民法典基本原则属于“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但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法源类别,也不同于抽象的法理,而是作为抽象化分类、具有实质意义的法理,可以参照法理进行适用。⑦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 页。这两种观点,或将基本原则作为独立法源类别,或将基本原则参照法理适用,仍处于“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下末位法源、补充法源、兜底性法源地位。与前述两种观点不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民法典基本原则属于法律的范畴,作为民法典确立“法律与习惯”中“法律”的内容。科尔曼的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直接认可了规范既包括规则也包含原则。①维护承认规则中“充分性条款”的可能性,有时候道德性原则也可能被视作法律。参见[美]朱尔斯·L.科尔曼:《原则的实践——为法律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辩护》,丁海俊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89-173 页。如有学者认为,若作宽泛理解,法律规范可分为规则与原则两种类型,原则作为法律规范的一种,应隶属于《民法总则》第10 条“法律”的范畴。②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 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1 期。
由此可知,民法学界大都承认民法典基本原则的法源地位,且有观点认为可将“法官依民法基本原则确立的规则”作为兜底性法源。③参见李敏:《论法理与学说的民法法源地位》,载《法学》2018 年第6 期。但民法学界对于民法典基本原则的法源类别的划分存在争论,或认为属于独立类别法源,或认为参照法理,又或认为归属于法律范畴。
焦点三,“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的司法困境。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采用“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当制定法出现漏洞时,则顺位至习惯,甚至法理或基本原则,寻求对制定法漏洞的填补。而当制定法、习惯同时存在时,过于强调较高位阶法源的优先适用,特别是制定法的优先适用,有时可能背离常识,产生实质上的不公。此时,法官应选择何者作为案件裁决的依据?例如,在山东省青岛市的“顶盆过继案”中,若强行适用制定法进行判决,则会明显违背常识,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最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选择适用当地的习俗进行判决,照顾了当地的民风民俗,平衡了当事人的民事权益。④参见石坊昌诉石忠雪顶盆过继案,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05)李民初字3460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青民一终字206 号民事判决书。可见,无论是“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或是“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又或是“法律—习惯”第一层次和基本原则第二层次之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由于人为追求民法法源的先后排序进而导致司法适用的呆滞与僵化,从而很难指引法官进行司法实践。相对于制定法的优位法源地位,排列在制定法之后的习惯即使被肯定了法源地位,依旧很难获得法官青睐,长久处于弃而不用的局面。例如,《民法典》实施以来,截止2021 年7 月16 日,虽然适用“习惯”的案件有82374 例,但全部的民事案件有4188326 例,适用“习惯”的民事案件只占0.19%左右。①参见李可、韩秋杰:《〈民法典〉施行前后习惯司法适用机制疑难问题研究》,载《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
民法法典化过程中,使得民法具备了两种品格,分别是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②参见[美]艾伦·沃森:《民法体系的演变及形成》,李静冰、姚新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版,第262 页。理性化思潮使得民法典在编纂与制定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形具有一定的预判性与可欲性。依据哈耶克社会理论中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唯理主义”,民法典现行法源模式实际受到“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影响。③所谓“建构论唯理主义”,是指那种立基于每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为和个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极端赞扬人的理性能力,确信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即达到全知的“全知论”。而所谓 “进化论理性主义”则是指那种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甚至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处于“无知之幕”原初状态的“无知论”。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10-16 页。哈耶克认为:“所谓增进理论知识能够使我们越来越把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转变成一系列可以探明并确定的特定事实这种幻想,常常引发新的科学谬误。”④[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知识的僭妄:哈耶克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集》,邓正来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2 页。《民法典》第10 条确立的法律与习惯两大法源,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其序列、互动与转换远远比预想的更加复杂。而建构论唯理主义支配下所预想的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将原本司法实践中动态、多样、差异的法源适用路径静态化、单一化、趋同化处理,造成了“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二、基于立法的民法典二元差序化静态法源模式
“人不能屈服于理性,也不能满足于理性。”⑤[德]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权力意志》,吴崇庆译,台海出版社2016 年版,第67 页。民法典在建构论唯理主义支配下试图将法源进行分门别类,然后构建一种放之四海皆准、普遍适用的民法典法源模式。如前所述,“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以及“法律—习惯”第一层次和基本原则第二层次之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背后实际仍是“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顺位适用的内在逻辑。《民法典》第10 条以语句形式进行表述,背后隐含且存在的适用规则往往依附着一种行为惯性——制定法优位,最终导致制定法越发强势,不断挤占习惯的适用空间,造成倚重制定法、偏废习惯的情势。
对于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的解构,可以分别从立法层面与司法适用层面进行具体分析。立法层面解构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的同时,拟将基本原则划归法律范畴,重构法律与习惯为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中的二元,并从民法成典的角度分析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的形成与建立。
(一)法理不属于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的法源
“法典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的映照,而且不容忽视的是,它还是对社会生活的塑造。”①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增补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87 页。任何法典的编纂必须立足社会实际,符合当下时代发展状况,更好地指引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及人民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处理,如果超脱现行阶段构建一种不切实际的预想,则会带来更多的不便与混乱。
对于法理是否为民法法源,民法学界持有两种观点,即肯定法理的法源地位与否认法理的法源地位。如前者,有学者指出:“‘法理’渊源的合理性显而易见。”②耿林:《民法典应当如何制定?——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第一章的修改意见》,载《北航法律评论》2016 年第1 辑。如后者,也有学者提出,法理的概念不明确,难以在立法中规定。③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94 页。民法典并无明确法理法源地位的必要,此既是从法理自身角度而言,也是从民法典整体体系及司法适用层面作出的制度设定。
首先,从法理自身角度而言,法理的概念与范围不明确,使得民法典引入法理存在极大风险。法理本身的概念是模糊的,很难获得一个统一的共识。④参见李永军:《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版,第94 页。且关于法理的范围,也没有明确的界定,目前来看主要包括一些共同的原则、学者学说等。其中学者学说多为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普遍性,公信力多受质疑。此外,学者学说并非观点一致,有时甚至互相诘难,贸然引入会导致裁判标准失准,弱化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其次,与民法典施行相配套的方法论发展,已最大限度补足制定法与习惯适用上存在的漏洞,尚无通过法理补足漏洞的必要。如与民法典配套施行的司法解释,是填补制定法高度抽象化弊端的重要手段。加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为漏洞的补足提供了解决方法。此外,民法典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近乎涵盖民法典的全部范围,足以补足制定法与习惯适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漏洞。
再次,从法理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情况来看,民法典引入法理极易导致法理的误用或滥用。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法理存在“通货膨胀”式的滥用。⑤参见吴从周:《论民法第1 条之“法理”》,载《东吴法律学报》2004 年第2 期。李敏认为,具体来看法理的误用或滥用,主要有五种情形。①具体情形划分,大致有“名依法理,实依法条”“应依法条,逃向法理”“套话式引用法理”“名为依法理,实有悖法理”“借法理之名误用规则”等情形。参见李敏:《民法法源论》,法律出版社2020 年版,第207 页。另据统计,司法实务中约有27.9%的裁判文书属于法理的误用或滥用。②参见李敏:《论法理与学说的民法法源地位》,载《法学》2018 年第6 期。因此,引入法理补足漏洞、协助法官进行司法判决的本意,落实到司法实务中恐怕会造成法官司法裁量权的滥用。
由此可见,对比引入法理和通过其它方式补足制定法与习惯适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漏洞,当前阶段尚无引入法理之必要。且法理自身不确定性的局限并无好的举措予以克服与完善,贸然引入极易造成司法适用层面的混乱。
(二)基本原则属于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中法律的范畴
如前所述,关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存在三种观点,即独立为一种类别的法源、参照法理进行适用以及划分到法律的范畴。其中独立为一种法源类别,主要是“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持有的观点。民法典基本原则作为民法典的法源,似无争议,争议在于民法典基本原则是否属于法律的范畴。
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出发,民法典确立的基本原则属于《民法典》第10 条“法律”的范畴。法律为民法典的法源,不仅指规范性法律,即通过立法以法律表现出来的形式。“对于法官而言,为解决事实的裁断依据是法律,而那些为裁断依据提供规则的却是法律渊源。”③彭中礼:《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载《北方法学》2013 年第1 期。如庞德认为,所谓的法律渊源是指形成法律规则的原因。④See Roscoe Pound, Jurisprudence(Ⅲ), West Publishing Co., 1959, p.383.因此,法律不等同于法律渊源,此处的“法律”应当作广义理解。法律规范可以分为规则与原则两种类型。其中构成“完全法条”的规则需具备具体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规则之外,凡构成实在法规范的基础或“镶嵌”于其中的基本理念为原则。⑤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 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1 期。可见,民法典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应当划归于《民法典》第10 条中“法律”的范畴。
依据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的形成逻辑,基本原则替代法理,有简单拼接之嫌。“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中制定法、习惯、法理三者法源性质不同,可以明显区分。“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将基本原则作为第三位阶的兜底性法源,逻辑的出发点是从《民法典》第10 条的语句结构出发,先定地认为基本原则处于制定法、习惯之后,并未明确分析制定法、习惯、基本原则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虽然基本原则在民事司法适用层面作为末位法源与兜底性法源适用,但这只是从其适用的效力而言,并不是从其含义出发,也就是说“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中制定法、习惯、基本原则类别划分的依据是法源效力的大小,而不是法源自身的性质。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实际上制定法和习惯的划分依据是各自的性质,在法源效力的大小方面并不是制定法天然的绝对优位。而不顾法源性质的不同,将基本原则简单地续接在法律与习惯之后,犹如在梨树上嫁接苹果树的枝条,最后破坏的是果园的整体区分。
(三)“法律—习惯”二元法源模式的立法形成
民法典法源的确立,除开学理层面的争论,本国立法活动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耶林宣称:“法的诞生如同人的诞生,通常伴随着剧烈的分娩阵痛。”①[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12 年版,第8 页。民法成典的过程中,民法学者对于民法典法源的选择提出了不同的方案,最终才得以确立制定法与习惯为民法典的法源。
制定民法典采用了“两步走”的立法思路,围绕民法典法源的确立,大致可以从民法典的专家建议稿、起草稿与最终民法典立法确立的文本出发,探寻制定法与习惯成为民法典法源的缘由,以及从立法角度重构“法律—习惯”二元法源模式。
从民法学者的建议稿来看,对于民法典法源的选择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认为民法典的法源应当是“法律、习惯、法理”,持此种观点的有梁慧星、杨立新、李永军;②分别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2 页。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2.0 版》,载中国法学创新网2015 年5 月11 日,http://www.fxcxw.org.cn/dyna/content.php?id=1410。李永军:《中国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及理由(中国政法大学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5 页。二是认为民法典的法源包括“法律、习惯、基本原则”,持此种观点的有孙宪忠、王利明;③分别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孙宪忠主持):《民法总则建议稿》,载中国法学网,http://iolaw.cssn.cn/zl/mf/xsjl/201603/t20160301_4638985.shtml。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 页。三是民法典的法源包括法律与习惯两种,此种观点可见中国法学会之建议稿;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提交稿)》,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16 年2 月24 日,http:// www.civillaw.com.cn/zt/t/ ? id = 30198。四是认为民法典的法源应包括法律与惯例,持此种观点的主要是龙卫球。⑤参见北航法学院课题组(龙卫球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通则编〉草案建议稿》,载中国法学创新网2015 年11 月2 日,http://www.fxcxw.org/index.php/home/xuejie/artindex/id/9597.html。此外,于海涌认为民法典法源应包括商业惯例,徐国栋认为民法典法源应包括事理之性质等。⑥分别参见于海涌:《中国民法典草案立法建议(提交稿)》,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2 页。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第4 页。由此可知,民法学者在民法典建议稿中对于民法典应包含何种法源的观点不一,且分歧较大。
从民法总则与民法典的建议稿来看,法律与习惯法源地位的确立过程也十分曲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共有6 稿,首次肯定习惯的法源地位是2016 年7 月5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10 条之规定,尔后民法总则及民法典总则编都对其予以承继,最终为官方正式确定。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10 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最终民法典确立法律与习惯为其法源,并未肯定法理、惯例等的法源地位。由此可以看出,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与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在立法层面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民法典并未肯定法理、惯例为其法源,而立足于此,以法律和习惯为民法典法源的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更加契合民法典的立法本意,有其解释及适用的空间。
综上所述,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出发,将基本原则划归“法律”的范畴更加符合民法典依据法源性质划分民法典法源的标准,且依据法源的效力大小进行法源之间的位阶排序不符合司法实践中法源适用的实际情况,也无法解决法源的适用冲突。《民法典》第10 条只是法源语句的表达形式,其立法本意倾向于依据法源性质对民法典法源进行划分,而非依据效力大小进行位阶排序。因此,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的重构更加契合《民法典》第10 条对民法典法源划分的本意。
三、基于司法适用的民法典二元差序化动态法源模式
如前所述,现行民法典法源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将原本司法实践中动态的、多样的、差异的法源适用路径静态化、单一化、趋同化处理,造成了民法典法源司法适用的困境。目前来看,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的法源适用冲突,一是同一法源类型之间的冲突,如民法典“法律”法源中的冲突,制定法种类复杂,大致有七种类型。②民法制定法的七种类型分别是:一是宪法中的民事规范;二是民法典及民事单行立法;三是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民事法规;四是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五是规章中的民事规范;六是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解释的规范性文件;七是国际条约中的民事规范。对于同一民事纠纷可能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适用何种类型的制定法或适用哪一法条也需要法官的裁量。例如,在常见的医疗纠纷中,适用民法典合同编或是适用民法典侵权编的法条,不同的适用选择带来的赔付标准也是不同的。二是不同法源类型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表现在制定法与习惯同时存在时,若依据《民法典》第10 条之规定优先适用制定法可能出现明显违背伦理常识、损害民事主体权益的情形。例如,彭宇案的司法判决,极大地冲击了民众的认知观念。①参见徐寿兰诉彭宇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 号民事判决书。
因此,重构的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乃是立足确定法律与习惯为民法典基本法源的基础上,对于同一法源类型之间(法律或习惯)、不同法源类型之间(法律和习惯),形成结合具体案件进行差序化动态调适的司法适用模式。该模式并非采取制定法绝对法源优位、习惯绝对法源末位的适用路径,而是将不同类型的法源进行对比,结合具体案件裁量出更加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符合公众预期、兼顾社情民情、尊重传统与习惯的民事判决。
(一)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司法适用的逻辑进路
如前所述,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虽然在法源类型划分上以能否全有或全无适用为标准进行划分,做到了逻辑周延,实际和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一样,依旧受到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影响,采用“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此种静态的、人为预想的先后适用次序的排列,不利于司法层面法官案件的判决,反而造成制定法越发强势,不断挤占其它法源适用空间的局面。
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将以制定法为依据,从三个维度论述不同情形下民法典法源适用的方法。制定法内的适用、制定法外的适用和背离制定法的适用,作为传统找法基础架构的三个范畴,大致相当于现行民法适用方法中的依照制定法、补充制定法和背离制定法三种民法适用方法。②See Tschentscher, Emmenegger, Art. 1 ZGB, Berner Kommentar. Stämpli, Bern 2012, SS. 225 - 226,229 - 230.
有鉴于此,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司法适用的逻辑进路,将围绕法律与习惯二元法源,以上述三种民法适用方法展开,结合具体案件适当地进行法源位置的差序化动态调适。首先,基于制定法内的适用,当只有制定法而无习惯时,适用制定法。其次,基于制定法外的适用,当无制定法而有习惯时,适用习惯。再次,基于背离制定法的适用,当制定法与习惯同时存在时,应进行综合考察,若适用制定法明显违背常识、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则应该放弃制定法的适用,进而适用习惯。此时,习惯跃迁至制定法之前处于优位法源地位,制定法则处于末位法源地位。
而《民法典》第10 条所确立的法源,从形式逻辑上讲,并不包含所谓的第三位阶法源。③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在定义纠纷(J)、法律(L)、习惯(C)、公序良俗原则(PP)之后,该条文可以被表述为:J → [L ∨(¬L ∧C ∧ ¬¬PP)],其中L 和(¬L ∧C ∧ ¬¬PP)是析取关系,从逻辑式中显然只看到两项析取,并不存在第三层的法源体系。参见陈双雄:《〈民法总则〉第10 条与我国的法源位阶体系——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载《南方论刊》2019 年第6 期。因此,不同于“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下制定法优位、习惯次位、法理/基本原则末位的预想,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下制定法与习惯的法源地位并不是简单的制定法优位、习惯末位,而是根据制定法内的适用、制定法外的适用和背离制定法的适用的民法适用方法,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差序化的动态调适,或是制定法处于优位法源地位,或是习惯处于优位法源地位。
(二)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司法适用的维度分析
“法律—习惯—法理”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法律—习惯—基本原则”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以及“法律—习惯”第一层次和基本原则第二层次之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采用的是“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当前者无法适用出现漏洞时,则顺位至后者寻求补足。现行的民法典法源模式企图构建一种恒久适用的法源模式,然而机械式的法源适用路径以牺牲法源活力为代价,很难应对司法实践中的复杂局面。
如同Rémy Cabrillac 教授毫不留情地下了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去魅”(disenchantment)型结论,对于通常被认为应该去消除的法律渊源的危机的解决,法典化“其实是无能为力的”。①See Rémy Cabrillac, Les codifications, PUF,2002,p303.《民法典》第10 条确立的简单的法源适用规则,很难应对实践层面法源的内部冲突难题。且从《民法典》第10 条的表述“应当”“可以”的词汇来看,并没有明确说明在司法适用中制定法必须是优位法源、习惯则必须是末位法源,而“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则将民法典法源的适用次序固化了。
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从民法典所确立的“法律”与“习惯”两类基础法源出发,二者在各自的纵向维度与横向维度也同样面临着复杂的情况。从纵向维度来看,民法典“法律”法源的类型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七类制定法,加之归属于法律范畴的基本原则,总共有八种法源类型。此外,民法典“习惯”法源的类型,主要包括民法典自身的规定和民法典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中,民法典所确立的习惯类型有交易习惯、风俗习惯、当地习惯、隐含习惯的公序良俗四种。而民法典司法解释则确立了民间习俗、惯常做法两种习惯类型。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第1 款:“ 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因此,从纵向维度来看,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总共确立的习惯类型有交易习惯、风俗习惯、当地习惯、民间习俗、惯常做法、隐含习惯的公序良俗六种类型。
从横向维度来看,以前述的三种民法适用方法为基础,法律和习惯之间存在三种情形,有法律无习惯、有习惯无法律、有法律且有习惯。前两种情形关系明确,第三种有法律且有习惯的情形下在司法适用层面存在巨大冲突。例如,民法典关于禁止结婚的血亲规定与地方的风俗习惯就存在冲突,其中新疆伊犁哈萨克族有七代以内禁止结婚的传统习惯。①分别参见《民法典》第1048 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第4 条:“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保持哈萨克族七代以内不结婚的传统习惯。”又如,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嫁后的女儿不再享有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司法实务中并不是依照制定法与同位顺序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②参见朱佳佳:《农村妇女继承权保护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
可见,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与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的法源适用路径过于僵化,不足以应对司法实践的复杂局面。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从其法律或习惯的纵向维度面临着不同的情形,司法适用中也不是简单的排序,横向维度的法律和习惯可能存在重合的情况,需要谨慎裁断适用习惯或是法律,由此对于法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司法适用的动态调适
如前所述,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分为两个维度,即同一法源(法律或习惯)的纵向维度,与不同法源(法律和习惯)之间的横向维度,两个维度之间不同类型的法源在司法适用层面并非简单的排序,而是需要结合具体案件进行裁量。例如,在法律的纵向维度上,基本原则相对于部门法规就处于次位法源地位。而在法律与习惯的横向维度中,习惯可能优先于部门法规适用,处于优位法源地位。
在习惯法源的纵向维度中,其法源效力也并非完全一样,存有一定的差别。在交易习惯、风俗习惯、当地习惯、民间习俗、惯常做法、隐含习惯的公序良俗六种“习惯”法源类型中,隐含习惯的公序良俗的法源效力要弱于其它“习惯”法源。民间习俗、当地习惯、风俗习惯因具有传统属性,为民众所知悉与遵循,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民族禁忌,其法源适用的效力要高于其它“习惯”法源,有时甚至可以优先于制定法适用。
有学者认为,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必须的法律渊源、应当的法律渊源和可以的法律渊源。③参见彭中礼:《法治之法是什么——法源理论视野的重新探索》,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1 期。也有学者提出,所谓的法源体系,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④参见汪洋:《私法多元法源的观念、历史与中国实践——〈民法总则〉第10 条的理论构造及司法适用》,载《中外法学》2018 年第1 期。其实不只是二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甚至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与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可能都无法在司法层面进行具体适用。
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下法律与习惯中不同类型的法源,各自在司法适用层面的法源效力存在差别,产生冲突时需要谨慎适用。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拟以法律与习惯二元的横向维度为基础,结合各自纵向维度中不同法源类型的效力强弱情况,将不同类型的法源划分为必须的法律渊源、应当的法律渊源和可以的法律渊源三种适用情形,从而进行差序化的动态调适,以克服“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的弊端。因此,将宪法中的民法规范划分为必须的法律渊源;将基本原则划分为可以的法律渊源;“法律”中其它的6 种法源类型划分为应当的法律渊源。而将“习惯”中交易习惯、风俗习惯、当地习惯、民间习俗、惯常做法划分为应当的法律渊源;隐含习惯的公序良俗划分为可以的法律渊源。
由此,在司法适用层面,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下法律与习惯并非制定法天然优位,习惯天然末位,而是根据不同类型法源的比较,进行差序化的动态调适。其具体差序化的动态调适模式见表1。法律与习惯二元的差序化调适犹如“田忌赛马”,法律法源类型中的“上等马”是必须的法律渊源,处于绝对的优位法源地位,而习惯法源类型中的“上等马”对比于法律法源类型中的“下等马”,则跃迁至优位法源地位。例如,“习惯”法源中的交易习惯、风俗习惯、当地习惯、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相对于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部分制定法的法源类型,则处于优位法源地位,优先进行司法适用。

表1 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的适用调适
综上所述,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试图克服三位阶民法典法源模式与层次民法典法源模式中“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路径的弊端,防止过于倚重制定法导致有所偏废。如有学者所言,法律秩序中的平等与差序是相辅相成的,差序则是更好地应对事物的差异性,平等与差序是和而不同的。①参见龙大轩:《道与中国法律传统》,商务印书馆2022 年版,第127 页。例如,在古代中国,蕴含习惯的礼与国家制定的法之间,经历了援礼入法、礼法结合、礼法合一的发展阶段,通过礼的适用来克服制定法的弊端,从而达到和谐有序的状态。“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①《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张景、张松辉译注,中华书局2021 年版,第178 页。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和合”的法文化观,在应对法律与习惯两大法源之间的张力与冲突、侧重与偏废,仍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结 语
现行的民法典法源模式采用“法律→习惯→法理/基本原则”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将司法实践中多样、动态的法源适用路径静态化、单一化处理,使得民法典法源司法运用的可操作性降低。民法典二元差序化法源模式将基本原则划属“法律”范畴,依据法源性质划分为法律与习惯之二元法源,且并非采取“法律→习惯”法源顺位适用的路径,单纯寻求习惯对制定法漏洞的填补,而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差序化动态调适,习惯具有跃迁至制定法之前优先适用的可能。
法律与习惯在司法适用层面,犹如“田忌赛马”。法律中“必须的法律渊源”相对于习惯法源处于绝对优位法源地位,而习惯中“应当的法律渊源”相对于法律中“可以的法律渊源”处于相对优位法源地位。对于法律与习惯中均属于“应当的法律渊源”的法源类型,可由法官自行裁定,决定何者优先适用。也可基于民法典确立的自愿原则,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由当事人决定制定法和习惯何者优先适用,且提出适用习惯的一方具有证明责任,证明有困难的,法官可依职权查明。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 条第2 款:“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查明。”此外,习惯跃迁至制定法之前优先进行司法适用,应建立在适用制定法明显违背伦理常识、损害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