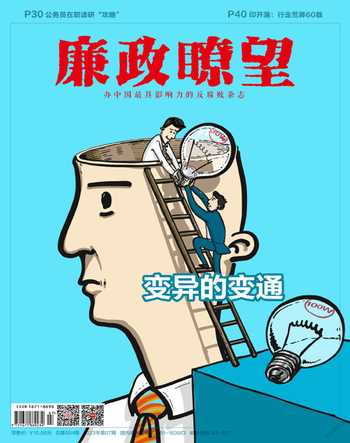《翦商》:商周革命的另一种书写
2023-05-08林屋公子
林屋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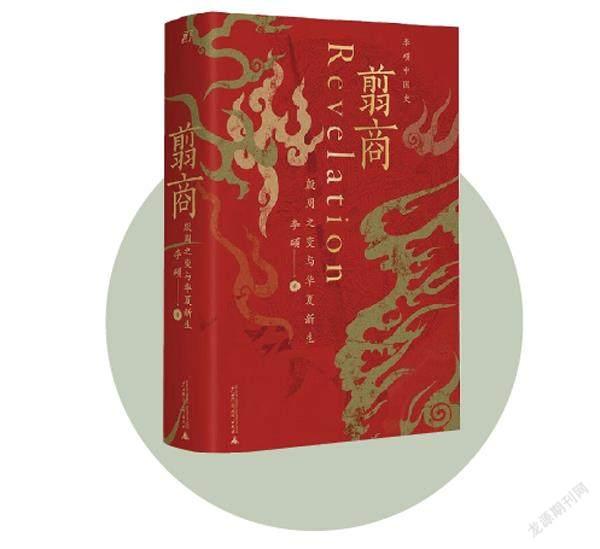
公元前21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商周革命。周国本来是活动在关中平原一带的商朝附庸小邦,国君周文王开始反商。文王去世后,子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新乡)大败商朝军队,之后攻入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商纣王自杀。武王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建立周朝,封纣王子武庚为商国国君,以武王三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监管。武王大约在位四年后去世,因子成王年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
周公旦的摄政,引来“三监”猜忌。武庚趁机联合“三监”反叛,又有东夷部落加入。之后,周公旦率领大军东征,消灭了武庚与“三监”,并将战线拉到东方。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和东方的统治,周公旦又主持修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并推行了分封制,将周族子弟、姻亲功臣等分封出去建立诸侯国。之后,周公旦又进行了“制礼作乐”,规定了一套礼乐制度,并且提出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等一系列政治思想,周王朝才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人对于商周革命的评价非常高。战国大思想家孟子阅读《尚书·武成》篇,见到其中有武王伐纣“血流漂杵”的记录,意思是战争非常残酷,鲜血把盾牌都漂浮了起来。孟子表示不相信,他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武王是无敌于天下的仁者,以最仁的去讨伐最不仁的,怎么会“血流漂杵”这么惨烈呢?他还认为,纣王是危害仁爱、伤害道义的“独夫”,武王杀的是独夫纣,并非以下犯上、以臣弑君。
可见,至晚在战国时期,就有把商周革命赋予明显道德化色彩的倾向。既然商周革命是“吊民伐罪”,征讨有罪者以抚慰百姓,那么商纣就应该是个彻头彻尾的昏君加暴君。所以,在自战国以来的文献中,对纣王罪状的批判也接连不断。在文人的笔下,纣王就是个奢侈无度、宠幸奸臣、疏远贤臣、滥用酷刑、杀害忠良的十恶不赦之君;而与之相反,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都是圣王贤者。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也即是以商周革命作为背景,将神魔故事与历史记载融为一炉。
但这样的解释,自古就有人质疑。孔子弟子子贡就认为,纣王并没有这么坏,只不过纣王是失败者,所以一切罪名都归于他的头上。近代学者顾颉刚先生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认真梳理了关于纣王罪状的历史文献,发现有一个明显的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的规律。在周初《尚书》中,纣王的最大罪名不过是“酗酒”而已,而在据说是《尚书》遗篇的《逸周书》里,也有武王克商后,大行杀戮并且使用人祭的记录。
那么,商周革命的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史料的空缺,留给后人无数的遐想。清华大学李硕博士这本《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以下简称《翦商》),正是从一个全新角度探求商周革命的历史著作。
“翦商”一词,出自《诗·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说的是后稷的后人周大(太)王,定居在岐山(今陕西岐山)的南面,实际开启了翦(剪)除商朝的进程。周太王是文王的祖父,被认为是周国的肇建者。
所谓“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不仅强调了商周革命前后时代变化,而且还点明了华夏文明得以新生。这种说法,可以溯源于上世纪王国维先生的《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而周人制度与商朝最大的区别,在于确定了立子立嫡制和衍生的宗法、丧服、分封、君臣,以及庙数、同姓不婚制度。《翦商》一书明显也支持王国维的中心论点,但给出具体的论据却不同,作者是从“人祭”的角度来论述。
“人祭”也称人牲,是古代将人杀死祭祀神灵、祖先的一种风俗;与之类似又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人殉”,“人殉”是古代将人杀死为墓主陪葬的一种风俗。两者的区别在于,人祭是将人杀死后让神灵食用,所以人祭的对象一般是战俘、敌人;而人殉是将人杀死后,使其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为墓主服务,所以人祭的对象一般是墓主生前的近侍、亲随。最早、最系统研究人祭与人殉的,是考古学者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
《通论》列举了殷墟出土的三处祭祀坑,并指出它们“时代均属殷墟前期”,作者同时还引用了胡厚宣先生对甲骨文中人牲记录的统计,同样发现集中在殷墟早期,而往后逐渐减少。故作者认为,“青壮年俘虏中已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奴隶,这是生产进步的必然结果”。不过,《翦商》的作者却较真地查看了三个祭祀坑的考古报告,从而得出结论,《通论》中提到的三处祭祀坑有两处属于殷墟末期,另外一处(小屯南地H33)则时间不详。
笔者核对了三份考古报告,发现前两处正如《翦商》所言,但第三处又如《通论》所言是殷墟前期遗址(见《考古学集刊09》P124),这反映《翦商》也存在疏漏。至于甲骨文反映的人祭现象逐渐减少,《翦商》解释是祭祀制度的变化,导致样本不能代表真实比例。这实际上是作者推测。但这些构成了《翦商》的论证基础,即人祭制度在商朝末期发展到顶峰。而周人也帮助商人捕获人祭,到周公旦时才废除人祭,并毁灭前朝相关档案,华夏得以新生。
作者另外反复强调的一部作品是《周易》。《周易》是儒家“五经”之一,分为《古经》和《大传》两部分。传统一般认为,《古经》是文王作品,记录的占卜资料;《大传》是孔子作品,是儒家对《古经》的解释补充。现代解释更宽泛,把《古经》理解为商末周初作品,《大传》是战国西汉儒家作品。而在作者看来,《古经》是文王的作品,是文王翦商的记录,其中暗藏大量人祭信息;周公为了掩盖这些信息,作《象传》(《大传》之一)来刻意曲解。
《翦商》系作者于2012年发表的《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的扩充版,可谓是“十年磨一剑”。《周灭商与华夏新生》一文笔者早有拜读,对其汪洋恣肆的文笔、大气磅礴的气势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非常钦佩,读之有史诗之感。《翦商》一书延续了《周灭商与华夏新生》的基本论点和论证方式,某些论点趋于保守(如之前认为商是食人族),又补充了大量关于人祭的考古资料。作为一位魏晋史博士,能够写出一部这样有分量的先秦史著作,实属难得。更为难得是竟一时洛阳纸贵,使得商周史这个非常冷门的断代走进大众视野,极具科普之功。
不过,笔者也发现《翦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往往都有立场先行之嫌。
如前所述,作者对于小屯南地H33的祭祀坑的断代失察;而对于甲骨文中的信息又以样本不能反映全体称之,又没有具体的论证。诚然,考古发现不能代表历史事实,但毕竟要讲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至于对《周易》的解释,亦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嫌,如作者根据只言片语,竟得出文王在商与武庚、妲己有联络的结论;甚至还有完全虚构的情节,如文王子伯邑考与吕尚邑姜先在商都相识,文王与吕尚也就互相认识进而结盟了。
除了完全出于想象的观点外,《翦商》中不少观点虽有依据,但非通说。如认为《象传》是周公所作;如认为《周易》暗示伯邑考被做成人祭且为文王食用,并在后世史料中隐秘流传。而按照顾颉刚先生观点,这些史料本就是层累形成的不可靠记录;如对“周”字的解释,先是认为周字代表周围,后又认为周字从“用”“口”,象征周人为商人提供人牲。此二说既未能自洽,而后者又以《说文》为依据,并不符合商周文字字形,“周”更可能是“雕”的初文。
此外,《翦商》还有一些明显的讹误。如称二里头—夏朝存在近四百年,但抛开二里头性质争议,其绝对年代是前1750—前1520年,顶多算夏朝晚期都城;如认为王子孝己在西晋之前没有记录,实际上战国《吕氏春秋》就有;如认为崇国国君都可以叫崇侯虎,并以西周虢仲虢叔举例,但虎是私名;如认为狄人姓隗,但这只是赤狄;如认为春秋齊侯丰作了一件尊彝,实际上是西周丰国国君作了一套青铜器;甚至使用《伪古文尚书·泰誓》的材料……
不过,《翦商》仍是一部瑕不掩瑜的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商周史的另一种书写,既是《殷周制度论》的一次印证和发扬,又为通俗著作的写作提供了模范作用。当然,笔者认为,《翦商》整体上还不能动摇《通论》的观点,即人祭制度应该是随着时代演进而慢慢消亡的;至于商周之际的制度兴替,更多还应视为继承而非革新,而真正从根本上影响古代社会面貌的事件,应当还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