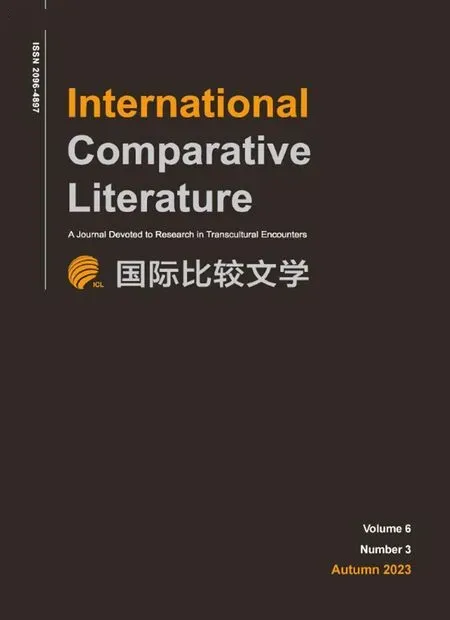浮士德与《西方的没落》:论歌德对斯宾格勒历史哲学的影响*#
2023-05-01刘珊同济大学
刘珊 同济大学
一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1880年出生于德国的布兰肯堡,曾在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攻读学业,并在1904年以论文《赫拉克利特断简研究》1斯宾格勒的博士论文《赫拉克利特断简研究》(“Der metaphysische Grundgedanke der Heraklitischen Philosophie” /“The Fundamental Metaphysical Ideas of Heraclitean Philosophy”), 1904年由Halle a.S., Hofbuchdruckerei von C.A.Kaemmerer & Co.出版,内容分为Die reine Bewegung (The Pure Movement)和Das formale Prinzip (The Formal Principle) 两部分,成为他以后历史哲学研究的坚实学术基础。获得了哈雷大学的博士学位。1905年斯宾格勒以《视觉器官在动物一生几个主要阶段的发展》一文获得了高中教师的资格,2《视觉器官在动物一生几个主要阶段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ehorgans bei den Hauptstufen des Tierreiches”),斯宾格勒通过此文通过了Staatsexamen考试。参考:Mark Sedgwick, ed., Key Thinkers of the Radical Right: Behind the New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5.并开始在中学担任教职。1911年斯宾格勒辞去教职,开始了在慕尼黑的隐修生活,他的创作也在此时展开。斯宾格勒代表性的著作有《西方的没落》《人与技术》《关键的时刻》等书,内容涉及范围包括历史、文化、哲学、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
斯宾格勒1912年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期间,接触到了来自于古代史教授奥托·泽克(Otto Seeck,1850-1921)的《古代世界没落的历史》(GeschichtedesUntergangsderantiken Welt)一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方的没落》的书名也由此而来。1918年7月,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在维也纳出版。书中所使用的文化形态学以及历史观相学等研究方法,以及斯宾格勒宣扬的“我们时代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unserer Zeit),打破了学院哲学一贯以来以概念进行逻辑推导的方法论,在当时的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西方的没落》的声名鹊起,是和历史背景有着深刻联系的,此书出版后4个月,德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一战宣告结束,德意志帝国崩溃,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成立,政治局势动荡之际,斯宾格勒的“西方文化终结论”格外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和共鸣。不仅在学术圈内,在圈外乃至普通读者都被书中所宣讲的观念深深吸引。1922年,斯宾格勒对《西方的没落》第一卷进行了订正和修改,并整理出版了第二版。
一直到现在,“西方的没落”仍然是贴在斯宾格勒身上最为著名的一个标签,被人们不断的提及。那么斯宾格勒的观点究竟是占卜者的巫言呢,还是先知对未来时代敲响的警钟?先来看看斯宾格勒自己对“西方的没落”的描述,“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3(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32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32.]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是一个有机体,文明在经历新生、发展、繁荣之后,最终也会像其他有生命的事物一样衰亡,而西方文明已经越过了它的顶点,正处于“盛极而衰”的趋势之中。
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并非空穴来风,在《西方的没落》1922年的修订版序言中,斯宾格勒直接坦诚:“歌德给了我方法”“这是一种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实上,它根基于歌德的原创现象的观念……可以扩展到迄今为止无人敢奢望的整个历史领域”。4同上,第16页。[Ibid., 16.]纵观《西方的没落》上下两卷,可以发现歌德及其作品乃至其思想观点在文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歌德则是作为一个显形的在场统摄着一切”。5同上,第15页。[Ibid., 15.]歌德对斯宾格勒的影响不仅仅体现方法论上,他的自然哲学思想以及其代表作《浮士德》当中的精神内涵,都深深内化在了《西方的没落》中。
二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而除了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歌德对自然科学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他早期的剧本《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中,歌德就借马丁修士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如果上帝让我成为园丁或者实验室研究员,我会非常高兴”(Wollte,Gott hätte mich zum Gärtner oder zum Laboranten gemacht,ich könnte glücklich sein.)6出自Götz von Berlichingen (1773).中文为笔者自译。这份兴趣推动着歌德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实践,并贯穿了他的一生。
歌德在地质学、矿物学、人体解剖学、植物学、色彩学以及光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方面都颇有研究,撰写出多部关于自然科学的著作及论文,如《植物形态学》《植物的螺旋形倾向》《论人类与动物的颌间骨》《光学论文》《论色彩学》等,并主办了《形态学》杂志。歌德的自然科学研究折射出了他的哲学思想,但也遇到了相应的问题:即注重直观,排斥数学和现代科学的试验方法。因此除了植物形态学外,歌德的其他自然科学研究并不为当时的主流学界所承认。但在斯宾格勒眼里,歌德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个自然主义科学家,或者说是一个自然哲学家。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和研究方法,成为了斯宾格勒分析历史文化形态的有力佐证。
(一) 世界历史的形态学
斯宾格勒把自己的历史哲学称之为“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他把生命、宇宙、历史、文化等抽象概念看做是有机体的“生命”,它们都有自己循环的周期和表现的形式,同时也像有机体一样,从出生到成熟再到衰亡。在书中,斯宾格勒多次借歌德的形态学理论、自然观等思想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我在这本书中的哲学,要归功于实际上至今还不为人知的歌德哲学,也要归功于尼采哲学(但少的多),下面这段话我只字未改:‘上帝只对生者有效,不对死者有效,只对生成的和变化的东西有效,不对已成的和固定的东西有效; 因此,同样地,理性(Vernunft)所关心的只是通过生成的和活生生的东西去追求神圣的东西,而知性(Verstand)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去利用已成的和固定了的东西’。(《致爱克曼》)这句话包括了我的全部哲学。”7(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47页。[Osward Spengler,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47.]
何谓“形态学”,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借歌德的原话来进行了解释,“‘形式是某种运动的、生成的、流逝的东西;形态(formation)的学说即是转型(transformation)的学说;变形(metamorphosis)是整个自然的关键。’——歌德如是说”。8同上,第95页。[Ibid., 95.]1790 年歌德发表了《植物的变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植物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变化的规律,并正式提出了“形态学”(Morphologie)的概念:“植物各外部器官具有隐秘的亲缘关系,亦即叶子、花萼、花冠、花丝,它们次第出现并且似乎后者都是从前者发展而来。对于这种关系,研究者们早就有了大体的认识,甚至也有过特别的处理。同一个器官经过变化呈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这种效果叫作植物的形变。”9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erke (Goethe-HA), 14 Bde.Hrsg.von Erich Trunz, Hamburg: Chr.Wegner, 1948-1960.Dazu: Reg.-Bd., 1964, Bd.13, S.64.” Die geheime Verwandtschaft der verschiedenen äußern Pflanzenteile, als der Blatter, des Kelchs, der Krone, der Staub- fäden, welche sich nacheinander und gleichsam auseinander ent- wickeln, ist von den Forschern im allgemeinen längst erkannt.ja auch besonders bearbeitet worden, und man hat die Wirkung.wodurch ein und dasselbe Organ sich uns mannigfaltig verän- dert sehen läßt, die 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 genannt.”在歌德看来,植物各器官的形态变化规律,也即生物形态的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在自然界具有普遍的意义。而在这种规律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处于生成的、变化的状态中,这也构成了歌德形态学的核心思想:“一切形态……绝不会保持不变,绝不会静止不动或是终结性的。准确地讲,一切都在永远的运动中摇摆不定。”10Goethe-HA, Bd.13, S.55.“Betrachten wir aber alle Gestalten, besonders die organischen, so Enden wir, daß mirgend ein Bestehendes, nirgend ein Ruhendes, ein Abgeschlossenes vorkommt sondern daß vielmehr alles in einer steten Bewegung schwanke.”在歌德的形态学视域中,万物都是具有其所属形态的有机体,存在于运动、变化和消失的过程中。
斯宾格勒全盘继承了歌德的形态学观点和态度,他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描述为一种‘形态学’。机械的和广延的的实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Systematic)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Physiognomic)形态学。”11(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98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WU Qiong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98.]在斯宾格勒看来,这两种形态学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已经沿用了很久,并且已不适合对现代社会和世界进行处理,而观相的方法才是未来掌握世界最有效的方法,观相的形态学能够将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所有科学都解释为与人有关的一切现象和形态,斯宾格勒认为,这正是世界历史形态学的意义。而他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进行观相的研究,从而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必然性。
斯宾格勒认为歌德自然研究中所提出“形态学”观念,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形态研究有着直接的影响和帮助,“所谓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就是纯粹的观相的活动。对于这一研究,除了借助歌德的自然研究的过程,不可能得到更好的说明。”12同上,第157页。[Ibid., 157.]歌德的形态学思想在实践中体现为观相法,所谓“观相法”,即是指对事物和现象进行直观的、直接的认识,运用心灵内视的方法,去掌握其背后所体现的特征和命运。要求观察者要融入到对象中,对生命和生存的世界进行切身的体验:“生活在对象之中,以内在之眼去体验、经历对象的生活。”受形态学思维影响,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的世界也是一种有机体,所以“观相法”也是具有有机逻辑的,它遵循有机体的生命循环,以此来分析历史文化现象及其发展历程,最终用来揭示世界历史形态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的未来命运。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称,历史世界的形态学与自然世界的形态学是正相对照的,不要把历史世界看做是即成的事物,而是看做是生成的事物。在阐述“文化是一种有机体”时,斯宾格勒宣称“植物和动物的比较形态学很久以前就给了我们方法”13同上,第102页。[Ibid., 102.],并在注释中明确指出“不是达尔文式的只关注因果关系的实用动物学的解剖形态学,而是歌德意义上的观看与俯瞰的形态学”。14同上。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是在有机单位的内在结构中完成的,而歌德的形态学是一种深入到事物核心的看法,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究这些有机单位的内在结构。我们对于历史研究的任务并非是探究达尔文主义的因果关系,而是人类历史的周期结构和有机逻辑。
(二) 文化有机论
歌德是一个兴趣爱好十分广泛的文学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自然科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虽然常常有人惋惜他要是将这些热情投入在文学创作中或许会更好,但不可否认的是,歌德在自然科学方面提出的观点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歌德的形态学以植物的生长周期为基础,将其扩展到对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乃至宇宙万物的思考中。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1912-2015)在《镜与灯》一书中就说:“他(歌德)既是生物研究者又是艺术理论家,他同时从事这两项工作有特殊用意,他认为这两项工作是互相启迪的活动,每当他在生物学中做出新的假设或者做出一个新发现,必定会在他的批评领域以一种新的组织原则或洞察力形式再现出来。”15(美)艾布拉姆斯著,丽稚牛等译,《镜与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23页。[Meyer Howard Abrams,Jing yu deng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trans.LI Zhini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323.]而斯宾格勒则在歌德的基础上,将形态学的方法和观点移植到历史文化领域。在《西方的没落》中他提出了文化有机论:“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则是有机体的集体传记”。16(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102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102.]将历史和文化这些抽象概念看做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来加以研究,斯宾格勒的观点在史学界有褒有贬,我们暂借悬置这些外界的评价,单纯的来分析他的文化有机体论。
斯宾格勒所提出的文化有机论是一个来自于生物学中的概念,不论是有生命的生物,还是抽象的文化形态,作为“有机体”都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有机体是一个由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完整自足的整体;二,有机体包含着一个从生长到死亡的生成过程。文化有机论认为,人类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如同植物的生长,不是因果式的直线性发展,而是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依照生物在自然界中生长到衰落的过程不断循环。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都是一个有机体,具有各自的特征和精神,依循各自的内在节律向前发展。因此斯宾格勒称:“一切宇宙的东西都有周期性的(Periodicity)的标志,或者说具有‘节奏’(beat)[节律(rhythm)]。”17同上,第2卷第2页。[Ibid., vol.2, 2.]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作为有机体,遵循的是宇宙运动的周期性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规律。
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中,“永恒轮回”思想是一个常见的话题,如赫拉克利特,斯宾诺莎,歌德,尼采等人都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过“永恒轮回”。歌德认为,自然是“活生生的”,具有永恒轮回的循环周期性,他在《自然(断片)》一诗中称:“她里面永远有着生命,变化,流动,可是她毫不见进展。她永远迁化,没有顷刻间歇。她不知有静止,她诅咒固定。她是灵活的。”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是基于歌德所谓“活生生的自然”的形态学观点之上的,他将歌德的自然观与牛顿的自然观、以及达尔文主义的因果关系对立起来,他认为,牛顿意义上的自然是“死气沉沉的自然”,达尔文式的只注重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都不能用来解释自然、社会、乃至历史文化形态的演进,在“活生生的自然”这些纯粹的现象中,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每一文化的自我表现都有各种新的可能性,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18同上,第1卷第20页。[Ibid., vol.1, 20.]歌德认为世界是生成的,而非已成的,一切存在都存在着轮回周期性循环(der Wiedergeburstzykius)。斯宾格勒也继承了这种周期循环性思考,“我把世界历史看做是一幅漫无止境的形成与转变的图象,一幅有机形式的奇妙的盈亏的图象。”19同上。[Ibid.]因此他提出了“西方的没落”这一论断。斯宾格勒以古典文化的没落为例,来阐述“历史的没落”的意义:每一种文化都要经历一种内在含义和外在形式的完成,并且最后终结。
《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以及“历史周期循环观”(zyklisches Denkprinzip),强调对历史文化形态进行直观的研究,注重以象征和类比的方法对历史形态做形而上的整体把握,这给西方历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历史进步论带来了严重的碰撞。汤因比、卡西尔、柯林德等人都对《西方的没落》做出了严厉的批评。直到现在,仍有人对斯宾格勒的研究理论持质疑态度,如奥拉夫·高丁与皮特·怀特在《歌德与尼采之于斯宾格勒》一书中就说,“斯宾格勒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循环模式是对主流的历史进步论的原则性背离。”20Olaf Gaudig & Peter veit Gbr, “Goethe und Nietzsche bei Spengler,” 2006 Wissenschaftlicher Verlabg Berlin,S11, “Mit Spengler kommt in diesem Buch ein umstrittener Denker zu Wort,dessen zyklisches Geschichtsmodell vom herrschenden Fortschrittsparadigma grundsätzlich abweicht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斯宾格勒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形态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开启了西方历史哲学以文化为历史的基本单位来研究的传统,对后来的汤因比、雅斯贝斯等历史哲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
《浮士德》是西方文学创作中的一棵母题常青树,经过几百年的加工和发展,逐渐有了小说、戏剧、歌剧、电影、漫画乃至网络游戏等多种表现形式。历史上不同版本和形式 (小说和戏剧,尤其是木偶剧)的浮士德故事,给歌德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创作诗剧《浮士德》的灵感和素材。歌德在1774年左右开始创作《浮士德》,于1775年完成了第一部的初稿,这部手稿成为现在《浮士德》第一部的前身,此后的数十年间,歌德断断续续地创作了一些片段,直到1831年8月才彻底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的写作。歌德历时60多年完成的诗剧《浮士德》,结构庞大,其中所蕴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其他版本的浮士德故事,而歌德自己80多年的生活历程和思想也深深的印刻在了这部作品里。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称《浮士德》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文艺批评家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赞誉它为“现代诗歌的王冠”。21杨武能、刘硕良主编,《歌德文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页。[YANG Wuneng and LIU Shuoliang, eds., Gede wenji diyijuan (Collected Works of Goethe, vol.1),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9, 30.]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再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艺术形象,而是成为了一个性格复杂,形象立体的人物,他的身上或多或少投射了歌德的生活和思想,可以看做是歌德一生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浮士德本是一个老朽的知识分子,因为不满霉腐的书斋生活和贫乏的心灵,而与魔鬼梅菲斯特订立赌约:梅菲斯特满足浮士德的一切要求,但浮士德如果对某一瞬间感到“满足”的话,就把灵魂交给梅菲斯特,成为他的仆人。此后浮士德先后经历了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事业悲剧等,险些坠入地狱、灵魂被恶魔所占有,但在最终还是获得了上帝的拯救,进入了天堂。
浮士德的一生,可以看做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理想而孜孜奋斗,努力进取的一生,在有限的生命里去追求无限,虽然他也误入过歧途,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拯救。浮士德的精神,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的思想主线是一致的,斯宾格勒认为,任何事物,只有处在生成的过程中才具有生命力,一旦既成,就宣告死亡。《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梅菲斯特召来鬼怪为浮士德挖掘墓穴,但瞎眼的浮士德却以为铲锹的声音是在进行围海造田的工程,并说出了“停一停吧,你真美丽!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永世永劫不会消失。——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22(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浮士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53页。[Goethe,Fushide (Faust), trans.QIAN Chunq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453.]在魔法的帮助下,浮士德任由自己的追求(或欲望)无限发展,但却满足于假象,虽然最终被救入天堂,但天堂却是一种最高状态的满足,意味着浮士德的种种追求也宣告结束,看似圆满实则是“悲剧”。23在《浮士德》中,第一部与第二部都被命名为“悲剧”。
在《西方的没落》上卷扉页,斯宾格勒引用了歌德的诗集《驯服仙妮亚》(ZahmeXenien)当中的一首诗:“在无尽之中,自我重复,终要万川归一。无数拱顶,辐射交会,终为扶持,那巍峨的构型。万川之川流,只眷恋生命,巨星和泥土。任由一切孜孜不止,终要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恒的安息。——歌德”,24“Zahme Xenien von J.W.Goethe und Friedrich Schiller.Erstes Heft.1797”:Wenn im Unendlichen Dasselbe Sich wiederholend ewig fliesst, Das tausendfältige Gewölbe Sich kräfig in einander schliesst; Strömt Lebenslust aus allen Dingen,Dem kleinsten wie dem grössten Stern, Und alles Drängen, alles Ringen Ist ew’ge Ruh in Gott dem Herrn.这段话在第四章“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中又再一次出现。结合歌德的形态学思想,这段话不仅可看做是《浮士德》核心思想的一个概括,同时也体现了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的思想倾向和对历史研究的态度。在斯宾格勒看来,历史与文化是具有绵延的循环周期的,一旦此周期处于静止状态,历史与文化也就将告以终结。斯宾格勒关于“西方的没落”的论断,也是借浮士德这一人物做出的,“在他身上,歌德从心理学上预示了西欧的整个未来。他就是取代文化的文明,是取代内在有机体的外在机械物,是作为熄灭的心灵的石化的材质。”2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354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354.]浮士德的一生,成了斯宾格勒分析西方历史的具体案例。
随着浮士德形象的不断丰富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歌德的加工和创作,鲜明的“浮士德精神”使其升华于同类题材的作品。什么是“浮士德”精神?虽然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却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观点:“浮士德精神”代表了西方人的现代精神,“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26董问樵,《〈浮士德〉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1~45页。[DONG Wenqiao,Fushide yanjiu (Faust Studie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41-45.]浮士德从书斋到自然社会,再到宫廷中,甚至回到古希腊,不论追求的对象是抽象的知识,美和理想,还是具体的功名事业,浮士德都以一种高昂的热情支撑着自己向前,这种热情即是渴望将个人最高理想和最大价值实现。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是一个注重发挥自己主观能动作用的人物,对书斋生活的厌倦即表明了他对行动和实践的渴望,这在他翻译《圣经》首句时就可以看出,从“太初有言”到“太初有思”,再到“太初有力”,直到最后的“太初有为”,这个过程反映了一个启蒙时代的人认识自我时的历程。后来在魔鬼的帮助下,浮士德时而上天入地,时而穿越历史,时而围海造田,用自己有限的条件去实现自己无限的追求。他和梅菲斯特订立赌约时有一段著名的誓言:“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停一停吧!你真美丽!那时就给我套上枷锁,那时我也情愿毁灭!那时就让丧钟敲响,让你的职务就此告终,让时钟停止,指针垂降,让我的一生就此断送!”27(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浮士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3页。[Goethe,Fushide (Faust), trans.QIAN Chunq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53.]这段话清晰有力的表明了浮士德的人生态度:永不满足,满足即象征着死亡!浮士德追求的不仅仅是对个人私欲的满足,他要的是对宇宙之中一切事物的认知和体验,重视生成的过程,而非既成的结果。同时,在歌德自然有机论的影响下,浮士德这一人物虽然渴望追求无限,但也明白作为一个人,要面临怎样的结局:“将我的小我扩充为人类的大我,最后我也像人类一样没落。”28同上,第56页。[Ibid., 56.]这种悲观但却客观的认识,与斯宾格勒对历史的预言何其相似。
(一) “浮士德文化”
浮士德以有限对无限的追求、对于生命体验的执着、欲望与道德的矛盾,使他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个象征。著名的美学家、歌德研究专家宗白华(1897—1986)在《美学与意境》中谈到歌德及其《浮士德》时就清楚的指出了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并提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将近代西方文化称之为“浮士德文化”。
“近代人失去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协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伟大的代表。他的主著《浮士德》,是人生全部的反映与其他问题的解决(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在他的名著《西土沉沦》中,称近代文化为浮士德文化)。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求解决其问题,指出解决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29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6页。[ZONG Baihua, Meixue yu yijing (Aesthetics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66.]
在《西方的没落》中,“文化”这一概念通常是指各种文明的总体表现形态,比如“古典文化”、“浮士德文化”、“阿拉伯文化”等;在少数情况下,斯宾格勒也会用“文化”来表示具体的文化形态或文化事实,例如建筑、音乐、雕塑。其中,前一种“文化”的表达,与斯宾格勒的“大宇宙”30大宇宙(Macrocosm):“即把现实性视作是与一种心灵相关联的所有象征的总和”。(Macrocosm: regarding reality as the sum of all symbols associated with a certain state of mind.)观念是相符合的,整个西方文化也是“大宇宙”的一个表现形式。宇宙一词来源于柏拉图(Plato,ca.427-347 B.C.)的《蒂迈欧篇》(Timaeus),柏拉图认为宇宙也是一种具有灵魂和理性的有机体,它是一个绝对的整体。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斯宾格勒所提出的“大宇宙”是指由世间万物组成的整体,阐释了生命的规律。因此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是“纯粹和无限度的空间”,这种对无限的渴望的精神以及实践,在斯宾格勒历史形态学的视角下,可以从科学、建筑、政治、绘画、经济等等表现形式中找到契合点。
在分析这些具体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事实时,斯宾格勒总是将它们与浮士德的性格与经历联系起来,使得原本抽象机械的学科概念,变得如同活生生的人一样生动形象。例如在《数字的意义》这一章中,斯宾格勒将西方数学称为“浮士德心灵的观念的投影和最纯粹的表现”。他认为,作为量的数,是属于“古典心灵”的,因为它是固定、既成不变的,而作为一种“纯粹的关系”的数,则是“西方心灵”,这种作为关系的数,是一种像浮士德一样狂热向往无限的倾向的产物,比如函数,“西方文化的象征是其他文化所从未想到的一种观念,那就是函数的观念。”31(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73页。[Osward Spengler,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73.]众所周知,函数中有两个变量,自变量的变化会使因变量发生变化,这种对应的变化使数字从计量单位的身份跳脱出来,成为一种对于“极限问题”(limitproblem)的研究。对于无限的追寻,将数字与浮士德这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连接在一起,并以象征的手法来阐释了历史文化的发展变化:“新数学的发展,其实就是为对抗量的观念而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秘密的且最终获得胜利的战斗。”32同上,第74页。[Ibid., 74.]“新数学”是西方历史文化的象征,“量”则意喻古典文化历史,西方文化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不断摆脱古典思想文化的过程中进行的。
在歌德形态学思想的基础上,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他将其视为是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在这一基础上,斯宾格勒做出了“西方的没落”的论断:“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33同上,译者导言第32页。[Ibid., 32.]歌德在《论温克尔曼》一文中在评论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Velleius Paterculus,c.19 BC-c.AD 31)34韦利奥斯·帕特库洛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撰写过自源起到公元29年为止的罗马史。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基于他的立足点,他不会把所有艺术看作是像其他所有有机体一样有着一个难以察觉的开端、一个缓慢的成长、一个辉煌的完成时刻以及一个逐渐的衰亡过程的活生生的东西,尽管它是呈现在个体的背景中”。基于前人对于历史的分析与概括,斯宾格勒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对过去的文化历史形态进行了“俯瞰”式的研究,他认为“古典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及其具体的文化现象,最能体现“历史有机论”,而且“文化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原初现象。”35(德)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103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103.]因此他借种种原初现象的表现形式作为“西方的没落”的有力佐证,对“浮士德文化”的命运做出了判断。
(二) “浮士德心灵”
在《西方的没落中》,尤其在斯宾格勒在展开自己的历史比较形态学时,特别是在阐释古典文化、西方文化还有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差异时,他常常使用“心灵”一词来表示文化现象和文化材料。“文化心灵”这一概念,来源于德国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Leo Viktor Frobenius,1873-1938),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何谓“心灵”呢?斯宾格勒是这样说的:“‘心灵’,对于已从单纯的活着、感觉着的状态发展到警觉的、敏锐的状态的人来说,乃是一种源自十分原始的生与死的体验的意象。”36同上,第288页。[Ibid., 288.]这一说法似乎可以看出歌德“原初现象”理论的端倪,所以在斯宾格勒看来,“心灵”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是感性的,强调感受和体验,随着《西方的没落》对历史文化形态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斯宾格勒再次解释了“心灵”的含义:“它即是那奥秘,即是那永远的生成,即是那纯粹的体验。”斯宾格勒认为,用来表示“心灵”的形式有文字、音乐、图画、哲学、建筑等等。
在此基础上,斯宾格勒创造了“浮士德心灵”一词,和之前的“浮士德文化”一样,“浮士德心灵”这一概念也融合了歌德笔下的浮士德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生经历。按照斯宾格勒的定义,文化形式是心灵的实体,而心灵则是文化形式所要表达的一种精神或者意象。在进行世界历史文化的形态比较时,斯宾格勒认为体现“浮士德心灵”的有:“伽利略动力学、天主教和新教教义学、巴洛克时代的伟大王朝及其内阁外交、李尔的命运以及从但丁的贝亚德(Beatrice)到《浮士德》第二部最后一行诗句中的圣母理想。”37同上,第183页。[Ibid., 183.]这些列举出来的例子理解起来都颇为抽象,但都体现了相似的精神内涵——为了实体性的目标而追求一种永恒不朽的、无穷空间的精神。这也就是斯宾格勒所谓的浮士德式的心灵。与此同时,上述的例子也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几个典型特点:对于自然的渴望和征服、求知精神和实践行动的结合、来自宗教的赎罪意识等。
在上述列举中,斯宾格勒提到了但丁《神曲》和歌德《浮士德》里的圣母理想,仔细研究这两部作品,会发现它们的结尾有着相似之处,主人公在众天使以及俗世恋人(贝亚德之于但丁,格蕾辛之于浮士德)的接引下进入天堂。这不仅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在歌德《浮士德》的最后一场中,悔罪女(旧名格蕾辛)和众天使一道带领浮士德来到天堂,对于浮士德而言,格蕾辛是一个灵魂引导者,她不仅使他明白,不加遏制的欲望会给人带来伤害,还带领他进入永恒不朽、空间无限的天堂。在最后“神秘的合唱”当中,众天使和教父以及悔罪女唱:“力不胜任者,在此处实现;一切无可名,在此处完成;永恒的女性,领我们飞升。”38(德)歌德著,钱春绮译,《浮士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475页。[Goethe,Fushide (Faust), trans.QIAN Chunq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7, 475.]关于“永恒的女性”,译者钱春绮先生在注释中说,“以圣母玛利亚和脱离尘世而超升天国的格蕾辛为代表的、永恒的天主之爱,这是一种纯洁无私的爱,通过女性之爱对人类显示其最完美的形式。”她象征着那些具有无限吸引力、在本质上不可穷尽的事物。浮士德与悔罪女格蕾辛的爱,是从世俗的小爱到永恒的大爱,也是有限到无限的一次飞升。而圣母的引领,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都是最高层次的升华,在她的带领下可以走向无限和永恒。所以《浮士德》中的圣母理想,体现了西方文化在宗教因素影响下渴望救赎,追求无限,向往永恒的思想精髓。
除了上述的圣母理想,斯宾格勒还借《浮士德》第一部“复活节”中的一个片段作为例子来说明浮士德式的心灵,“一种难言的亲切向往,驱使我前去草原和森林徘徊,我流下了热泪千行,觉得出现了新的世界。”39同上,第19页。[Ibid., 19.]浮士德在书斋中常年苦读,自己也厌倦了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尤其是在与瓦格纳进行过辩论之后,他更渴望在自然中能认识自我、提升自我,特别是在复活节中的宗教力量的感召下,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转引了上述片段,并据此对“浮士德心灵”做出了总结:“对森林的向往,对神秘的激情的渴望,对难以言喻的遗弃感的渴望——这便是浮士德式的心灵,也只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的一切。”40(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第1卷第179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179.]从前期对自然的敬畏和向往,到后期围海造田对自然的征服,再到对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敬服,这种永不止息、充满探索精神、浮士德式的心灵,在斯宾格勒看来,正是西方精神的体现。
斯宾格勒在论及建筑风格的时候也借用了浮士德心灵,在斯宾格勒看来,哥特式教堂最能体现浮士德文化,因为教堂高耸的尖顶,内部拱顶的空间,甚至从入口处到唱诗班的位置(“体现了一种动态的纵深”),显示了一种向上升腾、追求无限的意志。在绘画艺术中,透视法的运用是对浮士德文化的一种最佳诠释,因为它能够“极力冲破所有的感觉障碍物而通向无限。”41同上,第241页。[Ibid., 241.]特别是一些宗教题材和神话传说的西方绘画,比如达·芬奇的绘画作品,它们大都描绘了一些上天入地的景象,比如漂浮在空中云彩里的神圣形象,天使和圣徒的超尘脱俗,这些作品都表明了一种对摆脱地球重力的强调,一种心灵对于飞翔和无限的渴望。在斯宾格勒看来,这些特征正是浮士德式的艺术所特有的。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之后,浮士德迎来了自己命运的最大悲剧:在将魔鬼为自己挖掘坟墓的铲锹声误以为是围海造田的顺利进行,并说出了“停留一下”的违背誓言之语,灵魂险些被魔鬼带走,但最终在上帝的拯救下进入天堂。关于浮士德的命运结局,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浮士德究竟是灵魂毁灭了还是获得了拯救?文学评论家埃里希·赫勒(Erich Heller,1911-1990)曾就此分歧提出过如下看法:“浮士德的原罪是什么?精神的不安现状。浮士德怎样才能获得拯救?精神的不安现状。”42(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Harold Bloom,Xifang zhengdian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2011, 166.]这种分歧显示出了浮士德命运的矛盾性,或者可以说是歌德本人思想的矛盾性。在这种矛盾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浮士德进入天堂,即达到了永恒,是一种圆满的结局;而另一部分人的看法则与之相反,满足即意味着毁灭,浮士德进入天堂,他的求知和探索也就宣告终结,这是一种悲剧的结局。斯宾格勒的立场无疑是属于后一种看法的,他说:“《浮士德》第二部中,浮士德走向了死亡,因为他已达到了他的目标。”43(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西方的没落》,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 年,第1卷第404页。[Osward Spengler, Xifang de moluo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1, trans.WU Qiong,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404.]也就是在此立场上,斯宾格勒做出了“西方没落”的论断。
浮士德的结局不仅影响了斯宾格勒对于西方历史命运的论断,而且启发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应该以怎样的方法开展:“尚待写下一部各精确科学的形态学,去研究所有的定律、概念、理论如何内在地互相扭结在一起,而构成文化的诸般形式;以及它们在浮士德文化的生命历程中究竟意义何在。”44同上,第405页。[Ibid., 405.]斯宾格勒认为系统的研究是处于僵死状态的方法,不足以揭示历史的本质,只有以观相的方法入手,透过历史的诸种表现形态,才可以清楚的把握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脉络。这种在浮士德式的智慧影响下产生的形态学方法,在斯宾格勒看来,应该被引入历史研究的最终课题:“把一切的知识都融入到一个庞大的形态学的关系系统中。”45同上,第407页。[Ibid., 407.]
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开始,历经启蒙运动,再到黑格尔,西方历史哲学一直试图把西方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模式作为人类的全部历史整体来把握,斯宾格勒将之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而“历史的形态学”就是对这种研究模式的颠覆。它打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以时间线性发展为主轴的研究方式,提供了一种形象生动但在逻辑性上稍微欠缺的方法,例如从物理科学、建筑风格以及王朝政治这些具体形态中得出其内在规律的同一性。斯宾格勒将这种形态学的研究方法称之为“历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但这种“革命”在学界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的,正如评论家阿瑟·盖耶所说:“它(《西方的没落》)既以其悲观主义令我们沮丧,又以其对我们的已有观念的有力挑战而令我们振奋。”。
四
虽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序言中称“本书的范围和主题属于历史哲学”,但它却不是传统意义上以王朝政权更替以及制度发展为脉络的史学,而是关注世界历史形态的文化史,他曾提出了世界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这一说法,这点似乎也可以看做是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影子。《西方的没落》的研究重点是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事实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形态特征,斯宾格勒也据此对历史做出预言:“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做出大胆的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去追踪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46同上,导言。“预言”要求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这种诗性的智慧,无疑是与历史研究所要求的理性与逻辑是相悖的,斯宾格勒因此被调侃为“祭司”、“占卜者”。
或许《西方的没落》最使人们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它的预言性,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数次政治、金融以及社会危机带来的后果似乎都在极力证实这一预言。而除了“历史文化形态”的预言,斯宾格勒也注意到了现实因素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对社会文明造成的冲击,成为西方文化没落的加速器:“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47同上,第43页。[Ibid., 43.]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对物的崇拜超越了对精神的重视,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在过度追求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丧失了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从而导致文化的衰退和价值观的破碎,这就是一个时代没落的象征。在此意义上,《西方的没落》提供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和警示,同样对我们当下的社会也有着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