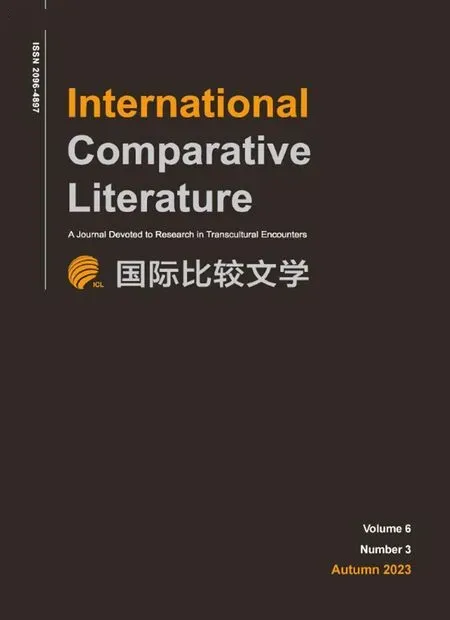逐爱的女人与无爱的家庭:资本语境里的中度空间*
2023-05-01董琳璐上海外国语大学
董琳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一、逐爱的终点:耶利内克笔下的家庭空间
“它,爱情,是永远不会来的,人们总是以为它在别处,总是在追逐它,而过不了多久,女猎手就变成了猎物。”1(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贪婪》,杜新华、吴裕康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0页。[Elfriede Jelinek, Tan Lan (Greed), trans.DU Xinhua, WU Yuka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5, 40.]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以“追逐”连接起了女性、爱情和家庭:家庭空间始终作为一种女性需要离开、进入的空间存在,而非“庇护所”。动物性的求偶行为或社会性的逐爱行为则构成离开原生家庭、组成新家庭两个部分之间的过程。
逐爱的起点是女性的原生家庭,而逐爱的终点是与男性共建的家庭空间。在《逐爱的女人》2Elfriede Jelinek, Die Liebhaberinnen (The Lovers)(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1975).中,耶利内克所塑造的正是在逐爱“路上(unterwegs)”的女人,只有在路上而不在家庭空间内部,她们才是“有爱者(Liebhaberinnen)3本文的节标题借用了中文译本的“逐爱”字样。而“Liebhaberin”或者“Liebhaber”的概念也多次在耶利内克的其他作品里出现,如“Dieser Mann ihr gegenüber widmet sich derzeit ganz seiner Laufbahn als Liebhaber” (This man in front of her is now entirely dedicating himself to an orbit that circles her exclusively as a lover).Elfriede Jelinek, Greed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2), 107.“在她面前,这个男人作为她的情人,献给她的是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轨道。”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贪婪》,杜新华、吴裕康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8页。[Elfriede Jelinek, Tan Lan (Greed),trans.DU Xinhua, WU Yuka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5, 68.]这句话实质上是将男子作为逐爱者的“后置身份”与男子想要将女性引向的男性为主的生活轨道的“前置身份”进行了并列对照,从而揭示了男女情爱中的追逐与被追逐的身份的转换,也由此与《逐爱的女人》的文本形成了互文。”,而一旦进入了家庭空间,她们就失去了爱,身份不再是“情人(Liebhaberin)”,而是妻子、儿媳,或者是奴隶、佣人,如女主之一,工厂女工布丽吉特视进入男方(海因茨)家庭为自己的使命:“随着故事的进展布丽吉特将会从海因茨那里得到一个姓,这要比金钱和财产更重要,这能带来金钱和财产。”4(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页。[Elfriede Jelinek, 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6.]
《逐爱的女人》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女性悲剧性的“逐爱”本能,并将家庭作为逐爱终点来观察,亦即关注女性进入(或离开)家庭空间的过程,逐爱是女性最主要的行为动机。“在《逐爱的女人》中我描写的是农村和城里的贫民。她们不是职员、秘书,而是农民的女儿和工厂女工。我有意识地创造一种封闭的环境,没有出路,……人不那么容易从那里逃出来,……如果女人不自己来掌握自己,而把自己的命放在男人手里,那一切就像是六合彩,全凭运气了。”5同上,第3-4页。[Ibid., 3-4.]耶利内克解释了她对家庭空间的阐释方向和基调:社会是封闭的,女性是无力的,家庭空间是一种必然的、需要运气的另一个未知封闭空间,而女性却必须要义无反顾地、盲目地进入。而家庭空间并非表层文本所显示的男女两性关系或者基于性欲、嫉妒心产生的矛盾,而是资本、权力关系结构:爱并非爱,逐爱当然也并非逐爱,逐爱的终点自然也不是传统童话里王子与公主的“大团圆”(Happy Ending)模式或者女性想象中的温暖家庭。也就消解了女性个体从封闭的社会空间(不论是工厂或者农村)逃向家庭空间的合理性和情感正义性,从而指向了最根本的问题:为何女性总要归附于一定的空间内、与不同的男人、女人建立“爱”的联系。对此,耶利内克在文本的标题中给出了回答。
《逐爱的女人》书名为“Liebhaberinnen”,英文书名为“Women as Lovers”,中文译名为“逐爱的女人”。从该词的男性词义“Liebhaber”来看,意为“向女子求爱者”,而女性词义则恰为“向男子求爱者”,但同样,女人们以为追求的是爱(Liebe),实际上却是一种“生活”(Leben)。这也和书中耶利内克所说的“好一点的生活”相呼应。书名的字面意思为“有爱的女人们”,按照德语构词法显示为动宾词组的名词化,但“有爱”的状态是极为短暂的:“b.和h.的故事不是那种缓慢成形的东西,而是突然出现的那种东西(闪电),它叫爱情。”6同上,第7页。[Ibid., 7.]
“逐爱”的过程才是耶利内克描写的主要内容,女人们以为追逐和占据的是“爱”,而实际上只是借由“爱”之名期待拥有的“生活”,逐爱者之一的工厂流水线女工布丽吉特将电器修理工海因茨当做生活:“海因茨就叫生活。真正的生活不仅叫海因茨,他就是生活本身。”7同上,第6页。[Ibid., 6.]一旦进入了家庭空间,他们就主动抛弃或者被动失去了“情人”(有爱之人)的身份。另一个逐爱者宝拉则向往与帅气的伐木工人埃里希的“电影爱情”,宝拉8宝拉在《逐爱的女人》中是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女工,这一形象还出现在耶利内克其他作品中,“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还创作了农村女工保拉这一形象。这个人物第一次出现在短篇作品《譬如保拉》中——后来这部短篇被原封不动地收人了长篇小说《逐爱的女人》——在短篇小说《保拉解读一篇自己出演主角的乡村小说》中,保拉又再次出现。小说的独白中,保拉坦承自己正是一生辛酸的始作俑者。保拉最后一次出场是在《逐爱的女人》中,她与城市女工布丽吉特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薇蕾娜·迈尔,罗兰德·科贝尔格:《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传:一幅肖像》,丁君君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79-80页。[Verena Mayer, Roland Koberg, Aierfulide·Yelineike Zhuan, Yi Fu Xiaoxiang (Elfriede Jelinek, a Portrait), trans.DING Junjun, Beijing: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8, 79-80.]是被动的、布丽吉特是主动的。但结果并无本质差异。她们都相信爱的浪漫性和幸福的偶然性,如布丽吉特认为“幸福是偶然的,不是依照规律或者一系列行为的逻辑结果”9(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9页。[Elfriede Jelinek, 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9.]。宝拉想找的丈夫是“电影里经常看到的那种”,“然后大家生活在一起并相爱”10同上,第18页。[Ibid., 18.]。
“逐爱的终点”也并不美好,“婚姻一般都是自个儿来,并不带来生活。”11同上,第14页。[Ibid., 7.]她们在逐爱的过程中失去了爱,又在逐爱的终点失去了生活,最后在家庭空间里失去了“最后的字母”“i”——自我(ich):因为她们进入家庭的过程与新婚后购置的家具无异:“家里的厨房是崭新的,吸尘器是新的,窗帘是新的,三角桌也同样,电视机是新的,新的长沙发是新的,新的炉灶虽然是二手货,但跟新的一样,地板虽然用旧了,但擦洗得跟新的一样。并且女儿跟新的一样,很快就要成为售货员,将飞快地衰老,被使用。……她也需要这样,来一个新的,更好的,比这里的牧师、教师、工厂工人、铁匠……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都新都好的人。”12同上,第15-16页。[Ibid., 15-16.]
二、家庭的女主人,或资本的女仆
所谓“女性的物化”、或者说“女性甘当奴仆”的悲剧性在《逐爱的女人》里体现为女性无意识附属于资本的行为逻辑,表现为一种女女竞争关系:不仅同龄女子之间要“雌竞”,男子的母亲和妻子之间也要竞争,竞争的对象当然是“男人”及男人所代表的稳定的家庭空间以及空间内的金钱、资产、稳定的身份。
因此,布丽吉特和宝拉在逐爱过程(实际上是对“稳定”生活的追逐过程,即“Leben haben”)中面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其他女性,尤其是男人的家庭空间内原本的女主人:海因茨和埃里希的妈妈都对渴望进入家庭空间的年轻女性抱有敌意,因为她们无法带来金钱,只能消耗金钱。围绕男人形成的竞争关系定义了女性的身份:一种死物——“埃里希四周都是女人身体堆砌成的墙”13同上,第113页。[Ibid., 113.],这一比喻让人联想起杨国忠之用婢女为肉屏御寒14(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见(清)李渔:《闲情偶寄》,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4页。[WANG Renyu, “Kaiyuan tianbao yishi”(Deed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in Xianqing ouji(Leisurely sentiments), LI Y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354.] 在某些小说中还有情节如女子殉葬时以跪姿充当卧榻的。这都是对父权社会中女子的人格、自由、价值的深度摧残。,而在耶利内克笔下,女人的功能却不止御寒了,虽然比婢女要有人身自由,但却放弃了自由而成为男人的附庸、奴仆。恰好,耶利内克对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女性刻画也主要以“女主人”或向“女主人”迈进的过程为主,其实质上则对应了女性逐步屈服于资本、被资本控制的过程,这也是父权社会中女性游走在家庭空间内发生的“异则侨易”。
“女主人”是胜利者,但进入了资本控制的家庭空间。耶利内克由此展开对资本、对受到资本控制而畸变的一切家庭关系、个体的讽刺和批判:家庭关系、成员的价值与“钱”或者其他资本符号相连:首先是孩子,他们是母亲“身上结出的果子”,是“搞”出来、“生产”、“拥有”的对象,是“母亲又可以有保障地存在,又有了存在的理由”15(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Elfriede Jelinek, 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113-114.],然后对丈夫来说是一个“可以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的东西”,而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激励”。家庭生活名义上围绕“爱”孩子,让母亲的家务劳动和父亲的社会劳动充满意义,但妈妈在家务劳动里被“砸得稀巴烂”,爸爸在社会劳动中“早已埋在坟墓里”16同上,第114页。[Ibid., 114.],父母间的“爱情”关系变成了对孩子输出的“爱”,而实质上,孩子“被裹挟、蹂躏……扇耳光……”17同上。[Ibid.],却惟独难以享受到爱人之爱(事实上,埃里希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婚生孩子),劳动平均地降临在三个对象身上,是“沉重的负担”,是资本逻辑的化身,主导着完整的家庭空间:母亲劳动而不赚钱,父亲赚钱而不做家务,孩子既不赚钱也不劳动但要挨打挨骂。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以及资本逻辑对家庭空间的主导。这种逻辑是从社会空间蔓延而来的,在家庭空间生根发芽,继而感染每一个家庭成员,通过孩子、孩子的成长为媒介再次蔓延到未来新的家庭空间内,而作为“果子”(Früchte)的孩子实际上并不是家庭的真正结晶,如海因茨父母心中认为的“果实”(Früchte)18同上,第130页。[Ibid., 130.]实际上是他们节俭所得的财产。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实质上仍然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一种“阶级压迫”,即“男性对女性的压迫”19(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页。[Engels, Jiating siyouzhi he guojia de qiyua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State), trans.Zhonggong Zhongyang makesi engesi liening sidalin zhuzuo bianyiju, Beijing: Renmin Press, 1999, 66.]。这种压迫在耶利内克笔下是资本压迫的一个重要面向,但资本暴力不等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性别战争永远不能解释或解决资本作为“第三者”对家庭的控制。宝拉看中的伐木工人埃里希作为非婚生子的身份影响了他在婚恋市场的价值,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他从儿时起就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母亲的责骂,长大后也要受到母亲的“教导”:你得找个有钱女人。电器修理工海因茨的父亲“脊梁骨已经老朽到几乎无用的地步,不仅对东家和资方来说无用,对父亲自身来说也毫无用处”,他的力气和能量只在是否“适合开长途货车”20(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Elfriede Jelinek,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130.]的层面被定义,而最后的下场是和妻子被海因茨和布丽吉特赶走,为年轻人空出房子,这正说明了资本逻辑在家庭空间内的代际传承,即便海因茨和布丽吉特当下对自己的孩子充满爱意,但也难以避免被资本之轮在下一个代际碾压,家庭里的女主人不断更换,每一个却都是资本的奴仆。
这些隐晦的背景正说明了由资本主导的家庭空间对于所有人平均的压迫,不分男女。也再次证明了“资本”作为外部因素入侵家庭内部空间的普遍性:
一方面,资本借家庭成员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权力符号进入家庭关系,任何一种“异则侨易”的畸变起点都来自于资本作为权力符号取代了个体所处的亲缘和血缘关系中的形象。另一方面,资本进入家庭空间后完全主导了家庭关系,以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取代了“爱人之爱”,使家庭空间丧失了一种可能的“流力”,成为恐怖的“爱”真空地带,被资本力牢牢绑缚的家庭关系只能畸变:虽然一般认为血缘和亲缘关系是极为稳定和牢固的关系保障,但在资本的强大力量之下却也出现了“变态”畸变,验证了资本逻辑对所有家庭关系摧枯拉朽般的打击,无论这种家庭关系是血缘、婚姻还是其他。
另一方面,“竞争”(Konkurrenzkampf)这一由资本主导的商业活动形式反而是家庭空间中,比如布丽吉特和宝拉生活中的主要关系表现,这也与家庭功能的历史性转变有关,“某些传统的家庭功能已经被其他组织形式功能所取代。经济功能已经进入工厂、商店和办公室。与其说威望和地位是以家庭为中心,不如说以个人为中心。……家庭除去仍是感情生活的中心和生育子女的地方以外,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功能了”21(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4页。[J.Ross Eshleman, Jia ting daolun (The Family: An Introduction), trans.PAN Yunk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1, 14.]。
至此,家庭空间实际变为由资本控制的类似经济空间:人(作为劳动力的人)、情(爱作为体现人性的高级情感层面)、欲(生理性和动物性主导的低级情感需求,在家庭中以性和暴力为表象)作为三个层面的“家庭成员”关系模式均受到资本逻辑的安排。甚至人、情、欲之间进一步形成了彼此“等价”交换的联系,这也从根本上确立了资本的霸权。不但女主人,女主人的主人(男主人)都是资本的奴仆。
三、资本域和精神域的“中度”:家庭域
简单将家庭空间等同于经济空间显然是有问题的,在此引入“中度”的概念,其是侨易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涉及如何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发现、观察、判断“侨易现象”:“在社会学的视角中,有一个所谓的‘中观’维度,即在宏观、微观之间去把握事物;……如何能在事物的两极之间寻求一种合适的张力维度,可能是各学科、各领域、各文化都面临的问题,我想提一个概念,即‘取中由度’。”22叶隽:《构序与取象:侨易学的方法》,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142页。[YE Jun, Gouxu yu quxiang:qiaoyixue de fangfa (Constructing Order and Taking Image: The Methodology of Qiao-Yiology),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21,142.]“即有效地在二元关系中把握那个可以导向平衡点的‘中点’,即‘度’。”“度”强调“维度”,也是“适度”,而“中度空间”则在维度和适度的层面上同时强调了宏观-理性、微观-感性两组常见的思维方式之间需要补全的思维“漏洞”23同上,第144-145页。[Ibid., 144-145.],升至一种“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交融之景。
比如家庭空间,其不仅是个体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空间中度”(从小到大的“中度”),也同样是时间维度的线性“中度”(幼年和老年均在家庭,而中年、壮年在社会空间),更进一步,仍有着一种介于个体空间和社会经济空间的“适度”性质。中度不仅仅是尺度上的中等,还包含了一种权力场和价值起效范畴的媒介角色。“中度”下的家庭域即成为沟通资本域24“资本域”的概念参见叶隽:《“渐逝”抑或“渐常”?——〈光芒渐逝的年代〉中的家族史、资本域与侨易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年2期,第45-54页。[YE Jun, “Jianshi yihuo jiangchang?- guangmang jianshi de niandai Zhong de jiazushi, zibenyu yu qiaoyixing”(“Jian-Shi (Slowly Fading)” Or “Jian-Chang (Slowly Normalizing)”-The Family History,Capital Domain, and Nature of Qiaoyi in “In Zeiten Des Abnehmenden Lichts (In Times Of Fading Light)”), Nanjing shifan daxue wenxueyuan xuebao(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 (2023):45-54.]和精神域的重要概念。
资本域的概念区分于“资本语境”,前者是“一种产自人类却又不能被人类如意操控的难以避免的语境,……一种具有强大规定性甚至规训的符号空间”25同上,第54页。[Ibid., 54.],强调资本因素生效的边界(资本语境则侧重人对资本因素的意识边界)。资本域的代表空间则不胜枚举,传统的市集作为经济活动和物资交换空间(甚至不能不提奴隶贸易以及自古以来就有的“卖淫”产业),以及多种经济和资本概念上行、下行后形成的新资本空间如“文化产业”等。精神域以形而上的思辨范畴为代表(文本如《象棋的故事》),体现了精神力的绝对优势,甚至可以“移山倒海”,拯救灵魂。
而家庭域则牵连了一方面作为精神域核心情感的“爱”,另一方面牵连了作为资本域核心的“贪欲”,成为中度空间:这也涉及到如何分析和阐释发生在家庭空间内的事件,即从精神域角度、从资本域角度,或者从家庭域本身出发。
这三个阐释角度在具体的文本或社会观察中也均有显现,比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上野千鹤子(Ueno Chizuko)将家庭视为劳动力生产的起点和终点:个体在家庭中成长为劳动力,然后输送至社会空间劳动,年迈或出现伤病则回归家庭空间26(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Ueno Chizuko,Fuquanzhi yu ziben zhuyi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trans.ZOU Yun, XUE Mei,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20.]。而恩格斯认为,女性被视为私有制经济制度中封闭的家庭空间的财产,与社会空间隔绝。在耶利内克笔下,家庭空间的“中度”性质得以彰显,综合回答了作为家庭内部行为逻辑的“人”、“情”、“欲”三个层次的逻辑为何冲突的问题。也就揭示了家庭域的起效规则。
首先,家庭域尊重资本域的法律规定和准则,尤其是社会经济空间的秩序:《逐爱的女人》中宝拉和布丽吉特的家庭显然是畸形的,但是乡民邻居却认为被埃里希家暴着的“妻子”宝拉(有家庭)的地位要高于“非婚单亲妈妈”(无家庭)的宝拉,布丽吉特的妈妈也允许海因茨在预设要娶其女儿(共建家庭)的前提下进行的非婚性行为。正是因为家庭结构给男女个体带来的身份确立、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的认同的重要性,才导致了作为社会经济空间内逻辑的资本成为家庭施令者。这样的家庭空间显然成为连接个体和社会空间的中度。社会人不必另外学习一套家庭空间的律法,而能熟谙“弱肉强食”、“等价交换”的资本铁律就足够了,结婚证只是经济合同副本,“已婚妇女专门从事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务劳动,所以她们就需要与丈夫签订长期‘契约’,……‘结婚’就是男女要共同承担一项长期义务”27(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1页。[Gary Stanley Becker, Jiating lun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trans.WANG Xiansheng, WANG Y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41.]。家庭商品包括“孩子、声望和尊严……羡慕和感官享受”28同上,第33页。[Ibid., 33.]。而妇女的身体在家庭空间中被分解为生产资料,以各个身体部位和器官成为各种工具和功能的载体,这种载体是对应了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力功能的。
其次,家庭域的形成又与个体天性和动物“恃强凌弱”“逐色慕强”的本能无法分开,即作为精神域的极底层的“欲”也在家庭关系中(前家庭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男男女女在求偶阶段体现出的动物性尤为明确。而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则更为激烈。如布丽吉特时时处于被海因茨抛弃的恐惧之中,她具有的资本只是作为女性的性资源和生育价值:“布丽吉特只有身体可提供……这些其他人也有,其质量有时甚至要比她的更为上乘。……布丽吉特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像女人,她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像女人。”29(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Elfriede Jelinek,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10-11.]而宝拉在做售货员时与作为顾客出现的已婚女性之间是相互鄙视又羡慕的“围城”心态,“进来的那些家庭妇女已经有过爱情,那是很久以前,她们既同情又蔑视女售货员,……受到保护的女人蔑视没有受到保护的。而女售货员也仇恨家庭妇女,因为她们已经走出一切,而她们还处于艰苦卓绝的竞争战中,……此处充斥着仇恨,仇恨蔓延着,熏染一切,无人能幸免,女人在她们之间看不到任何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对立”30同上,第34页。[Ibid., 34.]。社会经济单位中重要个体的女工人或者售货员不自视为“社会人”,而时刻处于动物求偶期的备战状态,也是被恐惧“欲”或者仇恨“欲”推动,战胜者进入家庭,保卫家庭:维持家庭空间的排他性。
第三,理想的家庭域无疑与精神域的高级层面即“情”相关,也就是“爱情”、女人、家庭三者的和谐关系。然而耶利内克首先否认了“爱情”能带来好的家庭的可能性:宝拉的故事反映了浪漫电影中爱情的虚假性、完美的男爱人想象带来的伤害。所谓爱情也是资本社会商业电影的造物,这就恢复了家庭空间本来的“资本属性”,切断了家庭空间与虚伪爱情的关联,揭露了家庭域本质上未能融合精神域的真相。
“情”的缺失、“人”的利用、“欲”的赤裸导致了家庭的僵化,耶利内克将这种僵化的家庭模式解读为“慢性死亡”:“男人和女人一道慢慢死去,男人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些调剂的可能,他像一条看家狗那样,从外面看守着他的老婆,他看守着她的死亡。而女人从里面看守男人、那些来度假的女游客、她们的女儿和家用钱不被拿去喝老酒喝掉。男人从外面看守着他的老婆、来度假的男游客、女儿和家用钱,为的是能从中抠点出来喝老酒。这样一来,他们面对面一步步走向死亡。”31同上,第16-17页。[Ibid., 16-17.]死亡是家庭空间的终点,但他们的“情感”、“爱”、“夫妻”关系的死亡却早已发生。“在那座雄伟的宫殿里,……它,爱情,将走向何处。那是连载的。一直走向婚姻。一直走向死亡。”32(奥)艾尔芙丽德·耶利内克:《贪婪》,杜新华、吴裕康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8页。[Elfriede Jelinek, Tan lan (Greed), trans.DU Xinhua, WU Yuka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05, 68.]
父亲成为赚钱机器,母亲成为家务机器,孩子因其颇具未来的可能性而成为有价值的储值物品,大家只能“慢慢死亡”,以一种固定模式存续直至赚钱的机器不再赚钱、家务机器磨损坏掉、孩子长大成为新的赚钱机器或者家务机器……这样的家庭空间又反而影响了社会空间:即社会视线下的个体身份只是一种去除了个性和精神的机器符号,男性价值通过赚钱能力体现,女性价值通过外貌、阶级、家庭体现。而在遵循资本逻辑的社会空间和家庭空间内,男性居于主导就不奇怪了:男性可以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向内凝视家庭,而女性被困在家庭内部,只能凝视她的丈夫,显然,享有全景监视权的是能够进入社会空间的那个人,而家庭空间内的亲密关系则被永远“相向”(gegenseitig)的敌对关系取代。
因而,家庭空间成为男女个体与社会空间发生联系的中度。女性以家庭为媒介同社会发生有限的联系,而男性以社会空间为主导向下兼容家庭空间,我们能理解:家庭同时也是性别之差、阶级之差、城乡之差的交叠空间33指来度假的男女游客分别形成了对家庭空间内部主体的诱惑。(奥)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逐爱的女人》,陈良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6-17页。[Elfriede Jelinek, Zhu Ai de Nvren (Women as Lovers), trans.CHEN Liangme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5, 16-17.],即具有“中度”和多空间交叉性质:在“断链点续”34叶隽:《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YE Jun, Zhongguo xiandai liuou xueren yu waijiaguan, huagongqun de hudong (Intera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in Europe with Diplomats and Chinese Worker Groups),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2.] 书中对于三个群体在中西交汇的大变动背景下的交往、影响以及相关意义的研究,实际上也展示了本来由阶层、职业、地域差异而决定的“社会空间”如何互动并产生新的“思想”、“制度”乃至独特的时代影响和从“家国一体”到“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大同理想。其中有关“断链点续”的方法可作为家庭空间与女性重要连接点的参考:“所谓网链,即网络中的生物链,或关系链,用网来比喻,就是强调其涉及面的广泛性和立体性。……必须强调‘点’、‘链’的环环相扣。每个个体可以被视作网络中的‘点’,而相关或同类的个体又结成关联性的链性群体,也就是说,通过相互关联的‘点’结成这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动脉系统,……‘点续’……有点像互联网络下载系统的‘断点下载’一样,他是可以通过不断地截断、重续、积蓄的过程完成的。” 同上,第25页。[Ibid., 25.]的视角内,家庭空间具有了勾连个体与社会的中度意义,尤其是勾连女性个体与社会外部空间的作用,家庭空间作为连接个体的“生理本能”与“社会人性”中度空间、家庭关系作为个体之间血脉生理关系以及社会性质的(劳资、纯爱)关系的中度均体现出来。
家庭也成为“阶层结构性重建”的空间:广而推之,不仅女性、几乎所有个体的成长是在家庭空间内“点续”完成的(另一种类似家庭提供养育职能的“福利院”也是非常独特的空间,但与以血缘、亲缘为基础建立的家庭有本质区别,此处不论),个体所铭记的永远是阶段性的家庭记忆,社会的进步也是建立在个体家庭的网链基础上的。而《逐爱的女人》揭示出资本如何调控家庭“中度”空间,叙述了家庭作为阶级、性别、城乡差异的交叉空间是如何变形的,其意义也超出了以性别为界限的女性文学批评范畴——借由宝拉和布丽吉特,我们才醒悟女性如何在家庭空间这一重要的侨易节点获得“情”层面的高变,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逐爱的女人”一旦进入家庭便“无爱”的症结,而从“逐爱”到“有爱”,不但是女性及其所属家庭之幸,也是社会、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