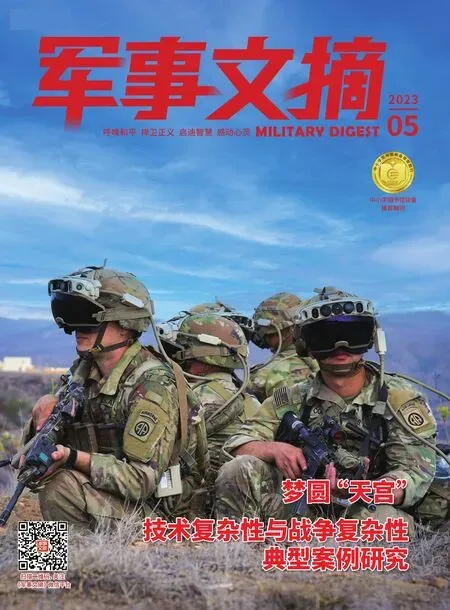上帝最后的“折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僧格林沁与蒙古骑兵
2023-04-30王栋
王 栋
13世纪的蒙古铁骑曾纵横欧亚大陆,被西方惊呼为“上帝之鞭”。时至清朝末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登上历史舞台,一度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击败英法联军,为清廷承担起了抗击西方侵略的重任。但在之后的八里桥一战中,面对英法联军先进的武器与战法,僧格林沁引以为荣的蒙古骑兵全军覆没,向当时的中国宣告了传统骑兵时代的彻底结束,也为西方“上帝之鞭”的历史想象拉下了帷幕。
西方世界的“末日审判”与“上帝之鞭”的历史想象
宗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公元392年,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对外宣示基督教为罗马帝国之国教之后,基督教便确立了其在西方世界核心宗教的地位。根据基督教教义,上帝将于“世界末日”之时审判一切已死去的和当时仍然活着的人们,善者奖励,恶者受罚,而“上帝之鞭”的历史想象,则与这种“末日审判”思想密不可分。

蒙古军攻陷巴格达
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霸主,因此活跃于内亚草原且骁勇善战的游牧族群史不绝书,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阿提拉与成吉思汗。游牧骑兵的征战伴随着杀戮和暴力,这无疑给西方造成极大的恐慌,部分基督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帝降下的“末日审判”,于是将其称为“上帝之鞭”。
首先给西方制造“上帝之鞭”恐慌的是匈人首领阿提拉。匈人拉丁语为“Hvnnvs”,古罗马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所著《地理》一书认为,匈人是居住在里海北岸的游牧民族,公元4世纪中后期,开始向西方更肥沃的草原地区扩张。以阿提拉为代表的匈人四处征伐,给欧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并对此后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中世纪北欧古老的英雄诗歌《埃达》中,最重要的两篇是《阿特里诗篇》与《格林兰阿特里诗篇》,阿特里即是阿提拉在北欧诗歌中的名字。
震惊西方的第二次“上帝之鞭”则是以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为代表的蒙古铁骑。“蒙古”原本只是蒙古高原诸部之一,随着铁木真统一各部,建立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草原帝国“大蒙古国”,对西方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蒙古的三次西征。第一次西征在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远征中亚强国花剌子模;第二次西征为窝阔台汗时的“长子西征”,最远攻至维也纳近郊;1252年蒙哥汗命其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于1258年攻入巴格达,灭黑衣大食,1260年攻占大马士革。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南征北战,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亚的强大帝国。
蒙古三次西征对亚欧众多国家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当时的罗马教皇在致贝拉四世书中亦将蒙古人比喻为上帝的惩罚之鞭:“上帝虽降炎以罚罪,终必易严烈为温和,先持罚罪之鞭,终伸慰抚之手。”基督教徒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惩罚而恐慌不已,甚至部分教徒常在乡间结队游行,手举十字架,口唱圣诗,并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即所谓的“鞭笞派”,此派更是传入法国、英国和荷兰等地,足见“上帝之鞭”这一历史想象的影响之广。

僧格林沁照片
蒙古再次名震西方: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蒙古西征几百年后的清朝末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凭借卓越战功,再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僧格林沁为蒙古科尔沁人,生年不详(一般认为生于1811年),《蒙古世系》称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26世孙。其父毕启虽为四等台吉,实已家道中落,僧格林沁的破土而出则得益于其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济。索特纳木多布济娶嘉庆皇帝之女,然而公主无后,道光皇帝便为其在族众中选嗣,见僧格林沁仪表不凡,便选其为嗣,道光五年(1825年)承袭郡王爵位。僧格林沁的崛起,与当时清朝军事力量的构成密切相关。清代最初的正规军由八旗与绿营构成。随着承平日久,八旗与绿营日益腐败,武备废弛,战斗力下降严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清军的军事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革,以“湘军”“淮军”为代表的乡勇、团练逐步取代八旗、绿营的地位。僧格林沁所处时代,正是八旗、绿营衰落,地方乡勇、团练兴起,而其麾下的蒙古骑兵则是八旗中蒙古八旗的代表,在八旗整体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僧格林沁及他麾下的蒙古骑兵,可以说是八旗最后一支可战之兵。
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是从镇压太平军开始的。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建立起了与清廷相抗衡的政权,并开始计划北伐与西征。北伐意在直取清廷首都北京,“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林凤翔、李开芳率北伐军由扬州出发,最后深入直隶,威胁清廷京畿。此时的僧格林沁受命专办京师团防,任参赞大臣,率军镇压。在王庆坨之战、连镇大败北伐军后,僧格林沁在连镇木城生擒北伐军主帅林凤翔,冯官屯之战又生擒李开芳,立下赫赫战功。僧格林沁并非有勇无谋的将领,其战术思想灵活,且能合理利用天时地利。如冯官屯之战时,正值雨水较多,僧格林沁意识到“阴雨浃旬,河水日涨”,根据“旧有河形,可以引水”的地形,制定了水攻的策略。北伐失败是太平天国衰落的原因之一,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总结太平天国教训时,提出“天朝之误有十”,而“误国之首”即是“扫北败亡之大误”,且“十误”中前三条都是在谈北伐,足见僧格林沁功勋之大。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克广州后引军北犯,攻陷大沽口后随即占领天津,扬言占领北京。清廷见此急忙议和,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对条约“万难允诺”的咸丰帝在英法联军南撤后,即命僧格林沁整顿大沽防御。大沽为京、津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接过大沽的烂摊子后,僧格林沁整顿军队,巩固防御工事,他在给咸丰的折子中谈到“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不特不可令其经由,且不可令其窥伺”。1859年,侵略者卷土重来,英海军司令贺布率军进犯大沽炮台,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爆发。僧格林沁临危不惧,从容应敌,在其指挥之下,英法联军参战舰船几乎全被击伤,旗舰“鸻鸟”号被击毁,炮艇“茶华”号和“庇护”号被击沉,“鸽鹅”号等几艘炮艇搁浅。此时的贺布仍不认输,而在海口南岸强行登陆。上岸后的联军再次遭到僧格林沁的猛烈进攻,加之土地泥泞,行军困难,只得退回舰船,仓皇撤出战场。是役,法军阵亡16人,军官1人;英军伤亡430人,贺布本人亦受重伤。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抗击西方侵略的第一次大胜,其意义不言而喻。僧格林沁前往大沽口布防之初,中国的火炮武器本就落后,又值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新败,众多炮台及防御工事损坏严重,且清军士气低落,可谓“受命于败军之际”。对此,僧格林沁有条不紊地布防,“大沽海口及双港地方,修筑炮台,安设营垒,并置木筏以扼海口要隘,各项工程均于一月十七日完成”。当英法联军入侵之时,无论是对付敌军舰船还是登陆,僧格林沁都应付自如,最终取胜。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固然有英法联军轻敌的因素在内,但更重要的还是僧格林沁积极的准备以及正确的指挥。
此战对西方震动极大,法国《星期日快报》指出:“在中国耗费巨大的战争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开支的增加,给士兵则带来可怕的贫困——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法国全权大使葛罗1860年随侵略军再次来到大沽口时,在其《黄皮书日记》中写道:“与1859年一样,这些炮台与工事均由僧格林沁负责防卫,这是一位鞑靼名将……僧格林沁是蒙古科尔沁部首领,精明能干,令人生畏。他是清军中唯一有才干的将军。正是他在1859年的大获全胜,才击退了贺布上将对大沽的进攻。也正是他,从那时起在大沽修筑了浩大的防御工事。而且据说此次驻守炮台的正是他率领的军队,足有25000人到30000人之多。”可见,即便一年后联军再次来到大沽口,对僧格林沁仍然心有余悸。僧格林沁及“两万蒙古军队”一战而闻名世界。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让西方人意识到,在清廷“不堪一击”的军事力量中还有僧格林沁这样一位同他的祖先一样拥有高超军事才能的蒙古将领,正是他导致了西方侵略者的惨败。
“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八里桥之战
1859年11月,英法联军卷土重来,英军18000人、法军7000人,以孟托班为总指挥,再次引兵寇境。在相继攻克大连、烟台等重镇后,对大沽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英法联军吸取教训,从清军防守薄弱的北塘登陆,后挥师南下,攻陷新河、军粮城、唐儿沽等地后,大沽已腹背受敌,僧格林沁无奈撤出大沽,天津也相继失守。第三次大沽口之战虽以清军大败告终,但僧格林沁并不服气,他在大沽失守、退至通州时称,“倘该夷敢于北犯,临时酌量,总须与之野战,断不可株守营垒,转致受敌”,认为之前败因在于固守堡垒,没有以骑兵与英法联军展开大规模野战。可见,此时他仍旧寄希望于蒙古骑兵,认为在空旷之地凭借骑兵便可取胜,这种误判为八里桥之战蒙古骑兵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费利斯·比特于1860年拍摄的永通桥(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
大沽、天津相继失陷后,僧格林沁退至八里桥一带,希望以蒙古铁骑在此与英法联军野战。1860年9月21日,联军对清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清军骑兵则按照原定部署朝联军阵地冲锋,联军则以枪炮迎敌,结果“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以致不能成列,纷纷退后”,蒙古骑兵在密集的火力下伤亡惨重,败退之时又冲散了其后的步兵。联军乘势发起攻击,清军大败,僧格林沁亦慌忙撤退,八里桥失陷。消息传到北京后,咸丰帝立刻逃离北京,“先幸热河”。
若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僧格林沁还心有不甘的话,那么八里桥之战则正是其求之不得的野战,但结果却是蒙古骑兵的一败涂地。僧格林沁在奏报中称,“奴才所带马步官兵,卓索图盟归化城、吉林、黑龙江马队溃散极多……京旗各营官兵,屡次挫失,心胆已寒”,并指出“枪箭刀矛焉能抵敌炮火”。联军军官杜潘在他的《远征中国》也写道,“人员方面,敌人的损失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肯定他们的死伤绝对在2000人以上……周围的土地上堆满了尸体,由于我们不可能掩埋这么多的尸体,引来了一些狗和乌鸦前来猎食”。联军主帅蒙托邦在其回忆录中称,“战场上到处都是清军的尸体……放眼望去,遍地清军”。而联军方面损失极少,据瓦兰·保罗回忆,“联军部队伤亡极少,法军死3人,伤17人;英军方面也差不多”。尽管这些伤亡数字未必准确,但也反映出联军惊人的战损比。
经此一役,僧格林沁引以为豪的蒙古铁骑损失殆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与西方侵略者的角逐以僧格林沁的彻底失败告终。

八里桥伯爵:夏尔·库赞·蒙托邦
上帝最后的“折鞭”
在西方人眼中,僧格林沁并非清廷军事体系中的一名普通将领,尤其是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失败,让西方人注意到一触即溃的晚清军事力量中,还存在这样一位蒙古将领。例如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即谈道:“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舰队进行猛烈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结果进攻者完全失败。”此战则被马克思用为反抗西方殖民侵略斗争的典型。通过当事人的记述,我们也可以窥得当时西方人对僧格林沁及其麾下蒙古骑兵的格外关注。
瓦兰·保罗在《远征中国》中称,“像僧格林沁这样的将军,他拥有大批的马队……个个都十分勇敢,因此他可能隐约察觉到我们现在的危险,并要让我们遭受世界上最彻底的灾难”,“他以‘僧王’的名义身负指挥战事和领导军队的重任。所以,比起与我们交战的第一支部队,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支新的部队,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即便是在击败僧格林沁之后,瓦兰·保罗也再次强调了游牧人的战斗本能,“假如这位将军(僧格林沁)……消灭单独的敌人,并且摧毁桥和船只,切断道路,堵塞运河,甚至毁灭整个地区(对这样的游牧民族来说,这么做完全属于一种本能)那么我们的士兵可能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国”。不难看出,即便在战法及武器上拥有绝对优势,但英法联军还是将僧格林沁及其麾下的蒙古骑兵视为一种极其危险恐怖的存在。
即便当时的清政府已是软弱不堪,但当英法联军正面战胜蒙古骑兵之后,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如英法联军随军翻译阿尔芒·吕西即在其给家人的信中表达了战胜蒙古将军的喜悦:“伟大的胜利!我的好父亲!……中国方面损失惨重。中国军队的蒙古将军僧格林沁和他的兄弟都在这场战役中战死了!”这是阿尔芒·吕西写给父亲的家书,在信中阿尔芒·吕西难以抑制击败蒙古将军的喜悦与激动之情,可见在西方人眼中,“蒙古”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存在,即便击杀的并非僧格林沁本人,都足以令西方人齐欢呼雀跃,并不惜在战时的家书中多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英法联军统帅蒙托邦事后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足见其对八里桥一战的重视。
英法联军凭借先进的武器与战法,在正面战场以少胜多击溃蒙古骑兵,可以说为长期以来“上帝之鞭”的历史想象彻底拉下了“帷幕”,助长了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从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对蒙古骑兵野战的自信,到战败后蒙古骑兵的覆灭,无疑反映出当时中国武器装备、军事观念的落后。此战也向当时的中国宣告了传统骑兵时代的结束,为之后的“自强”“求富”,以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