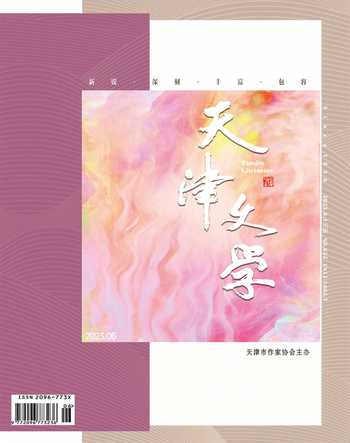去恩城
2023-04-29苏宁
1
过了洪泽收费站,下了一夜的小雨似乎停了,天光大亮。冉老师伸出手看了看时间,手表昨晚洗过澡就戴在腕上了,这是他多年的习惯,逢到上讲台,都把手表戴上。站到讲台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腕上摘下手表,放到讲桌上,然后依次拿出讲课提纲、电脑。七点四十,到恩城还有70公里。恩城是冉老师一家对南京的别称。在冉老师出生的小镇,“硬”的读音类似“恩”,自己高中后到南京读书,家里人说:那是一个恩(硬)正城市。“恩”后的“正”念出来要是轻音。论坛九点开幕,他在分会场的讲座是九点半,两边都能赶上。组委会想请他头天晚上过去,可昨天下午系里有活动,活动后有聚会,几个嘉宾是自己请的,要陪一下。他谢绝了接送,说自己开车。
他把手伸进衬衣口袋,口袋是空的,再伸进裤子口袋,也是空的。他腾出右手去打开副驾上的双肩包时,已经想起来,昨晚临睡前,怕忘事,把手机放进了西装口袋并挂在了鞋柜上方的小衣架上。早上六点十分出门,出门时还掏出手机和会议组的小秦老师说了一条语音留言:已出发。然后他回身取背包。冉老师看了看空空的副驾,西装忘了拿上了。
会议议程是电子文件,在手机里,地点他是记得的。车上有导航。回去取手机,时间是来不及了。中途折回去说临时失邀,更是极为不妥。停在紧急停车道上,冉老师迅速想了两个办法,一是到服务区找电话叫朋友、熟人去家里把手机给拿出来;二是到服务区报停。因为身份证也在西装口袋里,买个新手机、办个新卡眼前这点时间是搞不定了。要先到会议上,请熟悉的朋友借他们的身份证用一下,再找移动营业厅。
前面的服务区是眙盱,七点五十,车进服务区,他在超市借到了电话,他打给自己的同学阿程。阿程没有接——也许是睡着,也许醒的,非工作时间,又是一个陌生电话,大约不会接的。又打给自己的学生,拨出去,就摁掉了,他觉得不合适。打给妈妈,可是他记不清妈妈的电话号。还有谁可以帮这个忙呢?而且,电话号码他一概不记得,都存在手机通讯录里,平常用时就调出名字,从不会去记号码。记得阿程,并不是交情深、交集多,是有一次,阿程和他说,老冉,我们的尾号数字相连啊。自己这个手机号,是单位统一发下来让大家自行挑选的,几页纸的号码,被人选走的就用笔圈掉。因为这个他才记住了。平时他能记得的,除了儿子的号码就是弟弟的,但弟弟在北京,儿子在扬州上学。
他又打了一遍阿程的。论距离,阿程住城北,自己在城南,也很远,就是接了电话去帮自己也要一个多小时,这个时间差不多可以到会上了。到了会上又不能离开,只有请会议组帮助了——自然,自从钱和手机卡关联在一起后,他几乎没再带过银行卡在身上,更无现金。买个新手机需要借钱,这很尴尬。他没有注意会议名单,如果自己的学生张新力也来参加会议,那就好了。
这一遍,阿程居然接了。之所以接了,阿程说是想摁掉迷迷糊糊地摁错了键,才宿命般听到冉老师的声音传过来。冉老师迅速说了下情况,不知我们家罗老师出门没,或者,你请胡司,他离我近,他去拿下,我想找他可我忘了他的手机号了。别多说,把衣服拎出来就行,就说我需要正装,你也别见笑,别惊动罗老师,此地无银地提醒说拿手机,说不定就拿不出来了。家里门是有密码的,是数字的,如果罗老师已经出门了最好,衣服在门口,手机在口袋里,直接拿出来就行。家门的临时密码是000111,你不要打趣我,这件事太严重了,我冒着让你见笑的风险了。你拿到拿不到,过一小时都打到新街口的金陵饭店,请前台找我,我还不知住哪个房间,请饭店转会议组找我。哎,四五十人的会,好找人。我在服务区借的电话,细情回去说,兄弟,这个会议要是不重要,我现在自己折回去拿了。这样,阿程,不管拿到拿不到,你现在先帮我报失报停。
至于吗?
至于,请你了,立即。
你里面有一座金山吗?
不说这些,请你帮忙。我现在往会议上赶。到了宾馆,我再打给你。
八点五十,冉老师到达会议。到了宾馆,他用前台电话打给程老师。程老师接了电话说,你可真赶点,西装拿到了,两三分钟前,手机也拿到了,我来的路上也先给你的手机挂失了。
会议要周五结束,今天外,还有两天议程,明天看情况,如果安排得开,明早我回来拿一下手机。
我给你快递吧,不要来回跑了。
快递要隔日。
要不,我现在叫个车给你跑一趟吧。上次调研的费用还没报,一起走下。这样你中午就能拿到了。新办个手机你还要找营业厅,借现金,找身份证,惊动一大片。
也是办法。还是送来吧。冉老师小声说,还是送来的办法更稳,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付钱,没卡、没现金,命都在手机里。太黑暗了。
理解,我现在就找车,到时给你放前台,办好了我告诉你,我有事我就不单独跑了。
好的,那我收到再复机。
还有,我得告诉你,你的手机不是在西装口袋里,罗老师在家,我拿了衣服,都要走了,顺手一摸,口袋是空的,我又转头,和罗老师说,在峰说手机好像也落家里了,让我一起拿下,要不您打下,看手机在家不。罗老师一伸手就把手机递给我了,手机在罗老师手里。
不要送了,我上午做完讲座就回来。
放下电话,罗老师请小秦安排会议上一个同学帮忙买一个新手机,说用一两天后就注销,手机和身份证都落家里了,不能没有联系工具,临时用一会儿就销户,还用原来的。钱呢,也先请小秦垫付一下,自己拿回手机后转给小秦。
2
冉老师打开手机,失散了一天,似没有任何异常。罗老师正在准备晚餐,看他进门,“噢”了一下,说,以为三天的会议,那我加一点米,程老师手机给你带去了没?
冉老师说,下午系里有个比较急的会,让我主持,我中餐后回来了。实际上,他并没去系里,去了阿程那。上午会议上,小秦帮他买了新手机。从阿程那拿到手机后,他先去营业厅复机。然后,冉老师把自己关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他之前就隐约觉得罗老师是知道他的开机密码的,但为了扫除罗老师的疑虑,他也一直没有换成指纹锁。一早上出门到程老师拿到手机有三个多小时。罗老师解锁一个手机的时间是充分的。微信里有六七万块钱,罗老师从微信里转了两笔钱出去,一笔是给儿子转了一个2000,一笔是给爷爷,也是2000。数字很平常,也很奇怪,这不是罗老师的风格。按理,这是最能让自己知道她动过手机的证据。理由只有一个,罗老师就是想让他知道,她打开了他的手机。
罗老师是徐州人,冉老师是淮安人。在所有江苏人眼里,徐州人都是山东人。而在徐州人看来,除了徐州,整个苏北人都是乡下人。罗老师生在徐州,以前偶尔自许过是山东姑娘。这个在医学院里教解剖课的山东姑娘,身上没有山东姑娘的风风火火,不是不假思索中就推起小推车冲上战场的作风,遇事波澜不惊,也绝不轻易表达宽容,行事滴水不漏,又稳又准,心里什么都装得住,平静深沉,有一个不见底的、能盛大东西的深渊。
既然转钱,那微信信息自然也能看到。坐在车里的一个小时,他把自己所有微信记录翻了一遍。
先等她开口,她不说自己也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没多想。想好了这一条,冉老师进了家门。晚上也是可以赶回会场的,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回家看看情况再说,明早再去恩城。再有,这一天,他过得心里累,太累了,他需要休息一下。
罗老师上下看他,没有再说话。等他洗了澡出来,准备开电脑时,罗老师说,看你手机在,我就用了下——我把这月的钱都存成定期了,一时想起来下星期是端午,就给儿子和爸爸各转了两千块钱。你看看短信,有提示。你转的,他们也开心。老是我转——我也就过个手,你也露个头,刷个存在感。没等你回来,也是怕一转头又忘了。
手机明明是在西装口袋而且是静音——话到嘴边,冉老师咽了回去。阿程到家里来的时间,是九点多,按理,这个时间罗老师应是在学校了。
冉老师知道她有每月把钱存成定期的习惯,也是两人约定,冉老师负责日常开销,罗老师负责存下来支付大额。自己是个存不住钱、又不能忍受钱包里没有可随时支配的钱的人。
冉老师只好接,去年就忙忘了。
开电脑只是缓解一下慌乱,也正好看看有没有没处理的邮件,信箱刚开,手机震动了一下,一看,是井井。
她说,你不是九点多就到了吗?怎么晚餐时没看到你。
你几点到的?你也参加今天的议程了吗?
我上午不是回你了吗?
冉老师愣住了,对话框除了以上几句全是空白,自己什么时候发微信问了?
正在犹疑间,一张对话截图发过来。早上时间六点三十二分,井井发来微信:你到会了吗?
自己发的微信:我九点左右到。
自己又发:你呢?
井井回:我上午不参加,下午有课,下课后出发,大约晚上七点到。
静默了几分钟。大约是井井自己意识到才说的是一个有句号的话。
井井发来:你自己开车吗?
自己:对。这个字分明是自己的常用语。
井井便回:那不说了,注意安全,晚上见。
和井井说话的显然不是自己,也不会是阿程。说过又删除,是罗老师自己感到了代答消息的不适合?还是在质问这种不分时间、地点的来讯。
冉老师想起在流言里,已知的和自己有过什么的另两位女性,想到这,不禁打了个寒颤。
回头看罗老师,正站在阳台上看星星或窗外的路灯,手里端着茶杯,茶杯上蒸起水雾,顺着罗老师的视线向外望。冉老师心里一凉,夜有这么深的颜色吗?气息里透着诡异。
自己在怕什么呢?自己的手机里有什么呢?怕得不敢质问这种不安全感和背叛。灵魂被复制了吗,并且被手机同步了?取消这份复制?戒掉?有电脑就足够了,只是慢一点。像系里的老名士金教授那样,用的是第一代手机且不常开机,找他只有留纸条、写电邮。更新的手机系统方便了,又是什么方便了呢?辗转反侧中,冉老师定了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六点、六点十分三个提醒闹钟。喝完罗老师递来的睡前牛奶,关掉手机。准备第二天一早返回会议。
等第二天睁开眼睛,拿过手机一看,时间已经是正午十点了。居然睡得这么沉。喊罗老师,罗老师没有应,似不在家,而自己,仍不想起床。会议人多,即使位置牌在那,只要不是主持人,来不来,都没有人在意。能睡到第二天正午,不是年轻,是体力在慢慢减退。对体力变化的感受与觉知,罗老师和系里几个老师谈论过。阿程在场。
阿程说,三十年前的人谈论过相同问题。
谈笑间,阿程讲起三十年前,在某大的校园里,自己和老师一起从教室出来,去一个什么地方,大约是回了老师办公室一下,再一起去食堂。教室和办公室不在一个楼。和老师一起出电梯、进电梯,在电梯里人是靠得很近的。当时还有老师的两个朋友在。阿程说才被电梯里女孩子的头发梢扫了一下,以为是电梯漏电了,自己过电了,吓了半死。老师的朋友对老师说,你看,什么是年轻,这就是年轻啊!浑身都是开关,一碰就开,洋溢着灵敏性、敏感度。想当年,我年轻时,读一个小说里性感的句子,都能从天灵盖到脚趾头起反应,更别说偶然和哪个异性坐近了一点、不小心碰到了异性的手了啥的——那碰,对我,就是事故。“麻”啊——麻的感觉,半麻半木时,身体里到处都能一碰就是火花。
正午的校园,四处是骑在自行车上飞驰的少年。老师和朋友看着这些少年,看看自己,又看看阿程,相视微笑。老师说,我是到了四十岁才慢慢理解了年轻身体的灵敏性和敏感度的,还有那种一根铁钉咽下去都能消化的消化能力与接受力。什么都能接引进来——都能吸收,泥沙俱入,心怀一个大海或一个不见底的特别能收东西的黑洞似的。眼睛里有光,在这层光的照射与过滤之下,一切都是纯粹的、可以结晶的,可以去信任和有余力追逐的,这是把混沌劈开后,分层分出来的部分,透亮、莹洁。然后,你慢慢通关这个层次,往另一层里流去。什么叫天命之年和老之将至呢?老师停了一下,说,就是再美好的异性在眼前,或者,是各种美好的实物,你看着这些,可能想用手去抚触一下——我是会有想法,但这想法一有就是一个打包文件,一起打包进很多东西,想到礼、法、年纪、社会眼光,这么一想,这些念头就熄灭了,我就正襟危坐了,庄严了,精神自洽,身体也自安其形了。相不是空的,是实心、实用、可彰、可效的理从中撑着的,里面是一个大空间。外面又是一个大空间。我能做的,只是赏赞这种美好,敬畏这种美好,不会去惊动、评议,不会非分地想去参与、分享或破坏。人身内部的生态系统太奇妙了!也是到了一定时间身体的某些开关就自动关闭了。
对对,老师的朋友接道,我反对那些有的没的站过来就说事的心理学说,但我热爱、信任科学,还有造物者的伟大,给我们一个神圣绝伦的肉体系统,又给予精神、血管、七窍以及语言、味觉、视觉,感知功能设置得也妙啊。
阿程停下,眼睛望向冉老师,说,在峰,我那时多年轻啊,可我一听我就理解了,一句不差地明白了,我们老师当时,和我现在差不多年纪吧。
冉老师说,还有能割齐一切不平的锋利、尖锐以及愈合力。但到后来,就都没有了。你有的都会被收回去。
阿程抬起头说,在峰,你说的这点,我就有过。忽然之间没了。
这场谈话发生时,和阿程的关系还是普通同事。这次谈话带来微妙的变动。冉老师这一次托付他代自己取手机的底气,记得号码之外,得益于这次倾盖之谈。
思思想想间,又睡去,醒来是晚上了。一天睡下来,更觉浑身无力。要不要和会议组说一下呢?
今晚是宴会。这两年,很多活动改成线上和云端了。但这次是线下。桌次卡提前就打在会议手册上,冉老师在主桌。打开手机,想给小秦老师知会一声。与小秦老师说话的界面,还停在昨天,早上出发前自己的一条留言,然后是小秦的回复:我在前台等您,房卡我提前帮您办好。然后是昨天下午一拿到手机,换好卡,给小秦转的手机款。
一上午过来,小秦,井井,其他几位同会的老师都没有信息找自己。他们不找,我就不要主动知会了罢,会议要照应的地方多,说了就要调位置、拿席卡的,添忙乱。事在眼前,自然处置就好。
这样想着,冉老师放下手机。会议议程明天上午结束,下午离会。下午赶过去就是晚上了,剩半天会了,不去了也罢。
这一天,睡得太踏实了,把僵硬的背、腿、整个身体都睡软了。好像工作后就从没舍得这么一天摊在床上。
客厅的日光换成了灯光,罗老师回来了,向他瞅了一眼,没说话,自顾脱了外衣,向厨房去了。
两个人这些年几乎是这样,有对话也简洁无比,只说摘要,说关键词。
冉老师在现代文学所,罗老师在医学院。同在一个大学任教,却交集无多。
同住一个房子,一起生了一个小娃,儿子上学后需要的接送,是轮值,这很节约人工成本。偶尔一同出席一些家人、朋友间的聚会,一起去超市,当然有了网购后这一项也就自然取消了。
当年奇奇怪怪的一拨同学,幼儿园的、小学的、中学的,各自成长,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回了本城,陆续散布进各机关、哨卡,成为自己儿子的班主任、任课老师、给儿子打防疫针的护士、看伤风感冒的医生、路上的交警、给自己买的新楼盘画图纸的工程师、向父母推荐保健品的药商……这就是被罗老师打趣的“地面熟”吧。
和罗老师相亲前,两个人并不认识,但同一个学校任职给他们增加了见见无妨的想法,大不了以后继续只做同事。
结婚后,冉老师问罗老师,为什么选了我?
罗老师说,突然觉得找个本地人省心,有个地面熟,有根、有襻,组个家属团啥的,都不用跨区域,交通费都节约了。
罗老师问,你呢?
冉老师说,我爸说山东姑娘好,心大,只和工作较真,可是没碰上,一看徐州的,我就乐了,徐州在我心里就是山东的地盘。
3
要不去看看心理医生吧,体检不是没问题吗,做做心理检测没什么啊。晚饭时,两个人对面坐下,罗老师说,我自己学医的也在看的,感觉好了很多。
我以为是身体问题,想一想,是内驱力匮乏了,感觉不能自我发动了。
罗老师说,你似乎也很纠结你的记忆力,能把幻觉中的事当发生过的事。
冉老师一笑,半城熟人,真是不好意思去挂号,去恩城吧,为了一个心理号跑一趟觉得不值。当然,我反对有点心理活动就往心理问题、精神框架、原生家庭上扯。不是火山、冰山,内部什么样,都要测点数据出来。
罗老师搅动了一下汤里的绿叶菜,说,我就是看的熟人号,你看,我一个医学院给学生上解剖课的,还看心理医生呢,混了大半生,哪能没点心病。
冉老师点点头,说,我洗碗,我睡了一天了,我可能是被什么破事困住了。
两个再无话。
晚餐后半小时,冉老师拿出手机想打一个电话,手机刚拿在手,同事的电话进来了。
你看下群,你没看群吗?阿程老师突发心梗,走了,下午被发现的。被发现时走了有一会儿了。应是上午或是昨天夜里。一开始没发消息,都不敢信,下午证实了消息。我也不敢信。
他家里,自己昨天下午还去过,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我昨天还见到他。冉老师说。
昨晚临睡前,冉老师还打了阿程电话,冉老师说,昨天慌忙,拿了手机就走,也没好好说谢谢,让你一大早跑半个城。
电话里嘿嘿一笑,你平时很憨、很高冷的范啊,原来也有故事。
哎,防疑于未然,万一哪回酒喝大了,言辞轻佻,用了微信又没删,两个汉字换来翻车现场,不值得呀。我这记忆力,明明手机、西装和车钥匙放一起的,我怀疑我这个身体系统的处事能力了。
你的西装并不在门口,我眼见着罗老师开了衣柜拿出来的。不是挂在门口。阿程说,可能是你记错了。
前天夜里,阿程陪学生搞了一夜毕业论文,太迟,没有回去。这是前天。同事说,我才从他学校这边的家里出来,他家里人说他昨天上午本来还挂了去医院的号,但不知为什么没去。可能这一两天睡得太少了,他太累、太困。人是蜷坐在沙发上没的,今天下午被发现的,房子多了就这样,他自己住这边,发现时应走了有些时候了。
天啊。冉老师觉得话要说不出来了。
同事说,多保重啊,我也是才知道,两年多以前,他肺部就发现了些问题,但他硬是谁都没说,老人、孩子都不知道他生病,更别说外人了。他夫人说,她自己内心也是做过一些思想建设的,但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突然。这小子,从认识他就觉得他挺名士风的,表面上风清月朗,没料到内里这么硬,这么在意体面,我是不是太粗心了,一个病号和我共事,我都没发现他有病,看他天天西装革履、行云流水的,至少活一百年的人物,现在想,他每天仅穿这些衣服行走都该用了老大精神。
泪珠从冉老师眼里落出说,我昨天还见到他,昨晚还和他打了电话。如果昨天没见到,我可能心里还能接受点,我现在完全不能接受了。是做梦吗?
他喊,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你过来,我是不是才做了个梦——我接到电话,说昨天上午到你这给我拿手机和西装的阿程老师今天走了。
他又说,昨天的事我本来不想说,想忘了,他是让我不忘才这么来一出的吗?你说,这是幻觉吗?第一个走的怎么想都想不到是他,根本没听说他身体有状况。我不服气。冉老师大声对罗老师说,眼里充满无助。
他看着罗老师,迅速确认着眼前这个人是否就是和自己生儿子的人,他不太习惯和罗老师用这样的语气对话似的,忽然低下头。
我请他拿手机,我凭空用了他两个多小时,这时间他可以睡觉、复原体力的。我分了他的心。他上午跑了一趟,我下午又到他那去。
罗老师眼里的神气似乎想说,那你为什么非要拿呢?可是,她低下头说,在峰,这不是你可以预料的。
送别了阿程,回到家里。周一的晚上,罗老师说,这周去看下儿子吧,一个月没去了,去看看,马上就高二了,他上周一直在和我探讨去哪里读大学、专业方向和申请的条件呢,还有高考,是参加一下还是直接申请呢?我们一起过去和儿子聊聊。
我要去下恩城——我从南京过去,和你们在扬州会合。
你去几天?有什么会议吗?上周不是才开了一个吗?
冉老师点点头说,是会议,两天半。我明天早上六点十分出发。
那我和你一起去恩城,我这两天心里也乱,你忙你的,我到了自己走走。然后一起去扬州看儿子。
我要给同事办点事。我们分头去吧。
冉老师取过西装,将手机设成静音,放进西装口袋,又拿过车钥匙,一起放在门口。然后设了第二天早上五点五十、六点、六点十分三个提醒闹钟。
一夜无话。罗老师睡在另一个房间,闹钟在冉老师床边,声音不大,罗老师还是听到了。她看到冉老师起来洗漱后轻轻带上门出去了,但只拿了车钥匙。西装挂在门口,罗老师走过去,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到阳台上向下看,停车位已经空了。
苏宁,女,有随笔集《我住的城市》《消失的村庄》《平民之城》、诗集《栖息地》等出版。主要作品有《乡村孤儿院》《三天走一县》《回家》等。供职于淮安市文学艺术院,任淮安市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