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显现
2023-04-29肖瑞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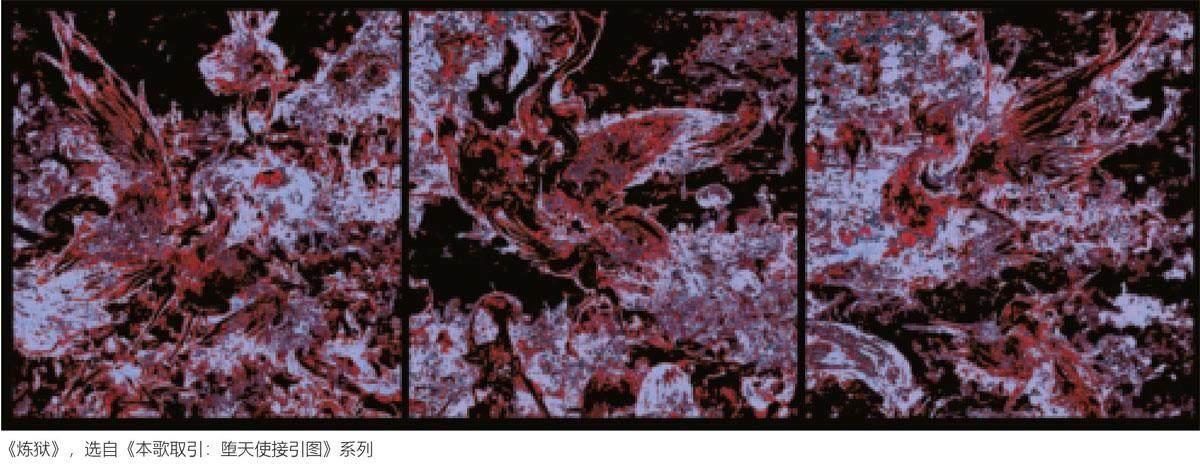


从19世纪初期到现在,摄影逐渐从记录性的工具演变成为一种文化,而作为一种文化,探索和实验是其发展的重要手段。从探索与实验的角度出发,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与年轻摄影师群体的合作——“锐像”便是一个专门介绍中、外年轻摄影师的栏目。《数码摄影》杂志通过对他们的深入采访,将他们和他们最具实验性、探索性的作品介绍给广大的读者群体。面对这些年轻人的“新锐”作品,也许很多人没有办法能够立刻接受,但是我们要以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好与坏、对与错并不是由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来盖棺定论,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事物发展的过程。本期的“锐像”栏目,向大家介绍年轻摄影艺术家朱浚侨,他在实验电影、摄影、多媒体装置和人工智能生成等不同领域中不断探索,其形成的艺术风格深受宗教、东西方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并努力在其中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共振的美学价值观。
QA对话朱浚侨 当AI 成为线索
在AI 影像的时代, 影像的生产开始摒弃传统影像中构成其基础的“光绘”,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引导词主宰的视觉颠覆。展览“世界的倒悬:AI之颜”将生成的面容作为情感切入点,审视数字生成艺术及其关联的主客体、媒介、身份等问题。当AI生成的影像投射在当下的环境中,人们的感知如同柏拉图所描述的洞穴,即囚徒将地穴里“影之相”视为世界。而《AI的偏见》《101场冰冷的夜》《地穴》等系列作品则回应了“忒修斯之船”中关于技术与人的关系的根本讨论——当作为媒介的AI技术充斥乃至操控了我们的生活,那么,人类将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导权?
——肖瑞昀
朱浚侨
1996年生于上海,视觉艺术家、摄影师和影像导演。2015-2019 年,他于加拿大温哥华艾米丽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学习电影、综合媒体与视频艺术专业,现工作生活于上海和温哥华。他在实验电影、摄影、多媒体装置和人工智能生成等不同领域中不断探索,其形成了的艺术风格深受宗教、东西方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并努力在其中建立起与现代社会共振的美学价值观。
FOTO: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尝试用AIGC媒介来进行创作的,能否分享几个重要的系列?
朱浚侨:我个人对于数字与算法本身的那种随机控制性非常着迷,于是就基于算法艺术(Algorithmic Ar t)进行了一些研究,而其中涉及到的Stylegan(对抗模型),成为了我选择实践算法艺术领域的第一步。
《本歌取引》《人工智能与我的双眼》《百相行者》《景观:电子计算》等系列作品是偏向于早期我接触AI生成时的浪漫主义创作。当时的自己会将更多自我的思考与感受通过意向性的象征,将文字或图像交付于AI进行处理(训练数据集/生成),最终转化成创作;而后,在我更为深入地理解了AI生成的底层逻辑以及其背后所带来的一些潜在可能性后,我开始进行更多偏向于批判性的AIGC作品创作。
《FMAO:A I的偏见》作品探讨了大众审美与偏见在A I生成中的影响,《一百零一场冰冷的夜》作品探讨了短视频与大数据推送时代下的信息茧房与趋于高欲望低需求的一种观看趋势,《地穴》作品则探讨了基于柏拉图地穴理论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超现实状态,同时,也是对于基于AIGC大潮下未来MR混合增强现实的一种预言。通过这些作品,我希望社会能够以一种更客观且理性的方式重新思考科技更迭时所带来的影响,向技术寡头发起社会性的监督,而非一味的吹捧或抵制。
FOTO: 人工智能算法实际上是一种“黑箱模式”,其决策机制宛如人类心理机制一般具有不可解释性,与此同时,这种模糊和偏差也会给创作带来更多的空间。那如何看待这种不确定呢?此外,你又做了哪些尝试?
朱浚侨:AIGC所生成的模糊与偏差,大多来自于不了解其生成指令的语法以及随机种子这两大变量。我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浪漫化创作状态,在自己相对了解每个模型背后的底层逻辑后,就已经不再具有其原有的那种未知性所带来的兴奋感受。反之,我会试图将AIGC的可拓展性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核心延伸点——我会试图将人工智能创作中的变量,以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元素来代替。
同时,在《地穴》作品的创作中,其使用的A I生成图像序列所组成的视频,显现出的无限延伸的状态,也是将这种不确定变量不断堆叠后的一种演绎状态。随机种子与前后序列生成的关系变量的控制,就像是在每一场选择中进入新的平行宇宙一样,最终仍然走向那被指定的“未来”(被文本或参数所控制的那一关键帧)。这种状态就类似于柏拉图所提出的地穴理论,囚徒将“影相”视为世界的全部,其火光的不确定性变化可以被不断地解读,但所投射至墙面的影子自身却是其背后的投影者所精心规划的产物。
FOTO:在《人工智能与我的双眼:交织态疆域》作品中,AI对游戏中的定格画面进行了再处理,这似乎是一种已知的既有规则与未知的算法演绎的交融,你如何看待最后的结果?
朱浚侨:这套作品的初衷是将游戏中携带着物理世界审美习惯的图像作为数据集,并观测算法生成模型最终所产生的结果,就像是另一时空中的旅人瞥见了异度空间的自己。我将游戏摄影图像与AI生成图像进行了互相筛选,最终在10000张生成图像与2000张游戏摄影图像之间寻找到了彼此呼应的10组图像,通过拼接与排比的方式达成了交织态疆域这一概念的图示化。
FOTO:《FMAO:AI的偏见》作品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议题:人们基于肥胖、残疾、性少数等人群外貌的刻板印象。你是出于怎样的个人经历来想到要做这样的作品呢?AI又是如何呈現这些刻板印象的?
朱浚侨:当我目睹了AIGC井喷式的发展过程后,不少反对AI的言论以及其背后拥趸所提出的观点,让自己不禁思考——这种对于一项新科技的信息误解究竟从何而来。于是,我使用了人像这一最能让广大观众群体理解并共情的创作方式来进行了关于AI对于人的丑美在语义与生成图像结果之间的一次实验性创作。其中,我们能明显地观察到相较于西方常见的高加索人与尼格利陀人等,黄种人的普遍生成效果质量要显得“较差”。通常,我们会看见的亚洲人的眯眯眼,以及各个族裔脸谱画的生成效果,包括女性角色的“前凸后翘”等偏见,都是基于“训练者”自身的偏见认知和其数据集所导致的。
而所谓的“优”“劣”之别,则来自于数据集本身被训练时所提供的样本数量,以及其多元的程度,再加上进行标注时,训练工程师的人为修正。而其中,从获取数据集到数据清理,以及数据标注本身都是人为偏见可以对结果进行干扰的“重灾区”。基于这种情况,所生成的结果其实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喂养给AI的“养料”以及其供给者——“算法工程师”。
FOTO:《101场冰冷的夜》作品里面的短视频给人一种以假乱真的错觉,能谈谈你对当今娱乐媒介和推荐算法的看法吗?
朱浚侨: 当我们已经将刷短视频这一行为以“电子榨菜”这种方式进行对待的当下,观众对于内容本身的需求已经极度扭曲。他们并不期待在这一类型的平台上观看过于精细制作的视频,而是希望在基于“短、平、快”的基础上,能够提供单一信息的、不需要经过大量思考的、但仍然能够提供一点功能价值的视频,而在推荐算法所构建的信息茧房中,观众将长期深陷于自己的舒适区之内。同时,其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现今的生活环境下,我们更愿意去接收这种被拆解为碎片的信息获取方式。
在此前提下,我使用ChatGPT,基于人们对于短视频的需求,进行了101条短篇故事的生成创作,然后使用自动通过文字进行声画配图的流水线操作,产生了101条符合短视频观众需求的短篇速读故事视频。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其背面的、可谓粗制滥造的技术堆叠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却与我们在短视频平台上所刷到的平均水准的视频相差无几。
FOTO:从逻辑上讲,《人工智能与我的双眼:交织态疆域》《FMAO:AI的偏见》《本歌取引》等作品是一种“后摄影”模式,那么,你觉得它们与自己之前的直接摄影的异同是什么?
朱浚僑:这三个系列与其说是“后摄影”,我更觉得这种基于混合媒介的图像处理方式,让画面与材料的关系更为模糊,反而让视觉与图像的关系更为纯粹。
过去,作为摄影师,我将镜头作为画布的延展,以图像处理软件作为画笔进行编辑创作。而在算法这一媒介加入后,我认为它从根本上解放了自己作为一名摄影师曾经固有的一种媒介依赖性与创作安全感,进而给予了我尝试更多媒介进行创作的可能性。
FOTO: 你认为AI是否有主体性呢?人工智能是否会有一天变成与人类同等的存在,还是它只是辅助人类的一个工具?
朱浚侨:我认为主体性这个问题在此刻我们很难界定。即便AI在未来具有主体性,我仍然认为它的地位可能会近似于目前我们对于猫狗类宠物这样的、拥有“类人权”的一种权利状态。而其本质究竟能否成为一种被“奴役的新物种”,还是成为“拥有自主权利的智能辅助工具”,其生杀大权终究取决于我们——傲慢的人类。
FOTO: 当下,AI对摄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实践与文化的讨论等领域,那么,你对AI未来的预想是怎么样的?
朱浚侨:我认为AI的未来会像过去的互联网一样,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构上的变革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人类从未停止过的对于地外生命的探索、对于造物主的猜想、对于模拟自然的假设,将会导致未来或许会出现一系列对人工智能产生人类共情,甚至将其视作新物种的一系列社会议题。不过,我相信傲慢的人类一定会以一种“神授王权”的姿态,在未来对更为完备形态下的AI制定各类服务于人类自身的法律与权益。
FOTO:在《FMAO:AI的偏见》作品中,你讨论了人类偏见对于AI的影响,那么,你觉得这种偏见的来源是什么?在未来,AI是否会对这种偏见产生影响?
朱浚侨:在目前的生成类图像模型中,偏见的来源主体是数据集以及对其进行训练时的标注。并且,在较为早期的图像生成模型中,因为其生成图像的拟真质量问题,导致偏见的可观测性较低。而在这一大前提下,不断满足训练者自身的产出需要的模型,在训练者的单一视角下不断反复进行训练。最终,再以优先满足少数关注此领域的使用者的情况下,其生成结果充满了偏见。同样的,在大语言模型中,数据污染也会带来一种类似于偏见的概念导向。不乏有着“垃圾场里建泳池”之类的说法以讽刺AI爬虫式训练背后所可能造成的“乌合之众型”的训练效益。我认为AI自身的训练与生成结果其实是充满着多元性的,而偏见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AI作为辅助人类的工具,所提出具体性的要求而产生。更深一层则是,生成式AI在未来蝴蝶效应式的渗透,以及其作为工具性束缚下,AI终究将屈服于人类所提出的主观偏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