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写”立场
2023-04-27申利锋
申利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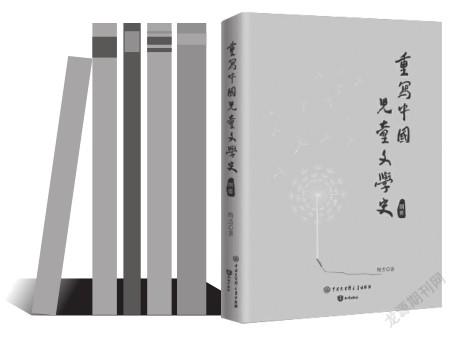
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其丰沛的成果、曲折的流变、繁多的元素等,为研究者留下了广博的阐释空间。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变进程时,学者们从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写作立场、评价标准等出发,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不懈梳理与挖掘。如在那些署名有“主编”或“编著”字样的文学史著作外,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年)、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年)、蒋风与韩进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年)、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9年)、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2012年)、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概论》(2015年)等著作,都从个人写史的学术立场,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价值取向、成就与不足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辨。
2022年,梅杰出版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后文中简称《重写》),为学界贡献了基于个人化立场考察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轨迹的又一重要著述。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梅杰以“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论”相结合的儿童文学观作为其立论基础。他认为,“从理论上讲,‘儿童本位’是理想、理论,是应然状态”(P187);而“泛儿童文学论……是一种儿童文学应用方法,为儿童文学出版者所使用,为儿童文学教育者所使用。”(P188)也就是说,在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历时性进程时,梅杰既关注到了那些基于“儿童本位”的“应然”现象,也关注到了那些基于“泛儿童文学”的“应用”事实;两相结合,构建起了他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史的系统性梳理与个性化评述。
“儿童本位论”是梅杰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动态演进与得失的重要标尺。以之为衡量,梅杰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划分为史前期(古代)、孕育期(清末民初)、诞生期(1917-1927)、发展期(1927-1937)、挫折期(1937-1949)、新生期(1949-1959)、断裂期(1960-1978)、重建期(1978-1999)、分化期(2000年至今)。这样的阶段划分,既有梅杰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纳,也有他基于个人化写史立场和“儿童本位论”标尺的思考与表达。比如,关于“挫折期”这一时段,梅杰既肯定“挫折期的提法是蒋风先生首次提出”(P26),又在此基础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的挫折期包括了“第二个十年”,我认为不妥,应从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起算(为宜)。这个“挫折”,我的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挫折,另一层意思是儿童本位论没有得到坚持,惨遭挫折,最后结果是好的作品不多。(P26)
梅杰曾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与蒋风先生之间的师承关系,他这里关于“挫折期”起始时间的观点,实则表明他是在吸纳前人成果后生成了新的认知与判断,因而也是他学术上承继与新创的例证。
在评述作家作品时,梅杰也坚持以“儿童本位论”为批评标准。如关于新文学运动中陈衡哲的短篇童话《小雨点》,张香还强调了陈衡哲真诚的创作态度和对孩子的爱,强调了该作的诗情画意、文笔流丽、寓意深刻又饶有趣味等特点,称陈氏及其作品在当时都“接近了小读者”;张之伟认为该作“语意浅近,故事性强,易为儿童理解”;杜传坤评价该作“在儿童心理的刻画上相当生动真实……小雨点的形象也因此而丰富、立体化起来”。他们的阐释无疑都贴合了《小雨点》的审美特点,但又在该作的价值归属上不够坚定。梅杰则态度鲜明地指出:“它是儿童本位的童话作品……不是现实主义的”(P89);他还结合陈衡哲的理论文章论证了陈氏的创作观就是“儿童本位论”的,以此说明陈衡哲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有着天然的一致性。
作为“儿童性”与“文学性”融合的产物,“儿童本位”可谓儿童文学拥有独立属性的标榜,“泛儿童文学”的文本则在事实上昭示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之本质。
发轫于20世纪初的中国儿童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还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高度”(朱自强:《论新文学运动中的儿童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4期)。换言之,“文学性”而非“教育性”“工具性”等,是儿童文学作为文学学科门类的基本特质。于是,文学史上必然会出现不是专门写给儿童,但却适宜儿童阅读的优秀之作。对于这一点,有过十多年儿童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经历的梅杰更是将其认知应用到了实践中。他曾先后策划或主编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大师童书系列”及《丰子恺全集》等多种大型丛书,通过打捞史料、编选作品等方面的努力,加上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促使其在“儿童本位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
在“泛儿童文学论”的观点下,俞平伯、废名、王统照、凌叔华等现代文学名家笔下那些适宜于儿童读者的作品自然也会出现在《重写》作者的视野中。雖然这些作家也被此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著者所关注,但在梅杰这里,因他采用的是“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论”——即“应然”与“应用”互补的儿童文学观,所以他对上述名家作品的解读会更显具体观点下的辩证性。如俞平伯的诗集《忆》被视为我国“第一部描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但梅杰却在和前辈学者一样解析了其中的童心、童趣、平凡而生动的儿童生活等之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
这种站在成年人的立场写出的充满童心童趣的作品,读者仍然是以成人为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忆》的局限,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遗憾。《忆》出版后,也没有吸引更多人来写儿童诗,这一客观史实,说明《忆》只有儿童文学史价值,而缺少儿童文学史上的影响。(P80)
值得注意的是,当梅杰言说着诸如“这种站在成年人的立场写出的充满童心童趣的作品,读者仍然是以成人为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之类话语的时候,他实际上仍在强调“儿童本位”当为儿童文学的“应然”。从这一准则出发,梅杰认为沈从文缺少“自觉的儿童文学意识”(P107),而包括郑振铎、沈从文、巴金等在内的文学巨匠,都被如何处理“儿童的”与“文学的”关系这道门槛拦在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园地之外,从而留给中国儿童文学史以极大的遗憾。显然,尽管有着“泛儿童文学论”这一“应用”准则的协调与补充,但《重写》在总体上是以“儿童本位论”作为观照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思想红线的,梅杰始终在强调“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P24)。
虽然该著也有明显的缺憾,如没有采用学院派的文献注释格式,对“分化期(2000年至今)”的文学现象未做单章的梳理和阐释等。但综合来看,《重写》一著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勾画较为清晰,在坚持用“应然”与“应用”互补的儿童文学观解读史料的同时,对不少文学现象做出了富于个性化的阐释,价值评判颇显学术见地,且常笔带锋芒,堪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也凸显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者“求真”的勇气和努力。
(作者系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