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继龙与一位隐没诗人的再发现
2023-04-27王泽龙
王泽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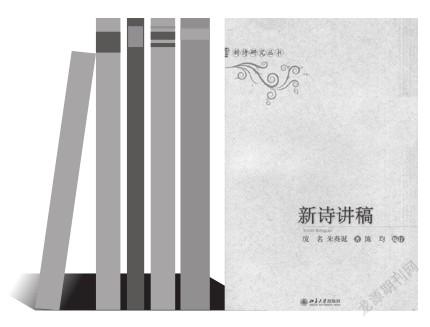
朱英诞的诗名对广大文学爱好者都是陌生的。许多从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几乎也没有听说过现代诗人朱英诞的名字。然而,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登诗坛,其诗艺才华就受到了林庚、废名的赏识,后来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了教师,给中文系学生专门讲授新诗与写作。1935年、1936年林庚、废名先后给朱英诞的新诗集《无题之秋》(又名《仙藻集》)、《小园集》作序。北京大学学生、同代青年诗人南星,专门以朱英诞的诗作集句为诗集《春怨集:集应淡句》出版(1940年),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也是少见的。谢冕先生评价:“朱英诞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更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学贯中西,艺通古今,诗文灿烂。”(《暮年诗赋动江关:纪念诗人朱英诞》)抗日战争胜利后,废名从家乡黄梅重返北大续写的中国新诗讲稿,专门将“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列为一章,收集在《谈新诗》一书中。朱英诞从1928年开始新诗创作,直至1983年,不间断地坚持诗歌创作50余年,给我们留下了3100多首新诗,现代旧体诗1300余首,谈诗论诗的文字近百万。经过我们整理,编辑为《朱英诞集》(十卷本),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这一位因为与新旧时代不断错位的诗人,以大时代的小人物的生存方式,在北京深巷里默默耕耘,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中国诗歌的富矿。
进入新时期以来,朱英诞的诗歌开始受到关注。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把朱英诞纳入北方沦陷区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校园诗人群。评价“朱英诞更是陶潜风范的渴慕者,在‘人淡如菊’的闲适的日常生活背后体味自然人性的真意”,朱英诞首次正式被记载入新诗史。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沦陷区,当时活跃着一批校园诗人。他们以燕京大学的《燕园集》《燕京文学》《篱树》,北大文学院的《文艺杂志》《北大文学》《文学集刊》,辅仁大学的《辅仁文苑》等校园刊物为主要阵地,坚守精神家园,并进行严肃的诗歌艺术试验,涌现出了以吴兴华、黄雨、沈宝基、查显琳、张秀亚、刘荣恩、孙羽等为代表的一批年轻诗人。南星、朱英诞、沈启无等成名诗人也在这些杂志上发表了大量诗作。这一批诗人一方面醉心于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的诗学,另一方面又受到以废名、林庚、卞之琳等京派文人古典主义趣味的影响 ,在古今互涉的诗歌精神与艺术取向上,探索着中国新诗的现代路径。可以说,朱英诞就是这一京派诗人群体中最为活跃、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1998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诗歌卷》(吴晓东选编),收录朱英诞诗歌16首。2010年,由谢冕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收录了朱英诞新诗25首,在所收入新诗人中,收录诗歌的数量列第3位(列艾青、闻一多之后)。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朱英诞诗歌开始受到学界、出版界逐步关注,陆续开始有少量研究朱英诞诗歌、介绍朱英诞生平与创作的文章发表。因为朱英诞作品公开发表不多,要较系统全面研究朱英诞诗歌的条件尚不成熟。
2011年10月,朱英诞长女朱纹经过北京学界朋友介绍,与我取得联系,我们正式开始了朱英诞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其中北京大学陈均先生也加盟我们的团队,同时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孙玉石先生、洪子诚先生的大力支持(三位先生担任顾问)。2011年秋天,程继龙来到桂子山随我读博士,幸逢其时,自然加入到了朱英诞诗歌资料的收集整理队伍,这样他有了接触第一手研究资料的条件。记得我们研究生初次看到朱英诞大量手稿的欣喜与激动,朱英诞的手稿大多用毛笔小楷竖排撰写(后期部分钢笔书写),字迹清秀俊逸,流畅工整,修改处也笔墨干净,细致用心,只是基本用繁体字,学生们经过了一段辨识与熟悉的阶段。当时给学生们分工时,把文献中最难整理的学术卷,现代诗歌卷中的660多行的长诗《远水》分给了程继龙,其中大量名词、典故需要注释,程继龙知难而进,凭着西北汉子的一股韧劲、斗志,最后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
程继龙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研究朱英诞新诗。程继龙喜爱新诗,大学期间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受老师沈奇诗人影响,关注新诗、创作新诗(被《诗刊》评为2022年年度青年诗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可以说是与诗人朱英诞的一次相遇,对被遗忘的朱英诞的一次重访与再发现。他的论文首次建构了一个朱英诞诗歌研究的系统框架。论文从诗学观念、主题、艺术性以及与中西诗歌的关系四方面研究朱英诞新诗,对朱英诞新诗作了第一次较全面的寻访、考察与阐释。
论文开篇对朱英诞诗学本质观念的提取与阐释,紧紧拧住了朱英诞诗歌的精髓。什么是新诗,新诗别于旧诗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为朱英诞理论思考的一个出发点。诗人意识到,新诗成立的根本條件在新诗自身,他在诗学本质层面上设想了新诗的内在规定性,新诗的体验与表达是新诗得以实现的具体途径。程继龙认为,朱英诞注重“诗性体验”的心理认知过程,开发感官、重视知性,以综合的认知能力把握自我和世界。朱英诞意识到表达之于诗歌的重要性,认为新诗人应该以散文写诗,写出完全的自由诗,争取经验与表达的双向自由与丰美。调整新诗形态使之趋于形与质的自由辩证状态以便与多重文化因素发生密切关联,这是胡适、周作人、废名等人思考新诗的共同核心问题,朱英诞继续而且深化了他们的思考。
中国新诗经过了上世纪20年代草创期的探索后,新诗仍在西化的道路上摸索,自身的新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朱英诞对新诗有着高度自觉诗性意识,他不满意上世纪20年代盛行诗坛的新月派将新诗带到新的格律胡同,朱英诞认为新月派借来的西方形式,限制了新诗的自由,新月派的格律主张与音乐性形式还是旧外套。他倡导的是新诗的自然法则与自由的生命。新诗的问题主要不在用什么手段写而首先在写的是什么东西,他认定“今日的新诗之大势是自由诗”,“感情的形式是固定而有限的,而感觉的形式是自然的无穷的,从这无穷中得其崇高的一致,诗的无形正是其形式,自由中乃有严正的法则”,朱英诞反对新月派模仿海外旧诗所倡导的一套格律体制。他也并不是主张新诗完全抛弃音乐,是应该给“内在的耳朵听”,朱英诞所谓的“内在耳朵”说,显然反对的是诗歌外在音乐性,特别是对西方传统诗歌(英语近体诗)的借鉴或模仿,白话新诗可以不要音乐性,如果需要,它应该是内在的音乐,存在于诗歌的情绪变化上,存在于诗歌散文的语言节奏中。在他看来,诗歌没有唱的可能,这不要紧,重要的是“要看诗的本质之有无”。
主题构成诗歌的意义世界。日常、田园和梦幻基本撑起了朱英诞新诗的意义世界。论文也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进入了朱英诞诗歌的精神世界。“日常生活”代表了人置身其中的存在场所,在诗性意识的启示下,朱英诞认识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试图建构出日常与诗歌相依、相生的状态,发现日常生活的诗性意味。“田园”既代表了一种行将逝去的农耕生活,又代表了有着浓郁怀旧气息的精神原乡,朱英诞通过精细的抒写,建构出多层次的田园世界,扩大了传统田园诗的内涵与外延,呼应了现代文学在多变的现代世界追寻灵魂归宿的普遍潮流。“梦幻”则代表了更为深层的、隐秘的精神世界的图景,恋母、思乡和海天之思成为朱英诞书写梦幻世界的基本内容,对英年早逝的母亲的回忆使诗人朱英诞在亲情中获得一种略带宗教感的慰藉,对早年在津沽闹市、北平郊区生活追念和想象使他借助童年片段描繪出一种与此在不同的美好生活,对海天境界的玄想式沉迷又为诗人开放了一片陌生而遥远的异域风景。以上述三者为主骨,朱英诞建构了迷人梦幻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诗意的,唯美而忧伤的,而且高度个人化,与时代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程继龙对朱英诞诗歌主题的归纳与分析,深入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也体现了他感性体验与学理性分析的智慧与能力。
意象、语言和结构是构成诗歌本体的基本要素,程继龙的论文从三个方面深入朱英诞诗歌的艺术殿堂。朱英诞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意象,包括日常生活、自然风景和心灵梦幻等。他认为,在意象的创造上,朱英诞注重与旧诗意象互文,同时融入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使他的意象群带有象征色彩和晚唐风味。在意象运用上,注重意象间的呼应和关联,注重感官印象和知性思考的作用,区别于旧诗意象,具有强烈的现代感。朱英诞通过建构内视点的语言、意象化的语言和张力化的句法来实现理想的“诗的文字”,他的诗歌语言质地既感性又知性,句法错落灵活,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他的新诗结构有小诗、廊庑式和云烟式几种,他的结构艺术将自由诗性最大限度地带入了新诗内部,也在较深的层面上克服了早期新诗浅白散漫的不足。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在意象的探讨中更多创建,结构分析稍显不够深入。
朱英诞立志“做一个最后的古今中外派”。论文在古今中外互涉的关系中,阐释了朱英诞与中西诗歌深厚的渊源。朱英诞领悟了法国象征主义心物感应的精义,掌握了象征主义暗示的传达方式,获得了重新感知世界的方法。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是影响朱英诞诗艺发展的一个重要谱系,艾略特的诗学、诗艺吸引了朱英诞。他帮助朱英诞突破了象征主义“纯诗”抽象、封闭的窘境,培养出感情、知性和感觉协同运作的感受力,使他获得了更强劲的诗性思维与表现能力,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现代主义诗人的写作,形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是另一脉资源,唐宋诗歌的代表李贺、杨万里对朱英诞影响至深。李贺的“苦吟”激发朱英诞在体验方式上向内转,杨万里以“理趣”为内核的“幽默”诗风帮助朱英诞调整了写作理路,诗风倾向于深细平易。外来资源必须消化吸收进而融入新诗的血脉中去才能奏效,而且一定要打破千百年来格式、套语的影响,义无反顾地走向深处,走向无所依傍、独立不惧,自由成为新诗的命脉之一。程继龙认为,朱英诞在废名、林庚这些人的新诗中看到了理想的新诗形态希望,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唐诗宋词的私淑者,他们对庾信、李贺、温李的兴趣不亚于对新诗,是那么旧又那么新,排除一切因袭的陈腐,义无反顾地向内挖掘生命、雕刻灵魂,捕捉最真实自由的诗的内质,同时带动表达的变革,塑造出经验想象与抒写表达相互激发扶持的全新形态,使诗最终成为一种璀璨的珠玉、重拙的器具那样的存在物。诗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超越古今。自由诗的使命、魅力之一便是奔跃到更为恒久的艺术境界里去。朱英诞诗艺的形成和变化离不开与中西诗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为自己的写作提供了资源,丰富了新诗的形态,而且滋生出一种“大诗”观念,超越了五四以来新旧对立思维,打通了中西诗歌互联互通的一条路径。对朱英诞大诗观念的领悟,更加深入了对朱英诞诗歌内在精神与外部艺术形式的理解,也为我们较准确地揭示了朱英诞诗歌的艺术经验。
读程继龙的论文,常常有行游在诗歌现场与艺术风景中的美感。他的文字在学理的思辨中,追求诗性的灵动,在事项的呈现与文本的解析中,时刻保持与对象对话的姿态,主体意识活跃,勇于自我表达,敏于判断,观点鲜明;行文洒脱,不落俗套,给人以愉悦的美感。
他在阐释朱英诞有意识地区分感觉、感情的性质时指出:
感觉具有流动的源发性,感情却是类的存在。感觉原始而生动地流动在感官所及的事物之上,自由地摄取光影声色,优美的意绪、宏大的境界皆可成为诗的材料;而人类的感情,无论怎样细分,不外乎喜怒哀乐、忧伤爱恨几种,诗缘情自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诗人如若执着于这么几个大而含混的类,则显然只能局限于古典的人文世界,难以迈入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难以触摸现代人内心的复杂意绪,不能刻画现代世界在现代诗人精神中的投影,绝无可能达到“灵魂的真”,因为诗在现代本是一种“灵魂的冒险”。……在朱英诞看来,诗歌正如其他艰苦而精密的精神劳作一样,诗歌要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生存术”,只有在感觉的层次上作业,诗歌才可以具备这一性能。感觉是无穷的,感情则是有限的。由于感觉建立在人的感官的物质性和精神的能动性上,所以它有能力和世界、和存在物建立一种扎实而广大的血肉关联,所以它可以自由衍生、自由拓展,古今中外、远大细微,任何事物只要进入感官的世界,皆可成为感觉之物,最后进入诗歌。相反,感情因其类的性质,则受到的限制要严格得多,感情也需要感觉的作用,才能激活,需要诗人运用其斧向顽石般的感情下手。感觉是感情之母,由于感觉具有源发性、流动性等优长,感觉之于诗的价值,自然在感情至上,完全可以想象,感情就像渊深浩渺的大海,而感觉则犹如大海之上的波浪,在现代诗中,感情只有取得感觉这个汪洋恣肆、逸态横生的肉身、根基,才能立足,才能成长健壮后再回返传统本身。
对研究对象的关键性概念、范畴的阐释能力,体现在对其内涵的精准开掘、外延的合理扩展,形成自己的判断,转换为学理性的表述,这是一种思维的能力,表达的智慧,程继龙的论文较好地体现了这样的一种能力与智慧。
对诗歌的研究还需要有对文本敏锐的感受与灵动的解析,不能紧紧停留在阅读的感受上,需要与学理的分析与综合的概括结合,形成独到的创新性判断或结论,程继龙的论文体现了他在诗歌研究方面的这种规范性、学术性追求。他分析朱英诞数十年保持充沛的诗情,默默写下数以千计的诗作,一个秘密即在于,他保持了主体澄明的醒觉状态:
虽然我们不能亲见朱英诞怎样修身养性,但是从他的诗中,可以想见,他是怎样像一个禅师那样时时拂拭着心的明镜,使其免遭尘俗的污染。
一颗石头投入水中
像一句誓言
涟漪展示我以无极
海上的鸟儿还在飞复着吗
无边的风,花木不动
无边的安详,那甜蜜的
人声也隐隐的直到不复看见
静意如一片阴凉
(《习静》)
由静入动的过程就像在一石击破水中天的瞬间所见到的种种幻象,此时、彼时,此地、彼地,纷繁摇曳而又秩序井然。如果没有澄明而醒着的主体状态,可以入于如此精微的境界吗?写诗犹如一种没有尽头的修为,在朱英诞这里尤其如此。主体的澄明照亮了自我,也照亮了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连污秽之物也具有了诗性的光芒。
程继龙毕业后,到岭南师范学院工作,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之余,较多关注当代诗歌现场,常有新诗评论文章见刊,他喜爱的新诗创作也没有间断过,对朱英诞诗歌研究的继续扩展与深耕没有进一步展开。我希望他今后能在朱英诞诗歌园地里做一些继续耕耘,收获一批新的成果。《朱英诞集》已经出版,为朱英诞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资源。希望程继龙的《朱英诞新诗研究》有机会再版时,能做新的校正、补充、完善。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