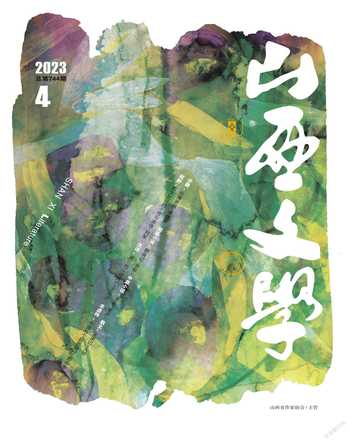保卫记忆
2023-04-24李路平
李路平
前日傍晚收到消息,华南地区将迎来今年最强一轮降雨,时至今日,窗外浓云变幻,仍未出现电闪雷鸣,而我还在急风浓雨的期许中,不曾遣怀。
我总是容易被某种意象或情绪萦绕,时常难以消散,比如鹰,它离开我的生活将近二十年了。当它忽然出现时,记忆里很多东西就被搅起来,有的没的,在脑海中隐现,直到让我似乎了然什么。
很难说清楚那只鹰是怎样出现的,是以它的声音,还是惊怯翻飞的身影,站在离地百米的阳台上,它就那样重新进入我的生活。那并非我家,而是出于某件极偶然的事,让我在那里与鹰相遇。那是一件极具悲情之事,我此刻想起时,内心仍满怀歉意。倘若是那些平常时间——也确实曾经历过那些时刻——我应该不会对那里的一草一物有如此深刻的感觉,是那悲情笼罩的氛围,让我身体里长久关闭的部分打开了,是后知后觉,哪怕过去那么久了,让我还是可以写下来。
鹰和那个地方所有的东西,成为这个全然不同故事里的原型,仅仅是最表面的背景。我在文字里试图理清的,仍旧是死的教义。几年前我曾不由自主地写下一篇短文,试图让自己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写到“死”,在那个短文之前,我写下了《喑哑者》《复活的祖母》和“活着”系列等散文,逐渐把心底里那些难以忘怀的东西缓慢吐露,当然,都是关于死亡的往事。我曾无数次想过要成为一个轻快无负担的人,这些记忆定然是我很想忘记的,可现实就像科马克·麦卡锡在《远路》中借小说人物之口所说的一样:
“人不会忘记吗?
“会,人会忘了他想留住的,留住他想忘记的。”
母亲曾说我小時候是个酒鬼,家里每年年末酿的甜米酒,都留不到除夕夜,因为早就被我喝光了,喝醉的我就像一个真正的酒鬼,躺在床上打呼噜,总也叫不醒。我的记忆里这段时光却全然空白,酒的印象是从大学开始的。
如果记忆可以选择,我想我很愿意记住那些醉生梦死的日子,一个小酒鬼无忧无虑的往日。如今的记忆显得太过沉重,我就像把重担从肩头卸下来,把文字当作承载一切的坚实地面,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卸下的担子不会一劳永逸,仍旧会被重新挎上肩头,文字也是这样,写下的只是其中一面,还有无数个面相不知何时又会在脑海里浮现。《比鹰更高》是我首次试图通过虚构的方式,从另一条路向这个主题接近,我写出的虚构作品里,零星会触及“死亡”,但并未成为整个作品的主题。在这个小说中如此密集地剖露那些不忍提及的伤痛,我也无法知晓它究竟是对记忆的释怀,还是背叛。无疑这些事件的呈现,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写作的逻辑,也流露了我的一些心思。它读起来或许更像一篇散文,我只能告诉你,并非如此,它虚构的部分比真实的更多。
但仍然应该感谢那只鹰,当我略带惊恐,给房间做完清洁,在寂静的午后,忽然就出现在我眼前。我不像小时候那样,仰着脖子看它在高处滑翔,而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俯视它略带褐黄的背脊和警觉的利眼。一瞬间的新奇之后,更多的悲悯充斥了我的心。在那一刻,我一定感受到了比我以为的更多,它如闪电般贯穿了我的一生,照亮了许多蒙尘往事,让我知晓我并未忘记。我想读到它的人无不如此,可能在某一刻被击溃,但仍有足够的时间重燃激情。
近些日子,读诗人保罗·策兰的传记,作为“一个困在历史中的人,既困于纳粹的残暴历史,又困于战后意欲‘清结这一段历史的历史”,他不仅被记忆折磨,也被现实围困。我的记忆与现实无法与他相提并论,这些留下的“想忘记的”部分,是否在以另一种方式向我暗示,这些才应当铭记于心,回想起它们,或许会愧疚和痛不欲生,但只有记忆,才让人生如此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