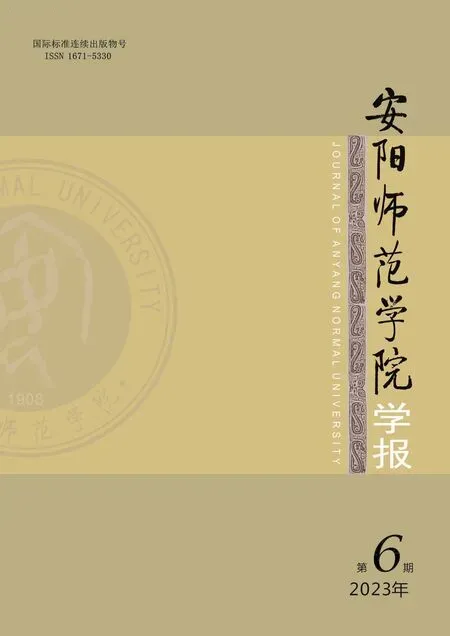回望传统,生态批评的现实转化
2023-04-22刘军
刘 军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改革开放以来中原文科知名学者版图中,鲁枢元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源于其跨学科研究的特色,源于其一直所高扬的人的精神主体性,源于其理论研究的底子以及对新生思潮、观念的高度敏感和迅捷反应,使得其学术研究趋于一棵枝叶众多绿茵匝地的大树之形状。从人生足迹来看,鲁枢元20世纪80年任教于郑州大学,20世纪90年代南迁至海南大学任教,新世纪初调任苏州大学,荣休之后返回河南,于黄河科技学院牵头成立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于河南大学牵头成立生态文化研究所。从学术履历来看,多级跳的经历使得他的思维和学术眼光一直处于一种动量装置中,如此能够准确捕捉学术的前沿问题,也使得其在子学科建设上成绩卓然,比如,在文艺心理学领域,他是开拓者,在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上,他是奠基人。丰富的学术思考和介入社会的人文情怀,奠定了他在人文学界的活跃度,40年来,鲁枢元在人文学术界的一直在场一直发声,展现出中原文脉与学统持续生长的一面。
一、从跨学科研究到生态文艺学的转向
在许多次的讲座、会议现场,鲁枢元皆自谦地将自己比拟为学术界的游击部队,而非正规军。这里所谓“打游击”的说辞照应了其学术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特色以及不断跃迁的学术历程。就学术研究而言,深挖一口井和多点开花只不过是不同的选择而已。回顾鲁枢元的学术历程,跨学科研究似乎是他一直以来的学术追求,无论是过去的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还是如今的生态学领域,鲁枢元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并贡献了应该有的成就。鲁枢元通过“跨界研究”,将文艺学与心理学、语言学及生态学结合起来加以考量,提出了一系列的学术命题,为文艺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话语空间。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批评界展露头角后不久,鲁枢元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文艺心理学学科的建构上,不仅参与编译了中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丛书,他个人也创作出两部文艺心理学相关专著,即《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阐释》。这一时期的鲁枢元被国内学术界公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学科的创建者和代表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日丹诺夫为代表的前苏联文论成为指导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和指导思想,在此模式的框定下,文艺创作理论中存在着过多的机械反映论,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则被打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基于当时思想解放的基本语境,鲁枢元试图打通文艺学和心理学间的阙域,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重新高扬人的精神主体性。就文艺心理学的学科特性,他曾指出:“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人的各方面生存状态为中心,将‘自然’和‘精神’作为重点,特别是人的精神方面,应以此作为学科建设和开展研究的基础。”[1]关于文学学科和心理学学科的交汇, 美国学者里恩·艾德尔曾表明:“文学与心理学这两门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都涉及到了人的意识和行为,以及人对知识、符号的创造和使用能力,因此,二者在关注人的主体性方面应当是一致的。”[2](P70)鲁枢元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握住了这种内在的关联,才如此重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的沟通。在他看来,文学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文学的创作就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而文学作品就成了“作家心灵、生命与实践联合运作的结晶。”[3](P310)在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比如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形态是什么?心理批评的理论资源有哪些?以及关于创作心理的探究。而在阐释这些命题时,鲁枢元又力图提炼出一个个相应的独立概念,如“情感记忆”“艺术感知”“心理定势”“创作心境”等,这些概念构筑了他在文艺心理学领域创建的理论谱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文学从社会话语的中心位置迅速后撤,文学的边缘化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界常言常新的话题。大众文化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知识阶层的精英意识,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知识分子由“建构者”的角色向着“阐释者”的角色加以转换。启蒙进程就此被迫中断,之后发端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持续了几年,最后无果而终。文学理论与批评受限于时代话语的转折,无论是话语形态、主体的嬗变还是传达方式,在深层结构上皆产生了变化。
1990年,鲁枢元新著《《超越语言——文学言语学刍议》出版,预示着其跨学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即从文艺心理学研究转向文学言语学研究。这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作家心中涌动的情感和意识是如何转化为语言并融入作品的。在作者看来,文学语言的转化过程,就是文学作品的创生过程,所以,对文学言语学的研究,当以“创作心理学”为依托。基于此,“心灵”“言语”“作品”,便成了鲁枢元展开文学言语学研究的关键词。众所周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延伸出两种路向:一种是科学主义,另一种则是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鲁枢元的文学言语学研究站在人本主义立场,对于以结构主义批评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范式展开了批评。他反对结构主义对文学言语的消解,认为结构主义批评过分主张逻辑论证的方式,过于追求理论的“科学性”,从而丧失了文艺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和有效性,譬如对于人的精神丰富性的关注和表现。同时,鲁枢元认为文学批评的使命不只是分析消解,它还应当促使整合与创见;语言研究的目的也不只是强调语言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并进行人际交往的工具与手段,还应认识到言语应该具有的更为丰富的关于“人性”的内涵。基于此,鲁枢元在对文学言语进行探索时,更倾向于南帆所说的“竭力地探索语言形式,其目的就是要更充分真实地展露主体的内心世界”[4],他认为语言寄寓了人的生命存在,更使得精神得以自由遨游。总之,在文学言语学的跨学科研究框架下,鲁枢元以文学精神的丰富性为基点,对文学语言研究领域中看重科学手段却忽视精神内涵的研究状况表示质疑,进而提炼出文学言语的“个体性”“心灵性”“创生性”“流动性”等一系列特征。
这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推动了国内创作界、评论界对文学言语学研究的关注。
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愈演愈烈并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世界范围内,环境伦理学和生态美学的萌生推动着人文社科领域内的生态学转向,其中的部分成果在这一时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此外,徐刚、李存葆等作家也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生态主题的报告文学、生态散文作品。在此背景下,2000年,鲁枢元《生态文艺学》出版,结合2006年出版的《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预示着在21世纪初期,鲁枢元完成了学术研究的再次转向,即转向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及生态批评的领域中来。其实,在调任海南大学不久,鲁枢元就萌生了对人之精神生态的关注。回望其生态研究与批评的历程,他不是简单地将生态与环境划上等号,而是将“生态”作为一个总的问题加以对待。如其所言,“拯救地球和拯救人心就是这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5]。“人心”作为一个精神因素,在生态领域一直被忽视,然而事实上,全球性生态危机加剧的一个契机就在于人类精神危机的出现。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然与人的分离愈发显明,高蹈的启蒙理性不断强化了人们的工具理性思维,使得技术崇拜、经济至上等狭隘功利的价值取向演变为社会的主流,并随着全球化波及至全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不断强化的技术理性,善于领悟玄思的感性逐渐衰落,人类的精神空间也越来越狭仄,精神世界日益枯竭,从而造成了人类自身的精神危机。基于此,鲁枢元认识到,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科技发展”或“行政管理”的问题, 更是涉及人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观念,以及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故而,治理生态危机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控制或科学措施的管理,更要引入“人心”这一精神因素,同时也离不开能够丰富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学艺术活动。他的这一理念,也为后期生态批评的具体实践埋下伏笔。
除了在理论话语中表达其对生态问题的忧思之外,鲁枢元还做出了诸多具有实践性、可行性的现实动作。比如,他撰写生态文论,如《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等著作;创作生态随笔,如《精神守望》《心中的旷野》等图书;编辑生态刊物,如《精神生态通讯》等。他还组织生态考察,并转化为《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这样的结集成果;还多次举办各种生态会议等等。他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倡导文艺界的众多学者走上这条生态拯救之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相比于同时期的许多生态文化研究者、生态批评学家,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研究不局限于讲台或书斋, 而是将“走出去思考”当作宗旨, 所以他经常走进田野,爬上高山,去感受大自然的神圣、神秘和诗意,因此其生态思考更具知行合一的特色。
总结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研究上的贡献,除了首先创设“精神生态”概念之外,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他还首先提出了生态学三分法的理论模型。所谓生态学三分法即精神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所构成的系统论思维模型。其中精神生态指人类的价值观、信仰和心理状态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意思为人类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上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生态指人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意味着人类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自然生态指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生态环境,意为人类在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方面的可持续发展。梳理鲁枢元生态文艺观的构成,其主体内容和生态学三分法息息相关,其中包括:从“祛魅”到“复魅”的自然观,以重振文学艺术中的“自然之维”为指向;从“现代性”到“生态型”的社会观,以生态社会的路标确立为旨归;从“污染”到“解困”的精神观,以发起一场生态领域的“精神革命”为指向。
二、回归传统,确立人与观念的双重路标
如前所述,在鲁枢元生态文艺观的内容框架内,已经有了确立现代社会生态路标的理论倡导。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他相继出版了《陶渊明的幽灵》《天地之中说聊斋》这两本图书,可视为是对其理论倡导的实践落实,意欲发掘传统古典资源,在不同的路向上确立殊途同归的生态路标。
《陶渊明的幽灵》有两个版本,分别为2012年版和2021年版,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旧版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新版则加上了“悠悠柴桑云”这一副标题,这一小节的论述以新版为对象,借以探查鲁枢元在最近几年的生态思考和具体成果。新版共分五章,对应的标题分别为“伟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的自然人生”“陶渊明的海外盟友”“陶渊明成了时代亡魂”“陶渊明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尽管出于可读性的考虑,新版加入了更多的感性细节,不过,从章节的演进来看,做为一本理论著作,其内在的逻辑依然恪守了次第演进的严谨性。前两章重点钩沉的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即自然人生观的确立,如同胡适所指出:“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他一生只行得‘自然’两个字。”[6](P14)源于生态视角的进入,鲁枢元并没有将过多的笔墨集中于大诗人陶潜的诗意人生或者人生艺术化上面,也绕开了陶渊明诗歌艺术成就这一窠臼,而是集中于提炼陶渊明生活方式的生态意义上面,并推导出“低能耗高品质的生活”的命题。这一命题构成了这本理论著作最高的思考结晶,也是作者苦心孤诣为当代人开出的药方,它暗喻了“人皆成尧舜”的所指,它对应了现代人自觉地减少消费、降低欲望、提升内心生活的层次的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选择不需要匹配高端的物质条件,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容易做到,如同陶渊明的自白,“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而“低能耗高品质的生活”并非理论的空转,在当代史上,就曾诞生了苇岸这样的觉醒者,苇岸就曾宣称“为了这个星球的现在与未来自觉地尽可能减少消费!”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经过海德格尔的改造,建构起一种全新的大地美学,也形成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低能耗高品质的生活”与西方的“诗意地栖居”命题构成了遥相呼应的关系,彼此间也拥有了很大的契合度。
《陶渊明的幽灵》第三章引入了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作者借鉴了德里达“幽灵学”理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以及其他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成果,加以阐发陶渊明身上的美学符号意义。给出了“自然浪漫主义”方法路径,并在此路径上开掘如卢梭、梭罗、斯奈德等陶渊明的西方盟友。后两章既指出了陶渊明的寂寞身后事,意即其生态美学意义未得以充分开掘,又道及了陶渊明对当代人的生态启示。
总之,通过理论综合的方式,鲁枢元借助《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在生态路径上洞见了陶渊明诗文中的回归诗学和哲思中的自然哲学,并以“樊笼”“回归”“自然”为关键词,探求陶渊明可以带给身处生态困境的现代人的一些启示。如此一来,针对当代人普遍的焦虑感和不满足感,鲁枢元尝试着在宏观层面思索文化精神的指向性,并对现代生活方式进行整体性考虑,诊治其中得失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一路标是他在反思现代文明弊病的基础上,所开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药方。因以低消耗为基础,便在一定程度也烙上了当代世界生态转向的印记。鲁枢元借助学理化的思路和感性的表达,以中国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为范例,将其清贫自守的存在方式、闲逸散淡的田园情怀、东方乌托邦式的桃源生活,视作重振人与自然、与社会、与其自我的和谐关系的内容,视为缓解存在的无根性、生活方式的符号化、个人的工具化的典范。在现代化模式突飞猛进的今天,这种思想在一些激进主义者看来或许不合时宜,但事实上,这是鲁枢元在深刻反思了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文化、城市文化、审美取向等一系列问题后所发出的呼吁,以纠偏人们的生存理念,缓解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给社会带来的危机。
作为随笔体著作,鲁枢元的《天地之中说聊斋》以漫谈的方式聚焦于《聊斋志异》这一古典名著之上。同样是基于确立生态路标的考虑,但这一本书与《陶渊明的幽灵》却大有不同。首先,从结构和体例上看,前一本以学理性为基础,有着严谨的学术考辩和学术论证,内里包含诸多命题、理论阐释与生发、跨学科的综合运用,章节之间也追求逻辑自洽。而《天地之中说聊斋》一书从学术高阶落入到人间烟火之中,带入了作者个人很多人生经验的内容,这些荡漾的人生细节使得这本书的感性因素大于理性因素。在体例上,这本书由两个平行的部分构成,一部分解析蒲松龄的思想脉络和人文底色,另一部分则摘取《聊斋志异》的经典名篇,纳入生态视角加以细读,如此则形成了平行和并列的结构。其次,从言说方式上,《陶渊明的幽灵》隶属于学术表达体系,内中有着大量的论证、分析、说明式的话语,而《天地之中说聊斋》一书则选择了自由放达的文学表达方式,更注意口语化和可读性。最后,从生态路标的确立方向来说,《陶渊明的幽灵》以陶潜“低能耗高品味的生活”为路标,涉及到生活方式的借鉴性和实践的可能。而《天地之中说聊斋》所确立的生态路标集中于“万物平等,善待万物”的观念层面,将传统的民胞物与的观念拓展到生物圈,在生态纪的时代里,倡导万物与我等同的理念,倡导一种善意法则。
作为一名前现代作家,作为一名乡先生,蒲松龄钟情于“青林黑塞”的自在自为。他的写作在劝诫的主题之外,还渗透着对荒野生物的青睐和对女性的尊重。幻化不过是表象,自然属性的保存和人格化的投射方是重中之重。人格化承载着文化精神的延续,而自然属性的天性存留却在无形中契合了生态纪的诸种观念。鲁枢元的重新观照和梳理恰集中于自然属性存留背后的作家观念层面,在这本新著中,生态路径的进入主要集中于“山野”与“乡野”这两个关键词的提炼上。山野对应着自然属性与自然秩序的确立,总体而言,山野就是万物有成理而不言的状态,也表征出众多生灵自在自由的生命状态。其中,《万物有灵》一篇集中阐发了鲁枢元开掘出的山野理念,作者首先列出了《聊斋志异》书写到的众多植物和动物,在传统移情说的解读思路上,又发掘出蒲松龄身上“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倾向。并以具体作品为例,论及《聊斋志异》中内蕴的万物有灵及生物平等思想,并结合远古神话和古代哲学中首肯的人兽和谐共生关系,升格出“众生互缘而生,万物相依想存”的生命共同体观念。所谓乡野,主要指的是蒲松龄的乡先生身份和自我认同,他埋身乡野,以文化人的身份自觉托举起赓续道德礼法的使命,并执笔书写万物传奇,以推动乡野之人善待万物、敬畏天理。
回溯鲁枢元的学术历程,跨学科研究似乎是他一直以来的学术追求,无论是之前的心理学和言语学领域,还是近些年的生态研究,鲁枢元皆予以及时地关注,并展开系统性思考,且多有建树。纵观之后可以发现,其学术探索路径存在一个明晰的轨迹,那就是,从对文艺心理的研究,到对文学言语的探究,再到对生态文艺的深究,其间跨度看上去很大,实际上又有着内在逻辑的统一,既恪守文学是人学的理念,又追求学术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同时,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领域,还是在话语建构方面,鲁枢元都强调关注人的心灵,重视文艺的精神价值,并将精神的丰富性和有效性看作反抗物质性压迫和工具主义理性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