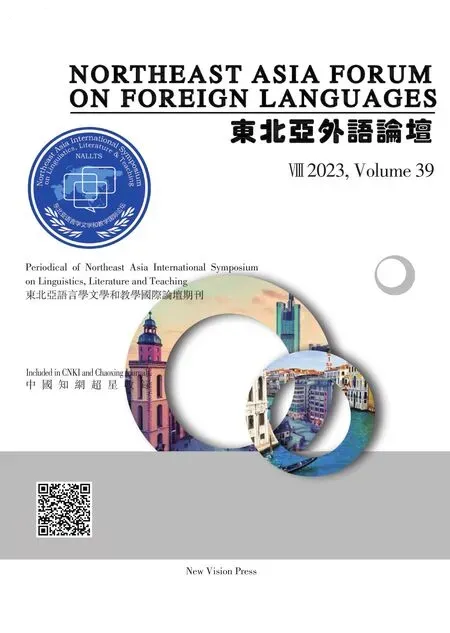伯纳丁·埃瓦雷斯托《金色的根》的倒错书写研究
2023-04-21穆苏林
穆苏林 王 卉
大连外国语大学 大 连 116044 中 国
伯纳丁·埃瓦雷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1959年出生在伦敦的伍尔维奇,母亲是英国人,有英国、爱尔兰、德国血统,父亲是尼日利亚人,有尼日利亚和巴西血统。作品是作者的诠释性假定的产物,而这些假定由她在历史中的位置铸定(Thomas,2013:186),多种族的身份促使埃瓦雷斯托的写作关注欧洲和加勒比等地区的文化和历史。“作为一名小说家和诗人,我着迷于研究人员挖掘出的历史,这些历史已经丢失、被遗忘或被故意忽略了,他们的缺失使世界伟大的白色大陆的黑人历史无效”(Evaristo,2008:3),因此她致力于“挖掘或重塑被边缘化的过去”(Gustar,2015:434)。2007年废除奴隶贸易200周年更加促进了黑人作家讲述祖先的故事。《金色的根》(BlondeRoots)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倒错书写,为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段历史提供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历史和种族的关系。
一、时空倒错
在《金色的根》中,埃瓦雷斯托通过倒错的写作手法瓦解了这段看似为史实的奴隶贸易历史,打破了黑人奴隶、白人奴隶主这一二元对立的范式,“颠覆了文明和野蛮的历史概念”(Evaristo,2021:55),在将时间和空间倒错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段全新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
《金色的根》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原名为多丽丝·斯卡格索普(Doris Scagglethorpe)的白人女性被奴役,最终获得自由的经历。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和虚拟的大西洋世界,为了让读者更加理解这一空间倒错,埃瓦雷斯托将其绘成地图,使其可视化。在地图上非洲(Aphrika)代替了位于北部的欧洲,地处赤道,西边是以安伯森联合王国(UK of Great Ambossa)命名的一个轮廓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相似的岛屿,被安伯森海峡(Ambossan Channel)(取代了英吉利海峡)分隔,朗多罗(Londolo)代替了伦敦,小说的叙事就是以女主人公多丽丝在伦敦做家庭奴隶开始的;欧洲(Europa)取代的是位于南部的非洲,潮湿阴冷,在它的西北南海岸有一个叫英格兰的地区,其中卷心菜海岸暗指非洲曾经的黄金海岸,多丽丝被贩卖之前就居住在卷心菜海岸;跨过大西洋的是美洲(Amarika)大陆、原为西印度群岛的西日本群岛(West Indian Islands)、新安伯森小岛(New Ambossa)和小伦敦(Little Londolo),这些地方遍布种植园,里边雇佣了许多从欧洲捕获的奴隶,多丽丝第一次逃跑就被送到了新安伯森的种植园。
小说的情节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理环境展开,在这幅新的奴隶贸易地图中,非洲人(Aphrikans)把白人(Whyte Europa)作为货物运往美洲,大西洋奴隶制的事实基础(欧洲人奴役和运送非洲人)被颠覆了。在这篇小说中,埃瓦雷斯托对国家边界的重新划分和对大陆的替换,不仅打乱了读者对空间和国家的假设,也表明了空间的难以捉摸,由此显示出“地图也可以被用来操纵和篡改以达成具体目的(王卉,2022:228)。”同时小说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所有事物都受制于解释,在特定的时间内,任何解释都是权力的功能,而非真理”(Evaristo,2008)作为题词,强调了在记录奴隶贸易的历史时,“传统上,白人的观点决定了什么是真理”(Muñoz-Valdivieso,2012:53)的事实,即白人有能力形成他们对真理的概念,有能力去构建历史,但这并不一定真实可靠,历史也可以如同埃瓦雷斯托这样以另一种方式构建。
在引发读者空间错乱的同时,埃瓦雷斯托也打破了时间框架。小说的定位并非局限于奴隶贸易时期,如同《皇帝的宝贝》将时代错乱,《金色的根》中穿插着中世纪的农奴制度和当代社会的人口贩卖,创造了一个历史和当代混合的平行宇宙,旨在让读者从过去了解现在,“通过现在构想过去”(Gustar,2015:437),也突出奴隶制度存在于任何时期这一主题。“天鹅绒绿色的连体大衣”“丝质过膝马裤”“带小高跟的过膝棕皮靴”(64)等都是中世纪高贵的欧洲“绅士”的打扮,符合中世纪的特点。地下铁路、咖啡店里的招牌产品卡布奇诺等都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同时埃瓦雷斯托将三角贸易的产品朗姆酒与“象征文化帝国主义的可乐”(Dagbovie-Mullins,2017:8)联系在一起,敦促读者将奴隶贸易与当代联系起来,这并非巧合。小说开篇回忆多丽丝被贩卖之前的农奴生活,她十岁前和父母以及三个姐妹生活在由珀西瓦尔·蒙塔古勋爵(Lord Perceval Montague)统治的英格兰北部的卷心菜海岸,“我们是农奴,处于农业食物链的最底层,尽管我们走动时没有真正的链条在地上叮当作响,但我们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壤里……一代又一代”(Evaristo,2008:8)。珀西地牢里的俘虏被打包发往新世界,也说明了农奴制时期就存在贩卖人口交易。埃瓦雷斯托以逃亡后的生活作为尾声,暗指当代甘蔗工人的隐喻性奴役:“二十一世纪,布瓦纳的后代仍然拥有甘蔗产业,他们是安伯森联合王国是最伟大、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甘蔗工人是有报酬的,其中许多是原来奴隶的后代”(269)。在小说中,大西洋奴隶制度和中世纪的农奴制、当代的人口贩卖都能找到共通点,“呈现出了历史事件的无限循环和相互重叠”(王卉,2022:229)。
小说通过时空倒错,揭示了奴隶制度存在于历史的每个阶段,分布于世界的每个角落,不论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都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被美化的奴隶制在今天仍然存在。
二、审美倒错
种族化等级制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将黑色视为令人鄙夷的特征,进而将其延展覆盖黑人的所有身份特征,包括肤色、发质、嘴唇厚度、眼睛颜色、鼻子形状等。“白人主导的文化将审美种族化,将美本身定义为白人的美,界定为白人更可能拥有的身体特征。”对非洲人来说,种族资本主义不断地将其社会化,使他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霸权地鼓励黑人“接受自己的丑陋,并据此采取行动”(Taylor,1999:17)。
“欧洲殖民者建立肤色等级制度的习惯迫使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处理种族问题,种族主义是一种种族间的等级制度,它传达了白人的种族优越性,而肤色歧视则是一种种族内部的等级制度,它传达了浅色的种族优越性”(Robinson,2011:362)。赫林(Herring)认为“肤色歧视”(colorism)是对同一“种族群体”中的个人基于肤色的歧视性待遇。种族内的肤色歧视发生在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他们根据自己种族的肤色进行区分。种族间的肤色歧视发生在一个种族群体的成员之间,他们根据另一个种族群体的肤色进行区分”(2004:3)。一直延续至今的以白为美,一白遮百丑的观念在埃瓦雷斯托的笔下彻底被推翻,多丽丝的室友西坦比勒(Sitembile)为了追求黑人眼里的美“把赭石抹在皮肤上”(16),使其色素变深,以便吸引到黑人男性的目光,摆脱奴隶生活;“日光浴在郊区也很流行”(30),白人女性为了迎合黑人眼中的美想法设法去改变自己的肤色。在肤色等级制度中,肤色越深,等级越低,作为拥有比白人更深肤色的混血儿可以享受比白人奴隶更好的待遇。在当代,人们对白人和肤色接近白色的人与黑人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态度,足以说明白人主导的审美,将肤色等级化,凸显了白人的高贵与黑人的低贱。这种审美是主观的,是由当权者控制与决定的,而当代审美仍受这一制度的束缚。
种族化的审美标准使头发与皮肤颜色一样成为黑人女性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罗宾逊指出,白人主导的文化将美种族化,因此反映欧洲血统的头发比反映非洲血统的头发更具有吸引力。种族等级制度推崇一种单一的审美标准,这种标准贬低并排斥非洲人的头发质地,迫使黑人女性适应欧洲中心的审美标准(2011:360)。泰勒也在文中提出了“直发规则”,指出拉直头发是黑人女性“最容易接近白人标准的方向”(1999:18)。在《金色的根》中,埃瓦雷斯托将审美倒错书写,将黑人的卷发定义为美的标准,那些芭比女性为了追求美,理发师“先剃掉她们本身的头发,然后接上浓密的假发,结果就是非常不自然的非洲发式。”(30)故事的主人公多丽丝作为家里地位最高的奴隶,主人强迫将她金黄色的长直发“用铁丝穿起来,编成辫子箍在头上”(19)虽然她知道白人没有足够的骨骼结构来完成,但她必须遵从黑人世界的审美标准。美与丑的标准是由当权者规定的,他们为了将自己的特质定义为美,贬低其他种族的外貌特征,将其定义为丑。当代我们仍然以西方白人的特质为标杆,想当然的质疑其他民族人民的长相,模仿西方白人的外貌特征。
“你也可以用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做一个鼻子整形手术,尽管我一直认为白人脸上长一个扁平而肥大的鼻孔看起来非常可笑。一想到槌子砸在我的鼻子上,我就害怕的说不出话来”(30),埃瓦雷斯托运用幽默的手法批判了种族化下审美的扭曲,“奴隶制度时期的黑人女性被种族化的偏狭审美而异化和物化”,(王卉,2022:201)黑人女性深受其奴役与残害。在欧洲,拥有突出的锁骨、波纹状的胸骨、凹陷的腹部和稀疏的金发的四号身材被认为是美的化身,而在安伯森人眼里这样的身材“丑得像个罪人”(31),“被贴上了性无能的标签”(32)。在衣着打扮方面,黑人也将白人的衣服帽子鞋都视为野蛮人的物品,污秽的东西。
埃瓦雷斯托用倒错的手法控诉了当今仍然存在的种族化审美,展现了历史的不可靠性与主观性,体现了美与丑的标准是人为定义的,是可以被权力控制和改变的。历史是由当权者书写的,审美也是由当权者控制和决定的,我们现代社会评判美与丑的标准仍然是由资本主义控制的,但我们麻木地接受这一压迫,认为这就是真理。
三、地位倒错
在一次访谈中埃瓦雷斯托表示“在英国,人不能超越种族。如果你是黑人作家,你就被认为是在写黑人题材,而且一般被认为是为黑人读者写的”(Niven,2001:18)。这一表述透露出在当代种族歧视仍然存在,地位不平等仍然是一大问题。
法国人种学家约瑟夫·阿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在《人种不平等论》(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the Races)中肯定了被广泛接受的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种族划分,并引入了文明本身就是基于种族的观点,白种人是唯一有创造性思维和文明建设能力的种族。2005年,英国人类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通过科学归纳法得出“黑人在能力和智商方面至少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低两个等级”的结论(Jackson,2005:67)。奴隶制下,黑人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民族,逐渐被物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而这种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在《金色的根》中,埃瓦雷斯托将黑人和白人的地位发生转换,黑人化身为“正义的”奴隶主,白人成为“面目可憎的”奴隶,咖啡店“新鲜奴隶”的招牌也反映了关系的透明化。
法国作家瓦切尔·德·拉普热(Vacher de Lapouge)指出种族标志的关键是头颅指数,不仅将该指数与头型联系起来,而且与一系列社会理想特征联系起来。认为长头、金发、蓝眼的双头型雅利安人(dolichocephalic Aryans)有创造力、强壮,是天生的领导者。相比之下,圆头,皮肤黝黑的短头颅型的(brachycephalic)人胆小、没有创造和领导的必要想象力,是天生的追随者(Jackson,2005:71)。在《金色的根》的第二册奴隶主卡加·科纳塔·卡坦巴(Kaga Konata Katamba)向读者展示了精确的颅骨人类学科学,并将其划分为三类:
第1号——黑人,是非洲大陆的土著。
第2号——蒙古人,是亚洲地区的土著。
第3号——高加索人,是被称为“欧洲”地狱之地的土著。
黑人的头部有一个宽大、突出的前额,其背部宽敞而圆润,而且有一个所谓前突的下巴。几千年来,黑人宽大的头骨已经能够在其结构中容纳一个非常大的大脑。这使得高度复杂的智力得以进化。
……
颅骨人体测量学证明,黑人在生物学上优于其他两种类型。事实上,虽然黑人属于被称为人类的属种,但蒙古人和高加索人属于更广泛的人类定义,其范围从完全进化的物种人类到被归类为新灵长类的得到较少进化的物种(124-126)。
埃瓦雷斯托通过将科学倒错的方式来达到种族地位的倒错,从而推翻在当代仍然盛行的欧洲国家控制下的“科学”,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科学,也说明了科学并不科学,解释权归强权国家所有。
在语言方面,语言专家也尚未证实欧罗巴人是否拥有自己的语言。将Doris改名为omorenomwara(因为Doris在非洲语言体系中是不发音的)也暗指了白人是发不出声音的,是没有话语权的,由此构建了一段高加索人低等,黑人高等的历史。正是由于这种“黑人至上主义”的思想,他们理所应当的认为“欧洲的奴隶被从最可怕的死亡、惩罚、道德上应受谴责的放纵和农奴制中拯救出来,同时有机会接受文明人的礼仪和习俗”是一种“仁慈的行为”。黑人对白人的非人待遇也揭示了奴隶制度的残酷,在运输奴隶中,为了利益最大化,选择运送更多的货物,给奴隶提供更少的空间,造成更多的死亡人数,登船时的四百名奴隶,仅有二百二十七人幸存了下来。在挑选奴隶时,更是不顾及人的尊严,“用散发着烟草臭味的手指侵入我的嘴里”(95),“把他那些肉乎乎的手指伸进我的处女膜”(96),体现了奴隶制中白人,尤其是白人女性遭受的非人待遇。
通过种族地位的倒错书写,埃瓦雷斯托运用幽默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也构建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凸显了历史的主观性与建构性。同时也揭示了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西方的强权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侵占了人们的固有认知,默认白人高人一等,黑人低人一头的现状,而这一种族地位是由权力决定的,是当权者所建构的。
埃瓦雷斯托的文学作品大多与历史密切相关,《金色的根》作为新奴隶叙事,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带到了英国公众代表面前,揭开了一段英国政府不愿承认的历史。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用倒错的手法建构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解构了现存的奴隶制历史。通过时空倒错、审美倒错和地位倒错有意将历史语境打乱,展现了权力是解释、把控世界的根本,以及历史叙事的不可靠性。同时她的小说善于打破线性时间,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带我们回到历史的同时,仍立足当下,让我们通过过去了解现在,通过现在分析过去,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奴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