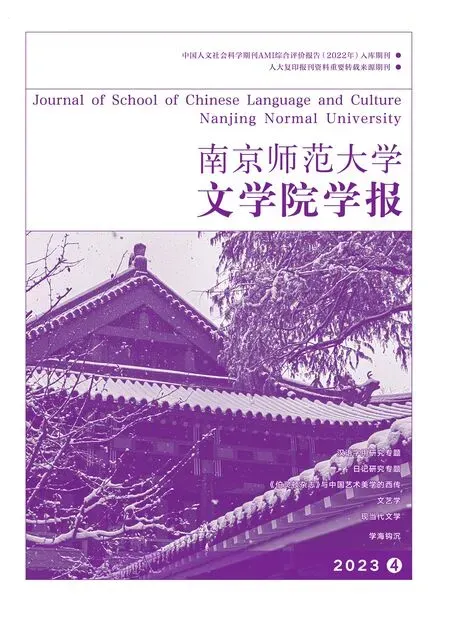1935年“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与中国书画美学的西传
—— 以蒋彝为中心
2023-04-20马菁茹
马菁茹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1935年11月至次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伯灵顿大厦(Burlington House)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展览会历时104天,约42万人前去参观,掀起自18世纪东学西渐以来的第二次“中国热”。同期,英国皇家艺术学会开设了24场关于中国艺术的系列讲座,《伯灵顿杂志》(TheBurlingtonMagazineforConnoisseurs)作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研究刊物,在此期间发表了近30篇与中国艺术相关的研究和书评,介绍并说明中国多个门类艺术的发展史和鉴赏方法。其中,中国书画这一艺术门类的讲解人和主要传播者是华裔画家、诗人蒋彝(ChiangYee)。蒋彝最负盛名的书画研究专著《中国之眼:中国绘画的阐释》(TheChineseEye:AnInterpretationofChinesePainting)是为迎接1935年的中国艺术展览而写就,另一部《中国书法》(ChineseCalligraphy)则是将展览期间在伦敦大学的讲课记录重编修订出版。1935年的展览是一关键契机,两部著作乘着展览期间“中国热”的东风一举成名,同时,蒋彝也透过中国书画的窗口将中国美学的基本原则和文化根基传播出去。然而,目前学界对蒋彝在展览会中发挥的作用多有忽视,基于此,本文以蒋彝为中心,试勾勒其在“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中的位置、为传播中国书画美学做出的贡献并探究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持的文明立场。
一、蒋彝与1935年“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
19世纪末期,以英国、法国、德国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不仅借“考古”之名来华勘探,挖掘中国的古物遗迹,更在侵略战争中掠夺大量的华夏珍宝,纷繁涌现的古迹和流散海外的珍宝引起了西方考古学家、艺术家和汉学家等对中国艺术的强烈兴趣,随后激起了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艺术的探究热潮。例如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雷伊·阿什顿(Leigh Ashton)和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等汉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器物等多门类艺术加以鉴赏研究。在此背景下,1934年,由知名的中国陶瓷收藏家珀西瓦尔·大维德(Percival David)牵头,在大英博物馆陶瓷和人种学系的霍布森(R.L.Hobson)和东方陶瓷学会的创始人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等汉学爱好者的支持下,英国政府通过驻英大使郭泰祺向中国申请名物出借,同时向全球范围内的收藏家募集中国艺术品,为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际性中国艺术展览。中华民国政府以“使西方人士得见中国艺术之伟美”(1)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全四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 第iii页。为目的决定选品参展,展览的筹备理事会于同年11月正式确立。
由于世纪初的侵华历史已令国人深恶痛绝,1935年又恰逢英皇乔治五世在位25周年,国内对此次文物出海的性质十分怀疑,一时间舆论四起。几番商榷后,中英双方敲定如下原则:其一,选品由中方主导,复与英方专家交换意见,且孤品不外借;其二,文物的护送须有英国军舰全权负责安全;其三,送伦敦展前须在上海预展,伦敦展后再回南京办复展,前后清点,以昭信守。随后,中国选送近一千件艺术珍品漂洋过海,另有世界各地出借的中国艺术品三千余件(2)洪振强. 1935-1936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论述.[J]. 近代史学刊, 2019(1)。,共同打造了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吸引全球各国人士赴伦敦一饱眼福。
这场国际盛宴启幕的前两年,时任江西九江县县长的蒋彝因阻止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行贿购置九江地产而被强加“买卖国土”之污名,与当局政府产生冲突,于是被迫辞去县长职务(3)任一鸣.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蒋彝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第12页。,在哥哥蒋笈的帮助下远赴英国留学。初到伦敦的蒋彝只会5个英文单词,和他自取的笔名“哑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一样,在完全陌生的异质文化中是个“失语者”。而大概三十年后,蒋彝已被收入20世纪50年代编纂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美国版《世界名人传》(4)任一鸣.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蒋彝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第102页。,作为著名的中国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在海外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林语堂。从背井离乡的“县长”到享誉盛名的“艺术家”,蒋彝的成名是时运人际等多方因素促成的。
首先,社会交往为蒋彝在海外影响力的扩大奠定了基础。蒋彝1933年抵达伦敦后结识了两位对其影响极深的关键人物,第一位是租房期间结识了自己的同乡、戏剧家熊式一。基于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对中国文化的好奇,熊式一改编的通俗剧《王宝钏》在伦敦的展演座无虚席,在文化圈享有极好的声誉,这一“华人成功”的案例令蒋彝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1935年英国诸多出版公司想借助国际中国艺术展的声势促销同类书籍,经熊式一引荐,蒋彝结识了伦敦麦勋出版公司(Methuen &Company)的编辑艾伦·怀特(Allen White),此人负责了蒋彝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中国之眼:中国绘画的阐释》(后文统一简称《中国之眼》)的出版与发行,是蒋彝名声大噪的重要中介。第二位是汉学家詹姆斯·斯图尔特·洛克哈特(James Stewart Lockhart),他为蒋彝争取了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汉语的教职,并间接导致他结识了远东语言文化系的汉学家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和他的天才学生英妮斯·杰克逊(Innes Jackson)(5)英妮斯·杰克逊(Innes Jackson)中文名为“贾静如”,此名为蒋彝所起。二人是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初级古代汉语”班上结识,英妮斯帮助润色修改了蒋彝包括《中国之眼》在内的多部作品,二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蒋彝写作《中国书法》时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英妮斯。,后者帮助蒋彝完成了《中国之眼》英文版的翻译和润色。值得一提的是,在伦敦大学教书的经历为蒋彝拓展了英国汉学圈的交际,蒋彝随后结识了收藏家W.W.温克沃斯(W.W.Winkworth)、乔治·尤摩弗帕勒斯、罗杰·弗莱(Roger Fry)和劳伦斯·宾庸(Laurence Binyon)等人。除了弗莱,其他人都是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上的中坚力量。
再者,展览前后英国社会中持续存在的“东方旨趣”是很关键的背景。蒋彝本就喜爱书法和绘画,加之扩大的社交圈,1935年的展览会上,蒋彝以“中国书法家和画家”的特殊身份崭露头角并获得认可。《中国之眼》第一版发行于1935年11月21日,恰逢中国艺术国际展开幕前一周,在艺术展的氛围下英国人对中国不同门类的艺术充满新奇感,此书一个月内便一售而空,并迅速再版。同期的《伯灵顿杂志》上刊有书评,称该书“展示了中国人心中画与诗的联系”(6)C.J.H. review: Chinese Art by Leigh Ashton and Basil Gray; Background to Chinese Art by Hugh Gordon Porteous; The Chinese Eye by Chiang Yee[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35(393).,虽然论述的深度不足,但引起英国人兴趣已然足够。展览期间,蒋彝还举办了“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原理与技法”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同样广受追捧,乔治·尤摩弗帕勒斯自费前往,从不缺席(7)任一鸣. 文化翻译与文化传播:蒋彝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第62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的身份对蒋彝在中国艺术阐释领域的“权威性”有绝佳的巩固作用,如劳伦斯·宾庸对此书赞赏有加,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中国画家的内在观点,与欧洲人的观点之间差异很大”(8)Laurence Binyon. Reviewed Work(s): 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by Chiang Yee[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37(1).,因此,中国人视阈下的中国绘画研究更有助于海外对中国艺术鉴赏的纠偏。
总而言之,1935年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不仅是中国文物第一次出海参加如此规模的展览盛会、向世界展示灿烂的中华艺术与文明的契机,同时也是蒋彝的契机。自1935年之后,蒋彝完成了从“离家流亡的游子”到“华裔艺术家”的身份转变,也担负起了传播中国艺术的责任,从“失语者”而真正变成一位在跨文化语境中促进中西文化互鉴的“行者”。
二、以中释中:中国书画的美学原则及跨文化阐释
前文提及过自20世纪初,中国古代画论就已经在西方传播开来。例如日本现代美术的引导者冈仓天心的著作《东方的理想》(TheIdealsoftheEast,1903)、英国艺术史学者劳伦斯·宾庸的中日绘画通史著作《远东绘画》(PaintingintheFarEast,1908)、阿瑟·韦利的《中国艺术中的哲学》(ChinesePhilosophyofArts,1920)和《中国绘画导论》(IntroductiontotheStudyofChinesePainting,1923)、瑞典艺术学者喜龙仁(OsvaldSiren)的《中国早期绘画史》(AhistoryofEarlyChinesePainting,1933)和作家坂西志保英译北宋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1935)等等。然而,诸上研究都是“以西释中”的范例,三十余年里,对中国艺术美学的阐释始终缺乏中国人本土的视角,这就标明了蒋彝作为阐释者的特殊性,诚如熊式一在《中国之眼》的序言中点出:“关于中国艺术的论著西方研究者们已经写了很多,观点纵然是有价值的,可是和中国艺术家相比总还有些差距。”(9)Chiang Yee. 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 p. ix.
《中国之眼》是对中国画形式和风格要素最早的现代理论概括(10)邵宏. 东西美术互释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233页。。蒋彝在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我相信真正的美与艺术对世界上任两种文明或国家之间其实是共通的,只是在技法和媒介上有些不同罢了。”(11)Chiang Yee. 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p.3.基于此,该著主要从绘画的史论、工具、题材、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对中国画独有的技法和媒介论述详实。在这一点上,《中国书法》承继了《中国之眼》对技法和媒介的重视,除简要介绍汉字的起源与构成、汉字书体的演变和基本美学原则外,蒋彝用了四章的篇幅来介绍技法、笔画、结构以及如何练习书法的问题。
由于书法和美术的亲缘关系,两部著作中体现出的美学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之眼》中,蒋彝梳理出画论的基本原则,首要是线条轮廓的控制,其次是对自然事物的表现倾向,再者是形式的简化,最后是适度的艺术夸张。诸上原则在《中国书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因为蒋彝认为:书法居于中国一切艺术门类之首,“如果没有欣赏书法的知识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美学”(12)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315页。。中国的书画是同源的,所以中国画对线条的骨法、节奏的掌控,对画面中自然山水或花鸟鱼虫的表现,都离不开书法的美学。
既然书法的美学原则被确立为中国艺术之根本,蒋彝便在《中国书法》中做了更完整的“四大原则”如下:一为简明,尽量用精简的笔墨来结构作品,此原则在画作和诗作中均可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二为“暗示性”,蒋彝指出汉字增删或连接部分笔画都能添新意,创造出不同的装饰效果;三为想象性,指出书法艺术始终留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各部分相得益彰,但需整体领悟,延伸到画作中可视为“留白”的意义;四为普遍性,即任何艺术作品最终都和中国儒释道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表达文人的自然体悟和人生态度,艺术品虽是“个人化”的,艺术观却是普世的。《中国书法》和《中国画》前后承继、珠联璧合,相对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书画的起源、发展和独特性。同时,两部著作的语言平实、娓娓道来,偶尔穿插文人故事,趣味性与学术性并存,不仅实现了中国人对书画艺术的阐释和传播,在商业上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中国之眼》在展览会的盛事下销量极好,《中国书法》出版后虽初受冷遇,随后便在机缘巧合中作为别致的“圣诞礼物”远销美国,在美国影响深远。
蒋彝以中国的绘画和书法为阐释对象,不仅因为这是他擅长的领域,更因为中国书画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的确是个难题。这一点从1935年展览会上书画选品的比例及展厅的陈设便可见一斑。一方面,选品数量少,侧面印证了英方兴趣不足。有学者考证,送展的1022件中国宝物中仅有172件是书画作品(13)洪振强. 1935-1936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论述.[J]. 近代史学刊, 2019(1)。,数量不足瓷器选品的二分之一。另一方面,展厅的陈设也体现出对书画的忽视,W.W.温克沃斯和蒋彝合作发表在《伯灵顿杂志》上的文章直言展览上的书画悬挂很高、很偏,不易观赏,戏称“看这些中国画需要配备望远镜”(14)W. W. Winkworth. Chiang Yee,“The Paintings.”[J].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36(394).。蒋彝还在《中国书法》中提到,由于英方选品的偏好,展览会上陈设的书法作品中很多是王公贵胄的作品,如乾隆皇帝的手迹,但这些较之于中国书法家的作品而言“结构糟糕”,没有太多的欣赏价值。
由此可见,书画在中国虽是艺术领域的翘楚,但其与传统文化、哲学观念和审美旨趣等关系紧密而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写意性”,同西方致力于探求形式规律、摹仿现实的“写实”倾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再者,中国书画之间的界限模糊,构图多讲究留白,工具倚重水墨,与西方重视色块和透视法构图等的创作技法也多有不同。面对中西方在书画方面的艺术鸿沟,蒋彝的跨文化身份形成的比较眼光,通过图文共叙、妙用隐喻和不求甚解三种策略拉近中西美学的距离,帮助西方人理解“有门槛的”中国艺术。
首先,图像符号系统本就具有表意、叙事和交流的作用,在跨文化语境中,视觉艺术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尤其有助于促进异质文明间的沟通和理解。蒋彝的两部专著都运用了大量图像来辅助阐释。《中国之眼》中引用人像、风景画和花鸟画三类共24幅,主要选取了唐宋明清四代的名家之作,《中国书法》中更是将伏羲八卦图、象形文字以及从小篆、大篆到隶书和楷书的各类书法作品一并收入,仅从图像的流变中也可管窥汉字的发展。尤其在论述古文字起源时,蒋彝将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与汉字的象形文字并置比较,透过图像可以直观地看出三种文字体系描述物象的不同:“汉字是有力的简化线条,是‘理想主义的’,而埃及字是‘照相机’式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图画。”(15)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51页。由此可见,蒋彝通过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一来生动形象可引起读者兴趣,二来图文可以互为参照、互相补充,以达到增强理解的效果。
再者,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中指出,人惯以日常的、具体的和熟悉的事物来联系和理解抽象的、无形的和陌生的定义,这构成语言和思维隐喻模式的根基。蒋彝的实践便是对这一隐喻思维的妙用。他常从西方语境更熟悉的事物出发,类比书画艺术以帮助西方人理解和接受。如《中国之眼》中,蒋彝先讨论喝茶的文化差异:“英国人喝茶似乎应该加奶加糖,配一块小蛋糕……我们的习惯不是这样,我们喜欢的时候就喝,不仅仅是下午茶”(16)Chiang Yee. 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p.5.,而后引申至中国人绘画少用颜色,就像“我们不会加奶和糖一样”(17)Chiang Yee. 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4,p.5.,寥寥数语从生活旨趣上升到审美趣味,点明文化根基的不同对艺术表现的影响。《中国书法》同样如此,他先描述英文字母的天然构成对字形变化有所限制的客观条件,后论及汉字在方格空间中可千变万化的姿态,以此阐明中国书法艺术性的根源。类似的表述在蒋彝的著作中数见不鲜,他擅长用无偏倚的隐喻轻柔地勾勒出两种文明的差别,既便于理解,又不会引起任一方的不适。
最后,蒋彝深谙中国书画之博大精深是难以用两部作品轻易描摹的,令西方读者全盘接受也是困难的,所以蒋彝在论述时点到为止,《中国书法》体现的尤为明显。在序言中,蒋彝坦言称希望这部作品成为“有意探究书法原理的人的简易指南”(18)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3页。,对于不具备汉学知识的普罗大众而言,也可以“凭借对线条运动的感受和事物组织结构的认识来欣赏线条的美”(19)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5页。。基于此,蒋彝无意面面俱到,他尽可能规避了汉语对西方人而言的障碍,力求从线条结构切入剖析书法的对称与和谐美。由此可见,在跨文化语境中为了译入语读者的接受难免有所取舍,但这种对形式之美的关注暗合了彼时英国正兴的现代主义思潮,对书画艺术的传播亦有所帮助。
综上,以跨文化的身份穿梭在中西文化之间,蒋彝尝试打破“以西释中”的单向局面,转而建构双向互动的交流平台。尽管蒋彝一生都没再撰写类似的专著,但这两部作品达成了蒋彝“被世界记住、与平凡为敌”的心愿,也为搭建中西书画艺术沟通的桥梁贡献了重要力量。
三、线条的普遍诗性:东西方美学的对话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曾存在过两次“中国热”。第一次在17-18世纪,以茶叶、漆器、屏风、瓷器、壁纸等器物和园林建筑风格的广泛传播为主,相对地改变了欧洲人的中国印象,在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方面掀起新的潮流。而20世纪初的第二次“中国热”,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扩张与对华侵略掠夺了大量的珍品瑰宝,导致更多精美的书卷画轴、青铜器、瓷器、织物、雕塑等流散海外,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上千余件海外私人收藏品的出借足以证明。不过,这些流散海外的珍品也进一步更新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从器物层面上升到美学层面。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赞誉这次“中国热”为“东方文艺复兴”(Oriental Renaissance),暗示中国的古典美学为彼时渴望挣脱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代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然如前文所论,中西方在艺术领域的核心观念其实大相径庭。东西方绘画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中国的书画是同源的,文字也天然具备图像性,而这种融合在西方的艺术中是缺失的。以书法和诗歌表现飘逸灵动的自然哲思为基础,中国绘画也以追求强烈的写意性、动态感、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和谐统一为目标,其美学总体是抽象的。反观西方的绘画和雕塑的关系更紧密,注重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其美学是偏具象的。如此迥异的两种艺术形式要实现美学互鉴,便需要寻找一个共同点来达成对话的可能,在蒋彝看来,这个共同点就是“线条”。
无论是《中国之眼》还是《中国书法》,蒋彝强调“线条”作为美学原则的基础性和纲领性。“线条”代表着对普遍意义的求索,因为中国书画的基础都是线条,线条具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无限性,所以无论以何种技法,线条的变化所迸发出的有机生命力,能够展现出人与人、自然和宇宙之间的联系,从而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域的感染力。
线条的普遍性不仅存在于书画艺术本身的形式美感,还存在于书画和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紧密关系中。《中国书法》中,蒋彝十分详细地介绍了书法的线条结构、流动性、不对称美、想象空间等美学原则在中国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的运用,如水墨画里的层峦叠嶂、画作里配合书法撰写的诗歌、玉雕和木刻的精美线条、陶器或漆器上的纹理、佛教塑像的衣服褶皱、建筑物椽梁骨架的线条感等等。因此,中国古典艺术本质上没有西方现代艺术中“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派系的分野,一切以线条为基础,以自然为灵感,追求从“小我”中见非个体化的“大我”。蒋彝希望从这一角度将中国书画的美学原则上升到世界艺术的普遍性追求,以勾连起中西方艺术的审美旨趣,这种建构有效地吸引了西方学者的注意。
1933-1939年担任《伯灵顿杂志》编辑的英国美学家赫伯特·里德(Hebert Read)为《中国书法》第二版作序时便称“书法这一艺术的基本美学原则,实际上也是所有真正的艺术的美学原则”(20)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xi页。,“我立即被它对一般艺术哲理的意义,特别是与现代艺术某些方面的联系所吸引”(21)蒋彝.中国书法[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第xi页。。美国学者帕特里卡·劳伦斯(Lawrence Patrick)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线条’存在于中国汉字和书法艺术当中,并延伸到中国的视觉艺术和设计当中,这就是中国艺术总能吸引现代主义者的原因所在”(22)帕特里卡·劳伦斯. 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 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564页。。再如美国汉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汉字诗学研究,他关注汉字的造字和形体,强调汉字作为“表意符号”的力量,本质上也是对线条气韵的关注。尽管费诺罗萨由于捏造构字法、忽视汉语语音特点等缘故饱受诟病,但不可置否其对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产生的巨大影响。
西方艺术批评者对“线条”之无限性、艺术性和普遍性的论述,最典型的当属英国现代主义形式美学批评家罗杰·弗莱,他提出的“线性韵律”(Linear Rhythm)和蒋彝看重书画线条的观念是不谋而合的。弗莱早在1918年于《伯灵顿杂志》发表《线条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段》一文中,便以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为对象探寻过线条艺术的美感:
物质的无限复杂性、丰富性,与心灵的纯粹抽象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并不是以一个点汇聚,而是汇聚成一条线。在艺术中,世界的两个不可调和的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为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而在绘画中,这种调和体现在最简单的方面。我们从来没有像中国人和波斯人那样推崇书法……但事实上,纯粹的线条表达是有可能的,它的节奏可能是无限多样的,表达着无限的心情和状态(23)Roger Fry. Line as a Means of Expression in Modern Art[J].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1918(189).。
了解中国书画之笔法和韵律的弗莱,在西方现代艺术中看见了线条的极简与无限,洞察了线条中蕴含的细致与感性。弗莱运用东方美学中线条的韵律感重新阐释和发掘了西方艺术,这在美学层面实现了东西方的汇通。
《中国书法》远销美国后再版售罄,受里德赞誉“线条与现代艺术关系”的鼓舞,蒋彝还研究过中国青铜玉器和西方未来主义及立体艺术之间的联系,他希望借助共性的类比拉近中西文化的关系,这种努力鲜明地体现在1956年蒋彝应邀于哈佛大学纪念堂为优秀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发表的名为“中国画家”(The Chinese Painter)的演讲中。作为获此殊誉的第一个中国人,蒋彝演讲时有意与爱默生“美国学者”的民族独立式宣言拉开距离,转而传达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艺术观。他坚称艺术是具有共通性的,尤其在全球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差异,而应当在流派和技巧等表层结构下深入探寻艺术领域普遍的“人类和自然的诗意真理”(24)Chiang Yee. The Chinese Painter[J].Daedalus, 1957(3).。他强调“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是无边界的、公正的、客观的和永恒的”(25)Chiang Yee. The Chinese Painter[J].Daedalus, 1957(3).,因为它很少表现痛苦、恐惧、纠葛等具体的事物和情绪,而是汲取超脱自然之能量,在动态的美感中把握恒久的和谐与平静,如此便可具备一种普遍的、哲学性的慰人效果。这种具有世界眼光的普遍性美学,是中国书画的独特贡献。
F.S.C诺斯莱普(F.S.C.Northrop)在其作《东西方相遇:对世界理解的探寻》(TheMeetingofEastandWest:AnInquiryConcerningWorldUnderstanding)中引入认知关联(epistemic correlation)的概念以解决东西方文明碰撞引发的意识形态冲突。他指出,东方的文化大多依靠经验和直觉,是一种美学建构,而西方文化多来自假设和推导,是一种逻辑建构,这就需要“认知的关联性通过共同指涉的真实、终极的意义将两个冲突调和在一起,使世界文明成为可能”(26)F.S.C.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449.。诺斯莱普认为,东西方文明互鉴的本质不应该是对他者的排斥,而应该基于彼此的需要。诚如蒋彝对其“世界主义”文明观的重申:“我到处旅行,寻找各国人民之间的共同之处,而不是迥异。”(27)郑达. 西行画记——蒋彝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222页。
结 语
总而言之,蒋彝因之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殊身份“以中释中”,借助“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背景下的中国艺术热,将书画美学阐发并传播到西方,他的本土立场与“世界主义”美学观兼具,希望在“同”中化解“异”,打破东西方艺术交汇的壁垒。这种建构无疑对传播书画艺术及其美学起到了推进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抽离出“线条”的形式美感上升到艺术普遍性的做法其实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强调线条之视觉美感,势必会忽略书画艺术背后隐含的文化秩序和思想内涵。艺术品凝结的不仅是创作者的灵感,还汇聚了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避开个性而只谈共性实为一种简化的做法,忽视了“这些知识阶层和艺术家们的“编码的眼睛”仍旧不自觉地怀有某种‘象征性的暴力’”(28)帕特里卡·劳伦斯. 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M]. 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345页。。不过蒋彝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的,如同其传记作者、美国萨福克大学英语系教授郑达的评价:“有蒋先生的启发,我们至少更容易理解其中的原则,尽管我们总是会忽略细微的欣赏,但我们的美学家是否认可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至少不要误解。”(29)郑达. 西行画记——蒋彝传[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