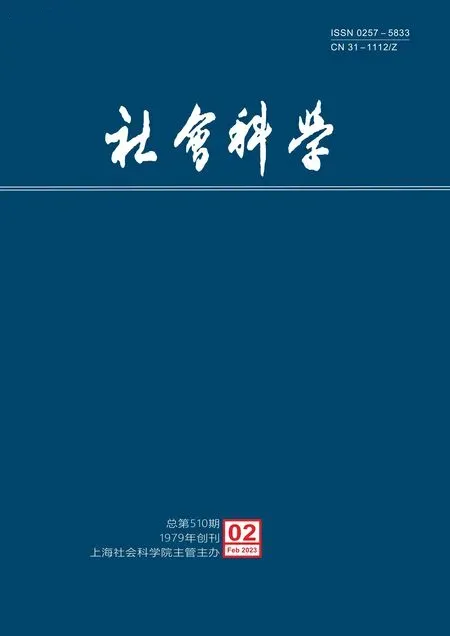高校心理育人体系的现实困境与历史反思*
2023-04-16吕小康
吕小康
一、“心理育人”的政策网络与现实困境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向来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整体上看,近年来青年人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普遍下降趋势,①辛自强、池丽萍:《当代中国人心理健康变迁趋势》,《人民论坛》2020 年第1 期。焦虑、抑郁、睡眠问题和自杀未遂的检出率显著上升。②于晓琪、张亚利、俞国良:《2010~2020 中国内地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022 年第5 期。同时,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生“躺平”“内卷”“空心病”等非精神障碍类消极心态的讨论也不鲜见,③黎娟娟、黎文华:《Z 世代大学生多重矛盾性社会心态解析》,《中国青年研究》2022 年第7 期;胡锐军:《大学生“躺平” 心态的文化根源及其矫治路径分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 年第1 期;吴玲:《现代性视角下中国青年“空心病”的 诊断与治疗》,《当代青年研究》2018 年第1 期。这些消极心态本身虽然并不构成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心理疾病,但疏导此类心态也是心理育人工作的重点议题。为此,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已出台了多种举措,以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生率,同时培养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这集中体现在2017 年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以下简称《实施纲要》)“十大育人体系”之一的“心理育人体系”建设内容中——要求“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结合,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入构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平台保障‘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这为当前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供了根本性的方向指引。
在《实施纲要》出台前后,与心理育人功能高度相关的政策文件也陆续发布,主要包括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与教育部等22 个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卫疾控发〔2016〕77 号),2018 年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 〔2018〕41 号),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宣部、教育部等12 个部门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国卫疾控发〔2019〕63 号),2020 年教育部等8 个部门颁布的《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1 号)等高校心理健康相关的政策文件。 2021 年11 月,教育部又召开了全国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进会,要求“把全面加强和改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内容”。另外,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中央政法委等10 个部委于2018 年11 月印发的《关于印发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8〕44 号)中,也要求“高等院校普遍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室),健全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在此后3 年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的重点任务中,均要求“完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其具体指标为“试点地区所有高等院校按照师生比不少于1∶4000 的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实质上仍是前述心理育人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上述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会议精神和试点行动,共同构成了当下我国心理育人体系的政策网络。
但是,当下的心理育人工作仍存在诸多挑战与困境。首先是人才困境。纵观各项相关政策文件中要求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要求高校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计划、编写和开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及在线课程、按师生比不低于1∶4000 的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教师,以及推进心理健康筛查和网络测评系统等,以期建立学校、院系、班级、宿舍“四级”预警防控体系。另外,2017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43 号)同时要求,“高等学校应当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 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是专职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之一,他们负责“协助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初步排查和疏导,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活动,培育学生理性平和、乐观向上的健康心态”。不过,无论是按1∶4000 还是1∶200 的比例计,以当下各个高校心理健康中心、学生工作部自身有限的人手,要高质量地完成面向规模庞大的全体高校师生的心理育人体系建设,仍显得捉襟见肘。
其次是实践成效的困境。当前高校的心理健康工作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仅以“抑郁症”①应注意“抑郁症”在不同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指涉,包括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抑郁障碍甚至是抑郁情 绪体验几种常见语义(其界定标准依次放宽),从而造成所谓“患病率”的差异。为例,根据人民日报客户端及其主管的健康时报联合相关心理健康机构于2022 年6 月29 日共同发布的《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5%—20%,其中的50%为在校学生,这些在校生更有41%曾因抑郁而休学。②参见《〈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发布,应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健康时报网,http://www.jksb.com.cn/html/life/psychology/ 2022/0704/177205.html, 2022-12-01。该报告虽未直接明确地指出大学生的占比,但报告了18—24 岁的抑郁症患者占比为35%,而这一年龄段正是多数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可见大学生群体的抑郁症患病率不容低估。其他一些更严谨的近期系统分析(meta-analysis)也显示,基于各类抑郁症筛查工具得出的大学生抑郁障碍检出率高达26%、28%,甚至31%。③这3 个患病率分别出自以下3 个文献:Luo W., Zhong B. L., Chiu H. F. K.,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Vol.30, No.e31, 2021, pp.1-21; Gao L., Xie Y., Jia C., Wang W.,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Scientific Reports, Vol.10, No.1, 2020, pp.1-11; 王蜜源、刘佳、吴鑫、李磊、 郝肖迪、沈庆、黄敏婷、孙瑞华:《近十年中国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的Meta 分析》,《海南医学院学报》2020 年第9 期。虽然其具体比例并不相同,但都提示在四分之一甚至更高比例的大学生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障碍。这还仅是抑郁症一种心理障碍,如果考虑到焦虑症等其他心理障碍,仅仅是常态化情景下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就已不容乐观。
再次是工作思路的困境。由于心理育人体系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十大体系之一,它不可避免要承担思政教育的功能。但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高校辅导员队伍在实践中却普遍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实现相对专业化和学科化(具体而言即心理学化和精神医学化)的心理健康教育与相对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以同时应对心理病理层面与一般性情绪体验层面的心理健康问题。本质上,高校并非治疗机构而是育人场所,要在“育人空间”起到“治疗功能”本已不易。况且多数辅导员本身既不具备精神医学的行医资质,也不完全具备能够达到心理卫生协会等专业机构认证的心理咨询能力,要让他们同时完成“防+治”的任务要求,既要对少数学生的病理性心理问题建立起良好的预警、干预、转介和社会支持体系,又要培育所有学生的健康向上的积极心态,这难免形成一些思想上的认知困惑和行动上的顾此失彼,既加重了实际工作的负担,又挫伤了高校辅导员和心理咨询教师对自身胜任力的感知,还会整体上形成对高校心理育人体系合理性的疑惑。
与前两种困境相比,最后一种困境对于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实际困扰要大得多。理论上,人才的困境可通过增加人员编制而解决,成效的困境可通过完善心理咨询技术、提升心理育人体系的效能而解决——虽然现实中总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妨碍了这些理想目标的实现,但它们都属于认识上“想得通”的问题,因而不至于使高校心理育人体系的践行者感到思想上的困扰。但是,工作思路的困境恰是一种很难让人“想通”的认知困境。分析这一困境产生的内在根源,尤其是其历史根源,或可为减轻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内心困惑、认识高校心理育人的内在张力提供一种“长距离”的反思意识。
二、“心理育人”体系的双重功能与内在张力
从前述概括的心理育人相关政策要求看,教育部自身提出的心理育人体系,首先是隶属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一个子体系,同时又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工作要求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某种程度上讲,所谓的心理育人体系,其实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指导下,于高校系统内部建立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就形成了心理育人体系的双重政策功能:既要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又要体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高校思政工作的根本要求。一方面,它是个体层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着眼解决大学生的病理性心理健康问题和具有潜在病理性倾向的心理障碍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是群体层面的、非病理性的心态建设行动,着眼解决大学生的思想认知问题,主要属于“五位一体”中的“精神文明建设”。两者同时都整合在“心理育人体系”的建设要求中,成为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政策目标与内容的“兼容并蓄”,实质上反映出人们对于“心理健康”的多样看法及其解决之道的多元路径。长期以来,中国高校、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理解却有着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式心理咨询与精神医学的模式。国内对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关注总体上可归结为两大层面。一是类似于“空心病”、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价值失落、意义虚无、功利至上等思想状况层面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不属于医学范围,不能通过医学求助而缓解,而主要是通过中国式的思想政治和心理疏导工作解决,可以认为是一种本土化的心理问题解决模式,它具有自身的社会文化传统,并受意识形态工作的直接指导。另一类是以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为主要代表的大学生及青少年精神障碍高发的问题,这一问题也已得到各类流行病学调查的证实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通常涉及特定的生理机制,并高度依赖医学化的干预手段(如服用特定药物、进行其他的特定治疗等),它需要通过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部门与其所在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卫生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有效的预警、转介等联动机制而进行分级防控。此类模式主要借鉴国外的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的诊断与转介模式而成型,具有较强的国际通用性。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是国际通行的个体心理健康干预问题。有效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在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有效干预,并同时接受两方面的成效检验。
实际上双重政策目标的设置是逻辑自洽的。例如,许多“思想转不过弯来”的认识问题,确实常伴有负性的情绪体验,它们本身虽未达到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程度,并不能直接套用精神医学的方式加以解决,但它们“传染”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且在某些外部事件刺激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暂时的聚集性突发状态,以高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或专兼职辅导员的体量,又难以做到一对一的干预与追踪。如果放任这种负面心态而不加以干预,则又确实容易形成相关病理性心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因此,这种负性心态问题与狭义的心理健康问题确实存在一定的交集,把它们纳入心理健康工作的视角,可以视为“预防为主”的健康治理思路的体现。问题在于,防线前提的“度”究竟如何把握?这也在实践中造成了不少高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认知困惑,代表性的问题包括如何区分学生的“思想问题”与“心理问题”,如何把握“强化价值引领”与“遵守价值中立”之间的平衡,如何避免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化”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政治化”等。如何恰当地拿捏分寸,成为了一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实践技能和难以准确衡量的工作能力。这使得高校心理育人工作出现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裂痕,①参见章少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育人功能实现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 年第11 期;陈虹:《新 时代高校心理育人内涵、困境与应对》,《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 年第7 期;潘莉、董梅昊:《高校心理育人面临的现实难 题及其突破》,《思想理论教育》2019 年第3 期;马建青:《论思想品德问题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系》,《教育发展研究》2014 年第8 期。影响了心理育人体系的推进效率与工作成效。
对心理育人体系的上述困境,以及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两种“教育”的本质、方法及融合途径,已有不少国内学者、高校学生工作管理者和心理咨询实务工作者进行了各个角度的反思。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从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视角出发寻找两者的契合点。有研究在回顾我国高校自20 世纪80 年代初以来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之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提出应厘清“障碍性咨询”与“发展性咨询”的区别:前者是为各种有障碍性心理问题的咨询对象提供心理援助、支持和矫正,后者是帮助不同阶段的学生圆满地完成各自的心理发展课程,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质正在于后者。②参见仰滢:《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20 年回顾与展望》,《中国高教研究》2008 年第7 期;马建青:《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结合30 年的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137 页。有研究在系统性回顾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学”的主张,并对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体制建设提出了宏观性构想建议。③参见俞国良:《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政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俞国良:《心理健康教育前沿问题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俞国良:《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体系建设探微》,《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 年第7 期;郑安云、张文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40 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此类观点主要由具有高校心理咨询工作实务经验的研究者、咨询师和辅导员提出,有着明确的政策服务意识,力图为政策推进寻找学理依据并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
二是从心理教育(“心育”)与道德教育(“德育”)相结合的学术视角提出学校教育的新模式。
这一观点在心理健康教育之外提出“心理—道德教育”的主张,强调育心育德一体化、统整心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容,以促进精神建设、服务人生幸福。④参见班华、沈贵鹏、王曦斐:《探索一种新的教育形态:心理-道德教育——班华教授专访》,《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2 年第2 期;班华:《心理-道德教育服务人生幸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这种教育形态主要立足于学校教育本身,致力于将中国传统的德育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教育思想相融合,并把心理健康教育置于“心理—道德教育”的整体语境中加以推进,从而兼容心理咨询与思政教育的双重内涵。在这种教育理念中,心育是积极的、发展性的,针对心理问题的矫正性心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与前述“障碍性咨询”与“发展性咨询”的区分有相似之处。这一观点的提出者主要是从事教育心理学的学者,其所设计的学校教育模式不仅针对高校,还同时覆盖中小学学校教育。
三是从心理咨询本土化的角度构建多元文化咨询的途径。这一观点认为,应在平衡“三元”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混融三重自我(关系我、个体我和集体我)的过程中,凸显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集体我的指导地位,培养人格成熟、身心健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①参见王进、李强:《多元文化咨询之本土化路径初探》,《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8 年第15 辑;王进、李强:《当代中国 人的三重自我及“混融自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 年第5 期。与一般性的心理咨询本土化的探索不同,这种多元文化咨询途径的构建不止于心理咨询技术层面的融合,而是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核心指导思想,并以之平衡中国人自身的心理咨询传统与西方的心理咨询传统,从而使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局。此类观点主要由高校心理学专业中从事心理咨询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的教师及科研人员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性和反思性。
以上这些主张对完善当下的心理育人体系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其共同之处在于都对如何更好地把心理咨询工作融入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有深度的反思,都体现出面向中国实践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心理咨询模式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动性思维。但是,这些反思的历史纵深意识尚有所欠缺。从其对心理健康融入思想教育的相关政策演进的回溯过程看,多数研究都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为时间起点思考心理健康服务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程,而未将视野涉及更早时期的高校心理卫生实践。例如,有研究认为“心理卫生”的概念于1983 年才由心理学界率先提出;有研究把20 世纪80 年代起关于加强高校心理卫生工作的相关建议,②参见杜殿坤、采石:《要注意学生的“心理卫生”——苏霍姆林斯基论道德教育之五》,《湖南教育》1982 年第7 期;山佳:《浅 谈学校心理卫生教育的几个问题》,《教育科研通讯》1985 年第1 期;陈锡林:《应重视大学生的心理卫生教育》,《江苏高教》 1986 年第3 期。以及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开展的心理咨询工作,③黄希庭、郑涌、毕重增、陈幼贞:《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心理科学》2007 年第1 期。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与心理健康教育,即当下心理育人体系建设的时间起点;而对“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政策文本的追溯,则及至1994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及的主张。④俞国良:《心理健康教育理论政策研究》,第161 页。这种把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起始点界定为20 世纪80 年代初或改革开放以来的观点较具有代表性,也是前述文献中所谓心理健康教育“20 年”“30 年”“40年”的历史断代依据。从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溯源看,这种划分确有一定道理,也符合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重建心理学、逐步发展心理咨询和心理卫生的学科发展历程。
但是,“心理卫生”显然不是20 世纪80 年代才有的“新名词”,对大学生心理卫生的重视也不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新事物。实际上,中国高等教育界对大学生心理卫生或心理健康的重视已有百余年的历史。高校的心理卫生课程与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就已经在中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得到推行,当时许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等或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中医、佛教和儒学的身体观和健康观——来解释现代心理治疗与中国人心理健康的契合性,或借用现代心理治疗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造国民性,不少学术主张至今仍有启发意义,⑤参见王东美、桑志芹:《现代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开端——兼论心理治疗中国化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王东美:《历史的共情——基于中国知识传统的心理治疗可能》,《开放时代》2022 年第4 期。也针对当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开展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常因战火而中断,但早期先行者在高校展开心理咨询与心理卫生的原创性摸索仍值得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仍可启发当下的心理育人工作。因此,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历史追溯,有必要前推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期,从中寻找心理健康与高校育人“有机融合”与“内在矛盾”并存的发展脉络。
三、高校“心理育人”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张力
如果抛开“心理育人”的表面字眼而究其实质——即以提升心理健康的方式全方位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道德人格、从而培养时代所需要的新人——那么可以说这种传统自中国近代高校出现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存在。但这一传统与“心理健康”(当时更多称为“心理卫生”)产生关联,与民国时期的中国心理学人欲以心理学知识与技术改造国民心理,进而改造社会的现代化愿景相关,更与中国社会的治理传统习惯于从人心求解社会秩序的终极答案和进步源泉的巨大惯性有关。这两种力量的内外结合,使得民国高校的心理育人工作更多成为一种体制要求而非专业需求,也使得当时高校的心理卫生工作从“精神卫生”或“心理学”问题转化为教育学、社会学问题——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治理学”问题。而这恰好埋下了今日心理育人体系之内在困境的根源。
“心理卫生”(Mental Hygiene)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流行是清末西学东渐之后的产物。根据当下学者对中国心理卫生史的挖掘,可以确定它至少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已散见于各类报刊。与此同时,东南大学(1922 年)、南开大学(1923 年)、北京大学(1926 年)、燕京大学(1927 年)、清华大学(1929 年)都已开设《变态心理学》课程,讲授心理卫生知识和心理咨询方法。①参见王东美、钱铭怡、樊富珉、江光荣:《中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百年发展简史(1921—2021)》,《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 年第2 期;南开大学于1923 年的心理学系课程设置另见王文俊、梁吉生、杨珣、张书俭、夏家善:《南开大学校史资 料选(1919—1949)》,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186 页。1930 年,南京政府卫生部科长王祖祥等人已代表中国参加第一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并做了有关中国心理卫生情况的报告。同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硕士章颐年(1904—1960)回国后在上海暨南大学正式开设“心理卫生”课程,后将讲稿集合扩充成国内第一本心理卫生专著《心理卫生概论》(商务印书馆,1936 年);1932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吴南轩(1893—1980)回国后也在南京中央大学开设同名课程。此后,美国传教士夏仁德(Randolph Sailer, 1898—1981)曾在燕京大学讲授“心理卫生”课程,并出版了《人格与日常行为》(1935 年)教材;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黄翼(1903—1944)曾在浙江大学开设“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课程;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也在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开设“变态心理及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课程。 1941 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教育心理课程标准修订版中,也已经包括了心理卫生的内容。②相关史实文献参见胡延峰:《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陈学诗:《中国心理卫生的沿革与任 务》,《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 年第10 期;肖朗、范庭卫:《民国时期心理卫生的理念和思想对教育学术的影响》,《社会 科学战线》2010 年第11 期;舒跃育:《章颐年:中国心理卫生的开拓者》,《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 年第6 期;卓学仁、陈 巍:《无人信高洁 谁为表予心——“失落”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家章颐年》,《心理技术与应用》2015 年第4 期。当然,这些课程内容并不只针对大学生,而是涵盖全体国民,但其讲授、研究和实践中心无疑仍是当时的大学。
除了课程之外,与心理卫生相关的专业组织也已在民国时期得到普遍发展。 1936 年,吴南轩及其在中央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丁瓒(1910—1968)等人就已在南京成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宣称“以保护与促进国民之精神健康及防止国民之心理失常与疾病为唯一之目的,以研究心理卫生学术及推进心理卫生事业为唯一之工作”。③参见王蕴瑾、陈巍:《破的由来事 先锋孰敢争——中国心理卫生运动的领路人吴南轩》,《心理技术与应用》2015 年第1 期 (但该文中介绍的吴南轩生年有误)。1942 年,由丁瓒创办并任主任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室是由政府建立的第一个心理卫生研究机构,并制订了《中央卫生实验院心理卫生咨询办法》,后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43 年颁布施行,这也是我国最早以国家政策形式颁布的心理卫生文件。④范庭卫:《丁瓒与抗战时期的心理健康教育》,《海峡教育研究》2014 年第1 期。丁瓒本人1947 年至1948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并于1948 年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首届世界心理健康大会(8 月16 日至21 日)。这次会议由英国国家心理卫生协会主办,本身是关于世界心理卫生的大会,但会议的主题是“心理健康和世界公民”(Mental Health and World Citizenship),并在会上通过了同名决议文件。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促进了心理卫生工作从消极治疗转为积极预防,心理健康一词由此才逐渐取代心理卫生。此外,此次会议还推动了心理卫生从健康运动向公民运动的转变,即将心理健康技术视为现代公民之理想人格塑造的手段⑤José Bertolote, “The Roots of the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World Psychiatry, Vol.7, No.2, 2008, pp.113–116; Wu, Harry Yi-Jui, “World Citizenship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ocial Psychiatry Project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48–c.1965”, History of Psychiatry, Vol.26, No.2, 2015, pp.166–181.——这正与当时中国社会对心理学和心理卫生之社会功用的期待重合。
从中国近代史的宽广视野看,对民族心理的现代化改造一直是中国人借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这在晚清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中就已得到共识,并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就已经达到倡导国民性变革的高峰,①参见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袁洪亮:《人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同时也是当时民间高等教育办学实践者的共同心声。从晚清至民国的各类“教育救国论”中,通过教育改造民心、荡涤灵魂从来是这些教育先行者眼中唤醒国民、挽救民族的不二法门。如梁启超所言:“政治是国民心理的改造,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总是国民心理积极的或消极的表现……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上要改革国民心理。”②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第238 页。当时的许多年轻学子留洋学习心理学,往往是出自这种传统的士人心态和现实关怀,而非醉心于现代心理学自身的科学研究风格。曾任“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的汪敬熙(1898—1968,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主攻生理心理学)分析了民国初年心理学得以流行的原因:“那时候,许多人有一种信仰,以为想改革中国必须从改造社会入手;如想改造社会必须经过一番彻底的研究;心理学就是这种研究必须的工具之一,我记得那时候好些同学因为受到这种信仰的影响,而去读那些心理学书,听些心理学的功课。”③汪敬熙:《中国心理学的将来》,《独立评论》1933 年第40 期。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时代思潮,“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许多最初接触西方科学心理学的知识分子,都曾试图将心理学作为一种工具去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或历史问题”。④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84 页。
由此不难理解心理学界对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的热情。在首次出版于1918 年的《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心理建设”的政治主张,并将其作为三大建设之首(另外两大建设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⑤孙中山:《建国方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3 页。这一主张与梁启超之“政治是国民心理的改造”的思想一致,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角色将心理建设提升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种思想也得到心理学界的迅速响应并产生了长久的回音。 1934 年,吴南轩在介绍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时,就观点鲜明地指出:“中国今日正当国难严重之际,举国上下方力谋振作,以期民族复兴。但民族复兴之基本条件不是心理建设么?国民精神若不健康,心理若不健全,心理建设何从实现呢?不提倡防止心理失常和保持精神健康的心理卫生,国民健康的精神与健全的心理有何能达到呢?”⑥吴南轩:《国际心理卫生运动》,《教育丛刊》1934 年第1 期。1937 年,章颐年在介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之缘起时,也以同样激情可见的笔触写道:“国于大地,必有兴立,立国之基本之道为何?民心或民族之精神而已。无论任何国家,其民心健全者国必强盛,民心堕落者国必衰微,民心者实一国国力兴衰升降之寒暑计也。”1938 年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工作报告》还专门讨论了心理卫生运动与抗战的关系,明确指出这一运动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而是解除国难的一种努力,担负着重塑国民健康心理的重任。⑦陈四光:《民国时期心理卫生与心理训导中的“心理健康教育”》,《当代教育评论》2015 年第2 辑。可见,在当时的国内心理咨询界代表人物眼中,心理健康是心理建设的前提,进而也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心理健康不仅与民族前途挂钩,还成为了它的先决条件。他们的思想并非一己之说,而是代表了一代心理学人的集体理想:他们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完成了本土中小学“修身”教育,而后留洋取得心理学学位,最终回国并希冀通过心理学知识和教育教学技术来改造国民和改良社会。也正是这些秉持深厚淑世热情的心理学先行者,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心理卫生工作,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心理卫生事业也兼具科学风格与政治追求,并常因受此两种力量的内在冲突而体现出某种矛盾色彩。
更重要的是,这种内驱力还得到近代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体制性强化,并在这种强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心理学家与大学治理、心理健康技术与思政育人方法的有机结合。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一是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和大学治理者的角色重合。许多留洋心理学者回国后都受聘于各类高等学校,并有不少人身兼院系主任、大学教学部主任或校长等管理要职。前文提及的章颐年曾任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大夏大学(意即“光大华夏”)教育心理学系主任,吴南轩曾任清华大学代理校长和复旦大学校长。此外还有不少知名心理学家在不同大学任职,如张耀翔(1893—1964,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曾任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主任、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暨南大学教务长等;陈大齐(1887—1983,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学士,专攻心理学)曾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北京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校长;潘菽(1897—1988,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博士)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凌冰(1891—1993,克拉克大学教育心理学博士)、黄钰生(1898—1990,芝加哥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硕士)曾先后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凌冰另曾任河南省立中山大学校长);高觉敷(1896—1993,香港大学教育学学士)曾任金陵大学等多所大学的教育系主任;陈鹤琴(1892—1982,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市教育局教育课课长、东南大学教务长;廖世承(1892—1970,布朗大学心理学博士)曾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光华大学校长;周先庚(1903—1996,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并在西南联大期间主持哲学心理学系(分哲学组和心理组)下心理组的工作。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在1949 年之后、院系调整运动前仍担任大学或科研院所的领导职务。如此一来,他们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卫生的观点与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就得以较快地合二为一,汇聚成一种“强国先强身、强身必健心”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思潮。
专业知识与人事职能的交织缠绕、专任教师与管理人员的角色重合,对心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心理卫生)知识与技术深度介入近代德育制度和整个高等教育制度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当心理学家的职业认同与其发自肺腑的民族—国家认同汇聚,就生成一种共同的内在驱动力,并通过其所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占据的关键性角色而发挥出长久的作用,使通过改造个体心理而塑造全新国民的“心理育人”观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生根发芽。尽管后来心理学学科一度因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被取消,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拨乱反正”并开始恢复心理学等相关学科之后,关于“重视心理卫生”并将之贯穿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仍能迅速得到心理学界、教育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共同认同和实践,并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心理育人”政策脉络史。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强调后,关于心理建设的思想更是进一步为当下的心理学研究者所重视并进行重新阐发,①参见王静、霍涌泉、宋佩佩、张心怡、杨双娇、柏洋:《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心理学报》2019 年第11 期; 辛自强:《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年。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在学术会议、微信公众号等场合或平台发出应将“心理建设”提升为与“社会建设”等内容并列、使“五位一体”成为“六位一体”的呼声。而当下社会心理服务的建设,同样也体现出寓“社会治理”于“健康治理”、以“心理健康”促“社会平安”,力图通过心理健康服务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双重逻辑。②张淑敏、吕小康:《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政策语境与行动逻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6 期。由此也可见这一治理传统存在的普遍性。
二是心理卫生工作通过“训育”制度而逐渐成为思政教育的一个常规方法。“训育”(德语为Zucht,通常英译为discipline)一词源自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于19 世纪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意指对学生行为品德的训练和教育,③顾明远:《教育大辞典· 教育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5 页。其核心要义即是注重教育过程对个体道德品格的养成作用。这一主张与中国的文化传统高度契合,本无特殊之处。清末民初的训育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国家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国家政策的形式对之进行制度性的强化,从而体现强有力的国家意志。它不是道德教育探索的开端,而是道德教育制度化的阶段性成果。④毛君:《民国时期“训育”的本土化实践》,《教育学报》2019 年第1 期。这一理念在清末对新式学堂的“修身”课程设置中已见到雏形,并在民国时期得到全面推行。其时的政府相继通过《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案》(1929)、《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1931)、《训育纲要》(1939)、《专科以上学校训育标准》(1944)和《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委员会组织规程》(1947)等规章制度,确定了“训育应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养成德智体群美兼备之人格”的价值目标、制度框架和具体标准,使高校的训育制度日趋严格。而负责在高校落实训育制度的,有多人正是前述身兼高校负责人、教务长、训导主任的心理学家。这使得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身的“专业报国”理想,同时也能更直接地观察和体会到将心理技术应用于治理实践时可能发生的走样与矛盾。
例如,廖世承曾批评“过去的学校,把教学看作一件事,训育看作又一件事”的偏见,并专门论述了训育的目的和原则;①参见严军:《廖世承素质教育思想试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1 期。陈大齐在北大的学生陈雪屏(1901—1999)曾任国民党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青年部部长,同时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负责西南联大的训育事宜;周先庚认为对大学生实行训育的“最理想的办法”是设立心理卫生部,由精神病学家主持、由心理学家和职业指导员协助;②周先庚:《大学生的训育问题》,《独立评论》1935 年第165 期。高觉敷出版了《青年心理与训育》(1942 年)一书以致力于“予中等学校的训育实施法以理论的基础”;③高觉敷:《青年心理与训育》,重庆:正中书局1942 年,第6 页。姜琦(1886—1951,曾任西北联合大学教务长、遵义浙江大学训导长等职)的《训育与心理》一书还尝试建构一种新的“教育心理学或训育心理学”④姜琦:《训育与心理》,重庆:正中书局1942 年,“序”。。这些都体现出心理学界对训育工作的职业投入与学术努力。但是,这些心理学家所曾接受的科学心理学训练,又使得他们在执行训育过程中常意识到心理卫生工作自身的科学性常被训育制度的政治性消解。如黄翼曾指出现代心理卫生及辅导应不同于传统训育,注重的不应是社会准则的客观要求而是个体行为的主观心理原因,它不应是法律的而应是教育的。但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未改变国民党为加强思想控制而推行训育制度的本质,使得“在实际的训育工作中,专门的心理辅导并没有得到展开”。⑤范庭卫:《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心理学报》2009 年第2 期。
还应注意到,在1941 年,一位相对而言并不太知名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杨同芳(1915—1963,曾任华东大学教育系讲师、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等职)就明确指出,心理卫生的目的有二:一是注重精神疾患的治疗,二是健全人格的培养;前者是心理卫生的消极目的,由心理治疗家负责,后者的工作则由教育者(包括教师和父母)承担。⑥杨同芳:《中学训育》,上海:世界书局1941 年,第36 页。这一观点正与当下“心理育人”的双重功能相合。这并非巧合,也不只是当时学者的眼光超前,而恰说明心理卫生、心理健康和心理学的中国化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使得它竟长时间徘徊于同一问题而难以获得完美解决。虽然当今心理育人体系的指导思想较民国训育制度的指导思想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与提升,但要在实践层面融合其“消极”与“积极”功能,仍是一个有待摸索与创新的未竟过程。反思民国训育制度时,除了认清它的阶级立场与本质目的、认识到其实施过程流于说教和失之空洞的弊端之外,仍应看到其注重价值理念对高等教育的引领作用、注重人格教育和道德教化的做法其实与当下的心理育人工作存在贯通之处,⑦参见张均兵:《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 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年;田海洋:《道德之维:民国时期训 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还应肯定它促进高等教育学生管理制度的成型和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卫生)重视的客观功能。⑧参见王延强:《民国高校训育体系与学生管理的制度化发展》,《高教探索》2019 年第12 期;毛君:《民国时期“训育”的本 土化实践》,《教育学报》2019 年第1 期。这又进一步说明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路程,具有相对独立的客观规律性。
四、历史的共情与未竟的余思
心理育人工作主张注重育心与育德并重,注重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理念对心理健康和个人成长的全程引领作用。这种主张既符合中国教育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更是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中用于应对民族危机、改造现实面貌、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资源。但其具体做法也在实践中造成了某些操作层面的困惑。造成这种困惑的主要成因并不在于心理咨询方法或其他心理健康促进技术的“本土化不足”,而在于以心理健康的名义完成个体的现代化塑造这种贯穿着中国近现代史的持续性的、集“社会—政治—文化压力”于一身的一体性压力造成的结构性紧张。
本文的历史回顾虽限于篇幅未能详细展开,但已可说明如下事实:对“心理”的政治化解读与利用,对“心理健康”的教育学改造与体制性吸纳,是贯穿中国社会百余年发展进程的如何以“人的现代化”促成“教育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并因此兼具了政治启蒙、社会动员、科学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多重功能。这一行动逻辑其实很好地体现在早期教育家、被胞兄张伯苓称为“南开大学的计划人”、后曾任清华教务长(1923—1925)并协助清华学校改造为清华大学的另一留美博士张彭春(1892—1957,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的博士论文标题中:《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①Chang, Peng Chun, “Education for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Search for Criteria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e Transition in National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econdary Education”,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3。论文中文翻译版已收录于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张伯苓研究 会编:《中国价值 世界贡献——张彭春诞辰130 周年纪念文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 年。如其本人所言:“个人三十多年来……(的)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才能现代化。”②张彭春:《什么是现代化》,《公能报》1946 年第11 期。在这一代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教育改革者眼中,确保心理健康以激发精神斗志是塑造新国民、建设新社会的根本门径,并为此致力于调和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心理咨询技术、高等教育的专业性与政治目标的引导性之间的可能矛盾。这种解释不仅为执政者所看重,也为知识界所认同,并为教育界所实践,形成了一种自圆其说且环环相扣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核心使命感的自主驱动下,无论是作为民心、民意的表层社会心态,还是作为“国民性”的深层文化心理,“心理”与政治的联合一直强于作为学科体系的心理学与现实政治的联合。从灵魂到心理,从异常心理到常态心理,所有的心理内容都可通过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的解释,使心理问题变成社会问题的某种隐喻式表达,进而成为阻碍或促进民族现代化的精神 力量。
以文化传统论,这正是传统儒家式的“治心”学说的现代体现:通过个体层面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从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心灵、心理或灵魂既不是独立于躯体或肉身的生物学或哲学存在,也不是独立于文化与政治的实体存在,而永远处于与肉体、人事、政治、文化的复杂缠绕中。在这种融合了政治要求、社会思潮和学术观念的复合语境下,心理已经欠缺本体性的自然存在空间,只剩下功能性的存在状况;这种功能性存在既可沦至“被改造”的消极命运,又可变成“去改造”的动力源泉。如此,个体之“心理”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社会—政治—文化”压力的承受器,而代表民族之希望、社会之前途的青年人的“心理”更是成为育人技术的“实践空间”,因而也成为国家治理的“心灵空间”。
由是观之,相比近代中国以来的高等教育及整个教育体系对心理卫生与心理健康技术的制度性吸纳,当下“心理育人”体系中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合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虽然在指导思想与实现路径方面已经有了本质的改变与提升,但从文化心理层面看仍有一种潜在的传承和张力。“心理育人”的内在矛盾,其实是改造个体人格与整体国民性、从而使从“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人以追赶者的姿态提前完成现代化使命的内在矛盾。当然,话语层面的自圆其说并不代表实践层面的运转流畅,这种精神力量的激发方式与心理世界的改造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③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年,第181—202 页。甚至连自身的心理空间也不能例外。这可视为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借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源”④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66 页。这一问题解决模式在教育和心理健康领域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与历史余音。对这些兼具历史延续性与现实挑战性的复杂问题的求解方式,很难从西方的现有理论和传统的思想资源中找到完美的解决之道,还需要靠不间断的摸索进行探路且纠偏。
而了解此类现象的长时段性,或可使我们对当下心理育人体系中“科学性”与“政治性”等内在张力的认知增加一种“历史的共情”,从而保持一份从容与耐心。因为“在一个国家局势危如累卵的时代,再科学化的问题也难以避免被主义化的命运,社会问题的讨论尤其如此。”①唐小兵:《形塑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问题”系列图书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 史研究》2016 年第5 期。如今,中国社会的生存性危机或已基本解除,但发展性危机仍如影随形。因此,这种将社会问题的疾病化——不论是躯体疾病还是心理疾病——的隐喻式理解与治理思路,也仍将贯穿中国人的学术思考和治理实践。为此,对高校心理育人体系中之现存困境的破局,并不能完全寄期望于心理咨询方法自身的技术整合或本土化创新,而应在心理咨询、心理学甚至是整个教育体制之外反思更具本质性的宏大命题,那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自有传统如何与其时代使命更好衔接,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如何更有效地激发精神动力。这无疑需要更多的学术思考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