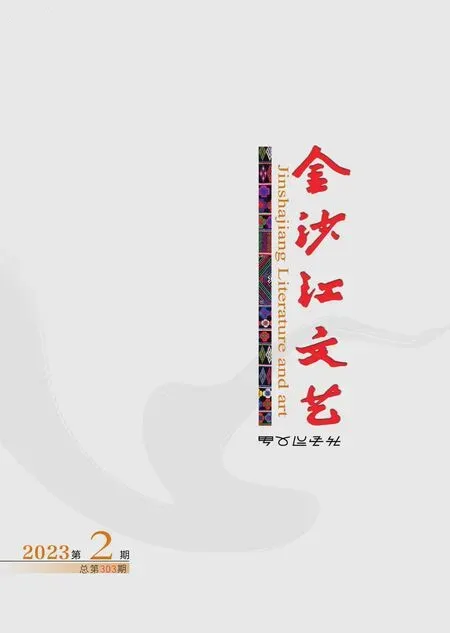大院里的岁月
2023-04-15李静白族
◎李静(白族)
下午五点半,太阳的光开始变得柔和,眼睛望向它的时候不再需要伸出手挡在额前。头顶的天空是四方形的,有几丝白云轻飘飘地浮在那里。对面张婶婶家屋顶的瓦片缝隙间生了许多草,他们从大院里搬出去两三年了,六月的雨水给了杂草放肆的理由。一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麻雀落在院子里,自如地啄食完全没把院子里的两个人放在眼里。小女孩完全被麻雀迷住了,起初她还乖乖地坐在板凳上只是用眼睛望着它,到后来头也跟着转来转去,完全不顾正在给她编辫子的孃孃。
“别动,好好坐着,快编完了。”
她赶紧把头转正,闭上眼睛不去理那麻雀,配合着孃孃的工作。
孃孃大我六岁,当时正在读初中。孃孃拥有一双巧手,一有空我总会缠着她给我梳好看的辫子。用梳子将头发轻轻地梳顺,扎一束马尾,再将那马尾大致均匀地分成十二份,分别扎上皮筋。接着,耐心地编十二个小辫子,在辫子临近收尾处依次扎上不同颜色的皮筋。从头到尾大概花了十分钟。我侧过头,看到了镜子里梦寐以求的麻花辫,感到无比的满足。明早我要穿好看的衣裳配上这麻花辫,昂着头去升国旗。
大院和我们家只离着三四分钟的脚程,从我出生起,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听爸爸说,大院建成已经八九十年了。大院原本是白族民居里典型的四合五天井设计,青砖白瓦,很有徽派建筑的韵味,但一场意外,西边的房子在火中烧为灰烬,只留下北南东三边的厢房。
在我小时候,大院总是热热闹闹的,七奶奶一家、大爷爷一家,还有张婶婶一家,给大院平添了生气。他们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里欢笑、拌嘴;在蛙声一片的农忙时节插秧,顶着夜色抹黑回家;在雨水连绵的七月里打牌闲聊。黄昏时分各家烟囱里升起的炊烟,带有淡淡的柴火的香味;大风狂扫之后偶尔从屋顶掉落的瓦片,是碎开的青黛色。院子角落里青砖上长出的苔藓,顽固地扎根。当然,大院给我的记忆不仅仅是这些,它给我的记忆更具体更细致,与实实际际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还没上学之前,爸妈白天很忙,压根没空照顾家里。于是把我寄养到大院里,请大爷爷照看我一两天,又让七奶奶照看我几天。大爷爷家的彩色电视买的很早,他和大奶奶都很爱看电视剧。大奶奶是汉族,和我们说汉话,刚开始不习惯到后来也爱跟着她玩。大奶奶的耳朵很背,眼睛也有点不好使,她总是坐在一张稍微有些高的藤椅上,而大爷爷坐在紧邻着她的矮矮的草墩上。每逢看电视的时候,大爷爷总要时不时地转头侧过身大声告诉大奶奶电视里发生了什么,妙善被谁诬陷为灾星,济公又把哪个狗腿子的脚镶满了铜钱。于是,我断断续续地跟着他们看完了或者说听完了济公,但是我一点儿也搞不懂为什么济公在新婚当天抛弃新娘,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要去当一个穷苦和尚,而 《观音传》 里常穿一身黑的张牙舞爪的女妖怪则成了我的童年噩梦之一。大爷爷家的楼梯很陡,但我爱跟着他上二楼,从窗户里俯瞰院子,要是看到院子里有人,我就铆足力气大喊一声想吓唬住他。下午六点多钟,爸妈来接我回家吃饭,日复一日。
七奶奶家每年都会种很多玉米,等把玉米收回家晾干了,就得把它剥了碾成玉米面。我小时候酷爱剥玉米,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喜欢剥玉米的感觉。每年到七奶奶家剥玉米的那段时间,我往大院里跑得尤其勤快。下午放学写完作业、星期六星期天,只要一得空就往大院跑。一年级刚接触算术的时候,总觉得有些难算不过来,院里的叔叔让我带着玉米粒去学校,说是遇到难算的就用玉米粒数数。临放学最后几分钟,老师提问了我一道两位数的加法,我从文具盒里拿出玉米粒一颗颗演算。铃声一响同学们急着回家,同桌的手肘一碰玉米掉地下了,我蹲下去捡,透过桌脚凳脚,我看到了同学们鱼贯而出的杂乱的脚,他们赶着回家而我蹲在地上,这样的我不属于他们。回家和爸妈撒气,再也不带玉米了,我一定要把数学学好。
我读三年级那会,妹妹刚上幼儿园,下午放学回家,家里的门锁着,我们没有带钥匙,大门底下的空隙很窄,钻进去也是行不通的了。七奶奶从家门口路过,把我们俩领到大院里,去灶房给我们烫了两碗饭,往里加了白糖。我还记得,我和妹妹一人坐了一个草墩,把碗放在一长条板凳上,在堂屋旁用勺舀着有滋有味地吃着。吃完饭,我们拿出课本和练习册,坐正身子认认真真写作业。
站在七奶奶家二楼楼梯口,刚好可以看见我家大门,门前的一切一览无遗。嬢嬢读初中,放学时间比我们小学晚两个小时,有时候吃完饭之后她会上楼梯口看看,如果我和妹妹恰好在门口玩,就喊我们过去大院里找她。但更多时候,是我领着妹妹早早地守在院子里等她,我们留心听到的任何声音,自行车的铃铛声一在大院门外响起,我们就知道这是嬢嬢放学回来了,妹妹总要抢着跑朝前去迎接她。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切身明白了等待和翘首以盼。
我们看着她把车推进大门再用手抓紧车身把它抬过二进门的石阶,我们跟着她走进灶房守着她吃饭。她涮完碗把我们领进她的房间,拿给我们图画书,然后拉开书包上的扣子拿出我看不懂的书开始一篇一篇写字。有时候,嬢嬢会给我看全是字的书,遇到不懂的字我就停下来问她。慢慢地我在她那里读完了安徒生童话全集,读她的语文课本,实在没书了就去看叔叔的高中语文课本,接触了朱自清、老舍。那会我最爱童话故事,其他只是我识字的工具,字里行间的意思晕叨叨的,我一点儿也不能明白。
逢年过节,是大院里最热闹的时候。两张四方桌拼在一起,各家拿出来几个板凳,老人坐主位,其他人挨着落座。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菜在这时候都能吃得着,这家端出来萝卜炖排骨,那家整一盘生皮。炸乳扇、油炸花生米、青菜汤、干煸洋芋丝……,空荡荡的饭桌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填满。大人们往碗里倒白酒,觥筹交错,小孩子喝百事可乐或者青梅爽,大一点的女娃娃也不准喝酒,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家有时候会参与到大院的大聚餐里,很多时候会把大院里的人请到家里吃饭。我和妹妹吃一小会就吃好了,我们退到饭桌外,坐在堂屋门前的石阶上,看着他们喝酒聊天。他们笑着,大声嚷着,过一会儿脸色变红。天黑下来不要紧,也不往院里格外拉灯,就让灶房里透出的昏黄灯光配上月色,为他们照明。
到后来,大爷爷家添了个大胖小子,又过了几年,添了个孙女,大院里越发热闹了。我和妹妹开始接过爷爷奶奶叔叔嬢嬢们手中的接力棒,成为照看小孩的主力军。这俩弟弟妹妹特别爱跟着我和妹妹玩,一口一个“大姐姐” “二姐姐”。婶婶会在白天把他们俩寄养到我们家里来,于是我们带着他们看电视、玩躲猫猫,等小妹妹再长大一点,她就能参加我们的跳皮筋活动。
在流动的光阴里,大院里的人来来去去,有人离开也有新生命降临。大奶奶临终前我和家人去病榻前看望了她,眼睛混浊;大爷爷生病了走路颤颤巍巍说话慢吞吞的,我和妹妹去给他送了晚饭,他客气地道谢看着我们走出大门,再过了两个月他溘然长逝。我眼看着嬢嬢去读高中读大学到后来成家,成为小时候我最想成为的大人;小妹妹一天天长大,到后来话变得越来越少转眼竟然已经读初三了。在单向的时间坐标轴上,每个人都在往前,带着从前的记忆往前。
现在每逢春节,我们仍然去大院里吃饭,在外求学工作的人通通回归到大院,坐在一块谈笑风生。年夜饭的原则是尽可能地抛开电器选用柴火烧菜,妈妈去生火煮鱼,七奶奶切生皮,叔叔烧水,我和妹妹帮着洗菜洗碗,七爷爷和爸爸在院子的一角下象棋,各司其职。炊烟升起来的时候,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有那些旧面孔的小时候。毫无疑问,在流动的光阴里,大院成了一个联结,我们的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以更好的身份出现在院子里,出现在和亲戚朋友们相聚的饭桌上。我们逼迫自个儿努力向上,因为只有出落得有本事,才能更坦荡地怀念那些消逝的身影。
像是系了一根线,高飞的风筝乐意受这绳线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