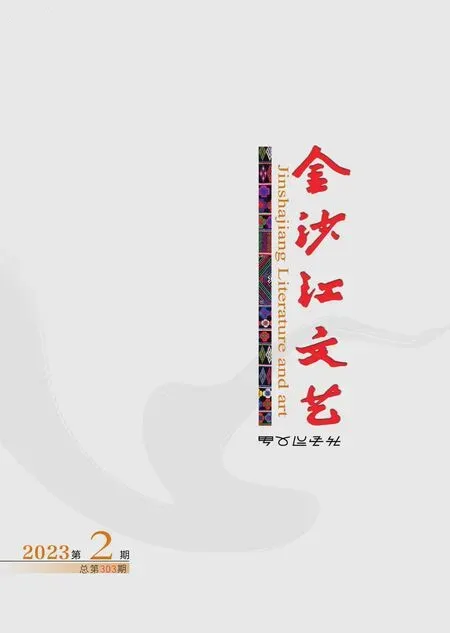游向太平洋的鱼
2023-04-15周海鸟浙江
◎周海鸟(浙江)
一大团一大团的墨云飞滚着,疾速而来,瞬间铺满了整个天空。鹤唳的风裹起枯叶、残枝,打着旋儿,杀气腾腾地横冲直撞。
浑黄的海浪,在极远处拉开一条长长的白链,如一排排行伍整齐、训练有素舍生忘死的勇士,所向披靡,猛烈地撞上礁石,发出惊心动魄的巨响。
我静静地站在岸边,心底掀起一波比一波更为强烈的海啸,汹涌而来,堵得心口一阵阵发疼。眼眸湿了,心,落泪了。记忆中弄潮的少年,鲜活了起来。
那少年是表哥,我二舅的儿子。表哥和我同龄,我们相处极为融洽。每年暑假去外婆家,他最喜欢带我到海边玩。我不识水性,每次去海边,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他和小伙伴们打水仗,扎猛子,玩憋气。只见他穿着小裤衩,光着被炽热的阳光染成酱黑色的身子,在海中时浮时潜,时快时慢,像一条光滑的黑鲶鱼穿梭自如。有时故意潜入水中好长时间不上来,急得我在沙滩上跺脚、叫喊,当我带着哭腔拖起长音急切呼唤的时候,哗啦啦一阵水响,刺啦一声,表哥钻出水面,抹了抹脸上的水珠,笑吟吟地望着我。表哥的水性极好,仰游,潜泳,蛙游,各种姿势都游刃有余,小伙伴都叫他 “小黑鲨”。
夏夜,凉风习习,在一棵被雷劈去一半的老树下,我们坐在嘎吱嘎吱响的竹椅上,外婆轻轻摇着蒲扇,不紧不慢,用她零星的几颗牙,不紧不慢地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海盗、台风、财宝、沙滩、小岛,断断续续,晚风呼呼,我们生拼硬凑出这片海,这块土地,这座小岛的前世今生。表哥悄咪咪地在我耳边低语:“明天,我们去沙滩,挖宝,别让其他人知道,就我们俩。” 我用力地点点头,黑暗中,两双眼睛烁烁生辉。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片沙滩,沙滩上到处都是人,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忙碌地挖沙子,细腻平整的一片沙滩转眼间就像是春耕后的田地。有人欢呼着,举着手中的宝贝,无比兴奋地炫耀着。
第二天中午,滚烫的日头炙烤着大地,大人们都休息了,只有树上的蝉还在撕心裂肺地鸣叫着。表哥带着我,偷偷地溜出来,奔向沙滩开始淘宝。大中午的沙滩很安静,除了哗哗的海浪声,就只有我们几个不安分的顽皮蛋儿,赤着脚,踩在滚烫滚烫的沙子上,跳跃式前进着。大家挖得很起劲,有带工具的,有干脆徒手挖的。沙子扬起来,满头满脸都是,一个个都是沙猴子。我严重怀疑,昨晚他们的奶奶外婆也都给他们讲了同样的故事。表哥长得高高大大的,力气很大,不一会儿,他就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每一寸的沙子都像过筛子式地滤了一遍。我有点心不在焉,火球般的日头烤得我没一点精神。表哥不断地安慰我,再挖深一点,就可以挖到了。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前几天,有人挖到了一个玉镯,有人挖到了银圆。很显然,他被这些信息鼓舞着,激励着。最后,我们带着一身的沙子回家,一无所获。接下来,说什么我都不愿再去沙滩了。表哥锲而不舍地又去了。晚上吃完饭,我坐在雷劈过的老树下,摇着蒲扇,表哥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无人的角落,悄悄地往我手心里塞了一个东西,嘱咐我没人的时候打开。我紧紧地攥在手里,生怕有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入夜,无人,趁着天窗投射进来的月光,摊开手,那东西硬是在手心里留下一道深红色的印痕。仔细一看,是一枚极细极细的银戒指。颜色发暗,显然是埋了很久,竟然没被腐蚀。这一刻,我感动得差点流下热泪。不知道表哥在烈日下曝晒了多长时间,挖了多久才挖到这么小的一枚戒指。
记忆中,我们曾无数次并肩坐在这片海滩上,一起望向海的极处,水天相接的地方。海蓝得像璀璨的宝石,天蓝得像外婆箱子底下簇新的蓝长叽布,云朵白得像刚从棉花树上剥下来的棉絮,整个画面像一首蓝色咏叹调的下行诗。
海的性情有点令人难以捉摸,有时候像西班牙斗牛场上的牛,旁敲侧击,横冲直撞;有时候像巴黎的绅士,浪漫温顺,彬彬有礼;有时候又像蒙着面纱的蒙娜丽莎,端庄、神秘。白天和黑夜,晴天和雨天,每个季节,甚至每个月,海的颜色变幻莫测,景色各异。有时浑黄,有时清,有时朦胧,恍如仙境。或娴静,或明媚,或疯狂,或深邃,或张扬,或妖娆,各具风情,这是表哥告诉我的。他还跟我说,水下的风景更美,有成群结队的鱼,体形各异,颜色,斑纹不同。有蹦着行进的虾,弓着身子,如给它拄上一根拐棍,活脱脱就是一个乡下佝偻着身子的老爷爷;有横行滩涂的蟹,骄横跋扈;有长长触角的墨鱼,触须舞动,忽而像盛开的芍药,忽而如带刺的蔷薇;还有美丽的珊瑚群,颜色鲜艳,绵延开去像一幅风景绮丽的山水画卷,蔚为壮观。这些都是他潜入水底看到的景象。我在他动情的描述中,想象那一片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
表哥说他这一生最崇拜的人是郑和。郑和浩浩荡荡下西洋的历史如一颗种子,在他的心头生根萌芽。他憧憬着有那么一天,像郑和一样,到父辈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到世界上最辽阔的大海上,扬帆起航,开拓海疆。我歪着脑袋,侧着身子,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表哥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神晶亮晶亮的,焕发出光彩。
表哥初中没毕业,就下海了。第一次出海,背着背包,挺着脊梁,精神抖擞,黑黝黝的脸蛋泛着油油的光。年迈的外婆站在自家的院门口,手搭凉棚,眼巴巴地看着表哥向码头走去。码头上,血一样红艳艳的旗帜呼啦啦地飘扬着,船尾的螺旋桨激起一长串欢快的浪花,船儿冒着滚滚的浓烟驶向大海,化为黑点,最终彻底消失在外婆的视线。年迈的外婆不停地抹着眼泪,一个劲骂舅舅心狠,怎么舍得让这么小的孩子下海。
表哥每次返航,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分获的海鲜,踱到生病的外婆床前:“阿浦 (方言:奶奶),这是孙子亲自捕来的鱼,透骨新鲜,您吃了返老还童。” 外婆看着表哥黧黑粗糙的脸庞,心疼得老泪纵横。
表哥的个性有点内向,不太喜欢讲话,每逢我去他家,便一股脑儿地倒出来,连同芝麻黄豆大小的事,无巨细。他说他看到大海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和他想象中的一样美,一样的波澜壮阔。早晨,太阳从海平线升起,绚丽的朝霞染红了天空,海面上金光闪闪。蔚蓝的海面上,洁白的海鸥扇动着翅膀,盘旋在船尾。夕阳西下,舟楫,云帆,海鸥,融合成一幅幅唯美的剪影。朝朝暮暮,在美丽的背景下,扬帆,起锚,劳作,生活像一首诗,如一幅画。
最激动的事情莫过于网徐徐出水的那一刻,所有人列队在甲板,看着鼓鼓囊囊的袋筒 (网的尾端,聚焦渔获的部分) 缓缓吊到甲板上方,一解开,瞬间,甲板上,舱面上,到处都是活蹦乱跳的鲜鱼、张牙舞爪的螃蟹、水蛇般滑腻的鳗鱼、扁着身子的鲳鱼、鼓着腮帮的红眼鱼、金灿灿的黄鱼、银闪闪的带鱼、磨砂质感的石斑鱼,层层叠叠,相互拥挤……它们蹦着跳着,不停地挣扎着,那场景有难以描述的壮观。遇上这情景,几天几夜不休不眠的劳累,转眼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望着他豪迈的神情和年轻的倦容,心中涌上的不舍被所描绘的壮丽场景层层覆盖了。
表哥慢条斯理地叙述着,我的心就像过山车一样,时而雀跃,时而凝重,时而在高山,时而在低谷。最令我揪心的就是他们经历大风浪的事。表哥说,一个浪头呼啸而来,足有三层楼高,没头没脑,从船头到船尾,直接把整艘船搂在怀里。船就像凋零的树叶,在大海上左右摇晃,上下颠簸。菜盆子、酒瓶子、饭碗,打着滑,打着转,不停地掉落、碰撞,乒乒乓乓的声音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像醉汉东倒西歪。最厉害的一次,船起船落之间,落差犹如庐山瀑布,船身与海面几乎呈直角,连多年的老水手都踉踉跄跄,必须得扶着,靠着,才能稳住身形。表哥不敢站起来,也站不起来,只得趴在甲板上,像只滑稽的八爪鱼,牢牢地贴在甲板的舱面上。尽管如此,在船前俯后仰的作用下,他在舱面上像个任人摆弄的布娃娃,浑身使不上劲儿,随着船身的剧烈摇撼从船这头滑到那头,又从那头滑向这头。船上到处都是尖锐的锚,碗口粗的绳索,高速运转的机器,一磕一碰,生死难卜啊。没办法,舅舅只得拿绳子将他绑在桅杆上,那模样就像个行将就义的小英雄。他说,那个过程真叫 “呕心沥血”,肚子里一阵阵排山倒海,脑子里一阵阵天旋地转,浑身都湿透了,不知道是汗还是水,大口大口地吐着,后来,实在没东西吐了就吐血,吐黄色的胆汁。我说,哥,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才怪呢,我想这次小命没了。想想很不甘心,我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还没有好好享受人生的快乐,难道我就这样走了? 然而,当我看到在大风浪中依然镇定自若的父辈们,他们不慌不忙地干着手里的活,下网,起网,拣货……各司其职,各就各位,有条不紊。这才是真正的水手,我要向他们学习,也要成为这样的男子汉。在那个滴水的屋檐下,我挥舞着稚嫩的拳头,给表哥鼓劲,祝福他从此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0岁的年纪,梦想很近又很远,当很多人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踌躇、游移的时候,表哥当机立断,只身踏上了去印尼远钓的船,因为梦想,也因为现实,一去就是三年。那时没有微信也没有QQ,我们之间跨越了千山万水的距离,只能通过信件来维系。一封信送达彼此的手中,辗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比愉悦地写信告诉我,他达成了毕生的夙愿,来到了世界上最大、最辽阔的海,太平洋。太平洋的辽阔超乎了他的想象,他们航行了整整一个月,感觉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表哥说,看到太平洋的刹那,心灵被深深地震撼,真正见识了什么叫海纳百川。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似乎有千言万语争先恐后地哽在喉间,少年时的梦想,如此真实地呈现在眼前,不是一厢情愿的梦,也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他想呐喊,想跳跃,想向全世界宣告,至终将汹涌澎湃的情感封存在心,诉于笔端,寄了封信给我。他说,妹,你真的应该来看看,太美了,瓦蓝瓦蓝的天,碧蓝碧蓝的水,一个个充满了异域风情的岛,星罗棋布般点缀其间,像波希米亚女子项链上镶嵌的宝石。海是陌生的,语言是陌生的,风土人情是陌生的,连空气也是陌生的,甚至鱼也是陌生的。表哥说,太平洋的鱼儿比我们这儿大两三倍,带鱼有成年男子的两个手掌宽,最长的跟人差不多高,蜷在一边,像条银色的水蛇;钓上来的鱿鱼体形硕大,肉质肥厚,口感却远不如家乡的鲜美。
晚风吹来,难得风平浪静的夜,星星在头顶闪烁着光芒,像亲人的眼睛。月光照在海面上,像是撒了一地的碎钻儿,波粼波粼得晃眼。依着船舷,同行的水手轻轻地哼起口哨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整整三年,漂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最初的悸动之后,便是无休止的寂寞。思念,象康河水波里荡漾的水草,缠绕、煎熬他的心。他说,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我们寄去的信,反复地读,一字一句地读,似乎想把我们从这些文字里活生生地抠出来。
太平洋多风暴,比在家乡的台风突兀、凶险。有一次,突遇风暴,船舱进水,差点就倾覆了。我说 “哥,何苦呢?” 他回 “妹,这是我平生的夙愿,再苦,再累,此生无憾了”。此时的他,不再是当年沙滩上信誓旦旦的顽童,也不再是被绑在桅杆上“呕心沥血” 的少年了,大海将他磨砺成了一个真正的水手,真正的男子汉,一个敢于只身离乡背井,在太平洋上漂了三年,笑傲风暴的男子汉。
三年后归来,结婚,生了个可爱的女儿,人生圆满了。他还是选择出海。
我劝他:“哥,在岸上找个活吧。” 他说:“妹啊,哥这一辈子就离不开海了,我像长了腮的鱼,离开海就窒息。”
理所当然地以为,哥守着他的人生,守着他的婚姻,守着他可爱的女儿,守着他心心念念的大海,直到暮色苍茫霜染两鬓,拄着拐棍抖抖索索,如我们的先辈们所经历的,生于厮,终老于厮,最终随风而逝,逐云而去。
28岁,风华正茂的年龄,我也是,表哥也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噩耗,将一盘蒸蒸日上的棋局彻底打乱,象,卒,马,车,四下乱蹦,乱跳,散了,碎了……
黎明前,天快亮了,船上的伙计们干完了活,几天几夜都没合过眼了,大家一沾上床,头刚挨上枕头,脚还没上来,已经进入梦乡了,太累了。悲剧就在此时,发生了……一艘国际货轮,在夜色里直直地驶来,碾压了表哥的船,又毫无知觉地往前驶去,海面重新恢复了平静,除了油污不断扩散,网儿散乱地漂浮着,黑暗如此厚重,十多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无声地消失在黑暗中,消失在了这个世界,无一生还。
噩耗传来的时候,我的手和脚不停地哆嗦,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实在无法相信,表哥就这么没了。那个被称为 “小黑鲨” 的少年,那个太平洋的风暴都没能将他吞噬的青年,怎么就在一个风平浪静的黎明,悄无声息地走了呢? 他五岁的女儿骑着一辆小自行车,懵懂地看着哭得呼天抢地的大人们。孩子依偎在妈妈的身边,偷偷地问:“妈妈,爸爸怎么了?”
他像一颗流星,陨落在海的深处;更像一尾鱼,永远留在了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