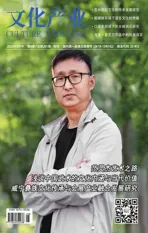诠释学视角下射礼的研究
2023-04-15杨婷杰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杨婷杰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是指在诠释学视角下对具有丰富形态的符号组织形式及符号意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礼记·射义》中记载的射礼内容渗透了先秦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现将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与科学的分析方式相结合,分析总结“射以观德”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
前言
从2014年内蒙古高校成立大学生传统射箭协会开始,射箭运动的普及化进程不断加快。本文旨在厘清射礼等多种符号的外部表现与内在含义,将符号意义与现实情况相结合,进而分析射礼符号体系中的优秀文化。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礼记·射义》的文本内容,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法、词频分析法、符号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图像学研究法。《礼记》主要记载了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其中,《礼记·射义》曰:“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显然,“射”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兼具德行礼仪教育的功能。
游戏文化机制的符号学能够对具有丰富形态的符号组织形式及其符号意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只有将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与科学的分析方式结合起来,才能体现出“射以观德”的历史文化价值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进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礼记·射义》的符号赋义
宗争在《游戏能否“讲故事”——游戏符号叙述学基本问题探索》中,尝试在游戏研究中引入符号学与叙述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廓清、剖析游戏文本,重新审视游戏及相关现象。他将游戏划分为“游戏文本”与“游戏内文本”两类:一是“游戏内文本”,其以“符号化”为基础,以“计算”为法则,不因时间变化而变更,不以游戏者的意志为转移,即其是以内部规则为主要联系的内文本,是游戏的核心;二是“游戏文本”,也就是游戏活动的最终样态,是游戏的观众阅读的文本,即用来描述最终文本的外在演绎模式,其可以随着不同情境的转换而发生变化。
《礼记·射义》中的“秩序情结”和“以德引争”等是由诸多文本符号构成的,只有经过符号解读的过程,才能对其进行精细化的文本分割。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射箭活动的游戏设计者是君主,游戏参与者主要是贵族、政治精英及士族阶层。对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将其分为:动作符号、声音符号、顺序符号、实物符号、方位符号。其中,动作符号主要为“直”“正”;声音符号主要为“节”“乐”;顺序符号主要为“君臣”“诸侯”;实物符号主要为“侯”;方位符号主要为“四方”。
动作符号(“直”“正”)是设计的强制性动作标准,是一种内在的专注、精神的修炼,代表心平气和,有规有矩;实物符号(“侯”)即侯为箭靶,射礼便是射“侯”,意味着争取上游,锻炼技能;顺序符号(“君臣”“诸侯”“大夫”)是“等级有序”,是秩序情结;方位符号(“四方”)为“上下天地为神佛”,即对自然的征服,表明人类不断向外探索,寻找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符号分析的综述来看,《礼记·射义》中的文本符号阐述了中国的射礼文化,游戏的符号规则构建了中国射箭领域的范畴体系,体现了“君子之德始于射箭场上的方寸之间,胜者,继续弘扬;败者,重新来过”的人生之道。文本也从竞赛的符号学视角进一步诠释展现了运动员的气度和技能。
依托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文本内容进行剖析,从四次赋义入手,通过“能指”“所指”等诠释学符号论,展现射礼规则,宣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礼记·射义》动作符号赋义
在《礼记·射义》中,“射”“直”“正”在动作符号中占前三位。“射”为射礼之本来动作,“直”是指在射箭时身体要保持立正,“正”是指持箭姿势和站立姿势要端正。
游戏设计者规定了射箭动作的标准。在第一次赋义时,身体保持立正是游戏设计者的要求;游戏参与者如贵族、士大夫则按照规定的标准,作出合乎规范的姿势,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呈现出游戏文本,完成第二次赋义;观者通过观摩反思,完成第三次赋义,即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最后人们遵守这些规则,使其具有丰富的社会意义,从而完成第四次赋义。
纵观四次赋义,在规范动作标准的过程中,游戏参与者一直都处于一种平静状态。《礼记·射义》中动作符号的赋义启迪当代人应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追求平静,在盲目的失调中寻求一种平衡。
《礼记·射义》声音符号赋义
《礼记·射义》声音符号
在《礼记·射义》中,“节”“乐”在声音符号中占前两位。“节”是指节奏,“乐”是指整个射礼过程中的音乐。
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文本的声音符号是一种依托听觉器官,从游戏设计者的自身属性延伸出来的较为重要的符号体系,在符号学中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
不同的声音节奏代表不同的频率,也象征着周天子对群臣的约束。在整个射箭过程中,不论是对音乐的选择,还是对音乐节奏的配合,都极具仪式感,可以让射击者的灵魂得到洗礼,让对仪式的欣赏达到新的高度,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前来观礼的人们。
声音符号的游戏学赋义
在第一次赋义时,节奏合拍是游戏设计者对射箭配乐及节奏的要求。游戏参与者如贵族、士大夫则按照规定的音乐节拍,呈现出游戏文本,完成第二次赋义。观者通过观摩反思,得出需要遵守的规则,完成第三次赋义,即确立了社会自上而下的制度;同时这也使得每个人明确自己的等级,不再存在非分之想,从而完成了第四次赋义。在当今社会,声音符号的游戏学赋义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许多商业电影都会选用旋律合适的伴奏,以烘托氛围,达到想要的效果。总之,声音符号在当今社会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
《礼记·射义》顺序符号赋义
《礼记·射义》中的顺序符号
顺序符号主要是对“君臣”“诸侯”“大夫”这些社会地位不同的人所面临的游戏规则进行详细分析。
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有不同的规则,对其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如《白虎通德论》中所言:“天子射百二十步,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远也,卑者所服近也。”另有一段自问自答,可以解释上文“尊卑之射”的描述。“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诸侯射麋者,示达远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射两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阴数偶也。侯者以布为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则末正矣。名之为侯者何?明诸侯有不朝者,则当射之。”在周王朝的等级制度中,包括射礼等在内的不同社会行为对各个等级的人都进行了详尽的约束[2]。但这并不是对低等级的人的压迫,相反,是对更高等级的人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越高等级的人,在规则上就越严格,将其衍生到德行层面,即高等级的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
顺序符号的游戏学赋义
规定射箭的“君臣”“诸侯”“大夫”的血缘宗法制是游戏规则的第一次赋义。在整场射箭仪式中,旁观者和参与者的“等级有序”,则是第二次赋义。射击结果与择士、封地等封赏挂钩,造成士大夫的“秩序情结”,从而完成第三次赋义。这种社会性活动在第四次赋义中兼具两个作用:首先是对各臣子的守礼程度,以及其对皇室的效忠程度;其次,将礼乐制度内化于心,展示自己的修养和德行。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都会出现一种现象:臣民无敬畏之心。比如,中国古人对神明的敬畏并不是恐惧,而是借由对神明的道德要求,维护社会秩序[3]。
《礼记·射义》实物符号赋义
《礼记·射义》中的实物符号
在《礼记·射义》中,“侯”被多次提及。根据《辞源》《辞海》的解释,“侯”即箭靶,一般是指用布或兽皮做成的靶子。参赛者是否能一击即中成为其是否能脱颖而出的标准,也成为其能否获得侯爵之位的唯一判断标准。
《周礼》郑注:“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饰其侧,又方制之以为,谓之鹄,著于侯中,所谓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诸侯之大射,熊侯,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国之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参七十,干五十,远尊得伸可同耳。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在整个瓜分土地和拟定爵位的过程中,射“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对“侯”的射击便是对制度和等级的追求。
实物符号的游戏学赋义
游戏设计者将箭靶命名为“侯”,完成了第一次赋义。“侯”为箭靶,射礼便是射“侯”,将“射侯”与官位和晋升挂钩,完成了第二次赋义。“侯”作为择优的标准,成为参射者对自我的要求,而在观者的潜意识中也会树立竞争意识,凭借射礼来获取功名,这是第三次赋义。诚信友善,相互竞争成为射箭者的规范,这是第四次赋义。同样,在现代社会,人们依托竞争来磨炼技能,对规则的向往和尊崇是一以贯之的。
《礼记·射义》方位符号赋义
《礼记·射义》中的方位符号
《礼记·射义》中记载:“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求反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诗》曰:‘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其中“四方”象征四方的天地,“射四方”代表了对“好男儿走四方”的期许[5]。
方位符号的游戏学赋义
“四方”是古人对时间空间的总体认知,此为第一次赋义。在对自然界的神秘充满好奇与恐惧的时代,“射四方”象征古人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他们在沟通中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此为第二次赋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中包含了理性的折射,从“自然发生”进入“社会创造”的层面。从自然方位的“四方”到时间轴的顺延,让人们在礼乐制度中获得了对整体意识的把控,此为第三次赋义。在当今社会,大局意识与信仰观念是方位符号的第四次赋义。大局意识是古人对“四方”的掌控,是对周天子“掌握天下”的折射,也是当代人向外探索更为广阔的天地的精神[6]。
研究结论
诠释学机制下的游戏规则模式为“文本原意”的核心,玩者通过读取“读者接受之义”参与其中。这一科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射礼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更科学的研究方向迈进[7],也推动了射箭运动的普及进程。
总之,《礼记·射义》中的文本原意阐释了中国的射礼文化,弘扬了“礼”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游戏的符号规则构建了中国在射箭领域的范畴体系,即射礼依托射箭竞技活动,为射箭行为赋予了检验“德行”的意义,从而将整个射箭活动改造为一种礼制文化系统,并要求参与者遵循“进退中还必中礼”的严格仪式规范。君子之德始于射箭场上的方寸之间:胜者,继续弘扬;败者,重新来过。前人的规则和制度,给予了吾辈思想上的启迪、行为上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