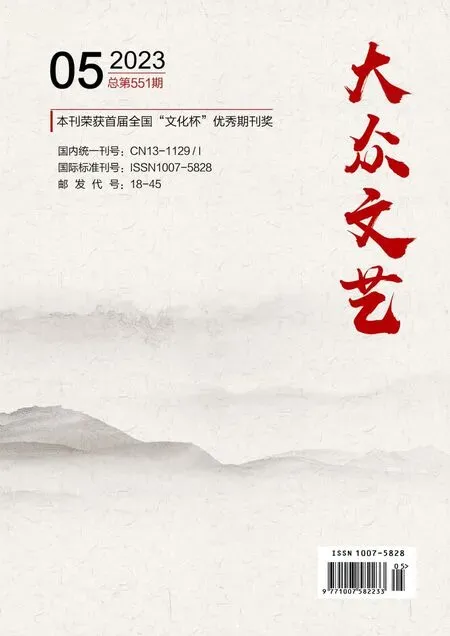蒲鲁东形象新论:无政府主义之父抑或小资产者
2023-04-15林剑锋
林剑锋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 310000)
1865年蒲鲁东去世,马克思写道:“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1]然而在学术界,蒲鲁东还有一个头衔——无政府主义之父。迄今为止,蒲鲁东无论是作为小资产者,还是作为无政府主义之父,国内学界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过研究。然而,蒲鲁东何以同时兼具这两个头衔呢?目前学界还未就两个头衔之间的张力做进一步的探究。本文在法国有关蒲鲁东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从法国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蒲鲁东的形象。
一、制造无政府主义之父
本节之所以用制造无政府主义之父这一标题,并非要褫夺蒲鲁东无政府之父的头衔,而是为了阐明蒲鲁东是何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之父。
在某些著作中,无政府主义的渊源可上溯至古代。克鲁泡特金等人就构建了一套无政府主义的谱系。从中国古代的老子到古希腊的芝诺、犬儒学派;从耶稣基督到16世纪的拉伯雷,各种人物都被打上了无政府主义的烙印。不过蒲鲁东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1840年,蒲鲁东第一次指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2]那么,无政府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有两个维度。一是进入民间话语的无政府主义;二是学术界探讨的无政府主义。
就第一种维度而言,无政府主义往往与反叛、暴乱等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并非无水之源。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塑造了大众的认知。1877年,安德烈·科斯塔提出了“行动宣传”的策略,即用行动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克鲁泡特金在《反抗者报》中提出:“我们应该通过言语、匕首、步枪、炸弹来进行不停的反抗……任何违法的行为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3]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于1892-1894年间达到了巅峰。1892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拉瓦绍尔杀死了两名法官,1894年6月法国总统萨迪·卡诺遇刺。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头衔就是在此种情境下诞生的。在1883年的六十六人大审判中,克鲁泡特金说道:“人们还在谴责我,说我是无政府主义之父……无政府主义之父是1848年第一次阐述这一思想的蒲鲁东。”[4]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将无政府主义之父同蒲鲁东联系了起来。
然而,此种无政府主义并不符合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写道:“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同样地,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5]在他看来,无政府状态首先是有序的。这是因为蒲鲁东对秩序有着特殊的认知:混乱的根源乃是由于存在着绝对、统一、集中。而他“把所有系列或匀称的安排称之为秩序。秩序必然意味着分裂、区别、差别。所有不可分、难以区别、没有差异的事物都不能被视为有秩序的:这些概念是相互排斥的。”[6]因此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所强调的乃是一种多元共存且互相协调的状态。
而且在19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蒲鲁东虽然享有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头衔,但在论述中却很少有文章提及他。据学者的研究,1914年前,蒲鲁东的任何著作都没有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再版。在不计其数的宣传册中,只有两部转载了他的文章。著名无政府主义者让·格雷夫回忆道,“其中一篇直接提到蒲鲁东名字的文章只发行了1万份,相较于《反抗者报》《反抗报》和《新时代报》在35年间所发行的两百万份册数,这样的发行量只是沧海一粟。”[7]
从第二种维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学说虽然很多,但基本秉持着否认任何权威的原则。德国无政府主义的著名代表斯蒂纳声称“以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他宣扬彻底的个人主义,追求绝对的自由。俄国的巴枯宁则对蒲鲁东最具“破坏性”的著作尤为推崇。然而,他却认为蒲鲁东晚年的著作偏离了原来的思想。在巴枯宁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他强调要消灭一切权威,建立个人的绝对自由。
然而,即便是在否认权威这一点上,蒲鲁东也不同于绝大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晚年的著作中,蒲鲁东已不再那么厌恶权威。他认为权威和自由相互依存,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二者之间找到均衡。而所有的政治架构,都可以归结于一句话,即“用自由来权衡权威,用权威来权衡自由”。[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转变是蒲鲁东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在其生涯早期,蒲鲁东的确对权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始终是言辞的激进大于实质的否定。这从蒲鲁东对所有权的批判就可以预见他日后对权威态度的转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1851年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颠覆了第二共和国。蒲鲁东却呼吁“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聚集在波拿巴的麾下……波拿巴代表了大众的利益,社会革命的实现只有通过一个人的专政集权才能实现。”[9]由此可见,虽然蒲鲁东反对权威,但反权威并不是第一位的。当权威可以用于推行社会革命时,蒲鲁东并不排斥个人的专政集权。
既然如此,蒲鲁东是否还能匹配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头衔呢?法国专家让·梅顿指出:“如果说蒲鲁东超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范围之外,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内容是在蒲鲁东的著作之内的。”[10]
蒲鲁东著作中所体现的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内容,就在于蒲鲁东对经济的重视。蒲鲁东首先是以批判所有权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在之后的生涯中,他也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分析经济现象。马克思对蒲鲁东1840年的著作大为赞赏,认为这一著作是国民经济学的一大飞跃,著作充满了科学性。而出版于1846年的《贫困的哲学》同样是一本分析经济现象的著作。蒲鲁东在其中指出了价值、分工、竞争等因素都存在着二律背反。他并不谋求消灭以上各种因素,而是寻求将它们调和起来。第二共和国期间,蒲鲁东组织人民银行,鼓吹无息信贷的理念。19世纪中叶的法国仍沉浸在密西西比泡沫和指券所带来的恐慌中。人们对纸币缺乏信任,产品的流通性很差。二月革命爆发后,现金缺乏和信贷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蒲鲁东是将无息信贷的理念当做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来看待的。除此之外,蒲鲁东还写了一系列有关经济的著作,例如《税收理论》《所有权理论》等。他在晚年还提出了互助主义的思想,希望通过公正的交易实现社会的变革。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果说蒲鲁东仍可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那么这并非由于他否定任何权威,而是因为他始终强调经济对政治的超越。用蒲鲁东的话来说,政府会消融于经济组织当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无愧于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头衔。
二、法国小资产者
既然蒲鲁东重视经济,那么他到底持有的经济思想呢?本文以为蒲鲁东确乎是一个小资产者,但应特别指出,他是一个法国小资产者。
在其生涯早期,蒲鲁东的确对所有权做了无情的攻击。在《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存在着一些耸人听闻的论调,比如所有权就是偷窃;所有权存在的话,社会就会灭亡;所有权是暴政的来源等。蒲鲁东在书中向当时的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开火,雄辩地驳斥了各种论证所有权合理的论据。如果据此认为蒲鲁东是个共产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蒲鲁东话锋一转,开始批判起共产主义来。他认为共产制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共产制是另外一种意义的不平等。私有制是强者剥削弱者,共产制则反之。
蒲鲁东既不支持私有制,也不支持共产制。事实上,蒲鲁东对占有情有独钟。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占有不同于所有,“占有不但可以导致平等;它还可以防止所有权。”[11]然而这一定义势必会引起困惑,占有在多大程度上能与所有区别开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理解那句名言“所有权就是盗窃”。马克思睿智地指出:“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12]既然所有权就是盗窃的话,那么盗窃所有权,就相当于盗窃了盗窃,这就荒诞不经了。因此蒲鲁东的所有权必然另有所指。蒲鲁东指出“所有权是收益权,即一种不劳动而生产的能力。”[13]这些收益权具体地来说是指地租、房租等收益。蒲鲁东在与阿道夫·布朗基的通信中进一步指出:“布朗基先生承认在所有权的行使上存在着很多流弊……在我这方面,我却专门把所有权称作这些流弊的总和。”[14]
因此,蒲鲁东既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支持共有制,而支持人人各食其力的小资产制度。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对蒲鲁东小资产者的评价切中肯綮。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蒲鲁东是否是一个小资产者,而在于小资产者的影响力。在一般的认知中,19世纪,西方现代社会方兴未艾。在此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了整个西方世界:机器的大规模运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遍布全球的铁路网等等。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日益撕裂成两个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时代最突出的形象往往会固化成一种不加区分的刻板印象。19世纪,英国是工业革命最为彻底的国家。因此英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无产阶级。工人们居住在工厂内,劳动产品不为自身所有,靠着微薄的工资度日。而且随着分工的细化,流水线的工作枯燥、乏味,终日操劳的工人非但没有习得一技之长,反倒在枯燥的工作中迷失了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但是英国的情况不能完全比附在法国身上。在19世纪的法国,工人阶级并非同质化的存在。工人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人们通常的认知。正如19世纪的一位工头所写的那样:“如同社会一样,纺织业或织工阶级也可以分化再分化。它有自身的穷人和富人,有自身的贵族和卑微的臣民……”[15]
里昂的纺织业为我们考察蒲鲁东的理论提供了范例。首先,里昂的工人群体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有权就是偷窃针对的正是不劳而获的那部分收益。里昂的8000余名作坊主与学徒一道在家中劳动。在成为作坊主之前,他们都对纺织技术有着一定的专业认知,懂得织机的组装和维护。在经营管理的同时,他们也和其他工人一样干活。在工厂中,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同一地点,工人们与老板的关系日渐疏远。而在这些分散的小作坊里,作坊主与学徒们仍保持着密切的直接联系。
其次,这些工人群体正是以占有的形式拥有生产工具。作坊主是织机的所有人,织机的购买和维护都由作坊主承担。一般情况下,这些生产工具不会成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也不会成为资本生息的来源。作坊主既是织机的所有人同时也是使用者。
第三,这些工人群体具有较好的生活水准和健康的精神状态。“里昂的纺织工人是一些能力卓著的劳动者。从体态来看,他们并不是人们经常描绘的那种营养不良、身体孱弱、满身油污的工人。另一方面,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的文化、活力、高尚的精神、艺术品位、正确的社会诉求观念、工人荣誉感使得他们同普通的工人区分开来。”[16]
因此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最契合的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具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事实上,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手工业所创造的产值是最高的,从业人数也是最多的。据学者的统计,“1835-1844年间,手工业的工业产值占总工业产值的近70%。考虑到当时的工业统计倾向于将一些属于手工业的产值归类到小企业中去,因此实际上手工业的产值可能会更高。”[17]劳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也佐证了手工业的统治地位,“在425000名工业劳动人口中,超过300000人从事手工业。”[18]
因此对于法国而言,19世纪不是小生产者的黄昏,而是其巅峰。由于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与法国小生产者的利益最为紧密,因此不难理解蒲鲁东后来成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
结语
因此蒲鲁东既是无政府主义之父,同时也是小资产者。但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倘若用传统的视角来看蒲鲁东,认为他要废除一切权威,那么似难解释他在所有权上所持有的中庸立场。因此,本文提出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只是在这一维度上,蒲鲁东方称得上是无政府主义之父。
至于他的所有权理论则很好地体现了小资产者属性。他批评私有制,但又批判共有制,青睐占有这一中间形式。1963年,商务印书馆在译介蒲鲁东时指出,在拉丁语系的各个国家中,蒲鲁东的理论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探究蒲鲁东的著作如今仍有一定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似乎还不曾有人指出研究蒲鲁东的实际意义。本文指出,蒲鲁东的所有权理论与小生产者的利益最为紧密。而小生产者在19世纪的法国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较英国等一些国家,法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迅猛发展。但是法国仍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法国的小生产者尚且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那么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就可见一斑了。
在新的时代重新研读蒲鲁东的思想,有助于我们跳出既有的理论框架,更好地理解世界社会主义整体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