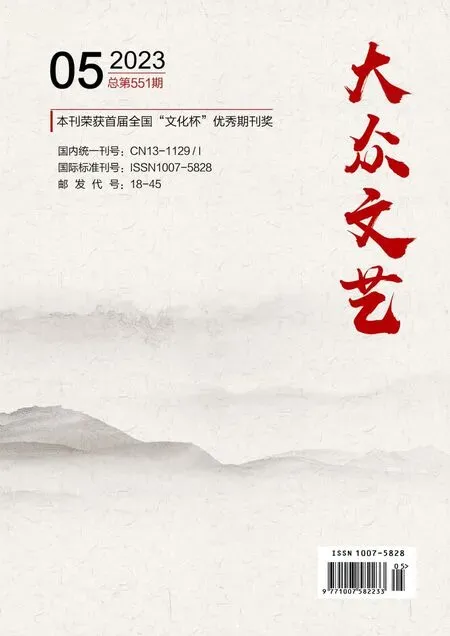镜像回忆与边缘凝视*
——张猛“东北三部曲”微观叙事呈现
2023-04-15黄一晋
黄一晋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012)
面对东北工业衰落悲壮宏大叙事难以为继的现实语境下,以“子一代”为主体的东北文艺创作已不再致力于生产建设波澜壮阔的意识形态理性言说,转而走向生活具体现实的细部回归,突破一体化叙事话语框架,实现了对元叙事硬性束缚的逐步摆脱,并向下渗透转化为微观叙事视角下对个体关怀心的培植。在个人命运的纠缠与时代议题的绑定间,覆盖于历史讲述的断层之上的集体记忆疤痕再被掀起,“东北文艺复兴”体表下真实血肉的每一次震颤,都是对个体经验的激活和集体记忆的回溯。
作为东北影视创作者的代表性人物,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的张猛将镜头对准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历着“下岗再就业”创伤时刻的东北普通工人,为废弃的车间擦去尘土,将爆破的烟囱重又竖起,将布满裂痕的厂区连同覆盖的坚冰挪移于银幕之上,描摹着“关停并转”大潮翻涌的裹挟下底层边缘人物的生命状态。《耳朵大有福》《钢的琴》《胜利》(合称“东北三部曲”)是张猛以地域空间内部下岗浪潮为文本背景所创作的电影三部曲,含有鲜明而成熟的个人化风格特色,契合着作者电影的类型定义:张猛在创作中担当着编导合一的中心身份,借助自身体验强调主观创作因素,延续着东北叙事空间的另类文化想象,对父辈的生产激情燃烧岁月和下岗苦痛以深情回望。在汹涌的外部变化与剧烈的情感震荡之外,封闭空间的相对停滞构成着社会群体稳固与颠覆的双向悖论,反复撕扯的强大张力形塑着工业热土之上的阐释空间。
一、隐喻:多层符号编码的藏匿
在新与旧的往复拉扯中,凋敝、彷徨、颓然与创伤中的所有情绪同未能完全磨损耗尽的生产激情各执一端,两端连接的纽带,正是寄托记忆的物质载体:空间是容器,符号是介质,空间内的社群整体,连同其集体记忆与情绪,都封闭在这一为时代所遗落的场景内。在“东北三部曲”的视觉空间内,张猛将东北时代转型的隐喻放置在空间的语法逻辑中,用一个接一个寓言的修辞排列切断旧现实、构建新秩序、储藏符号所指,替代现实的刻板视觉白描,启发观众记忆原型唤起。
三部曲中《钢的琴》的隐喻与象征最为典型,将群体所面对的新旧观念矛盾冲击以抽象形式进行展示,并成功发起受众更深层次的转译与解读。在影片开端,主人公陈桂林和即将离婚的妻子小菊分立于捡斤站的雨搭棚顶两侧,羽翼将二人聚拢又拨离——先前的夫妻如今在以冷若冰霜的姿态争夺孩子抚养权。这一如“劳燕分飞”般的场景画面极具隐喻与象征的意味:一方雨搭的棚顶上方稀疏零落仅剩支架,如“残翅”,另一方仍然充实规整,“丰羽”依然;一方雨搭背景皆是破败与倒塌,另一方屋舍俨然、道路平整……同一雨搭两翼的巨大反差正是二人现实境况差异的象征所在:原为夫妻关系的两个人如今即将分道扬镳、自此割裂,又因相连接的孩子抚养争端而拉扯,手持手风琴的陈桂林这边的破败寓意为人物正遭遇困境,只剩筋骨苦苦支撑,不能给女儿带来踏实的生活;而小菊的背景充实且安稳,呈现出一种秩序的压迫,也代表着小菊找寻到更好的归宿,并对陈桂林提出令其紧张的要求。以雨搭设计符号隐喻,暗示二人关联下实际代表力量的交锋:旧工厂工业时代宣告落幕,新商业资本正在孕育。特定空间中富含时代感的符号隐喻更具有形式的功能性作用,当陈桂林率领乐队为葬礼奏乐时,画外音提出演奏的俄罗斯歌曲《三套车》太过沉重,乐队随即改奏《步步高》。拆解其画面构图,葬礼仪式中并未悬挂逝者的照片,现场却赫然耸立着两座粗大的冷却塔,整个仪式的进行仿佛是为其唱诵挽歌。冷却塔作为火电厂的基础性设施,是工业区常见景观和必要建筑,可视为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符号。但两座高耸的冷却塔并未投入工业生产用途,反而和并不肃穆的葬礼融为一体,这也寓示着曾经宏伟壮阔的大工业面临着崩塌与衰亡的命运;黑棚上悬挂的“沉痛悼念母亲”的条幅也对工业组织解体、工人群体失去庇护形成喻指;而葬礼音乐氛围由庄严沉重转为轻松愉悦,代表着时代形势不容许工人群体过分悲伤,更要以乐观姿态投入新生活,为影片意旨平添荒诞色彩……纵览全篇,符号的隐喻同样藏匿于话语中:代表着建设时期老工人一辈的陈桂林的父亲,从未开口说话,指代着东北老工人颠覆中的噤声与失语;陈桂林对于小菊过上的“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日子”及她二婚的男人“卖假药的”“撑不死人,也药不死人”“钱也不少赚”的相关叙述,也包含着贬斥市场经济的现代性隐喻。“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自我”的话语对历史惰性论的回击亦同。电影中杂糅使用的各国各年代、各风格类型的电影也以声音符号映射现实社会转型中新旧势力、观念的纠缠与撕扯,呈现出颠倒的魔幻景观。
在东北讲述的舞台之上,隐喻符号的在场克服了特定符号持续生产与重复提及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更驱离了微观叙事的个体单调性。创作者根据自身主观经验对接表达冲动,运用细微的话语、常见的意象构造隐喻编码,赋予物象符号的普遍真实以虚幻的隐喻功能,又以非固定隐喻符号形式功能的解读反映现实,与社会现实在受众意识层面的投射构成互文,达到真实与虚幻的有限恒定与相对平衡,将宏大时代脉络植入纤细的微观个人命运,补录着影片微观视角所无法记叙的宏观现实,也牵动着观众根据固有认知的代入完成转译与传递,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更不受限制地释放作者意图的目的。
二、空间:记忆的还原与工业遗迹的流动
特定时间局域内的空间元素设置是东北城市题材影视作品微观叙事的核心布置,同样也是阐释影片的关键性线索。列斐伏尔的理论将空间形态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三方维度,[1]张猛执导的影视作品也正是以物理、精神、社会三层共同架构起东北城市镜像系统。影像资料强大的伪装性塑造着观感上的自然,创作主体游刃于三方维度,对三维的主要矛盾进行收拢聚合,对次要矛盾进行调和,将原有体制绑定下牢固的社会关系化为宿命翻覆的一切未知,精神的饱满向游荡的、零散的“再现”转变,替代现实“反映”成为空间的选择。在城市空间镜像系统之中,原本被割裂的物质空间与想象空间并置共存,建构起收缩历史、映照社会、虚实交替的空间复合体,调动城市空间的指代性滑向空间选择的两端分列,成就符号与空间的二分喻指。
“东北三部曲”的空间选取极富深意,着力于描摹工人生产生活空间景观,用微观空间内的工业元素巧妙迎合受众期待视野。在“回望”与“凝视”视界的接连切换中,厂区等已然被时间所淘汰的空间遗迹成为张猛摹写现实的纸张,这一部分城市影像的陈旧与萧条恰恰构成了刻意繁华之外的原生经验图景,现代化都市布景的主动缺失的背后正是工业重镇光环褪去后工人生活境遇与生存状态——映入视域中的尽是破败与落寞,压抑与黯淡构成底色,破败中却并不能见到商业与资本对城区发展建设的革新,反而过去生产喧嚷、干劲十足的工厂成为着连片的废墟与荒岛。
自建设时代起,东北工业城市就处于一种“静态”的空间环境,生产的周往与单调的重复赋予了空间秩序,同时也对空间功能形成了固化的限制,在时间的流动中形成空间的封闭,然而当下岗浪潮的席卷冲垮了厂区的外墙,裹挟着工人群体,涌入不再受秩序调节的时刻变动的社会时,浓烈的感情注入空间场景形成具有深层符指的集体记忆聚合[5],原本封闭的空间也就成了工人群体面对外界绝望的精神寄托与记忆载体。如影片《胜利》中,黑帮大哥陈胜利在出狱后见到阔别已久的城市时,现实破败与记忆印象的强烈反差使得他不得不重新适应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新规则,在“牢狱”的封闭中失去了对于时代更迭的感知,而在陡转的颠覆中落寞也孑然,仅剩下记忆的留存。在对空间典型特征的梳理中,镜头面向破败厂区与衰颓工业城市的巡回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历史惰性,更是影视创作者依照集体情绪的倾向性选择,是张猛的镜头惯习,同样也是他坚守的美学立场。
工业生产对社会所提出的大规模工人聚集的要求,是对工业城市产业规划与空间布局的初步确定,厂房与工业宿舍也成了工业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在张猛导演的镜头下,厂区的工业遗迹也成了叙事的载体,与叙事线络熔铸、紧密贴合。尽管空间与主体的从属关系被破坏,但空间的引力牢牢控制住逃逸的社群,拉扯着人的身体,使其和空间发生体验关系,在现代性分裂中宣示着主宰[3]:当厂区工人解除了起居时间与作息定点的束缚后,往复于街区与建筑之间的穿行不再乏味,是以一种“游荡者”的姿态与昔日的生产空间擦肩而过。[2]《钢的琴》中,工业遗迹浓缩在街景里,随人物行进而充盈感官的情节随处可见:陈桂林载着老父亲一边骑行一边对话,两侧宏伟的工业建筑耸立;陈桂林和淑娴酒后散步的行进,把一众破败的门市抛在身后;陈桂林追逐打麻将欠钱的工友胖头而遍历锅炉房、管道、烟囱等景观;工友们跨着摩托浩荡穿行过铁路、街区、厂房……更遑论《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用自行车与人力车在嘈杂街巷的反复漂流。空间的凝滞与身体的流动形成踏破挤压与接纳边界的节奏铿锵,生产性场所与生活区域的界限为身体感官的体验所抹去,填充着空间外壳里理性与非理性的在场,为微观叙事的集体狂欢清理出一处浅薄也深邃的舞台。
在横移镜头的辅助下,近景发起、配合远景镜头拉伸接续切换,城市空间与工业遗迹从叙事的微观视角处统摄全貌,压缩着画面构图中人物身体在空间景观的比例。老工人身体与旧工业空间的互动与碰撞将现代性的矛盾抛给经验过往,搭建起微观视线内的城市象征空间[3],收纳符号的隐喻性编码,扩张着“纪实冲动”外观下内在作者意图的表达功能。[4]
三、情感:家庭“离心”的瓦解与工友“向心”的聚合
家庭作为群体的基础单元与表征,随时代变革飘荡,曾经的亲缘关系网络甚至家庭关系在剧变中造成降维,横纵向强关系被削弱,关联、依附性的拟亲缘关系更难以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现实状况加剧着下岗工人群体的无力感,甚至引发更为严峻的亲情危机,同时也构成了“子一代”对下岗记忆的感同身受,甚至对父辈情绪与行为选择、价值判定的继承,如枷锁般将两辈人紧紧缚于铐链两端。
在张猛的文本叙事中,亲缘关系的降维得到了清晰的标示,甚至呈现出漠然的凝视态度:《耳朵大有福》中,王抗美退休生活的凌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庭的牵制:自己的妻子生病住院,不仅无法工作,还需要王抗美每天去送饭、陪护,子女则未曾出现;本打算和女婿商谈,女儿却因为婚外情与女婿大吵一架;儿子成日在外鬼混,不顾家庭,挑起事端;弟弟弟妹打麻将成瘾甚至冷落年迈的老父亲,导致其生活拮据、无人照料……本期待着为自己找寻依靠的王抗美,在短时间内被现实生活将幻想的屏风击得粉碎,原本当作援手的家人,此刻接二连三地成为新的精神压迫,与妻子病房中的对话也逐渐由侃侃而谈转为沉默不语。《钢的琴》中文本情节的设置同样如此,陈桂林的前妻小菊毫无拖曳地与他离婚;父亲已然年迈,少有沟通;甚至连女儿也提出拥有钢琴的欲求,让他背负重压……家庭成了功能性场所,而失去了情感寄托与精神归属的意义,伦理有机体本该持久而稳固的凝聚化为松散,漫长而剧烈的孤独成为亲缘关系的羁绊,长伴纠缠。
作为一个由生产计划主导的集体主义社会,在城市的现代性冲击下,工业生产生活所长期维持的固定时空规划、固定身心状况乃至固定个人价值与个人经验都产生了颠覆,在原有生产关系的瓦解同时,也应对工人的社会关系造成影响,然而在张猛的微观叙事中,工友的情感联络并未因下岗的现实冲击而产生裂隙,反而共同拾起旧工业组织崩塌的碎片,找寻盛放落寞与苦涩情绪的器皿,支撑起全新身份认识与价值认同的框架。在列斐伏尔的概念中,“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是为“空间的生产”,社会发展形塑着社会空间,社会群落则附着于空间之上并建构空间属性[1]。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时期所规划建设的大型工厂,同样也承担着社区的行政效能与生活功用:生产区域与生活区域在空间上极度重合,这也意味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形成了一种强力的交叉关系,工厂职工在共同参与劳动之外,同时也有着朋友、邻居、兴趣伙伴甚至亲人的身份关联,将集体主义的倾向插入个体生活。空间在生产主体,同一身份与归属的群体拥有着相近的同质性精神特征。跌宕迂回中,曾经的工友们裹挟于现实洪流,离弃于旧体制,却时刻充斥着难以将自己抛除、割舍在外的矛盾:在《钢的琴》中,陈桂林为了留下女儿急需一架钢琴,当他向曾经工友们借钱时,却发现工友们的生活也也都拮据不尽人意:时代的碎石击打在每个人的身上,曾经光荣的产业工人却无法适应新世界,弥漫着迷失与茫然。但当陈桂林向大家倾吐困难处境后,工友们挺身帮忙,从偷琴到造琴,从聚餐纵酒到承办婚礼……工人群体的友情丰满而细微,营设出一幅又一幅富含昔日生产激情的火热画面,构筑成一个宛如小型生产组织的新单元。
以失意工人为核心的个体关怀叙事中,家庭是“离心”的,冷漠、弃绝、不理解摩擦着本已撕裂的创伤,孤独与无助的情绪切入了一个又一个乐观积极的灵魂。与亲情的冰冷相异的是,工人群体之间的友情抵御住现代性的冲击:共享着下岗的失落与现实的失意,怀揣着共同的身份认同、经验认识与情绪认定,以目的与精神的“向心”于漫漫长夜中找寻,捡拾荣光,重拾自我。离心与向心的固有认知反差记叙着时代的颠倒,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精神交替盘踞,沉默也遮掩地给悖论以敞开。
四、螺旋式叙事线络:双重功能序列的组接
越过普罗普对神话文本编排演绎的叙事功能结构解析,“东北三部曲”的文本情节实际可以拆分为两个相互缠绕、彼此补充的功能序列重合,分别对接现实处境与精神困境:第一叙事线络是存在的证明,即工人群体在面临下岗危机之后追寻的生存寄托;第二叙事线络是价值的重拾,即在面临着工业组织解体,工人身份丧失,工业信仰亟待拯救的现实处境下,工人社群在迷茫与悲怆中将精神信仰投射至苦痛的现实,却无法适应后工业时代城市生活,在屡屡挫败中探寻自我价值的重塑。两条叙事线程是曾无限骄傲的工人群体在庸常人生中的主要轮转和次要穿插,在接连不断的主次切换间,完成螺旋式文本叙事结构的整体建立。
在影片《耳朵大有福》中,主角王抗美退休下岗,薪资待遇不如从前,需要找寻到新的经济来源以解决家庭拮据的困境,为此他先后误入传销、问教擦鞋匠、体验蹬人力车、向营销商家自荐组织乐队、个人试唱,上演着笑中带泪的啼笑皆非,此为第一叙事线络——下岗后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看似简单的叙事链条,串起了事件分列的圆环,主角沿着文本的锁链向圆环中接续穿行。在此过程中,王抗美极力维持着自己铁路机械工身份的尊严与体面:意图获取工伤补偿,却只说是姑爷让问;想向姑爷求助,却不断开腔场面话;打听擦鞋匠生意,却先声隔绝;尝试人力车,却以锻炼为借口……甚至连选择更便宜的烟都要高谈信仰以遮掩。这些细节的呈现为第二叙事线络所接受,着重凸显王抗美在身份更迭、生活方式变更、新旧话语对撞中的自我迷失,也是在变革中形成对自己社会身份的再定位:从嘴上说着不信、却笑逐颜开的街头电脑算命结果,到贯穿全篇的《长征组歌》,穿梭于街头巷尾的王抗美在遭遇工人“阶级空间”丢失的同时,也体会着“主体身份”的丢失,过去工人身份带来的荣光依然为其所怀念,推动戏剧冲突,代入叙事主题的文化意味。
电影《钢的琴》双重叙事线络则更加明晰:留住女儿是第一叙事线络的发起动机,购买/偷窃/制造钢琴是文本的主体主线。在主线推进的过程中,陈桂林与工友们先后完成了“串连”“聚合”“谋事”等几个关键步骤,最终生发制造钢琴的念头,并投入实践,催生矛盾直至高潮掀起,钢琴造成。第二叙事线络在对第一线络精神层面的情绪、情感吸纳之外,具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情节——保住烟囱:随大型国有工厂解体,厂区建筑的拆除是城市发展不可逆的现实趋向,但在工人群体眼中,这些建筑并非空间内单调的物理建筑群,更是工业建设辉煌历史与集体主义信仰的象征,同时也是怀揣工人身份的生产生活场所。工人们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成家,寄存着两代人的回忆与感情。烟囱的拆除不仅是现代性浪潮对城市记忆空间的冲击、夷平,更是将工人阶级功绩的整体清理。文本中,陈桂林等老工人群体在得知烟囱面临被拆除时,并未产生直白的不满与抵抗,而是想要寻求可行性方案来对自己的记忆标志进行挽救。随情节递进,烟囱爆破崩塌,山上坐满了观看的老工人,打招呼、点烟,如同欣赏挽歌唱诵记忆的埋葬与时代的缅怀。竭力挽留、默默离去,爆破是时代谢幕的宣告,而工友们以集体生产方式制造钢琴则如同仪式符号一般,张扬着力量感,告知集体记忆的返场与交接,重获自我拯救[6]。随着钢琴成功造出,存在价值实现激活,文本涌向结局,螺旋上升顶端,双重叙事线络也再度相交。
《胜利》的双重线络则分别是陈胜利结束十年的牢狱生活后角色转换,在城市辗转找寻自己的方向、慢慢去接受自我与城市在时代更迭中巨大的落差,当他巧妙化用监狱中学到的经验去经营一间幼稚园时,找到存在定位的他意图洗去文身,也正式向过去辉煌回忆作别,将记忆的残片碾得细碎,随着话语的颠覆成为新秩序妥帖的依附者,将物质与精神、存在的证明与价值推至螺旋的顶端。
作为文本情节推演的驱动性元素与微观叙事视角的核心载体,影视实践中的下岗工人往往被赋予了理想主义人格,象征着工业时代集体主义信仰的现实留存。随着功能序列双线程的推进,柔情被放置于中央,将更为紧迫的生计问题推至边缘。叙事文本未曾交代王抗美能否找到工作,陈桂林没有挽回烟囱,也没有挽留住自己的女儿,“耳朵大有福”“桂林山水甲天下”“胜利”成为自嘲自解的讽刺,但《长征组歌》在大道上依然嘹亮,钢铸的琴浑厚也凝重,这是“想象性抚慰”,是幻象视界愿景式的补偿。叙事双链的螺旋避开了生存的挣扎,也绕过了元叙事的宏大,在城市的象征性乡愁之地,将苦难的记忆一笔带过,揉花了黯淡的星,揉碎了残断的荒,也柔化了北地化为乌有的现实。
结语
东北三部曲是体制转型浪潮中厂区下岗工人的沉痛自述,骄傲连同激情都在身份置换的恍惚中悄然丧失,一瞬堕入软绵绵也空荡荡的虚无之间,如被乡土流放,成为“异乡人”。当张猛将镜头向着颓败的厂房对焦时,个体关怀叙事如催化剂一般,牵动集体记忆的拖尾在受众观念意识层面形成映射,经验的素材按压在微观叙事单元的底层逻辑之上,影像与记忆交替滑过,引发情感共鸣,以后现代主义要素对抗着历史话语划定的场域。视觉中心移转,是对历史立场与社会坐标的让渡,也掠过了主体自我的凸显与抹除:没有掩埋苦难,并未回避艰难,也拒绝被荒诞治愈,只是以一种平淡的语气、滑稽的表现手段拼接破碎的残片,启动记忆,在审美功能意义的判定中,取代历史宏大元叙事的操纵,为受众创建细微的情感释放点位,用原有的司空见惯补足延迟的愿望动机。
在沈阳重型文化广场伫立着一处每字重达三顿的“铁西”两字雕塑,是2009年北方重工搬迁停产前,由最后一炉铁水浇铸而成的。当燃油停注,轴承断裂,齿轮于啮合处生出锈迹斑驳,当螺钉脱离螺母,在历史的轨道上碾过、辙印凝固,工人的信仰与精神仍在这片流淌着工业血脉的黑土大地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