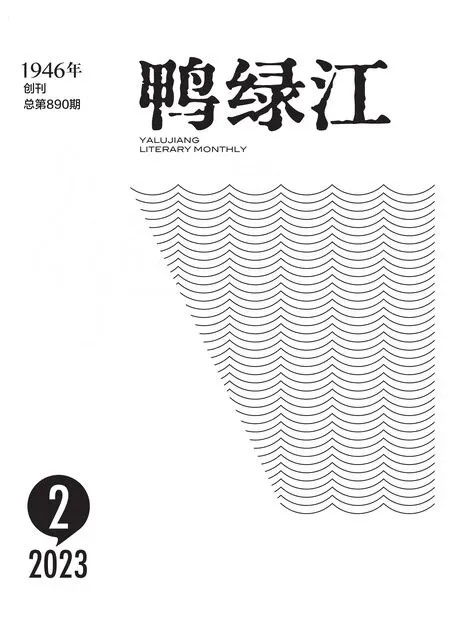流亡者的家园之思
——刘黑枷创作文本钩沉
2023-04-15高翔
高 翔
在九一八国难文学创作群体中,年轻的刘黑枷无疑属文学新人,但确有耀眼之处。据有关记述:“1942年4月,为了纪念《现代文艺》创刊两周年,举行了一次新作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三篇以上者)的征文竞赛,这次征文共收到应征稿63篇,选出了3篇最佳作品:一、《奴化教育下》(刘黑枷作);二、《张振华先生》(何阳作);三、《夜游魂》(缪雨作)。”其中刘黑枷的《奴化教育下》被“评为第一名,体现了评选者的良苦用心和独具慧眼”①。其实,仅言说评选者的“用心”和“慧眼”显然是不够的。《奴化教育下》的成功,自有作者的内在功力在,又与其破碎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刘黑枷是沈阳人,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其年仅11岁时,就随同家人开始了多年的漂泊和流亡生活,又不幸少年丧母,对国耻家难有着切肤之痛,在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全在预料之中。其间,刘黑枷先后考入东北中学、东北大学。离校后投身新四军,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主办的《七七日报》任副刊编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始于高中时代,20世纪40年代前后游走于小说、散文创作文体之间。相比之下,散文创作的数量更多,成就也许更高一些。围绕国难、怀乡主题的篇章不在少数,如《船上》(《东北》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5日)、《风雪的日子里》(《反攻》第十一卷第四期,1942年4月25日)、《炊烟》(《反攻》第十五卷第一二期,1944年4月15日);小说又有《回家》(《反攻》第九卷第五期,1940年12月31日)。1949年后,刘黑枷陆续出版了《母亲的行列》(署名陆海嘉)、《刘黑枷散文选》等多部作品集,细心查对,未见上述四篇收入,可谓新见之作。
怀乡,作为文学的重要母题,是作品“真正的力量和作用”②所在,也是刘黑枷新见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战的惨痛记忆密切相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归属感,是流亡者的家园之思。
《风雪的日子里》以风雪意象构筑全篇,由在四川少见的飞雪天气接到父亲从江西前线转寄来的东北家书生发开去,引起“我”对家乡一段温馨又痛苦的记忆和遥想:
祖母的老眼里怕正幻映着往年的风雪的日子里的景象,无邪的孙儿围绕着火盆,围绕着她,把一粒粒的苞米投在火盆里烧着白色的“爆花”,并且从竹扫帚上折下一枝枝桠,把烧好了的“爆花”一个个都夹在竹枝的叉丫上,插在案头的茶壶里,喊它叫“干枝梅”,这是出自无邪的儿童的手下的,一枝开在荒凉的冬日的土地上的梅花呀!
当孩子们跑到河泡子的冻冰上玩着游戏时,“祖母便从家里远远的赶来,穿着‘毡窝’,拄着拐棍,慈爱的斥责着,怕跌了脑袋,用着她的衰老多皱纹但极暖热的手温握着我的冰冷的‘红爪子’。”也是“满天满野都飘洒着绒片似的厚重紧密的雪花”季节里,祖母生日的那一天,引出“我”多端遐想:“老人是否安然的在吃着家擀的面条或自家收藏的鸡蛋来度过她的节日呢?还是坐在炕里烤着火盆,望着玻璃窗外阴霾的天空和巨大的风雪,想起了隔天外的儿孙,把眼泪滴在火盆里,而激腾起了一丝火炭?”不幸的是,家乡的人们正遭遇着雪天被捕捉的麻雀一样的命运,受到强暴者的任意屠杀。然而,“我们不怕严寒,更酷爱着冰雪,我们是严寒的土地上的人民,是冰雪之子。”“我们的性格就被寒冷的冰雪所磨炼,像冰雪一样的坚强,韧健而不屈啊,复仇!复仇!没有极严寒的冷度,是不会凝成坚冰和白雪的。”这里,刘黑枷构筑的冰雪意象,其实更突出了一种冰雪品格和冰雪精神,也就是作者所说的面对列强的“坚强、韧健而不屈”。整篇作品择纳的素材也许更见诸直观和感性,但无不具有暖意满满的亲情,温馨中又时而呈现对精神灵魂的叩问。
《炊烟》是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作品,依然荡漾着浓重的乡情。不同的,是以家乡的“炊烟”打造全篇。如果说,“江南的炊烟像窈窕的美女”,故乡的炊烟则“像朴舒的壮汉”。行走在关东辽阔的原野上,“村子里,每家的房上都少不了一个烟囱,高出房子有五六寸。有的是用砖砌成的,有的是用泥筑成的。当清晨或傍晚的时候,每一个灰色的茅草屋顶上,都仿佛一个生满了茸茸胡须的巨人的嘴巴含着巨大的烟管,向外喷吐着浓重的烟环。”这种“炊烟”随着季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霜冷风坚的秋天,为了给起早‘打场’的人制备晨餐,或在风雪扑窗的五更天,为赶车进城卖粮的人煮饭时,那从烟囱里升起的炊烟是更为矫壮的,不停地向外喷射着细碎的红色的星花,织绣出无数条巨大的火蛇,向漆黑的夜空飞舞。”到了冬天,“漫天飞卷着鹅掌大的雪片,雪扬着风,风卷着雪,在这个时节,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便如同强悍的巨龙,冲着风雪,无畏地向严寒的长空舞起愤怒的爪牙。”作者对故乡自家屋上不断升起的“夹带着高粱秫秸的浓烈的柴烟味”、“散发出高粱米饭的香甜味”的炊烟,其实是再熟悉不过了,以至于一个浪迹他乡十年之久的流亡者魂牵梦萦、万难忘怀。但“看得见我故园的烟囱上升起的炊烟”,却成为一种奢侈的愿望。作者何以如此沉湎于故家炊烟生动的表情、诗意的样态和绵绵的乡味中,全在于置身国难那盈满于胸的乡情、深藏时光的乡愁和栖息心灵的乡魂。作者笔下的炊烟,简约、清晰而淳朴,已远无古文字里行间的乡村炊烟升腾的宁静,迎面而来的,是苍凉而刚劲的图景,又客观表现出工业文明对人类生活异化的某种反拨。
《船上》则是怀乡篇中叙事格调极为别致之作,创作于1940年3月19日,这应当是作者高中毕业、考入东北大学的前夕。
叙事艺术无疑是衡估散文创作的重要方面。一般地说,文学叙事在中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叙事的传统在于聚焦,中国传统叙事则重散点透视。两者各有所长,当无高下之分。《船上》恰恰以对本土叙事传统的疏离而凸显出一种独特的聚焦艺术。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将焦点对准着不同年代的“船上”。
正在行驶中的“我们的船夹在四五艘和我们这艘同样大的盐船的行列里,挨靠着长江的边岸向上溯行着”;岸边坦露胸背、脚绑草鞋、下身围着“补丁盖补丁”长衫、“向着遥远而艰苦的生命的旅程上迈进”的纤夫,站立船头,将手握的竹篙“支向水底的沙石”;“把臀部用力的向后坐着”的船夫,伫立船尾;脸上“堆满了皱纹和皱纹所夹成的山岳”、指挥着“涨桅”和“落桅”的老舵师,共同喊唱着“一问众答粗壮而哀婉的歌”,艰难地拉纤、撑船、掌舵,一幅民国年代长江沿岸纤夫群体的凄凉生活画面,在作者笔下宛然出现。
然而,在乘船者“云”的“咱们每个人都要讲一讲自己的关于船的故事”的提议下,“我”开始了“船上”悲惨故事的叙述。那是国家危亡时刻、历史记忆中的“船上”:家乡的浑河,连接着乡村与城市,居住在浑河南岸村庄里的“我”,时常和祖母、伯父或哥哥“乘坐着那只大渡船,摇摇晃晃的来往在柔和而温静的绿波上”,穿梭于城乡之间。这种如常的生活突然终止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作者对此有着很艺术的表达:“一阵翻天的风暴,浑河里的河水被掀起了凶恶的波涛,人们用来过河的渡船被卷翻了,美满安静的生活被淹没。”离开家园流亡他乡,是在营口登上轮船的,“红膏药”的旗帜“正随着海风狂妄无耻的飘荡着”。舰船上“倭鬼”强逼一国人将自己同胞推下海去的一幕,给少年刘黑枷以强烈的刺激:“‘扑通’一声,青年同胞被自己的同胞推下海去了!他在海里挣扎,让可憎的浪花任意的戏弄着。我淌出了眼泪……”时间的魔鬼“毫不留情的把一个青春的生命葬在海中,海随着吼叫起来了,像是弱者的哀嚎,又像强者的狂笑”。从此,“我”远离了船。在古城北平流浪经历的“三个夏天里,我没有到公园里去划过一回船”,因为它会引起“我”对“那个在渤海湾被推下海去的”年轻同胞的忆念,“重泛起无边的疼痛”。不难得知,背负家园沦陷、同胞遭难、流落他乡的创伤,有家不能归的刘黑枷,很大程度是将怀乡作为杜绝遗忘和对社会记忆的文化重建、疗治精神病痛的憩息港湾。
叙事学奠基人热奈特曾一再提醒人们,叙事文中的“说”与“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有交叉又有分离。然而,这在刘黑枷的笔下,聚焦中的听觉与视觉得到了近乎完整的统一,形成视听一体的叙事模式,急缓适宜、张弛有度的文字,成为那个时代和历史“更为精确的见证”③。
《回家》是此次新见刘黑枷创作文本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与其散文作品中的蕴意不同的是,多融入了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战和东北人某种社会心态的深层思考。作品以“生长在遥远的北方的辽河上”的李景义的“回家”愿望编织故事。“一个大不幸”的九一八事变“降临”,迫使李景义带着妻儿离家“开始流浪,飘零在关内”;七七事变后,失业的李景义又“不得不和妻儿再向大后方流浪”,寄居在表哥邹玉亭家。时间一长,寄人篱下的不安与思乡成为难以排解的心结。李景义终于不顾表哥劝阻决心返乡。但乘船途中,突遇敌情:
近处天空却响起了沉重的金属的噪音,宣告杀人的恶魔来临了,于是大小船只纷乱的靠了岸,景义慌忙的携着细软领着妻儿杂在人丛中寻找着躲避的地方。敌机就在这时向地面上的一群用机枪疯狂扫射着。哭声、叫声凄惨的在四野上震荡着,江涛的歌唱都暗哑无声了。
景义的妻子的肚腹被射穿了,肠子翻流在地上,她斜着嘴,微闭着眼睛离开了这世界。
虽然,惨痛的事实“使景义把悲哀变成了愤怒,他以空前未有的诅咒哭叫着骂向苍天”,但对抗战已然发生了怀疑,觉得“‘胜利后,他能够回到老家’的话是不着边际的”,“在人生的苦海上,美丽的希望的泡沫太多了,但有哪一个不被当前的巨浪击破了呢?‘美丽的希望’只不过都是一些带着假面具的‘悲哀’所装扮的罢了!”正是基于这种悲观,当玉亭希望他到华北抗日游击队“担任一些文笔的差事”时,他想到的是:在那个“力量薄弱的队伍中,作着那种没有大希望的工作,是太没有意思了”。小说在玉亭与景义的想法相左且不言而互明中结束。
《回家》发表于1940年底。历史的实态是,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人中包括国民党政要在内,确有一些持亡国论者,导致有些民众抗战信心动摇,悲观情绪一时滋长、蔓延。直到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社会舆情才有了根本性好转。恰如中共中央在1941年12月9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所言:“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④《回家》真实反映了那个时期国人尤其是东北人的一种心态,是源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某种延展,应属于“抗战问题小说”之列,表明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孜孜探索和深入思考。而且,尽管作者并没有试图去解答问题,但对主人公悲惨身世的铺述,也深切蕴含着对主人公“怒其不争”、鼓动人们抗争的意义,显示出足够的国民性批判力量。这在九一八国难文学中是难能可贵的。
刘黑枷的怀乡之作,有着突出的寻根特征。按照植物学的观点,根系具有天然的中枢性功能,具有传递信息、调控植物整体的特征。故土是人类精神根系的所在,刘黑枷的怀乡之作,当是对作为人类精神根系的故乡的本真传达,寻根活动的自觉表现。正是这种根须相连的特质,延续和深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流亡宿命,形成了属于刘黑枷的流亡叙事和故园之思,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动荡漂泊中的作者,在异乡生发的怀乡叙事,既是对故土情愫的宣泄与释放、乡关经验隔离的接续与承传,表达着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呈现浓重的美学意义,又以对原乡社会的思考、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得失省察、积重之中国民意识的分解与批判,凸显出文化学的意义。自此,刘黑枷怀乡文学的历史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①参见林洪通、肖传坤:《抗战时期王西彦、章靳以主编的永安〈现代文艺〉》,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410页。
②[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③[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