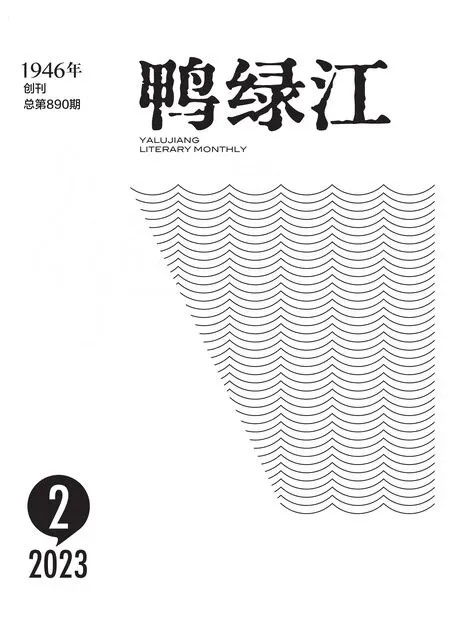河口(短篇)
2023-04-15于德北
于德北
大雾。
天刚蒙蒙亮,水汽就已经把房间浸满了,秋天的凉润让人醒得很舒服,况且,汗毛一根一根地紧贴皮肤,所有的毛细血管和汗毛孔都软塌塌,松阔到不忍提及。眼睛一点也不干涩,嘴唇饱满、圆润,鼻孔也干净得像涂了凡士林,提一提气,有涩涩的苦香,味道似苦艾,混合了一点野芹。听得见窗外流水的声音,先是水花拥挤的丝滑的呢喃,接着是跌下水坝的一连声的抱怨,再听,就是远去的绸缎推搡的调笑,然后,才在空气里拓展开迷人的静默。旅馆很小,二层楼,只有十余个房间。他住在二楼,靠里的202,窗外临着白天都很少有人走动的街,街的这边是包括旅馆在内的一排楼房——且住户并不多;而街的那边就是河,宽二十余米,对岸是山,莽莽的,被一层一层的兴安落叶松遮盖。河上有桥,走过去就是山门,铺了木质的栈道,一级一级地向上,转角就陷入阵阵鸟鸣。候鸟待发,留鸟蓄食,各自忙着各自的营生,不会顾及任何人类的介入。走廊里传来说话声,脚步听不出凌乱,虽然只隔了一道门,但那声音黏黏的,被什么东西裹住一般,吐不出,吞不进,就含在眼前二三寸的地方,悬浮着,艰难地下沉。
该起床了,他提醒自己。
小腹有一点点胀,酸麻感让他的心十分欢愉。
站到镜子前,他才发现自己是裸体的,身上一丝不挂。因为注意锻炼,他的肌肉并不松懈,甚至可以说十分结实。中等身材,和大部分东方人一样,上身略长,下身略短,穿衣服的时候,可以通过鞋子找平,现在没了遮掩,缺陷暴露无遗。进化的过程中省略了一个环节,或者上帝造人时少填了一块骨头,这种不成比例的身材,让所有的人都不自信,内心不自觉地生出恐慌,“卑微着羞涩”放在别人那里是掩耳盗铃,用在自己身上,则是一叶障目。
他回想前一天的情节。
他们见面后,先去吃烤肉,至于为什么吃烤肉,谁也没有向对方做出说明或解释。他从C城来,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在车上就发了微信给她,她说,我去接你。在车站,她远远地候在出站口的外边,他出现的时候,风正鼓动着她的裙摆。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直接打了一辆车,默默地穿越小城冷寂的街道,停在这家灯火通明的烤肉店前。A城三面环山,一面是大河冲击出来的狭窄的平原。他们吃烤肉,席地而坐,方桌中间是圆形的炉子,肉和青菜放置在四周。她穿着一双黑色的袜子,所以显得脚踝和小腿都很白;她的裙子也是黑色的,乌云一样簇拥起她的上身。她为他烤肉,一片一片,放在一种植物的叶子上,加了辣椒和蒜片,卷成一个绿色的荷包,正好一口吃掉。他说,你也吃吧。她笑一笑说,你吃吧,我喜欢让你吃,我想,我如果有一个哥哥,我就是这样包给他吃。他环顾小店的环境,布置似乎与C城不同,大抵是当地的风俗吧,进门就要除去鞋子,所谓的地板,实际上就是床铺;入门处放了一个展示食材的玻璃柜子,里边摆放着牛的各种部位,两根并列的肋骨中有一条被斩去一半,另一条就十分奢侈地沉睡;有一钵酱,流光溢彩,红黄混杂的颜色让人口涎欲滴。她问,家里都好吧?他低声回答,我和她已经很多年没有性生活了。她继续烤肉,像没听见一般,没有接话,更没有发问,只是调换了一下身姿,原来摆放在左侧的双腿,被她灵活地转移到了右侧。
饭后,他们决定去散步。
她说:“去河边吧。”说完,看看他身上的衣服,又说:“可能会有一点凉。”
他说:“没关系。”
于是,他们往一个黑暗的巷子里走。
他方向感很好,就问:“河不是在那边?”
她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地答道:“有两条河。”接着,向遥远的城郊方向指了指,“要到下游才汇到一起,变成一条河。”
他很吃惊。他一直以为A城只有一条河,而这条河是他所熟悉的,在他的笔记里,多次记录过这条河,在岸边,他所栖身的旅馆,窗户正对着240米的丘陵——严格意义上讲,它是某个山系的一部分,防空洞,岸边垂钓的人,正在维修的桥,被岁月毁掉的桥头堡。在这些记录里,有两段关于她的故事,皆发生在她的少女时期。一段是——一个男孩,比她大五六岁,头发蓬乱而松弛,食指纤细到总是略略弯曲。他们决定去防空洞的时候,就各自在口袋里带着一瓶木精,因为要走很远的路,她还细心地带上两块掺了红糖的饼子。他们从家里走出来,背着她的母亲。那是一个并不明朗的上午,太阳把大地上所有的物体的阴影缩短。他们一前一后,保持着陌生人眼里安全的距离。走到现在正维修、当时还完好无损的石桥时,一只大鸟从他们眼前飞过。那是一只他们从未见过的大鸟,飞翔的时候,翅膀发出沉重不堪的啪啪声;这只鸟身材高大,远远看去如同棕熊;对的,羽毛是棕色的,眼睛是绿色的,神色有点呆滞,耳朵上的羽簇像特意插上去的两朵花。大鸟落在桥栏杆上,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她很惊恐,但不能发出任何一点声音。那个男孩没有回头,他并未发觉大鸟的出现,不知为什么,大鸟张开翅膀,向她展示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她的内心是冲浪一般的暖流,从腿根到脊柱绽放开的是罂粟花那般又神秘又浓艳的痛楚。她发力奔走,踩踏着自己羞耻的形象。她想追上那个带她来此的男孩,然后拉着他一同回去。可是,男孩已经进入防空洞的洞口,他修长的身体挤压出一股腥咸的气流。后来,他们沿着防空洞走了很远的路,在木精点燃的火把的指引下,炙热地燃烧着未知的欲望。后来,木精引发了火灾,山体的内脏遭到毁坏,她的脊背也被大面积烧伤。
“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冷静地问。
她摇头,放弃回答。
“后来呢?”他又问。
她说:“没有后来。”
穿过幽深的巷子,就是A城另外的一条河,和他从前见过的那条河一样,依山蜿蜒,只是河面略窄,每块河石上都散发着青苔的味道。这里居民较多,所以河边也显得热闹,虽然灯光并不辉煌,但休闲的人热情颇高。由马路下到河边栈道,他轻轻抬了一下手臂,她迟疑一下,还是挽住了他。他们慢慢地穿梭在人群中间,如同两片泛黄的树叶。人多的时候,她就把他的胳膊抱紧一点;人若少了,她的肩头就略略向外倾斜。她说,我特别希望有一个哥哥。他问,没有吗?她摇头,说,没有。她说,她一直怀疑她的父亲也是一只鸟,邋遢,肮脏,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要在门口站立很长时间,夏天的时候赤膊,冬天的时候穿一件露了棉花的棉袄。他不怎么说话,包括坐在他们姐弟三人面前,最小的弟弟还习惯性地和他撒娇,可是每次都被他厌恶地推到一边。他一个人坐在灯下,自言自语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杀了他。他喝酒,傲慢地打发自己的恐慌。他的阴影穿透了墙壁,平铺着延伸到山麓一带。这阴影有着魔法的吸附力,收集着每一枚飞鸟的落羽。她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懦弱得像一具标本的空壳,无法看清天空和云朵,从而也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灵魂。他醉了,匍匐在地,潮湿而毛骨悚然地祈求着肉欲之爱,可回报给他的总是含混不清的竭力屏住呼吸的寒战。黑夜里,他不停地扇动双臂,奔跑在锈迹斑驳的道路上;到了白天,他则唐突地绷紧胳膊上的肌肉,一遍又一遍地支使她干同样的活儿。让她轮番洗涤自己仅有的两件衣服,让她用刀片修理自己脚底的锈蚀,他会在她刚刚打瞌睡的时候弄醒她,胸口激烈地起伏,像吞咽了什么不适物似的,大睁着眼睛。她无法休息,不能停歇,她父亲像修理他的工作一样,用道钉锤敲打她僵直的身子,尽量打开她渴睡意识里的每一个褶皱。后来,她父亲飞走了,翅羽不丰,绒毛凌乱,在她满腔的哀怨里,胡乱地拒绝了和这个世界的所有关系。
“我能做些什么呢?”他问她。
她无法正面回答。
他是观鸟人,是一个鸟类专家,从C城来到A城之前,他重新翻了一下自己的笔记,确认自己脑海的记忆。猫头鹰,又称鸮、枭,是夜行性鸟类。分布在中国的猫头鹰大概有26种,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多数种类几乎专以鼠类为食,是重要的益鸟。在某一天的笔记下边,他还抄录了一句话——“他们也仇恨吸血鬼和行凶犯,仇恨让其他人吸血和行凶的人,仇恨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人。”
她说:“我总怀疑我自己看不到真实的东西。”
“怎么会呢?”他有些苦恼。
“把梦境和现实混淆,把今天和过去混淆,把自己和别人混淆。”她停顿一下,“这些总是吧?啊?你说,总会是一种真实的自我感觉吧?”
“要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这一瞬间,他绝望。
“可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专家啊,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她靠近他。
“人和鸟毕竟不是一回事。”
“并无区别啊。”
她回忆她父亲飞走那天的样子,月亮惨白而空洞。他站在后窗的窗沿上,脱掉的衣服散落在炕上。他的头顶生出一个丝瓜一样的喙,软塌塌地垂在那里,喙的下边就是父亲的眼睛,已经开始向两边分移。眉毛变宽,像一条绶带,后颈的皮肉化成鳞羽,一环紧扣一环。母亲几乎是光着上身,抹胸遮挡住一只乳房。月光明显地把蛮荒的父亲和美丽的母亲清晰地分隔开,道路遥远而充满危险。他们没人注意黑暗角落里的孩子,悲伤正夸大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在肉欲面前,谁是谁的统治者,谁又是谁的神明,纯洁是否定吗?是道德至美和高尚的象征吗?毫无意义的结论以惯常的方式浪迹于乌有之中,谁也找不到安全的足以信赖的港湾。父亲飞走了,越过河流和沼泽地,越过公路和铁路,消失在永无尽头的天边。
她这样讲述着,使他们不知不觉地离开了河边——这条河的河边,他们向前走着,不到十分钟,就听到了另一条河在夜幕下的喧响。他的那家两层楼的旅馆就在前边,可她明显不想上去,他们就相对站着,不时下意识地躲避偶尔驶过的出租车。他看到她白皙的脖子,就低下头快速地亲吻一下。她有一刹那的慌张,又很快自我安慰,喃喃道,哥哥的吻都是这样的。他显得十分尴尬。旅馆的落地窗里,一个男人正在吸烟,他靠在大厅的沙发上,像逆水而来的激流一样涌动;烟雾缭绕着,让他的头发一点点变蓝,他的手指上——确切地说是中指——有厚厚的茧块,因为长期磨损和吸烟所致,茧块最中间的部分已经发黄;他正对着电话说着什么,面部表情温顺又可亲。他知道那个男人是做石头生意的,此时,他正对着手里的一块石头喋喋不休。他想说一说那个卖石头的人,不想她抓住他胳膊的手正一点点用力握紧,看得出,她是在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以确保整个夜晚的安全。她语气很快地说,我们家莫名其妙地来了一个男孩,脸色苍白,鼻子又尖又挺。他的手很长,可以用拇指和小指夹起学生用的格尺。他很能干活儿,从修窗修门,到抹泥苫屋,从担水劈柴,到割草喂猪。他走路的速度又轻又快,快到极致时左右摇摆。他担水的时候不用扁担,而是伸直双臂,脖子像天鹅一样有弯度地挺着。他的手指像梳子,可以顺利分开她的头发,每当手指划过她脊背的时候,她都像生硬的金属被催眠。他能把自己放到一个木箱里,头脚相抵地蜷成一团。他总是在太阳升到最高的一刻,眯起眼睛让阳光把瞳孔晾晒。他是一个哑巴,只会发出喔喔的怪叫,无论伤心还是高兴,他的眼睛始终可以流溢清澈的光芒。
“你喜欢他?”他问,嗓子很干,布满皴裂。
“我只是不用干那么多的活儿了。”她伸出双手,手指节又粗又大。
“你喜欢他。”他嗓子干得几乎发不出声音。
“棍击!”她说。
“什么?”他没听懂。
“棍击。就是用木棍互相击打。”她解释。
自从发生防空洞事件之后,她后背的灼伤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彻底愈合,愈合的皮肤暗红色,泛亮,干涸,板结,时时发痒。她不再让男孩给她梳头,也不再有意拦截男孩水蓝色的目光。有一天夜里,她的后背出现针刺般的点痛,豆子爆荚一般,疼痛每跳跃一下,都伴有扑波的声响。她幸福地微笑,开放的思维很快就激昏了大脑。她出现幻觉——她家门前的草地都变成了红色,树木在清晨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又高大又整齐,粗壮的白色的枝丫上系着秋千,一只大鸟羽翼丰满地坐在那里。鸟的眼睛是黄绿色的,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从鸟的眼睛的反光里,她很容易地看到自己,面容清癯,带着一点病态的潮红,臀部很窄,胸脯几乎没有起伏,嘴唇有一点厚,但挡不住一颗智齿隐隐作痛。自从男孩不再帮她梳头之后,她的头发也有一点干枯,最主要是眼睛无法泄密她的身体,她带有剧毒的闸门正拼尽全力抵制着生命本源发起的攻击。她背后受伤的地方长出羽毛了,和大鸟的羽毛一样,棕色的,显得纷乱,不合规矩。像那天去防空洞的桥上一样,她一时间分不清哪个是鸟,哪个是男孩。她听见男孩发出啊啊的喊声,如缶如瑟,沉闷得闪闪发亮,硬邦邦地略过所有的小节。他们一人手中抄起一根木棍,向屋后的旷野奔去。其实,哪有什么旷野,只不过是山脚下河滩上的一块平地。他们不等对方脚跟站稳,就开始决斗般地互殴,没头没脑,不分轻重。就是在这样的互殴下,男孩化成了一条瀑布,飞泻着汇入河流;而她瘫做一摊泥,紧紧地贴在河床的床底。
他有些冲动,却无法打断她。
她说:“其实每一个女人都是肮脏的。”
“都会有一点惋惜吧。”他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要是再看见那种鸟,我恐怕会呕吐。”她说。
“我要让它们飞起来,包括我们。”他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说。
“有一个哥哥多好。”她有些迷离。
“一直是这样。”他从她手里把胳膊抽出来了。
刚才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双手是离开他的,可不知什么时候又合围在一起。悲凉的空白,可叹的幻境,思维没有墨迹,却一样可以留下压力。他们分开了,匆匆地,她急于回去,而他也似乎突然来了困意。
夜显得格外平静。
雾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浸漫上来。
雾首先充填了河道,压制了河流的一切孟浪。它们停留在桥孔的水泥壁上,一点点地加厚,无须两刻钟的工夫,就把桥栏也吞噬到自己的胃里。水草不想把自己和同伴编织在一起,所以,一律束手站立;但是,它们忽略了雾的固执,它们潜入水草的根部,控制了它们的茎秆和叶脉,直至它们完全屈服,顺从它们的走势,要么偏向一侧,要么从某处折断自己,一头纳入河水的沉寂中。雾迈动脚步,沿着山脊的一切沟沟坎坎,咬合住一个物体就不再松口,用自己的肩膀或头部托举着同伴向上攀爬。灌木不见了,乔木不见了,山地的阴坡和阳坡滚动着无声的肉眼看不到的呓语的结晶,把天地彻底地混为一谈。雾最初是奶白色的,重叠起来就变灰,灰与灰在狭窄的地方缓慢地通过,那么,这条通道就又变黑。重的下坠,轻的上升,上升到一定高度,略略透明起来,但很快就被后来者重新推到底层,晕头转向地再次粉碎自己。树枝不堪重负,忍痛折去粗大的横枝。鱼浮出水面,在雾气里游动。飞鸟停在半空,根本就放弃了飞行。雾有自己的呼吸,但它们只含住一口气,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身体,道路屈服了,紧接着路灯和楼房屈服了,最后,人也屈服了,他们把半个身子趴在窗子上,不知所措地空对着这不堪幻灭的袭击。
他已经很多年没见到这么大的雾了。
他给她打电话,问她:“还去爬山吗?”
“去。”她的回答很简单。
紧接着,他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他没想到她来得这么早、这么快,胡乱地穿起衣服,把她让到屋里。他突然有点内急,就一头钻进卫生间。他重新褪下裤子,褪下内裤,小心地坐在马桶上,随手翻动手机。他想,自己大便的时候,声音一定不雅。所以,在腹内污秽急下的同时,按动了马桶的冲水。一股冷风扶摇而上,让他内心深处泛出一片寒意。他听不见她的动静,想象她大概是在照镜子。墙壁上乳白色涂漆流淌下来,他的神经忽紧忽松。从卫生间出来,他没有洗手,除了手机,再也没拿别的东西。他们一同下楼,穿过并不宽敞的大厅,离开旅馆,摸索着向山门进发。
大雾让他们看不清彼此,他们很自然地把手拉在一处。她的手很凉,像雾一样潮湿。因为雾压制了其他的声音,所以他听得见她的心跳,像一台小型的马达,很有规律地运行。因为看不清台阶,上山较比晴朗的日子要累,虽然沉默可以保持体力,但她还是断断续续,喘息着讲给他听。那个男孩又长高了,嘴唇上生出密密的绒毛,他们互殴频率加快,脸上和身上从未间断过青瘀。她母亲察觉了这件事,就开始追问他们缘由,她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身体,所以开始编织各种谎言。但是谎言是荒诞的孪生姐妹,欺骗不了高度敏锐的母亲。终于有一天,母亲从他们消失的时间上找到了破绽,一举揭穿了他们无边无垠的表演。她没有想到母亲会震怒,那歇斯底里的叫喊回荡了所有的山谷。母亲极尽职守地拔除了她背上的所有羽毛,还充满嘲笑地把一面镜子冷酷地托举在她面前。她害怕,特别想哭。可是一滴泪水也没有,她盯视着镜子里自己小小的胸脯,毫不丰满,像两只型号不大的气球,由于肋骨折了一根,她一侧的腰身臃肿,增加了丑陋的资本,也让她失去自信。羽毛落了一地,棕色的,毛管的根部有血迹,使死亡略显出一点生动。她看见男孩在母亲无法发觉的角落窥视她,于是,自然地垂下手臂,她忍不住笑了,疼痛迫使肋骨发出阵阵铮鸣。她几乎下定决心,做出自己应有的反应。但是,另一幅画面让她邂逅了自己骄横的心理,她的仇恨也自此变得具体而又小巧玲珑。就在她微笑着为自己包扎伤口的时候,她看见昏黄的灯光下男孩猥琐的背影,母亲在哭,在向他祈求,而他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忏悔的泪水洇湿了她的衣襟。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互殴。”她说。
“真是太决绝了。”他说。
“互殴也是有区别的啊。”她说。
“并不是同一种誓言。”他在雾里停下来。
“无法拒绝的练习。”
“总归是很愚蠢。”
他们到达一处缓台,都不想继续再往前走,靠在结实的栅栏上,她说起那两条河流交汇处的河口。这也是他笔记里记过的第二件事。她讲河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波澜壮阔,反而有些黏稠度很高的忐忑,羞怯地撞击,小心地试探,踉踉跄跄地向前,共同对应着前方未知的坎坷。她站在岸边,追索着水下的一处旋涡。依然是上午,布满车辙的大道坑洼不平,太阳白花花地照着,空气里搅动着罕见的紫烟。一个男子向她走来,嘴里冒出莫名其妙的劝慰,伸手去扯她的裤子,她麻木地后退,嘴边的冷笑却棱角分明。男人力气很大,表情也越来越夸张。她唱戏一般扭动身体,近乎浪笑地高喊:“大哥——大——哥——”呼啦啦,那只大鸟飞来了,铺天盖地,展翼有两米半长。它冲向那个男子,抓扯着他的头皮,剧烈的疼痛让男子惶恐地后退,手脚胡乱摆动,全身都发出失衡的颤抖。她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喘气。他拉了她一下,她顺势靠在他的怀里,他问,我可以亲你一下吗?她点头。他亲吻了她的额头。她满足地笑了。他又去亲她的嘴唇,她用手挡开。她说,亲额头是哥哥的吻,亲嘴是情人。他从后肩处环住她,手自然地搭在她的胸前,他触摸了那并不丰满的胸部的轮廓,感受到少女才有的坚挺。
他们原路折回,外衣上散发出潮气。
一回到旅馆二楼202房间,他就反锁了房门。他抱住她,不顾一切地亲吻,无论她怎样挣扎,如何拒绝。他吻她,她发出尽量合乎贞操的喘息。她的脸呈现出玫瑰色,身体像水母一样打开。他顺利地除去了她的上衣,如愿以偿地看见了她的乳房,小小的,毫不丰满,像两只型号不大的气球。他抚摸她的脊背,摸到了正在生长的羽毛,不用探寻也知道,棕色的,不整齐,甚至凌乱。她的身体在动,拳头一点一点地握紧;她的脚尖着地,脚背完全绷直,肩抵在门板上,从肩胛到小腿形成“弓”字形的虚空。突然,她的身体里爆发出一股蛮力,一把就把他推倒在床上。她冲去卫生间,抄起在墙角等候很久的拖布,一脚蹬去拖布头,只提回了白蜡木的拖布杆,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暴风骤雨一般的殴打将他彻底击昏。
她喊着:“大哥!大哥!大哥!”
他则像一潭死水,无论怎么兴波助澜,都无法抵达河口。